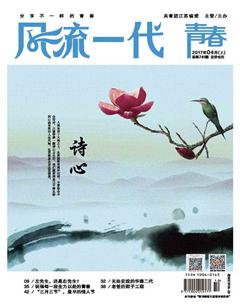詩教,把古詩唱成民謠
鄭晶心
梁俊曾是吉他教師、樂隊經紀人、廣告公司的活動策劃與文案、樂器行店長,但是他最想做的事情,卻是跟孩子有關的。2013年,他抱著一把吉他就遠赴烏蒙山區石門坎新中學校支教兩年。
2016年回城之后,他和同去支教的妻子周曉丹編輯整理了學生的文字和繪畫作品,并一一寫了中肯的評語,經過眾籌,于2012年12月底出版了《烏蒙山里的桃花源》。
《烏蒙山里的桃花源》一書的編輯蘇雪菲說:“有天我發現自己在上班的路上無意識地重復哼唱一首歌《邊草》:‘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聲愁絕。唱著唱著,一種安定感升起,霧霾的陰影、城市生活帶來的莫名壓力、人群中涌動的戾氣與絕望,慢慢地離開了我的心。”
把古詩唱成民謠
烏蒙山區荒漠貧乏,山高霧濃,不適人居。但在這樣的惡劣生存環境下,卻居住著苗族的一個分支———大花苗,而石門坎的大山深處,又有兩個大花苗的村寨:新營和中寨。
新中學校的名字取自兩個寨名的首字,寓意“好消息中的新生”。學校創立于2002年,是一位名叫吳彩金的女商人投資建造的。
當梁俊和支教伙伴們來到這里時,這里并沒有桃花源,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是留守兒童,他們缺乏照顧,頭發凌亂。但梁俊也捕捉到,苗族人生性愛唱歌,血液里流動著詩性。之前將要告別城市,準備去大花苗寨教書前的一段日子里,梁俊常常思考一個問題:“我能給大山里的孩子帶去什么呢?”
偶然間,他在網上看到一段文字,發現了一位低調的音樂人楊一,他“不務正業”地帶著幼兒園小朋友唱誦他譜曲的《桃花源記》。梁俊被他所做的事深深吸引,他想:“我會彈吉他,會唱歌,也可以帶大山里的孩子唱古詩文!”
梁俊開始在網上搜索古詩譜曲的作品,但聽了一些之后很失望,沒有找到他想象中的那種旋律朗朗上口、能用音樂詮釋古詩意境的作品。既然找不到,不如自己來。梁俊索性拿起吉他,開始為古詩譜曲。
支教生涯的第一個學期,梁俊就帶領孩子們吟唱經過他譜曲的古詩。對學前班、一二年級的孩子,梁俊教他們唱袁枚的冷門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帶著孩子們邊唱邊體會苔花雖小卻有價值的意蘊。三四年級的孩子,在春暖花開、蜜蜂忙碌的季節里,他們一起學唱羅隱的《蜂》:“采得百花成蜜后,為誰辛苦為誰甜。”有了三四年級的情感啟蒙,五六年級就可以慢慢了解邊塞詩的凄涼悲壯了,就一起唱辛棄疾的《青玉案》、蘇軾的《江城子》。

梁俊用民謠的方式為五六十首詩歌譜了曲,他不時陷入為一首詩譜曲尋找合適旋律的沉思中。靈感來的時候,也可以十分鐘寫兩首。不過剛開始的時候,他對自己的作品并不自信,但是當孩子們唱起來,隨著純凈的童音響起,他發現,孩子們賦予了這些歌新的生命。
第一個學期結束,孩子們學唱了不少古詩,校園里常常會出現這樣的畫面:放學后留在教室里值日的孩子,一邊掃地一邊高聲唱:“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中午排隊打飯的孩子突然高歌:“一帆一槳一漁舟,一個漁翁一釣鉤。一俯一仰一場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孩子們是真的愛上了詩,梁俊也教得越發用心了。
成為一個熱愛語文、有情趣的現代人
梁俊的詩教理念,深受上海交大附小的丁慈礦老師與作家冉云飛的教育理念影響。丁慈礦老師在他的詩教講臺上,實踐著當代教育家王尚文關于語文情趣的定義:“語文情趣基于愛美的天性,是形成于后天的對語文之美的愛好和追求。”丁慈礦也在他“每周一詩”的課堂上,和孩子一起感受詩歌、尤其是古典詩歌的情趣,并從這一語文情趣中獲得了無窮的快樂!
冉云飛引用顧隨的那句“學古詩文是為了做一個現代人”,則明確了梁俊教詩的態度———透過詩歌教育,引導孩子成為一個熱愛語文、有情趣的現代人。
因此,梁俊教給孩子們的詩歌類別有三個特點:以品格詩育人,用古詩詞讓孩子體會古人的情感與意境,以現代詩激發孩子的童真與想象力。
每天早晨,他帶領孩子們背誦現代詩《晨詩》,提醒孩子們每一天都是新的,昨天已經過去,我們又一次地面對太陽,為此獻上感恩,并立志全力以赴對待學習和工作。又帶孩子們背誦以色列最具智慧的國王所羅門教導兒子的箴言《懶惰人啊》,透過詩歌提醒孩子們要做個勤勞的人。
古詩詞的方面,梁俊則選擇貼近孩子們的生活,從好玩出發,由趣味詩入手。苗寨里家家戶戶養雞,于是他教孩子們袁枚的《雞》:“養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主人計固佳,不可與雞知。”學了這首詩后,孩子們樂呵呵地互相打趣著:“和雞相處要小心,千萬別讓雞看到你流著口水吃雞的樣子!”
寨子里常常有醉漢酒后鬧笑話,梁俊則應景地教孩子們辛棄疾的《西江月·遣興》:“醉里且貪歡笑,要愁那
得功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詩學完了,他還讓學生兩人一組演一遍詩中的場景,班上的同學樂開了鍋,自此人人把辛棄疾當哥們兒,親切地稱之為“老辛”。

除了趣味,梁俊還會按主題教學,春天唱誦:“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里雨如煙。鄉村四月閑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夏日唱誦:“懶搖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冬天唱誦:“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孩子們從來不覺得他們是在背詩,只覺得這些詩里講的全是自己身邊發生的事。
讀得多了,唱得多了,孩子們也詩情大發,愛寫愛畫,梁俊自然大加鼓勵。女生梁越梅情感細膩,有點膽小,每次被點名回答問題時,要扭捏半天才羞澀地開口,但是她的文字出色,歌聲也很動聽。唱過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句后,她寫下了《落日》:“落日金燦燦,似火把山燒。霧云滿天散,明月照人來。”男生吳榮興和外婆住一起,平常他話少,看上去有些木訥,但有天晚上,他看到寨子東邊有人放煙火,煙花一閃一閃的,又抬頭看到天上的月亮,亮得很好,就寫下了一句詩:“明月懸空照大地,東邊煙火亮點燈。”他在作文里把這句詩記錄下來,同時解釋他還沒有寫完,沒想好下句怎么寫,但是他在結尾處寫道,希望“可以一直坐在門口賞月亮”。有一個叫朱思語的男孩,平常調皮搗蛋,也愛撒謊,可是有一天他聽梁俊講“世上有些事物是看不見的”,他就寫下了這些詩句:“風,像夢一樣/你想把她抱住/可她還是去了/你看不見她/她卻可以穿過你。”
梁俊常常感動于孩子們的文字,這些并不是老師的命題作文,他們有感而發,真實地記錄下自己對身邊的世界和人的觀察與感受。其實教孩子們唱詩之初,梁俊也會疑惑:這樣子教到底會有什么樣的效果呢?有沒有用?看到這些作品,不用孩子們回答,梁俊也看到了其中的變化。孩子們寫村寨的景色、動物和植物,寫鄉野生活中的趣味,為他們去世的親人寫下思念,給脾氣不好的父親寫下“你要好好幫媽媽干活”的感人長文,也寫出“為什么讓我來到這個世界”這樣的句子,來表達自己挨了父母責罵后的委屈心情……
梁俊教過的學生中有一位年紀略大些的已經外出打工,但是他在每天辛苦的勞作之余,都要堅持寫一點東西,有時候是詩,有時候是日記。梁俊一直保持著跟他的聯系,鼓勵著他。
梁俊說,每個孩子心中都有一首詩,就像一粒種子,在所到之處扎下根,詩心會結出更多美好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