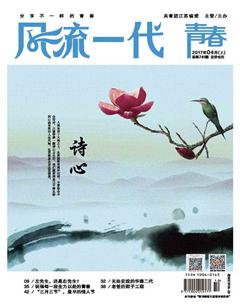從傳統(tǒng)文化到當(dāng)下
趙艷紅
一位鄰居開了家玩具商店,經(jīng)常有青年人到他那里打工。一位小伙子工作滿月領(lǐng)到薪水后就辭職了,給老板發(fā)短信說:“我是來打工賺錢的,不是聽你講做人大道理的。”那老板的確健談,每天不住嘴地說,只是觀念有些陳舊了。他大概是將打工的小伙子當(dāng)成舊社會(huì)里的學(xué)徒工了。
雖然如今的中國比80年前已進(jìn)步了太多,但是對(duì)照現(xiàn)實(shí)生活,這本寫于80年前的《新事論》所論所述依然不算過時(shí)。書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生產(chǎn)家庭化社會(huì),雖已漸行漸遠(yuǎn),但是與之相配套的觀念似乎依然存在。馮友蘭在書中寫道:中國原來是生產(chǎn)家庭化的社會(huì),所以原來的教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為中心者。現(xiàn)在我們要變成生產(chǎn)社會(huì)化的社會(huì),所以我們的新教育制度,亦是以社會(huì)所設(shè)教育機(jī)關(guān)為中心者。看慣了舊日的教育制度的人,看見現(xiàn)在的新教育制度,不免有許多地方不順眼。他們不知,兩種制度,本來就有許多差異。他們只見現(xiàn)在師生的關(guān)系,太疏遠(yuǎn)了。從前是“師徒如父子”,現(xiàn)在是“師徒如路人”。他們覺得,這亦是“世風(fēng)不古,人心日下”的一端。在這種工廠化的學(xué)校里,傳授知識(shí)固然還沒有什么困難,但關(guān)于道德修養(yǎng)方面的事,這些工廠化的學(xué)校,既不能有一個(gè)“人師”為中心,則學(xué)生在這一方面,完全得不了什么益處。
關(guān)于先進(jìn)文化同化落后人群的文化,馮友蘭將其打比方為鄉(xiāng)下人和城里人的關(guān)系。他幽默地寫道:“人若能坐在重樓疊閣的建筑里,有地爐暖得滿室生春,他萬不愿意再去坐在曠地里的蒙古包里,烤馬糞火。”當(dāng)然,城里與鄉(xiāng)下,既是相對(duì)的,又處于不斷變化當(dāng)中。中國人的城里人的資格,保持了一千多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國人遇見了一個(gè)空前的變局。中國人本來是城里人,到此時(shí)忽然成為鄉(xiāng)下人了。西方成了城里,東方成了鄉(xiāng)下,所以我們中國雖有的是原料,而制成品卻須往外國買。我們有麥子,而所謂洋面漸漸壓倒本地面。在這種情形下,如專提倡所謂“東方的精神文明”,以抵制西方勢(shì)力的侵入,那是絕對(duì)不能成功的。那該怎么辦呢?鄉(xiāng)下人如果想不吃虧,唯一的辦法,即是把自己亦變?yōu)槌抢锶恕?/p>
本書一再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家庭化的社會(huì)與生產(chǎn)社會(huì)化的社會(huì)之不同。不是說傳統(tǒng)文化都是落伍的,而是傳統(tǒng)文化的根變了,社會(huì)不再是以家庭化生產(chǎn)為主。馮友蘭重視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不空談社會(huì)制度改革,他說:一種社會(huì)制度,是跟著一種經(jīng)濟(jì)制度來的;一種經(jīng)濟(jì)制度,是跟一種生產(chǎn)方法來的。不從根本上著想,不從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講“應(yīng)該”,講“奮斗”,講“法律”,都是無補(bǔ)實(shí)際的。

我的一位親戚開了一個(gè)小廠子,她說她在車間做過一項(xiàng)調(diào)查:假如日本打來了,你會(huì)選擇怎么做?她事后說,做這個(gè)調(diào)查是有目的的,想看看員工的忠誠度。你若不愛國,又怎么會(huì)愛我的廠子呢?人們總是習(xí)慣用以小見大的方式類推,其實(shí),那十有八九是詭辯。馮友蘭書中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一種社會(huì)中的人的行為,只可以其社會(huì)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批評(píng)之。如其行為,照其社會(huì)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是道德的,則即永遠(yuǎn)是道德的。此猶如下象棋者,其棋之高低,只可以象棋的規(guī)矩批評(píng)之,不可以圍棋的規(guī)矩批評(píng)之。”脫離人之環(huán)境,空談道德,是不道德的。
- 風(fēng)流一代·青春的其它文章
- 小情緒
- 失戀博物館
- 萬里瀟湘,芙蓉國里盡朝暉
- 布衣暖,菜根香
- 種花無須賞花人
- 那個(gè)陪你說很多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