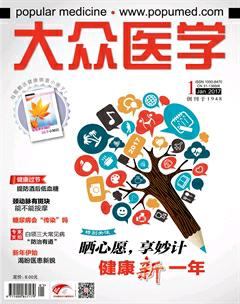《大眾醫學》是一塊干凈的科普寶地
1952年,我加入了醫學科普作家協會。那時重點宣傳的是戰傷自救知識,我也常在報刊上寫一些短文,很受群眾歡迎。同時,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創辦我國的小兒外科專業。新專業要獲得群眾的認可,非常需要科普宣傳。于是,我寫了些介紹小兒外科的短文,遍尋報刊發表。《大眾醫學》的出現,引起我很大興趣,她的辦刊方向與內容正好符合我的需要。
此外,客觀上也有個偶然的機緣促進了我們的長期合作。文化大革命以后,百廢待興,中華醫學會也逐漸恢復各項工作。當時,我擔任中華醫學會科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付連璋先生已故),聽學會的其他同志談起科普工作,都說《大眾醫學》辦得好,水平高,應該支持其發展。受中華醫學會的委托,通過《大眾醫學》創刊人裘法祖教授的介紹,我走訪了上海科技出版社,并轉達了中華醫學會對《大眾醫學》的關懷。此后,編輯部有個負責同志一直與我保持聯系。
后來,我就任中華醫學會小兒外科分會主任委員。為了宣傳新興的“小兒外科”工作,我成了《大眾醫學》的寫稿人。我的稿件送去必登,有時雜志也反映一些群眾的問題,要我寫點東西,我也是“有招必應”。
60年來,小兒外科從一個鮮為人知的新興學科迅速發展壯大,目前已是家喻戶曉。2000年,我獲得了國際小兒外科最高獎項“丹尼斯·布朗”金獎,該獎為國際小兒外科界最高成就獎。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的那樣,知識交給群眾,才是力量。我想,《大眾醫學》在這里肯定起了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宣傳作用。
現代科學的傳播,必須依靠“知識群體”。《大眾醫學》的讀者正是廣大知識群體,宣傳的內容以先進的科學理論與科學技術為主。知識群體的帶動與再傳播,才使全民思想科學化、現代化。我曾見到有的患兒家長拿著《大眾醫學》對我說:“我已經照雜志上說的做了,效果很好!”也有醫生同事向我反映:“我們沒有時間向家長詳細講解,我介紹他們看《大眾醫學》上你的文章。”這就是《大眾醫學》在群眾中反饋的具體實例。同時,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部分群眾需要的知識與技術,醫生本人沒有機會親身體驗,專業書及課堂上也不曾涉及(例如小兒怎樣使用開塞露等)。《大眾醫學》的內容與深度,正好滿足這些需求。
健康與醫療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由于醫學是從經驗醫學與神秘醫學(巫醫)開始的,人類至今仍對一些疾病不了解、治不好,醫學的神秘性仍未完全擺脫。不少患者病急亂投醫,各種偏方、秘方、神方,五花八門,令不少老百姓受騙、受害。
凈化醫學科普陣地,是我們臨床醫生份內的事。我現在雖然仍看門診,畢竟年齡大了。后起之秀們醫療任務太重,看一個患兒只有幾分鐘,沒有時間和病家細談,科普工作更是排不上日程。其實,在一線工作的醫務工作者,針對每天遇到的實際問題,每年寫兩三篇短文,負擔也不算重。群眾需要醫學科普,你不肯寫,有些“偽醫”就會乘虛而入,誤導群眾,損害醫學科普宣傳的聲譽。如果醫生拱手讓出科普陣地,將會是什么后果?《大眾醫學》是一塊干凈的醫學科普寶地,需要我們更多的同道努力保衛她的輝煌與聲望,充分利用這塊陣地,使她不斷發揚光大,永遠為人民健康保駕護航。
專家簡介
張金哲
中國小兒外科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金哲院士醫術精湛,醫德高尚,為我國的小兒外科事業傾注了畢生心血,被譽為“中國小兒外科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