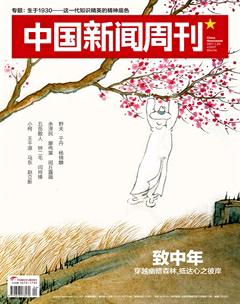樂黛云:我們這一代的理想和浪漫
龔龍飛
“我似乎還有可能返老還童,從頭開始。然而,即使一切再來一次,在所有關鍵時刻,我會作別的選擇嗎?我會走相反的方向嗎?我會變成另一個人嗎?我想不會,這歷史屬于我自己。”
樂黛云的家在北京大學的燕南園,家門總是虛掩的,以方便來客的出入。樂教授退休15年了,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博士生還常到她家里上課,她有時也坐著輪椅去參加一些公開的講座。她剛完成的新書《跨文化方法論初探》放在古琴邊上,每天她會花一些時間彈古琴。她親切熱情,很樂意和年輕人交流,對年輕人的世界充滿興趣。
談起往事,不管是歡愉還是困窘的經歷,她都坦誠相告,每說一段往事往往伴隨著爽朗的笑聲。
作為重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樂黛云推動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比較文學方向的碩士點、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
中國的比較文學不同于歐美,它并非誕生于象牙塔中。清末明初,在西學東漸的文化大背景下,中國產生了比較文學。在20世紀20到30年代中國進入學術繁榮的黃金時期,裘廷梁、蔡元培、魯迅、梁宗岱等都發表了重要的比較文學論著。但是跨文化文學研究課程的開設和內容設計都比較零散和隨意,并沒有涉及比較文學的學科源流和基本的理論方法和研究類型,也沒有學科體制的安排和有意識的學科建設。
季羨林曾評價樂黛云:“以開辟者的姿態,篳路藍縷,為中國比較文學這一門既舊又新的學科的重建或者說新建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新奇而浪漫的
1931年,樂黛云出生在貴陽市的樂家大院,她的父親因為英語口試時口音太重而未考取北京大學,做了幾年旁聽生。回到貴陽后,成為一名英語教師,他新潮的思想和英倫打扮在貴陽頗有名氣。樂黛云因此自小也接受西式教育,學習英文和古典音樂。
1946年,從西南聯大歸來的表哥向樂黛云帶來了革命的信息。他繪聲繪色地描述了聞一多如何痛斥國民黨,如何被暗殺,悼念活動如何悲壯,學生運動如何紅火,這讓偏居西南一隅的樂黛云目瞪口呆,“簡直是白活了!”她堅定地認為,“不打垮國民黨是無天理,投奔革命隊伍,必定是正義、新奇而浪漫的!”
1948年,17歲的樂黛云坐在貨運卡車的大木箱上,顛簸地穿行在云霧和峭壁之間,過金城江、下柳州,上抵武漢,她要去的地方是正被炮火圍城的北平,而身上僅有一紙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和7塊銀元。她不顧父親對于戰后中國將劃江而治的判斷,放棄了位于南方的中央大學,執意北上。她認為,北京大學是中國革命的搖籃。
這一年的冬天,因為沈從文的賞識,樂黛云從英文系轉入中文系,當時沈從文教授國文,系里還有廢名、唐蘭、齊良驥等著名教授。
很快,樂黛云就加入了地下黨的外圍青年組織,為解放軍進入北平做前期工作。在深夜,她用手電筒校對革命宣傳手冊;在地圖中,標出解放軍攻城時需要保護的文物古建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組織還委派她游說沈從文留在大陸。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告新中國的成立,18歲的樂黛云感到那時處都是“鮮花,陽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那樣的年紀,那樣的時刻,年長者不容易有,后來人又難以體會,那種熱情后來就成為我性格的一部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位自小學習英語和西方古典音樂、看歐洲小說美國電影的資產階級小姐,從此摒棄了腐朽的“小資情調”,開始將蘇聯小說《庫頁島的早晨》里那句話“生活應該燃燒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煙”當成自己新的人生信條。
1950年的青年節,樂黛云作為學生代表上天安門城樓給劉少奇獻花。
1952年,樂黛云在畢業后的第二天,與哲學系同學湯一介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張輝是樂黛云的學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原本她有機會去擔任北京市領導人彭真的秘書,也有機會成為一名外交官,但她喜歡學術,選擇了留校教書。”
畢業后,樂黛云成為了著名學者王瑤的助手。王瑤學貫古今,不論是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他都具有深厚的學養,這對樂黛云的影響和幫助很大,為她日后研究比較文學打下很好的基礎。樂黛云形容王瑤“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現代的、傳統的,新派的、舊派的,開闊的、嚴謹的、大刀闊斧的和拘泥執著的”。
張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樂黛云身上同樣傳承了這種有容乃大的精神,她對學術的前沿性和經典性問題的關注始終如一,與王瑤先生的那一代老北大人是一脈相承的。”
1956年,因為和其他7位青年教師合辦名為《當代英雄》的刊物,樂黛云被打成了右派。“當時的右派被分為六種,我是比較嚴重的‘極右派,開除黨籍,撤銷公職,每月只有16元工資,并下鄉勞動改造。”樂黛云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
“學生們經常問我學問為什么好,我說其實我的學問不好。我們這代人精力最好的20年時光就在批斗,寫檢查,壘豬圈,修水庫,養豬放羊,趕驢打磚中度過。我們的時間被剝奪了。”樂黛云說。
下放勞改時,她會系上一條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鮮艷的頭巾,以表達一種反抗。因為總不“認罪”,右派帽子始終不能摘掉。
1971年,北京大學二千余名教職工歷時兩年建立的江西鯉魚洲“草棚大學”結束了,身為教員的樂黛云也隨隊回到北京,她的15年光陰隨著“草棚大學”的農田、校舍一起荒蕪了。
一個“與時俱進”的人,一個不斷“革自己命”的人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元年,北京大學迎來了第一屆歐美學生。北大中文系要求“摘帽右派”樂黛云為留學生開一門《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

樂黛云。
樂黛云回憶說:“當時教留學生沒什么成績可言,將來升職稱,不算正規的成績,所以沒有人愿意做,我在系里地位比較低。其次是大家都害怕跟外國人接觸,擔心講錯話。中文系能講英文的人也很少,我當時還能講點英文,能和學生溝通。我上歐美班的課是中文英文混著講,再發點英文的材料給他們。”
當時規定只能講魯迅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樂黛云為確保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把“不讓講”的巴金、老舍、曹禺、徐志摩、聞一多也一一講解,很受歐美學生的歡迎。在備課中,樂黛云發現這些中國作家受西方文化影響很大,其中尼采的角色特別突出。尼采的超越平庸、超越舊我的理想,對晚清以來渴望推翻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1年,樂黛云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引起強烈的反響。它不但引發學界對研究尼采的興趣,也開拓了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關系研究的新的空間。
這一年,北京大學正式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會,季羨林與錢鐘書分別任會長和顧問,50歲的樂黛云任秘書長。她說自己就是“跑腿的”。這個比較文學研究會始終是一個民間獨立研究會,并沒有歸屬體制。
經人引薦,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專程到北大與樂黛云見面。在他們看來,《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文突破了當時中國學界一貫完全從單純的政治視角評價思想家、藝術家影響的觀念,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一名外國著名學者,并且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這是非常難得的。他邀請樂黛云到哈佛大學進修訪問一年。哈佛大學是比較文學的創始者,世界上第一個比較文學系就在那里成立,這次進修之后被樂黛云認為是她比較文學研究道路上的重要節點。
1983年8月,北京召開了第一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由此奠立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基礎,這次討論會由錢鐘書主持,中美兩國學術界的頂級人物紛紛到場。1984年,錢鐘書的《管錐編》問世,成為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的標志。
但熱鬧過后,中國的比較文學又沉寂下來,“說白了就是沒有做具體工作的人。”樂黛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從哈佛研修回國后,樂黛云回到北京大學,提出要建立比較文學研究所,但遭到了中文系和英語系的回絕。中文系的一些教員認為她中國文學不通,外國文學半拉子,就搞所謂的比較文學,根本行不通。就連丈夫湯一介也寫了一首打油詩調侃她,“摸爬滾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禪”。“他覺得我英文不太好,外國文學根基淺,中國文學古代部分也欠缺,建議我抱定一本書,把《文心雕龍》研究透了就算了。”可樂黛云不服。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人,一個不斷‘革自己命的人,不習慣于循規蹈矩,更不屑于人云亦云。”
此時,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正在創建深圳大學,北京大學是對口支援建設單位,樂黛云從這里看到了機會。她到這所如同白紙一張的大學兼任中文系主任。
在全球意識觀照下認識中國文化
在深圳大學,樂黛云開展比較文學研究的想法得到了校長張維的支持。在港臺各高校捐贈的比較文學資料室里,樂黛云等人編著了一套8本的《中國比較文學叢書》。
樂黛云還想在深圳成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對外她找到各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學者,對內則寫信聯系多家高校,最終國內有36個大學和研究機構表示了參會愿望,每家出資200元作為會費。之后經過上下一番奔走,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終于得到批準成立。學會組建第一屆比較文學講習班,授課專家來自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有超過200多青年教師參與。這次參加講習班的成員也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領域的“黃埔一期”。
樂黛云認識到推廣和普及比較文學在學科建設中的意義。當時以梁漱溟為主席、馮友蘭為名譽院長的中國文化書院提出,要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文化書院是80年代“文化熱”的重要陣地之一,樂黛云是首批加入中國文化書院的學者。
1987年,在她的推動下,中國文化書院舉辦了首屆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班,函授學員達到12000余人。他們是來自中國各地各個領域的知識人,其中有的人從山區趕來,帶著紙筆,甚至干糧。因為不愿花錢租住已經很便宜的學生宿舍床位,他們就露天鋪張草席睡在房檐下或涼亭里。
樂黛云就在屋檐下和涼亭里和他們聊天,一聊到深夜。她發現諸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然是知識分子普通的共識,盡管她試圖講述“男女平等平權”的道理,但大多數人認為“這根本不可行”。陳舊觀念還占據著大多數人的心靈的事實,讓樂黛云看到在大眾中推廣比較文學、加強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1990年,樂黛云回到北京大學,開設了比較文學課程,大受學生們的歡迎。此時,中國比較文學發展進入快速通道。據不完全統計,1990年至1993年期間,出版、發表的比較文學論著達到865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樂黛云和錢林森主編的大型叢書《中國文學在國外》全套十本(已出6本),規模宏大、視角新穎,以豐富翔實的材料展示了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接受、變形和匯流,得到眾多讀者的贊賞。樂黛云和王寧主編的論文集《西方文藝思潮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就西方多種思潮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影響,以及西方的意象派詩歌、表現主義戲劇、現代主義小說對中國創作模式的沖擊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扎實的論證。
1993年,樂黛云在北京大學建起了比較文學博士點。1997年,中國官方正式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確定為文學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的八個二級學科之一,這是比較文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我并不悲觀”
90年代末,樂黛云在自傳文章中寫到,“我似乎還有可能返老還童,從頭開始。然而,即使一切再來一次,在所有關鍵時刻,我會作別的選擇嗎?我會走相反的方向嗎?我會變成另一個人嗎?我想不會,這歷史屬于我自己。”
2010年,湯一介在樂黛云80歲生日時又寫了一首詩,他將“摸爬滾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禪”改成了“摸爬滾打在他鄉,翻江倒海開新章”。
她經常引用費孝通的話概括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清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那么就堅持下去。費孝通先生當年在反右派運動中始終保持著‘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心態,對我特別有啟發意義。不管別人說什么,要勇往直前。你們說你們的,我做我的。”
但不同于費孝通所認為的“在這種情況下面縱向的傳承很難繼續”的悲觀,樂黛云對于年輕人和當今社會保持著樂觀,“因為我看到了一些新的變化,我看到年輕人很多好的現象,特別是在一些90后的身上,他們思想獨立,關心國家,特別是愿意投身到公益事業中去,他們對傳統文化充滿熱情和興趣,而且我還知道很多學生學習是非常用功,所以,我并不悲觀。” 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