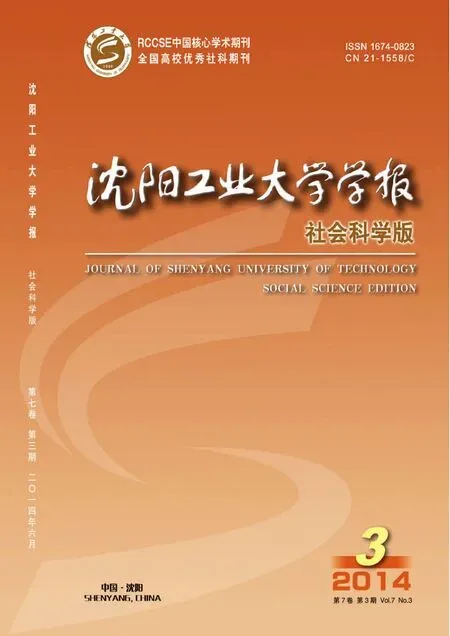城鎮化背景下大遺址管理體制的突破與困境*
郭 萍, 劉 潔
(1.北京工業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北京 100021; 2.北京物資學院 勞動科學與法律學院, 北京 101149)
城鎮化背景下大遺址管理體制的突破與困境*
郭 萍1, 劉 潔2
(1.北京工業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北京 100021; 2.北京物資學院 勞動科學與法律學院, 北京 101149)
對大遺址管理而言,我國正穩步推進的城鎮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為回應這些機遇或挑戰,“十一五”前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尋求大遺址管理體制中管理架構和機構的部分突破。這些突破對大遺址保護已經或正在產生積極影響,但也面臨著政策不具普適性、無法根除原管理框架痼疾等困境。促成大遺址保護需求與規劃的銜接、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大遺址管理,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
城鎮化; 遺址保護; 文物保護; 大遺址管理; 管理體制; 管理架構; 條塊分割
對大遺址管理而言,我國正穩步推進的城鎮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城鎮化是本文的主要研究背景。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標準來看,城鎮化率的提高,即城鎮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的提高[1],意味著農村往城鎮遷移常住人口比重的提高,并會帶來城鎮人口、產業甚至城市本身面積規模的擴張,引發更大范圍的城鎮工礦建設、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和住宅建設需求①這一需求在2008年發布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第一章第二節中,即在土地需求層面得到明確預期。該節認為,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城鎮工礦用地需求量將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較高水平”,“區域性基礎設施用地"將"進一步增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還需要一定規模的新增建設用地周轉支撐”。參見《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通知》(國發〔2008〕33號)。。
一、緣起:城鎮化之于大遺址的挑戰與機遇
城鎮化的全面展開,既對我國城鄉格局完善、經濟發展產生了正面影響,也給文物(尤其是大遺址)保護帶來新的挑戰——大范圍建設意味著城市和農村地上、地下空間的擴大與更新。由于與這些建設行為共享地下空間,且一旦建設即意味著對遺址的擾動,不少埋藏于地下且規模較大的大型古代遺址將不得不面臨與各種建設“爭空間”的命運。
基于這些遺址之于中華文明的重要性及保護緊迫性,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于2006年聯合發布《“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以下簡稱《大遺址十一五規劃》),并于2013年5月發布《大遺址保護“十二五”專項規劃》(以下簡稱《大遺址十二五規劃》),于開篇即明確其制定目的意在對抗“快速發展的城鄉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農民生產、生活”(或“大規模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等給大遺址帶來的威脅及破壞,將城鎮化發展中的建設行為列為大遺址遭受威脅或破壞的首要因素。與此同時,與這兩部國家級行動計劃配套,自2005年起財政部每年撥付2.5億元資金,專項用于大遺址保護[2]。
大遺址保護究竟有何特殊性和緊迫性,使得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在每年已撥付數目可觀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專項補助經費”的前提下,另外撥付如此大筆的經費專項用于特定類型文物(大遺址是否屬于文物的一類尚存爭議,為表述之便,這里姑且稱之)的保護?城鎮化背景下大遺址管理體制的突破及困境,由此進入筆者的研究視野。
二、大遺址管理體制的突破:從中央到地方
所謂“大遺址”*對于如何科學界定大遺址的內涵及外延,理論和實務界尚無定論。本文所提出的大遺址概念,主要源于《大遺址十一五規劃》。參見國家文物局、財政部《關于印發“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的通知》(文物辦發〔2006〕43號)。主要包括“反映中國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歷史文化信息,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因其“規模宏大”,且本體依附于土地而存在,具有較強的不可移動屬性,大遺址保護工作面臨保護范圍大、所涉群體廣、遷移異地保護難度極大且成本極高等其他較“小”的不可移動文物較少面臨的問題*嚴格說來,根據《文物保護法》第20條第1款規定:對文物保護單位應當盡可能實施原址保護。但在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某些地上的不可移動文物可能無法原址保護而必須異地保存,不可移動文物與環境的關聯性被切斷,其文物價值雖然減損但仍可部分保留。這一情況在我國和其他國家均有出現,前者如2012—2013年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舒坪劉氏節孝坊的異地保護(參見《自貢市首例文物異地保護工程順利通過竣工驗收》,載自貢市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zg.gov.cn/news/articles/2013/09/05/20130905112416-160976-00-000.asp),后者如20世紀50—60年代埃及為修建阿斯旺大壩遷移兩座神廟,因而直接促成后來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誕生(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由此對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城鎮化衍生的“地下空間爭奪戰”正如火如荼開展的當下,傳統管理體制逐漸不再能完全滿足新形勢需要,并直接影響到大遺址的保存狀況。
在這一情勢下,從中央到地方層面,從國家文物局到其他相關部門,都在或主動或被動地探索大遺址管理體制方面的突破口,以順應時勢所需。其中,在原有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下簡稱“國保”)*第一批重要大遺址名單公布時,僅有二處大遺址非國保單位,分別為:大辛莊遺址,第一批(1977年)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已公布為第七批國保單位;絲綢之路新疆段,雖然該段并未整體公布為國保單位,但在該段上分布有十多處國保單位。因此,絕大部分大遺址兼具“大遺址”和“國保單位”的雙重身份。管理方式之外,打破傳統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管理格局的中央主導的“央地共建大遺址保護”項目庫和地方層面各種形式綜合性管理機構的設立,成為這一嘗試中的代表。
1.管理體制突破前的“文物保護單位”管理方式及其“不適應癥”
大部分大遺址本身即為國保單位,基于考古工作需要,加之國家文物局早在1991年即發布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標志說明、記錄檔案和保管機構工作規范》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敦促國保單位規范其管理,不少大遺址較早即建立了保護機構。如今,相當數量的遺址保護機構(或發展為管理機構)仍以文管所、博物館以及由文物(文化)局或考古隊、博物館代管的過渡性管理機構三類形式[3]存在并運行,并以“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要求對大遺址進行管理,接受不同層級文物行政部門的行政管理,其主要職責為文物的“調查征集、保護管理、維護修繕、藏品保管、宣傳陳列和科學研究”*參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標志說明、記錄檔案和保管機構工作規范(試行)》,1991年3月25日由國家文物局公布并施行。等工作。這幾類管理形式基本以文物本體為中心開展工作,主要方式為在為文物保護單位劃定邊界(如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等)后進行相對封閉的管理。這種以文物本體為中心的封閉式管理方式,在“大遺址”這一概念提出并推行后產生了一系列“不適應癥”。有研究已經留意到,因各部門多頭管理而導致的決策分散、溝通不暢等問題以及對大遺址本體及管理方式不得不具有相對開放性這一特點的欠考慮,直接對遺址管理效率產生了負面影響[4]。
與較易確定保護邊界、面積相對較小、存在由文物管理機構進行封閉式管理可行性的地上文物保護單位不同,由于占地面積較廣,許多大遺址與居民的生產、生活區域重疊,且其邊界較難確定,難以進行封閉式保護,因此,以保留遺址區內的部分生產、生活為主要特征的開放式管理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也較為常見。開放式管理方式意味著遺址不再僅作為文物得到保護,而是需同時滿足當地居民生產、生活等方面需求。
在中央層面,根據相關法律,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公安部等部門也和國家文物局一樣擁有在大遺址區域范圍內行使法律賦予的土地、建筑、農業、林業和治安等方面管理權的權能。“這些職能部門從中央到省、市、縣有三個以上層級的垂直序列”,中央級的行業主管部門主要承擔業務指導和規劃、監督、審查等專業職能[5]116-117。
而從地方決策者層面來看,根據《憲法》第107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而文物保護不過是該條所列舉的7項事業中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因此,除文物部門外,工商、林業、公安、土地等部門也在這些區域內行使相應管理職權。例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金沙遺址已探明的遺址面積約3 km2[6],其中金沙遺址博物館占地面積30萬m2[7],其余面積則或將原規劃為中高層住宅區的地區調整為低層住宅區(金山片區),或部分建成永久性綠地等[8]93-94。類似情況在其他大遺址中也屬常見,即園林、工商、公安、國土等部門與文物部門一同在該遺址范圍內各自行使日常管理權能。在地方一級,這些部門為各級地方政府的業務部門,事權、財權均由地方政府統籌及解決。
綜上可見,在出現新的管理體制方面的突破之前,在中央一級,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主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業務指導、規劃、監督、審查等實現對地方一級行業內部門的管理,這一縱向分級管理方式,被業界稱之為“條”狀管理;在地方一級,大遺址多采屬地管理,由當地政府統籌遺址內各項事務,這一橫向分部門管理形式則被稱之為“塊”狀管理。傳統的以“文物保護單位”管理為代表的封閉式管理方式不適用于開放性較強的大遺址,并因其固有的條塊分割、多頭管理等弊端[4],產生責權不對等、管理主體多元化、管理目標多元化、市場尋租等問題[3],使得各地方職能部門在具體行使管理權時容易各自為政,割裂大遺址所涉事項的關聯性;一旦管理事項產生沖突,即有可能因缺乏協調機制而導致問題被擱置、得不到及時解決。這被認為是形成大遺址保護現狀的重要消極因素。
2.管理體制中央層面的突破:“央地共建大遺址保護”項目庫
以大遺址保護片區為主要表現形式、“央(局)地(省)共建”為主要特點的“央地共建大遺址保護”項目庫,雖然其本意未必如此,但卻為克服上述為學者詬病的條塊分割、多頭管理弊端提供了解決思路[9]。根據《大遺址十一五規劃》和《大遺址十二五規劃》,目前我國已將陜西西安片區、河南洛陽片區、湖北荊州片區、四川成都片區、山東曲阜片區、河南鄭州片區6個片區納入“央地共建大遺址保護”項目庫。雖然官方并未在任何法律、法規或其他規范性文件中對何為大遺址保護中的“央地共建”、“片區”進行解釋,但從已公布的上述大遺址片區來看,這些片區都具有覆蓋面積較大、分布相對集中、文化發展脈絡具有代表性、歷史與文化淵源在我國人類文明和文化進程中具有較高地位等特點[10],“片區”的運作方式則主要是由國家文物局直接對片區給予經費、人員培訓方面的傾斜,片區所處各級(主要是省級)人民政府承諾針對片區內大遺址主動開展保護工作[11]。筆者認為,大遺址保護片區這一管理方式至少能在如下兩方面取得突破:
(1) 調動地方政府主動開展大遺址保護工作的積極性。由于只有在其本體和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內禁止或限制建設活動才能有效保護大遺址,身負完成“城鎮化率”等各項指標任務的地方政府對于遺址保護的態度一直相對消極。這一態度由2012年因長沙古城墻被遷移異地保護事件而被輿論“一邊倒”地指責的長沙市市長張劍飛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的回應可見一斑:“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確實是一對矛盾……在建設中,如果一開挖發現文物古跡就停住不建,對于長沙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而言,可能就無法建設了。”一旦停止建設,可能動輒意味著“上億元”甚至“140多個億的損失”[12]。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頗具代表性,巨額的直接經濟損失和看不見現實、眼前利益的遺址保護之間“孰輕孰重”其實是相對清晰的。
“央地共建大遺址保護”項目庫的設立則多少減輕了地方政府對大遺址保護巨額投入的顧慮。一方面,根據與省政府簽訂的框架協議,國家文物局會承諾對片區給予項目實施、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傾斜[13],亦即地方政府能由項目中獲得中央層面從財權到事權方面的優惠,且遺址等文化資源還因其文化底蘊成為“城市名片”*將大遺址作為“城市名片”或其他城市形象代表的說法,在多位參加大遺址保護西安、良渚、洛陽、荊州論壇的地方執政者講話中均有提及,其中西安、洛陽、荊州論壇講話已匯編成《大遺址保護高峰論壇文集》(西安)、《大遺址保護洛陽高峰論壇文集》、《大遺址保護荊州高峰論壇文集》,分別于2009年、2010年、2013年由國家文物局出版。;另一方面,地方享受的上述優惠需以相關工作的開展為對價,由此推動地方由省一級支持遺址保護工作的開展,并承擔具體協調和統籌工作。
(2) 有助于協調文物管理部門與其他職能部門的關系。根據《憲法》第107條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是除中央以外的最高級別地方人民政府,負責全省行政區域內“經濟、教育、科學、文化”等行政工作。因此,其有能力在較高層面有計劃地協調大遺址保護工作開展中可能遇到的各部門職能交叉的狀況,既有利于預防市、縣級發生類似情況;其優先進行大遺址保護、主動開展大遺址相關項目建設的積極態度,也有利于在前述所涉部門發生管理職能沖突時作出有利于遺址保護的選擇,由此多少破解前述條塊分割中塊狀管理弊端。加之這一方式是由國家文物局與省級人民政府直接對話,即二者為“片區”框架協議的雙方,不必由國家文物局將經費逐層分解到地方各級文物管理部門,在一定程度上將條狀管理和塊狀管理結合起來,對于克服條塊分割的管理方式的弊端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3.管理體制地方層面的突破:綜合性遺址管理區、特區等的建立
如果說“央地共建大遺址保護”項目庫是在國家(主要是中央)層面試圖破解條塊分割的管理方式,那么遺址管理區、特區等綜合性管理體制的建立則是地方層面克服這一管理方式弊端的嘗試。就關涉群體如此之廣、占地面積如此之大的遺址而言,首先擺在決策者面前的問題是:分別負責完成前述多重目標的文物、園林、工商、公安、國土等行政(管理)部門與上級業務指導部門之間、相互之間已形成條塊分割的管理格局在先,如何統籌各職能部門之間的管理行為,才能實現對遺址的科學管理?以遺址為要素或中心,建立綜合性的管理機構,成為部分決策者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以筆者目力所及,目前此類管理機構的主要表現形式為遺址管理區或特區,其整體或部分為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代行政府職能。例如,2008年設立的統籌瓶窯、良渚兩鎮的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良渚管理區”,后其權力被弱化至主要為遺址事務管理機構),統籌大明宮遺址保護、開發事宜的西安曲江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辦公室(以下簡稱“大明宮保護改造辦”);2012年設立的漢長安城遺址保護特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漢長安城特區管委會”),等等。
就本文所述綜合性的遺址管理區或遺址特區而言,由于其設立目的即在于統籌遺址所涉范圍內事項,因此一般來說,其組織成員包括遺址范圍內行使行政管理職能的主要部門,如前述良渚遺址管理區委員會在設立之初下設辦公室、土地與規劃建設處、文物管理局、綜合發展處4個部門,另設余杭區財政局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分局和瑤山派出所,負責管理區范圍的文物保護、城鄉規劃、經濟開發、社會管理及其他工作的協調與監督等[14],實際上被賦予242 km2管理區域范圍*有關良渚遺址管理區的區域范圍,參見2001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設立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的批復》(浙政函〔2001〕205號)。轉引自余杭區人民政府《關于同意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發展規劃的批復》(余政發〔2012〕11號),載余杭區人民政府門戶網站,http://s.zj.gov.cn/wse/temp/S1/MR/964ed699ea8e500d1e31a85dc6d48c91.mht.-955443135.htm.內的國土、規劃、文物管理、財政、公安等主要行政權力,行使政府派出機構的職責。此外,為保證上述成員能達成一致意見,組織的領導層(如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或特區)一般由主管其中所涉某項業務的高級別行政領導兼任。前述大明宮遺址、良渚遺址、漢長安城遺址在其綜合性管理機構設立之初均大致循此思路。
由于這些綜合性管理機構的成立目標和管轄范圍均較為明確,專司統籌和協調遺址保護及相關事務,且一般較全面地設立了遺址所涉事項的主要職能部門,因此在處理問題的及時和有效方面具有較明顯的優勢。
三、大遺址管理體制突破中的困境、原因與解決思路
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條塊分割管理體制產生的部分問題,但是無論是大遺址保護片區抑或是遺址管理區、遺址特區,在其實現管理體制突破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困境。
1.管理體制突破后的困境
大遺址片區推廣的困境在于,這一管理方式不適用于所有的遺址類文物,不具備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的可行性。首先,要成為片區,需滿足前述所列遺址相對集中等諸多要求,而由我國大遺址的分布來看,顯然并非所有行政區域都具備成為片區的條件。其次,地方樂于推進片區項目的動力在于中央所給予的事權、財權方面的傾斜,而這方面的傾斜往往需要較大數額的中央財政專項支出的支持,考慮到我國已提出將中央專項轉移支付大幅壓縮1/3以上[15],獲得大力度的中央財政支持絕非易事。
置諸地方層面,遺址管理區、特區管理方式的推行也并非毫無障礙。由于大遺址保護邊界并非總與現有行政區劃邊界對應,因此在運作過程中,這些綜合性遺址管理區、管理辦公室、特區應如何與目前的行政區劃進行銜接,將是管理者首先需解決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相關部門為這些機構的日常運轉新增人員編制及日常經費;此外,一旦管理區、特區與其所處行政區域的行政級別相同(如良渚遺址管理區與其所處的余杭區同為正區級單位[15])或管理目標重合,則如何處理二者關系將成為新的協調需求。
2.管理體制困境產生的原因及其解決思路
筆者認為,撇除中央、地方決策者個人意志的影響,我國大遺址管理體制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大遺址保護需求與城市規劃的銜接不暢、條塊分割的管理格局無法從根本上打破等,也是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
(1) 大遺址保護需求與城市規劃的銜接問題。大遺址保護需求與城市規劃、尤其是土地利用規劃的銜接不暢,是造成地方決策層認為大遺址在與城市發展“爭空間”的重要原因。這種銜接上的不暢通,使得大遺址沒有在城市規劃階段得到合理定位,其保護需求也無法先期得到滿足。之所以如張劍飛等地方決策層認為大遺址保護即意味著需付出較大代價,直接原因即在于大遺址對土地的限制、禁止建設需求未在城市規劃中得以體現,而多是當開發商破土動工時,才發現其已支付巨額土地轉讓金(如根據前述南方周末所載張劍飛市長訪談,古城墻事件所涉開發商萬達集團支付的土地出讓金為24.5億元)的宗地地塊內有遺址遺存。考慮到已付出的土地轉讓金、征拆成本及可預期的豐厚收益,遺址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自然往往居于不被選擇的位置。因此,將大遺址保護需求與城市規劃相銜接,能使文物或相關部門在規劃階段即獲得遺址保護的主動權,預防各部門職能沖突狀況的出現。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將大遺址保護需求納入城市規劃(尤其是土地利用規劃)并非僅限于理論層面,而是已有十分成功的實踐,如美國聯邦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即在其管理手冊中規定,根據不同用途,在規劃土地范圍內,應為已知(known)或已立項(projected)的蘊藏有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s)*BLM所謂文化資源,包括考古遺址(archaeological sites),歷史遺跡(historical sites)和具傳統文化重要性的場所(pla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mportance)等。的區域預留一定的土地配額(allocation)[16]。這些預留配額體現于土地管理局的土地利用規劃(land use plan)性質的“資源管理規劃”(resource management plans)*RMPs主要用于評估并溝通公共用地方面的問題。參見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Land use planning[EB/OL].[2013-01-11].http://www.blm.gov/co/st/en/BLM_Programs/land_use_planning.html.部分,為強制性規定。經由這一具有前瞻性的規定,聯邦政府能先期保證文化資源用地不必與其他類型用地搶占配額;由于規劃是面向全社會公開的,且一般會在土地使用權買賣時明示,土地買受人無法借口不知土地為文化資源用地而對其進行破壞。
進一步深究,如果我國如美國一般將大遺址保護需求納入土地利用規劃,則至少還需開展如下基礎工作與其配套:勘定和劃定遺址保護所需土地面積(以使國土部門明確遺址所需土地配額),精確測量遺址坐標并將其反映到城市規劃中,在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證上載明遺址所處土地的使用限制事項等。
(2) 條塊分割的管理格局問題。從前文有關中央和地方層面管理體制突破的論述不難看出,這些突破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試圖消解條塊分割管理格局的弊端,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且其日常工作仍處于這一管理格局內。
雖然誠如某幾位學者的美好愿景,在中國建立類似美國的“國家公園體系”,以實現中央垂直管理(在地方層面表現為分片管理)能最終避免這一格局的弊端[5]4-125,但筆者認為,這一管理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且所涉甚廣,要改變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不過,由中央正逐年將行政許可權限下放或取消的趨勢來看,遺址管理也許能夠跳出目前遺址保護仍以行政管理為主、為重的窠臼,吸引社會力量參與其中,進而逐步在保護與利用中取得平衡,以另一種形式取得管理體制層面的突破。
[1] 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 [EB/OL].[2013-04-15].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4/t20130415_17743.html.
[2] 李韻.財政部設立每年2.5億元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 [N].光明日報,2005-06-15(A1).
[3] 陳穩亮.大遺址管理體制改革的探索:基于風景名勝區管理體制改革的經驗與教訓 [J].旅游學刊,2009(9):79-84.
[4] 劉衛紅.大遺址區土地利用管理分析 [J].中國土地,2011(9):5-8.
[5] 劉世錦.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報告(2013) [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6] 朱章義,張擎,王方.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與意義 [J].四川文物,2002(2):3-10.
[7] 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遺址 [EB/OL].[2014-01-20].http://www.jinshasitemuseum.com/about.html.
[8] 王忠林.認真搞好金沙大遺址保護與利用 積極引領成都城市新發展 [C]//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洛陽高峰論壇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15.
[9] 郭萍.大遺址保護管理體制與機制研究綜述 [J].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3(4):18-22.
[10]宋曉龍,王曉婷,孫霄.片區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編制方法初探:以《曲阜片區文化遺產保護總體規劃》為例 [J].北京規劃建設,2011(5):94-97.
[11]劉冰雅.從累贅到名片:大遺址華麗轉身之后的思考 [N].光明日報,2011-12-26(15).
[12]彭利國,鞠靖.“講我不注重保護文物,我感到很委屈”:專訪長沙市市長張劍飛 [N].南方周末,2012-02-23(5).
[13]滕敦齋,袁濤,汪海濤.國家文物局與省政府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EB/OL].[2011-03-17].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103/t20110317_6224410.html.
[14]余杭檔案信息網.2001年余杭大事記 [EB/OL].[2006-09-08].http://daj.yuhang.gov.cn/zjyh/yhdsj/200609/t20060908_3307.htm.
[15]財政部.削減專項轉移支付 有序推進預算公開 [N].政府采購信息報,2014-03-10(14).
[16]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Land use planning [EB/OL].[2013-01-11].http://www.blm.gov/co/st/en/BLM_Programs/land_use_planning.html.
Breakthoughanddilemmaofmanagementsystemofbigarchaeologicalsiteunderbackgroudofurbanization
GUO Ping1, LIU Jie2
(1.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1, China; 2.School of Labor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China)
The steady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to the management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Dayizhi).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adopt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ment to local goverments around the “11th Five-year Plan” in responding to the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so as to seek some breakthroughs of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s.The breakthroughs have had or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s, but they are still facing some predicaments of non-uniform policies and non-eradication of old management structure.To promote the linkage of demand and plan of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protection and introduce social forces into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mean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urbanization; archaeological site protection;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big archaeological site (Dayizhi) management;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structur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vision of management
2014-04-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1&ZD026)。
基金項目:郭 萍(1983-),女,湖北嘉魚人,助理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文化遺產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5-20 16∶52在中國知網優先數字出版。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525.1242.003.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3.02
D 912.6
A
1674-0823(2014)03-0201-06
(責任編輯:郭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