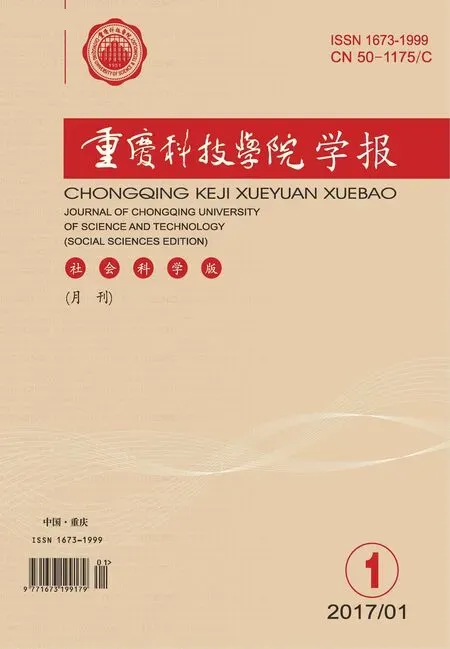艾麗絲·沃克小說的女性創傷書寫
——以小說三部曲為例
黃慧麗
艾麗絲·沃克小說的女性創傷書寫
——以小說三部曲為例
黃慧麗
艾麗絲·沃克的小說三部曲展現了黑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所遭受的種種創傷。她們所受的創傷不僅來自于社會,還來自于家庭;不僅是身體,而且心靈也飽受創傷。創傷敘事、回歸傳統文化和族裔身份,以及與周圍群體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有助于黑人女性走出創傷。
艾麗絲·沃克;小說三部曲;黑人女性;創傷
艾麗絲·沃克憑借長篇小說《紫顏色》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普利策獎的黑人女性作家。她的小說被譽為“永恒的經典”,是世界上被重讀次數最多的作品之一[1]2。早在1979年哈佛大學教授丹尼·霍夫曼在他主編的《哈佛當代文學導論》里就已經把艾麗絲·沃克、托尼·莫里森等人視為“有才華的小說家”[2]。沃克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她創作過詩歌、散文,寫過文學評論以及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迄今為止,已發表長篇小說7部。在她的前期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稱為小說三部曲的《格蘭奇·科普蘭的第三次生命》《梅麗迪安》和《紫顏色》。在這三部作品中,黑人婦女在以白人文化為中心的社會中和在黑人男權制度的控制下所遭受的肉體和心靈的創傷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本研究以創傷理論為視角,聚焦這三部小說中的主要女性人物,通過分析她們在成長過程中所遭受的種種創傷,揭示造成黑人女性悲劇的社會根源。
一、創傷理論概述
創傷理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美國學者凱西·卡魯斯在她的著作《沉默的經驗》中提出來的。“創傷”指的是某些人“對某一突發性或災難性事件的一次極不尋常的經歷”[3]11。該理論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社會邊緣群體的創傷經歷,如弱勢群體中的女性、兒童、少數族裔以及戰爭中幸存的士兵等。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與創傷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文學創作為人們提供了發泄壓抑情感的途徑,使壓抑身心的緊張狀態得到舒緩[4]7。作為黑人女性作家,沃克時刻關注著黑人婦女在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雙重壓迫下的悲慘處境。她們所遭受的創傷不僅來自于社會,還來自于家庭;不僅是身體,而且心靈也飽受創傷。
二、女性創傷書寫
沃克前期創作的三部作品描述了黑人社區中泛濫的暴力現象,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美國女權主義理論家貝爾·胡克斯認為:“不管是由于拋棄造成的情感暴力,還是由于種族主義、性別主義、階級精英主義追求統治帶來的暴力,黑人生活中暴力成為范式,這是黑人生活中創傷不斷的基礎。”[5]21
在沃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格蘭奇·科普蘭的第三次生命》中,梅姆是家庭暴力的典型受害者,她曾是一位美麗、天真的姑娘,對于婚姻生活有著美好的憧憬。她教丈夫布隆菲爾德識字,希望他能擺脫無知;她去教書、當傭人,希望能用自己的雙手為家人創造美好的生活;她忍耐、包容丈夫,焚燒了書籍和雜志,放棄了正規的語言,努力丑化自己的形象。布隆菲爾德也愛著梅姆,但是,這種愛并沒有給他帶來安全感,反而讓他覺得梅姆的關愛會威脅到他的男性氣質,這使他感到害怕。因為他“只想做個男人”,能控制自己的妻子,如同他能控制自己家的豬和雞一樣[6]127。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就是不想試著去喜歡一個人。”[6]256可見,是白人父權思想所強調的男性/父親/丈夫在家庭、社會生活中擁有絕對權威的中心地位的觀念否定和抹殺了黑人男性的個性;是大男子主義思想造就了黑人男子滅絕人性的家庭暴力。因而,當布隆菲爾德的孩子們想到“敵人”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父親。
布隆菲爾德逐漸蛻變成了一個家庭暴君,不斷地毆打自己的妻子,把她打得體無完膚,直至慘死在他的槍下。可以說,是父權制家庭暴力和種族主義的壓迫導致了這個家庭和梅姆的毀滅。
《梅麗迪安》中的女主人公梅麗迪安是沃克塑造的一位革命者的黑人女性形象。她所受的家庭暴力創傷并非是身體上的硬暴力,而是精神上的軟暴力。軟暴力不是以直接的肉體打罵對家庭成員進行施暴,而是通過冷漠、歧視、拒絕與家人溝通的態度和行為,對家人一種漠視的暴力形式[7]。梅麗迪安違背母親的意愿,沒有皈依基督教,她看到了母親由于失望對她擺出的一幅冷冰冰的表情,她不由得產生了一種負罪感,覺得自己失去了母親的愛。母親感情上的疏忽和冷漠給梅麗迪安的心靈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創傷。雖然她沖破了家庭的牢籠,但是卻為此付出了精神和身體的代價。她在承受著失去母愛和失去孩子煎熬的同時,還因不能認同其他民權運動者的觀點而遭到排斥。沉重的壓力和痛苦的迷茫使得梅麗迪安在精神上幾近崩潰,她甚至出現了短暫失明、腿部麻痹和昏厥癥狀。
《紫顏色》是沃克的又一部代表性作品。這是一部書信體小說,在這部作品中沃克塑造了一群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而努力奮斗的黑人女性形象。然而,這些女性也是歷經滄桑。女主人公西麗是一名黑人,在14歲時就慘遭繼父強奸并懷孕,繼而失去了生育能力。而后,又像轉讓物品一樣被嫁給了“某某先生”,淪為他4個孩子的繼母和發泄性欲的對象。家庭的暴力和生活的殘酷、冷漠和孤寂使她絕望。西麗心中的苦悶無人訴說,因而不停地給上帝寫信。她曾這樣寫道:“他打我像打孩子一樣……我對自己說:西麗,你是棵樹。”[8]23可以看出,西麗對待丈夫的虐待已經麻木了。就如廓爾克所說:“一種來自身體的或情感的麻木的無助感是造成創傷經驗最基本的因素。”[9]在繼父和丈夫的長期打壓下,西麗變得戰戰兢兢、麻木不仁。這是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之一:禁閉畏縮,反映出屈服放棄后的麻木反應。有時創傷還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進行下去,這樣多年前的受害者就變成了加害者[10]111。在《紫顏色》中,當哈波向西麗尋求如何馴服他那充滿主見的妻子索菲亞時,出于私心,西麗建議使用家庭暴力,而原因僅是因為嫉妒索菲亞做了她不敢做的事情。
三、沃克的女性創傷書寫成因
(一)沃克本人的經歷
艾麗絲·沃克出生于一個黑人佃農家庭,沃克的父母關系并不和睦,父親經常打罵母親和孩子。沃克8歲時,右眼被哥哥誤傷導致失明,并留下了疤痕。沃克的創作中經常有暴力和創傷意象,并將男性刻畫為暴力的實施者,這很大程度上與自己的童年創傷記憶有關。大學四年級時,沃克在非洲體驗非洲文化時失身懷孕,這一段經歷使沃克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幾次欲自殺。青年時期的沃克積極投身于民權運動,親眼見證了南方黑人的普遍不幸。所有這些經歷都為沃克的創傷書寫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二)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壓迫
個人命運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沃克三部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的命運與當時的種族問題、性別歧視等社會現象同樣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在《格蘭奇·科普蘭的第三次生命》中,沃克向我們展示了發生在貧窮的南方黑人家庭中的男人對女人施以暴力的事實。為了生存,布隆菲爾德去給白人地主當佃農,但辛苦的勞作并沒有讓他走出生活的困境,反而陷入了債務。在重重壓力之下,布隆菲爾德很快成了父親科普蘭的翻版,將妻子梅姆當成自己發泄苦悶憤怒的對象,成天毒打妻子,直至后來竟然開槍將她殺死。在《梅麗迪安》中,女主人公雖然生活在一個“可以選擇自己生活的年代”,但身為黑人婦女,她仍然逃脫不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造成的傷害,深受內心分裂的痛苦。梅麗迪安背叛了傳統賦予她的角色:她不是聽話順從的女兒,不是溫順服從的妻子,也不是盡責的母親。幾重負罪感和自我迷茫使得她在精神上幾近崩潰。在小說《紫顏色》中,我們也看到了黑人男權主義對黑人婦女思想的影響和對她們身心的摧殘。她們不僅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也是性別主義壓迫下的犧牲品。
四、走出創傷的途徑
(一)創傷敘事
治療心理創傷的一種有效手段是創傷敘事。Deblinger等人最先提出建立創傷敘事的概念。創傷敘事是通過反復閱讀、書寫以及仔細思考所發生的事,來達到受傷者對創傷暗示的脫敏。沃克在《紫顏色》中使用書信體讓西麗的創傷有了傾訴的對象,也在傾訴的過程中認同了自我,從一名唯唯諾諾的小女孩成長為獨立的黑人女性。
(二)文化、身份的回歸
作為一位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艾麗絲·沃克在寫作過程中不時地流露出對非洲傳統文化的喜愛。在她的眼中,非洲黑人的傳統文化應該是這樣的:熱愛愛情、熱愛音樂、熱愛斗爭、熱愛自己、熱愛完美的事物、熱愛自己的民族。在沃克的作品中,她對黑人婦女群體中一些傳統活動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如采集草藥、縫制被子、陶塑藝術等。
在以白人文化為中心的社會里,黑人族裔始終處于社會的邊緣。在殖民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侵略下,黑人變成了劣等民族,變成了沒有文化地位、沒有民族自尊的“原始野人”。這無疑給黑人造成了巨大的心靈創傷。在《梅麗迪安》中,作為民權運動的參與者,梅麗迪安熱愛自己的民族,選擇了回到南方黑人社區堅持做她的民權工作。她找到了自己的奮斗目標,最終成為了一位體現自我價值的黑人女性。因此,回歸黑人傳統文化和族裔身份有助于重塑黑人族裔的信心,走出創傷,迎接光明的未來。
(三)同周圍的群體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
沃克的作品關注的是包括黑人男性在內的全體黑人乃至全體人類的完整生存。格蘭奇的前兩種生活處于渾渾噩噩之中,在遭到白人女子拒絕后,他才清醒過來,開始了他的第三生,他不顧一切地保護著梅姆的女兒——他的孫女露西。梅麗迪安從一名普通的黑人女孩成長為了一個富有責任感的、堅定的革命者,勇于為黑人爭取人權的事業奉獻一生,她最終去看望了殺死自己孩子的女囚。西麗在莎格的幫助下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實現了經濟獨立,她原諒了艾爾波特。哈波和索菲亞也言歸于好,實現了沃克希望的完整生存。
五、結語
在這三部小說中,沃克通過對女主人公梅姆、梅麗迪安和西麗的悲慘命運的描寫,展現了黑人女性共同的生存困境。在白人統治的社會下,這3位女性受到了來自家庭和種族的創傷,造成了自我和民族意識的喪失。沃克通過作品表達了對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命運的關注與同情,同時也在激勵同胞探索生存之路,走出創傷,回歸黑人傳統文化和族裔身份。
[1]王曉英.走向完整生存的追尋:艾麗絲·沃克婦女主義文學創作研究[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8.
[2]王逢振.訪艾麗絲·沃克[J].讀書,1983(10).
[3]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Maryland:JohnshopkinsUP,1996.
[4]薛玉鳳.美國文學的精神創傷學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5]HOOKS B R.My soul,black people and self-esteem[M]. New York:Atria books,2003.
[6]Walker A.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M].New York:A hsrvest book,1970.
[7]王喜權.家庭軟暴力解析[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09(6).
[8]艾麗絲·沃克.紫顏色[M].陶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9]KOLK V,ONNO V D H.The intrusive past: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J].American imago,1991.
[10]朱迪斯·赫爾曼.創傷與復原[M].施宏達,陳文琪,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
(編輯:文汝)
I106.4
A
1673-1999(2017)01-0069-02
黃慧麗(1977—),女,碩士,黃山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講師,研究方向為英語語言文學。
2016-10-31
2015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研究項目“艾麗絲·沃克小說的創傷書寫研究”(SKHS2015B11)。
——黑人女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