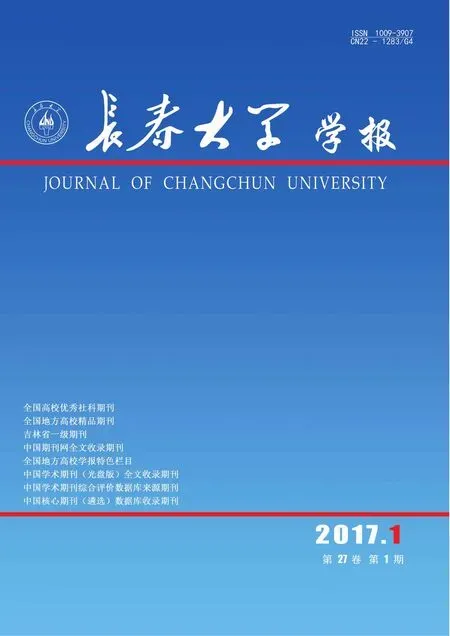多重視角下的托尼·莫里森文學價值研究
楊亞萍
(西安科技大學 人文與外語學院,西安 710061)
多重視角下的托尼·莫里森文學價值研究
楊亞萍
(西安科技大學 人文與外語學院,西安 710061)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 托尼·莫里森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對其研究也逐漸呈現深化、細化以及多樣化的趨勢。但遺憾的是,還沒有出現對其人其作進行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的綜述文章及論著。文章以此為切入點,對莫里森的文學價值從創作根由、黑人角色的深化和多層次化挖掘,到豐滿的“人”的形象的塑造以及黑人出路探討等多重視角進行概述及文學價值探討。
托尼·莫里森;多重視角;文學價值
托尼·莫里森(1931- )是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她因“在小說中以豐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詩意的表達方式使美國現實的一個極其重要方面充滿活力”而獲此殊榮。她出生于普普通通的黑人家庭,但是靠著自己的努力,逐漸成為黑人女性的佼佼者。20世紀60年代,她以極為優秀的能力在紐約蘭多姆出版社擔任高級編輯,她編輯的《黑人之書》,為美國黑人300多年的歷史作了系統客觀的介紹,這本書后來被稱為美國黑人史的百科全書。70年代起,莫里森進入到了思想與活動的最活躍的時期。她在多所大學進行美國黑人文學講座的同時,還為《紐約時報書評周報》撰寫過總計30篇高質量的書評文章,廣受好評。但學術界普遍認為,莫里森最杰出的成就與貢獻在于她的小說創作。她在70年代就創作了《最藍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羅門之歌》(1977)等3部作品。從第1部作品至今,莫里森創作小說共計11部,除以上提到的3部之外,還有《柏油娃娃》(1981)、《寵兒》(1987)、《爵士樂》(1992)、《天堂》(1999)、《愛》(2003)、《恩惠》(2008)、《家園》(Home, 2012),而最新的《God Help the Child》(2015)發表時,她已經是84歲高齡。她自始至終的創作力,獨特的思考能力以及高超的寫作水平,均令人嘆服。而她獲得的不計其數的獎項,尤其是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正是全世界文學界以及讀者對她成就的認可。
1 批評家向小說家的轉變根由
20世紀70年代對莫里森來說是重大轉折的時期,從批評家轉向小說家。眾所周知,作家的寫作往往與其所處時代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那么60年代與70年代的美國究竟發生了什么?二戰之后開始的黑人運動,是黑人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的大規模斗爭運動,其思想和方式都是比較極端和敵對的,賴特的《土生子》和拉爾夫的《看不見的人》可以說是反映這一政治運動特點的代表作。到了60年代中期,黑人的政治世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激進派開始分化出來,他們確信了解自身比在全世界推進種族激進主義更重要。同時,反主流文化(或稱新左派)開始盛行,后期盛行的文化政策則合并了這兩種反種族和反主流思潮的聚焦點,產生出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成為黑人運動政治團體的思考源泉,也成為黑人文學新階段的創作源泉,其影響力甚至都延續到90年代。當時許多優秀的黑人作家,包括莫里森,顯然受到了這種文化的影響,她積極地為黑人種族尋找除了激進以外的其他出路。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她從激進轉向了保守,也不意味著她為黑人謀求福祉的初衷有了改變,而是轉換了思路。這個轉換的結果就是:她從撰寫黑人運動的小冊子、整理與黑人有關的資料等轉向了文學,尤其是小說的創作。毫無疑問,文學的創作內容更廣泛,影響更深刻,她的寫作是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的。
這其中的深刻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首先,莫里森對黑人應該享有而實際上卻沒有的公平、正義有著強烈的訴求的愿望。她本身就是黑人,而且是女作家,與黑人朝夕相處的背景使她熟知這個團體的一切,痛苦、哀傷、不公、迷茫以及風俗、文化、傳說、思維、習慣等等都了如指掌,如果說她想將讀者融入到黑人這個特定群體的生活之中的話,小說無疑是最得心應手的表達方式。小說中,她對每個角色的細致、準確的把握,毫無疑問地證明了這一點。比如《最藍的眼睛》里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對自己黑人皮膚深深的自卑感和對“藍眼睛”的極度渴望的描寫,如果沒有作者對黑人生活的深刻體察,是絕對不會有這種入木三分的描寫的,那種自卑與向往在黑人族群中普遍存在,只有小說對特定人物的刻畫,而非政治小冊子,才能達到這種振聾發聵的效果。
其次,小說的特點就是讓不被聽見的聲音能通過文字所設定的場景顯現出來,受壓抑的聲音也因此得到表達。莫里森的初衷就是為黑人寫作。莫里森非常關注非裔群體的生活,她曾說:“如果我寫的東西不是關于(非裔)村莊或群體的,那么它就一無是處。”(Carolyn C.Denard,1991)因此,她想做的就是通過小說的方式使她所熟悉的但不被傾聽與關注的非裔黑人群體的聲音得以表達,因而被關注,被傾聽,以至被重視。
第三,她有豐富的生活閱歷,有著極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也熟悉黑人的文化以及語言技巧。她明白小說能帶給讀者想象力,而這種想象力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和理解歷史;而了解和理解黑人的歷史,對于理解黑人的現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品中的人物就能做到這一點,這是除小說之外的其他任何學術手段都無法企及的優點。
基于以上三點,莫里森從70年代起,將絕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小說的創作中來。
2 把黑人文學從淺層次反抗推進到深層次的挖掘、反思
既然是為黑人族群創作,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精神的、物質的、歷史的、現實的問題必然都會牽涉其中。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是必然會涉及的問題,如不公平的政治現狀與對社會現實的抗議等。但是莫里森并沒有停留在黑白對峙這個表面的層面上,而是進行深刻的挖掘和反思,最后把黑人許多的悲慘遭遇歸結到黑人文化無處可依的精神層面上。其實正是這一點使得莫里森的作品風格與影響大大區別于在其之前的黑人作家們,同時也使得讀者們從精神層面來理解黑人的困境。在此之前的黑人文學之所以處于邊緣化的尷尬境地,恐怕就在于之前的作者只強調了黑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及悲慘的境遇,黑人與白人之間激烈的沖突與對峙,以及為了達到其目的所創造出來的相對臉譜化的人物形象[1]。哈姆雷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都是從不同的方面去重新樹立黑人的主體意識,喚起黑人的民族自豪感。比如蘭斯頓·休斯的《黑人談河流》(1920)中覺醒的黑人,理查德·賴特的《土生子》(1940)中努力抗爭的黑人。美國評論家羅伯特·布恩在《美國的黑人小說》一書中說:“對賴特派來說,文學是感情的凈化劑——一種消除種族內部緊張關系的手段。他們的小說往往是痛苦與絕望交織的長聲呼號。”[2]又如拉爾夫·埃里森的《隱身人》(1952)中失落的黑人等,則是黑人在爭取民權與平等的道路上遭受挫折與失落的寫照。
毫無疑問,時代的大背景決定了小說家的創作內容。所以,黑人運動到了70年代,致力于為黑人寫作的作家們的思索方式呈現出與之前3種迥然不同的特點:既經歷了覺醒、抗爭,又有了挫折后的冷靜思考,以及對出路的追尋。亞歷克斯·哈利、艾麗絲·沃克以及托尼·莫里森都是這個時代黑人作家的杰出代表。他們的作品,哈利的《根》(1976)、沃克的《紫色》(1982)都呈現出這樣的特征。有一點非常明確,那就是這個時代的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莫里森的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黑人所處的被白人主流文化所毒害的精神困境,以及黑人們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都是跟以往及同時代的黑人作家完全不同的。這正是莫里森創作的獨特之處。
3 從單一黑人形象到多層次黑人形象的推進
然而,莫里森的創作也并非一直停留在同一個層面,從其作品中人物的特點來看,作者也是在不斷的思考過程當中,并且其種族意識、民族意識、女性意識等漸趨成熟。這些不同作品中每一個主角身份的確定、內心的構建,正是作者不斷思考的體現。以女性形象的塑造為例來看,最早的作品《最藍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從幼兒時代就從沒被注入黑人文化價值觀,被白人文化價值所控制,擾亂了心神,渴望著白皮膚藍眼睛的白人標準,對自己和整個種族的黑皮膚感到丑陋與極大的恥辱,并最終成為這種扭曲標準的犧牲品。《秀拉》中蔑視傳統、自我放逐的秀拉,是對高高在上的壓制女性的男性主義及黑人男性主義理念的終極反叛者。這個徹底的反叛形象與佩科拉的徹底的迷失形象正好形成非常有趣的鮮明的反照。也正是莫里森對黑人女性身份確認問題的探究,到底黑人女性的理想的形象應該是什么樣子?這個問題在第三部作品《所羅門之歌》[3]中的女主角派拉特·戴德身上給出了答案。看起來窮困潦倒的派拉特·戴德,卻是具有黑人美德的集大成者:吃苦耐勞,熱愛自然,不追求物質享受,極具慈愛、大度的熱心腸,不懼任何的壓迫與脅迫。她身上的魅力,吸引人心的力量,正來源于她身上濃厚的黑人特質。這個形象的塑造完全有別于70年代以前的黑人女性形象。
再比如《所羅門之歌》中的麥肯·戴德Ⅱ,他的形象最初是令人極其厭惡的。他被他的黑人同胞們厭惡,因為他想盡辦法變得富有,在成為富人后,對租房子的窮苦黑人殘酷刻薄,榨光他們最后一分錢,即使老人或孩子也不例外。之后,用從窮苦黑人身上得來的錢去揮霍,買豪華汽車,每周開著去兜風。他也被自己的親人厭惡著。他的妻子,受著他的冷遇,過著看似富足其實早已崩潰的日子,只在給兒子喂奶時才有存在感;他的兩個女兒,為數不多的受過教育的黑人姑娘,最好的工作卻是給白人充當女仆,或者被父親當作進入更高層社會如白人社會的籌碼,只可惜難以如愿,最終郁郁而活;他的親妹妹,與他一起逃脫白人的抓捕,最終歷經艱難才獲得自由,可兩個人卻幾乎不往來,一個以另一個為恥。同樣,他也被白人厭惡著,只因為他的黑皮膚,由此也導致了他自己對自己黑皮膚的痛恨。可這樣的一個人,卻在偷偷站在妹妹家破房子的后面聽她們快活歌唱時流出了眼淚。這讓我們對他有了重新認識,原來他的內心深處也有著人性的光輝,有著對他的黑人身份的認同和不敢承認的自豪感,對他的妹妹有著他拒絕承認的溫情與懷念。這樣的細節雖小,卻全然改變了曾經單一的、臉譜化的黑人形象描寫。這種深層次推進的描寫方式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體現,讓以往的讀者們讀到的黑人的可笑的、愚蠢的,沒有感情的等等形象趨向于完整的人性的形象。正如莫里森所說:“我始終在寫一個主題,那就是愛與愛的缺失。”而有愛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
4 打破傳統黑人女性形象,塑造豐滿的“人”的形象
著名美籍非裔問題研究專家Barbara Christian,在《黑人女性小說家》(Black Women Novelists,1980)中將1970年前的黑人女性形象總結為三種:一是專橫、喜劇化的媽咪形象;二是混血兒形象,混合種族的婦女,其生命必然是悲劇的;三是撒菲勒(Sapphire)形象,她主宰并閹割了黑人男性[4]。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莫里森之前,黑人文學作品中大部分女性形象都沒有超出定型化的范疇,不僅黑人女性形象如此,白人女性形象也是定型化的產物,只是由于歷史經驗不同,種族身份各異,黑人女性與白人女性形象存在較大差異而已。但莫里森的作品打破了這一桎梏。
國內外評論界對莫里森早期作品的關注與研究都著重在莫里森對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認為她對女性形象有所偏愛。事實上這個評論確實有據可循。但考慮到她的“黑人”及“女性作家”的雙重身份,就不難理解了。她對黑人女性的復雜身份曾親眼目睹并深有體會,因此創作的主體自然是黑人女性人物,而且是形形色色的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形象。《秀拉》中的秀拉,是一個打破傳統、我行我素的追夢的黑人女孩形象。《寵兒》中獲得自由的女奴賽絲,一輩子生活在失子之痛中難以自拔,卻不失為是對自己的孩子、對自己的家庭充滿了愛意的有情有義、有血有肉的黑人女性形象。《所羅門之歌》中的派拉特,她的家看起來家徒四壁,可是卻是充滿歌聲的魔力之家,這個以派拉特為主的家,不僅是麥肯·戴德家族的精神支柱,也是周圍窮苦黑人的精神支柱。她的獨立人格,叛逆不屈服的性格,是莫里森塑造的所有黑人女性形象中的標桿與理想,正如她的名字“Pilate”(代指“領航員”)。之后,更有《恩惠》中的女性形象弗洛倫斯,她甚至超越了作為女奴對黑人的深刻仇恨,為了挽救白人女主人貝卡的生命以及自己的愛情而向他人尋求幫助。這些女性主角的構建,每一個都是超越了以往的形象,無一不是在對自我身份進行確認,以及內心的構建。
她們不再只是作為白人的奴仆,家庭的從屬,社會的最暗無天日的底層,而是開始從內心里尋求出路以及自我身份的確認,無論是黑人身份的確認還是女性身份的確認。而她們的方式,無一不是堅持自己內心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總而言之,這些女性身份的自我追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莫里森對黑人文學的自始至終并不斷深化的理念的體現。也就是說,從實現自我價值的生存層面來講,黑人群體要想找回尊嚴和重拾身份,必須保持其群體獨有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宗教傳統。
5 黑人文化出路的探討:從自卑到自豪
20世紀初, 美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民權運動者、泛非主義者、作家和編輯杜波伊斯(W.DuBois),在《黑人的靈魂》(1903)一書中對美國黑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作了如下概括:“一個(黑)人總是感覺到他的兩重性(twoness)——自己是美國人,而同時又是黑人;感覺到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種不可調和的努力;在一個黑色軀體里,有兩種相互較量的思想,它單憑其頑強的力量避免了被撕裂開來。”[5]這句話非常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美國黑人所面臨的的兩難處境。這種處境,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身份的確定和靈魂的歸屬問題。身份上的自由并未解決他們內心深處的困惑。20年代的哈萊姆運動,代表了黑人新種族意識的覺醒,但未能讓黑人真正在靈魂深處找到歸屬感。四五十年代以賴特、埃利森、鮑德溫等為代表的黑人作家們,以“抗議”為武器,以仇恨和怒火表達他們的態度,以期引起白人對黑人群體的關注、思考或是畏懼,但也未能就黑人的靈魂歸屬問題找到答案。
到了7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如前所述,已經到達一種新的狀態。這種開始自省的趨勢也讓莫里森對黑人種族所面臨的精神困境進行重新思考。這種思考從她的作品來看,確實漸漸形成了一種比較成熟的思路。如果說1973年的《秀拉》已經開始尋找的話,那么1977年的《所羅門之歌》中的“奶娃”就已經找到了一條道路。許多學者將奶娃的“尋金之旅”總結為“尋根之旅”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奶娃”經歷了從自私無情到悔恨,從對黑人的厭惡到對黑人身份的由衷喜悅,從對財富的追捧到寧可與貧窮的姑母在一起也不愿回到他們的豪宅,從對黑人宗教的鄙視到最后的追隨。奶娃的“排斥”-“認可”-“追隨”這一系列的轉變,實際上就是托尼·莫里森想要表達的自我種族以及黑人宗教的信念。奶娃最后在南部曠野中的“飛行”意象,就是將黑人與黑人宗教真正的融合。這種發自內心的認可,就是托尼·莫里森想要將黑人群體帶出“兩難處境”的道路。民族自豪感在《所羅門之歌》以及之后的作品中是隨處可見,并被作者作為黑人精神根源來強調的。
綜上所述,美國現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一位將黑人文學引領到新高度的杰出作家。她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美國黑人族群以非常人性化的、全面的方式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他們的困境,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精神困境,是托尼·莫里森一直在關注、也一直努力尋求解決途徑的問題,也是她選擇寫小說的初衷。她最終選擇的不是以尋求白人關注獲取同情,而是讓黑人以黑人族群的自豪感以及黑人宗教作為“兩難處境”的出路。正是這種大氣磅礴的世界化民族觀,使莫里森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全世界讀者的認可。
[1] 習強毅.文學作品中的美國黑人形象變化[J].時代文學(上半月),2009(6):79-80.
[2] 理查·賴特.土生子[M].施咸榮,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前言.
[3] 托妮·莫瑞森.所羅門之歌[M].胡允桓,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4] 張良紅.托尼·莫里森筆下的風景:評小說《最藍的眼睛》敘事藝術[J].文教資料,2008(27):32-34.
[5] 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托妮·莫里森與美國二十世紀黑人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柳 克
Literary Value Research of Toni Morrison under Multiple Perspectives
YANG Ya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61, China)
Since late 1980s, especially after gaining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93, domestic academia′s attention on Morrison has grown dramatically, and the research on her also showed the trend of deepening, refine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no writings of systemic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Morrison and her works by now, which would be a great regret. This paper sums up and discusses the literary value of her work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reasons for composition, deepening of the Black roles and deep hierarchical mining, shaping of “full” human image and exploration on the way out from the dilemma for the American Black.
Toni Morris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literary value
2016-11-17
楊亞萍(1979- ),女,陜西鳳翔人,高級工程師,碩士,主要從事英語語言文學研究。
I712.074
A
1009-3907(2017)01-00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