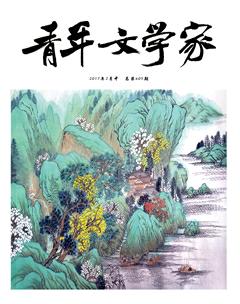論魯迅作品語言中的拯救與虛無
摘 要:作家的語言與其精神思想存在同一性,作家的內質決定了其語言的形式。同樣,魯迅的思想、精神氣質也必然會彌漫在其作品語言的字里行間。本文從語言學的微觀視角,結合文本細讀的方法,對魯迅作品語言的語法與修辭進行研究,解讀其語言中的拯救與虛無,論證魯迅作品的語言與存在的同一性。
關鍵詞:語言;存在;拯救;虛無;語法;修辭
作者簡介:程淳(1989-),女,白族,湖南張家界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語言教學、中國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02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人在語言中有他最本真的居處”[1]。語言如同作家的指紋,其獨特性源于作家固有的思想精神和深層心理意識。在魯迅的文學作品中,同樣可以看到其思想、精神內質與語言之間存在的某種同一性,也可以說,魯迅是以其的文學作品的獨特語言對現代中國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眾所周知,拯救民族的希望與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懷疑相互糾纏爭斗貫穿了魯迅的整個創作生命,也是其作品藝術魅力的來源之一。拯救與虛無的糾葛碰撞,也必然會體現在其文學作品的語言之中。因此,本文將從語言學的微觀視角,結合文本細讀的方法,從魯迅語言的語法、修辭與意象三個方面來闡釋其文學作品中的拯救與虛無。
一、語言中的拯救意識
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在其研究專著《魯迅六講》中,通過對比魯迅與胡適各自的文體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闡述了魯迅文體的“內涵”、“湛然”等特點,并將其歸結為“通儒體”,強調了魯迅作品語言與邏輯、思想的整體性。魯迅抱著“改良人生”的初衷,開始文學創作,是要揭示病態,拯救現代中國國民的麻木愚昧,試圖賦予其現代人的主體意識。他自己在《小雜感》中曾經說過:“創作總根于愛……創作雖說書寫自己的心,但總愿意有人看……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2]。
他的確希望在懂的人腦子里“留下一些印象”,深入國民精神的深處進行療救。這樣一種拯救意識自然而然就會流露在作品的語言當中。通過文學這一途徑來改良人生,就需要使讀者產生足夠深刻的理解。因此有別于胡適語言的清爽直白的說教,魯迅采取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策略。以語言的阻滯,斷裂,頓澀,省略造成留白,以期拉長讀者的感受與思考時間,避免語言理解的自動化機械化,為讀者的主動參與開辟了空間。魯迅要做的不僅是自己思考,而且還要讀者跟著他一起思考,通過這種看似難解的語言充分開發讀者主觀能動性。因為他的“內涵式”語言與思想渾然一體,不可分離。因此,理解了這些曲折阻滯的語言也就打開了理解魯迅思想的通道。
魯迅的語言策略首先體現在省略句式的大量運用。諸如《祝福》中:“我因為常見些但愿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3]。這里省略了“所料”和“一律”的賓語,這樣的省略加上百轉曲折的敘述方式,充分表明了隱含作者對于祥林嫂的憂慮,加深了悲劇前奏的陰郁。還有,魯四老爺得知祥林嫂是來歷之后的憤怒,“可惡!然而……”[4],魯四老爺的兩次“然而”后面究竟想說什么,這樣的留白為讀者開拓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間,究竟是對封建禮教的贊同還是對祥林嫂的同情?除了語法成份的省略,還有內容的省略,如《紀念劉和珍君》:“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由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啊!沉默!”[5]。默無聲息的緣由究竟是什么呢?此處,就在應當慷慨陳詞之時,魯迅用一個句號及時收住筆鋒,跳躍到對沉默的悲嘆。將“衰亡民族”沉默的緣由置入空白,由讀者自己進行思考和補充,這樣,順著魯迅指引的思路,讀者自己思索得出沉默的緣由才更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
除了省略,制造空白的方式還有因為缺少過度詞的銜接,而造成的語句之間的跳躍。最典型的是《藥》中,劊子手康大叔來華老栓店里講述夏瑜在獄中的勸說獄卒的一段,一群人就“可憐”的話題七嘴八舌討論許久: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汽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似的說。
……
‘小栓——你不要這么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著頭說”[6]。
這一段眾人的對話中,出現了三次跳躍。第一次是“眾人的眼光有些呆滯……”,“小栓已經吃完飯……”再到“花白胡子恍然大悟”,敘述者的聚焦由眾人跳躍到小栓然后又跳回眾人,如電影中的長鏡頭在沉默中來回切換。在眾人眼光呆滯與恍然大悟之間為何要插入小栓吃飯的情景,筆者認為一是起到了時間上的延宕,有意制造沉默的片刻,使讀者不禁思考這兩次跳躍之間的沉默,眾人何種心里活動使其恍然大悟,而這片刻的心理活動中便蘊含著心靈深處的麻木愚昧。第三次跳躍從小栓咳嗽到駝背五少爺,則充滿了對無知與盲從的諷刺,同時這句“瘋了”又帶有雙關的意味,諷刺駝背五少爺的同時也是在諷刺用人血饅頭為小栓治病的瘋狂至極又愚昧至極的行為。
最后,長定語的使用,以及長短句交替,形成語句間的張力和張馳有致的敘述節奏。如《傷逝》中:“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卻絕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7]。其中,中心詞“新葉”和“紫藤花”分別用了三個和四個形容詞做定語,并且每一個形容詞后都跟一個結構助詞“的”,使得句子看似冗長,但或許是作者有意為之。一系列形容詞及結構助詞的連續使用,是語句產生頓促感,延長了讀者對中心詞的感受時間,敘述者可以如此細致地對中心詞進行修飾,從側面凸顯他的悔意之深。另一方面,兩個長句之后,緊跟著是幾個短句,創造出喧鬧之后的沉寂的效果,使哀傷的氣氛更加濃厚。
二、語言中的虛無鬼氣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道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絕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8]。魯迅對于拯救國民改良人生的啟蒙信念自開始便是扎根在了“價值懷疑”的松軟的泥土中,希望與絕望的糾纏貫穿了作者的一生。
虛無不同于悲觀,悲觀是一個人對最終能否勝利的懷疑,而虛無則是對這種勝利的意義的懷疑,“倘若天地之間,只有黑暗是實有,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這樣的虛無感就會迅速失去行動的熱情,犧牲也罷,反對也罷,都沒有意義,人生只剩下一個詞:無聊”[9]。所以,虛無是比悲觀更加可怕,五四時期的作家盡管多憂愁感傷,但大多只是對眼下的渺茫和未來的悲觀,很少能像魯迅一樣深刻到洞悉了人生的終極意義而被虛無之鬼氣纏身。
這樣的虛無感,在《吶喊》中尚且不十分明顯。然而,即到《彷徨》和《野草》魯迅便通過自我解剖,開始了與這種鬼氣的較量,試圖用這樣的方式來將其驅逐。這種與虛無糾斗的痕跡依然彌漫于魯迅作品語言的字里行間。
體現在語法中,首先是標點符號中逗號的使用。諸如在《孤獨者》中:“可是到四更天才咽氣。最后的話,是……”,“他躺在床上,而且,似乎睡熟了”[10]。《孤獨者》是魯迅自我剖析的典型作品,敘述者與主人公魏連殳的對話實質上是隱含作者的自我對話。因為對啟蒙價值的懷疑而產生的虛無感,使隱含作者感到無能為力的輕飄。逗號的大量插入,起到了截斷語流的作用,放緩了語言節奏,短句似乎是隨嘆息而出,一種虛無的輕飄自然產生。又如《死火》中:“遺棄我的早已滅亡,消盡了”[11]。“滅亡”與“消盡”之間插入的逗號,突顯了悲哀與無奈的語氣,似乎是由悲憤轉為了絕望的哀傷。
其次,詞匯方面體現在虛詞的大量運用。帶有轉折或遞進關系的虛詞,導向著語流和語義的走向,使文章顯得迂回晦澀。魯迅對自我精神進行解剖但又不希望在公眾的視線中暴露無遺,這種剖析與遮掩的矛盾是其大量使用虛此的根源所在。例如《影的告別》中:“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與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然而我終于彷徨與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黎明還是黃昏”[12]。此處,由于虛詞“然而”的導向,使得語言沒有按照慣常的邏輯線性流動,而是循環往復,深刻體現出隱含作者在尋找人生意義,探索擺脫虛無的路徑時的糾結與徘徊,光明與黑暗究竟哪一個才是“實有”?又如《復仇(其二)》中:“他不肯喝那用沒藥調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樣對付他們的神之子,而且較永久的地悲憫他們的前途,然而仇恨他們的現在”[13]。“而且”與“然而”連用,遞進之后又轉折的結構,說明悲憫、愛與仇恨,對于眾人的復雜情緒以及對啟蒙的失望與希望同時糾葛在隱含作者心中,也體現了其對于人生意義的懷疑。
最后,修辭上的“絕端語式”與“曲婉語式”同樣也是虛無的體現。所謂“絕端語式”特指一種極限表達的大量使用,用來強化語義程度,如“必”、“絕無”、“無不”、“最……不……”;“曲婉語勢”則恰恰相反,是一種用來弱化語義程度的表達方式,如“未必”、“恐怕”、“大抵”、“大約”、“似乎”。資料統計顯示魯迅在“1903年的《斯巴達之魂》出現絕端式極限詞4例,曲婉極限次沒有出現。1907發表的《摩羅詩力說》中出現絕端語式的極限詞72例……而曲婉語式詞匯僅出現1次。……而到了1921年的《阿Q正傳》曲婉式極限詞出現的最多,共63例,僅‘似乎就出現了23次”[14]。魯迅發表《斯巴達之魂》與《摩羅詩力說》是在其留學日本期間。那時他初次接觸到進化論等西方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對人生和社會的新認識,熱烈討論著改造國民性的方法途徑,沉浸在理想主義的啟蒙熱情當中。然而,當魯迅1909年回到中國至1918年狂人日記發表,九年的時間,經歷了種種嘗試的失敗與打擊,孤獨與空虛的折磨之后,已經對啟蒙的意義深感懷疑 。由《斯巴達之魂》《摩羅詩力說》中的決斷語式變為了《吶喊》、《彷徨》與《野草》中的曲婉語式,不得不說這是魯迅心中虛無鬼氣在語言中的重要體現。
參考文獻:
[1]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80頁。
[2][3][4][5][6][7][8]魯迅.魯迅文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版,第347,88,90,319,19,144,5頁
[9]王小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
[10]魯迅.魯迅文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版,第131,132,133頁。
[11][12][13]魯迅.魯迅文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版,第209,152,284,287頁。
[14]黃瓊英.魯迅作品語言的歷時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