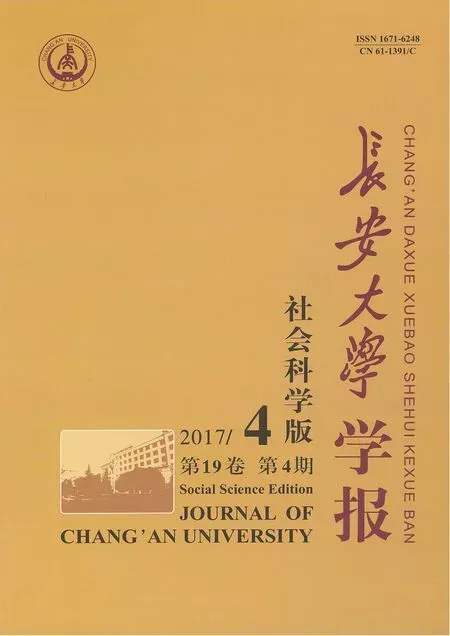《詩·周南·關雎》主旨:從“以色喻于禮”到“夫婦之德”再探
王國雨
(浙江傳媒學院 社會科學部,浙江 杭州 310018)
《詩·周南·關雎》主旨:從“以色喻于禮”到“夫婦之德”再探
王國雨
(浙江傳媒學院 社會科學部,浙江 杭州 310018)
對《詩·周南·關雎》篇主旨的解讀從先秦以來一直存在不同觀點:早期儒家從情感與禮義之關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禮”評論《關雎》主旨;漢儒則認為《關雎》體現著“后妃之德”,具有“風天下而正夫婦”的教化典范意義,將上博簡《孔子詩論》和帛書《五行》聯系起來,對歷史時期相關論述進行比較分析。研究認為,早期儒家和漢儒關于《關雎》主旨的評論看似頗有分歧,實際上則是內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禮”之論,是對《關雎》將生命意義上的男女戀情升華和規范為倫理意義上的夫婦之德的肯定;而漢儒對《關雎》具有“風天下而正夫婦”之政教意義的肯定,不僅與早期儒家夫婦倫理觀念相一致,而且與早期儒家《詩》學觀一脈相承;恰當理解《關雎》詩旨,才能有效解讀其蘊涵的禮樂教化與美善之德意義。
《關雎》;“以色喻于禮”;“夫婦之德”;《孔子詩論》;詩學派
作為傳頌千古的名篇,《詩·周南·關雎》篇的主旨從先秦以來一直聚訟紛紜。影響最大的當為漢儒《毛詩序》的“后妃之德”說,然而在竭力打破經學傳統的近代學者那里,《關雎》則被解讀為普通的男女戀情詩或婚戀詩,并視“后妃之德”說為無稽之談。上博簡《孔子詩論》問世后,人們清晰地看到,早期儒家多從情與禮之關系角度解讀《關雎》,一言以蔽之曰“以色喻于禮”。這種詮釋使學者大有“實獲我心”之感,認為遠勝于缺乏訓詁依據的所謂普通愛情詩的詮釋向度。然而,學者在肯定“以色喻于禮”的解讀優勝于漢儒和今人之詮釋的同時,往往并未深究漢儒“后妃之德”說與早期儒家“以色喻于禮”*《孔子詩論》的“以色喻于禮”,在帛書《五行》中被稱作“由色喻于禮”,并作了更為詳盡的解讀,詳后文。可見,從納情入禮的角度解讀《關雎》應是早期儒家詩學的共識。之論是否具有內在一致性。本來就重視夫婦倫理的早期儒家,以“以色喻于禮”詮解《關雎》過程中,蘊涵著怎樣的婚姻家庭和夫婦倫理觀念呢?漢儒將《關雎》看作“風天下而正夫婦”之典范是否有源自先秦舊說的訓詁依據呢?簡言之,如何理解早期儒家與漢儒在《關雎》詩旨論說中的差異呢?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內在一致性呢?對《關雎》詩旨的個案研究,有助于推進對早期經學意義上的《詩》學史的理解。故本文嘗試以先秦兩漢《關雎》詮釋史為中心展開討論,以就教于方家。
一、早期儒家與漢儒關于《關雎》主旨的分歧
先看漢儒對《關雎》詩旨的論說。首先,屬于今文經學的西漢齊、魯、韓三家詩認定《關雎》是“刺詩”,旨在諷刺周康王內傾于色、周康王夫婦晚朝之事。如清人王先謙所輯魯詩的觀點[1]:
魯說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又曰: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又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又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又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又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史記》《漢書》《后漢書》《列女傳》等文獻記載顯示,將《關雎》看作詩人有感于周康王夫婦晏起晚朝,以《關睢》諷喻康王夫人違背后妃之制,乃是西漢人的普遍觀念。他們認為“后妃之制”乃是“夭壽治亂存亡之端”。齊詩學派的漢代大儒匡衡在上書漢成帝的奏章中說:“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漢書·匡衡傳》)和“太上者”相對的“后夫人”即是“后妃”,這與毛詩的“后妃之德”說以及將《關雎》看作“風天下而正夫婦”之政教典范的思路實質上是一致的。
對后世經學影響最大的是“毛詩”的“后妃之德”說。與三家詩以為《關雎》旨在 “諷刺”“風諫”不同,毛詩以為是“頌美”。《毛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雎》是“國風”的開端。《毛詩·小序》認為《關雎》是教化、風化天下而規范夫婦倫理的典范。然而,何謂“后妃之德”頗令人費解,吟詠《關雎》詩篇,很難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主題中看出何謂“后妃之德”。不過,《毛詩·大序》對“《關雎》之義”和“后妃之德”有進一步的闡釋。《毛詩·大序》稱:“《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顯然,《毛詩·大序》這里刻意化用了孔子的“《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一語,所以特別將“樂”“淫”“哀”“傷”4字點出。可是,孔子的8個字意在肯定《關雎》詩樂符合“中和精神”,語義易曉,然而《毛詩·大序》的刻意化用,卻令人費解:“憂在進賢”的“賢”作何解?“哀窈窕”又是“哀”從何來?事實上,《毛詩序》或意在強調《關雎》中的“淑女”作為有德的“善女”,乃是“后妃”,與“君子”相配乃是德性的“逑和”,可以作為天下夫婦之表率。至于將“后妃之德”解讀為“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之德”,則源自鄭玄對《毛詩序》的“誤讀”,在此不贅述*清代學者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中辨析說:“《序》以《關雎》為后妃之德,而下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謂詩所稱淑女為后妃,非謂后妃求賢也。……后妃求賢之說,始于鄭箋誤會《詩序》‘憂在進賢’一語為后妃求賢。不知《序》所謂進賢者,亦進后妃之賢耳。”參見《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9頁。另外,清末學者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也指出這是“鄭與毛大不同者”,唐代孔穎達的“孔疏乃謂毛以為后妃思得淑女,強毛從鄭”,所以毛傳鄭箋之別,往往被后人所忽略。參見陳澧《東塾讀書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87頁。。宋儒朱熹雖然強調廢《詩序》,而實際上在對《關雎》解釋時,仍崇信“后妃之德”說,并進一步將“君子”“淑女”坐實為文王與大姒。
可見,漢儒四家詩雖在或諷諫或美頌的看法上觀點不一,卻都強調《關雎》在夫婦教化上的重要意義,這成為《詩》經學史上的主流觀點并深刻影響著兩千年來之社會人心。只是到了近代,傳統經學被當作應當掃除的瓦礫和斬斷的藤蔓,胡適、顧頡剛等學者強調恢復《詩經》本來是文學而非經學的真面目。于是,《關雎》便被解讀成一首普通的愛情詩或婚戀詩。近年來,學者則又開始重新反思《詩》的身份問題*劉毓慶等先生有諸多深刻論述,認為《詩》既是“詩”,更是“經”。參看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2001年上博簡《孔子詩論》問世后,引起學界更為廣泛的討論,尤其是提到《關雎》主旨時,用“以色喻于禮”一言以蔽之,聯系帛書《五行》的“由色喻于禮”之論,可以看出,在早期儒家尤其是《詩》學派那里,從人之情性與禮之關系的角度尋求禮樂秩序的合理性和根據,是一種共識。為方便討論,現將《孔子詩論》中相關簡文具引如下:
《關雎》之改,……《關雎》以色喻于禮(簡10)……好,反納于禮,不亦能改乎?(簡12)……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擬)好色之愿。以鐘鼓之樂……(簡14)《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簡11)
這段材料出現在“四陳七詩”的“《關雎》詩組”中,該詩組通過對“《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的論述,說明七首詩均有“動而皆賢于其初者也”的特點。“《關雎》之改”的“改”字,在馬承源最初的釋文中寫作“攺”[2],但學者們大多認為可釋讀為“改”。“改”是對《關雎》最凝練的評價,下面的文字均是對這一點的闡發。李學勤說:“‘改’訓為更易。作者以為《關雎》之詩由字面看系描寫男女愛情,即‘色’,而實際上要表現的是‘禮’,故云‘以色喻于禮’。”[3]將“改”訓為“更易”可從,《孔子詩論》認為《關雎》詩文本身體現著“以色喻于禮”“反納于禮”的內容表達。這里的關鍵還是對兩個“喻”字的解讀。有學者將“喻”解讀為“譬喻”“比喻”,認為“以色喻于禮”就是“由表面的好色,來比喻實質的好禮”[4-5],也有學者認為“喻”是“寓托、寄寓即興寄的意思”[6],均不恰當,因為如果是“比喻”,則要求“喻體”和“被喻體”之間具有相似性,而“色”與“禮”之間并不構成相似性;“興寄”說認為“禮”寄托在了“色”上,顯然不通。事實上,要理解這里的“喻”,需要和帛書《五行》聯系起來,因為那里對“喻”有專門解釋,而且是通過解讀《關雎》加以解釋的。帛書《五行》“說”部在解釋其對應的“經”文“喻而知之,謂之進之”時,主動引用《關雎》進行了如下分析[7-8]:
“喻而知之,謂之進之”,弗喻也,喻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喻之也者,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交諸父母之側,為諸?則有死弗為之矣。交諸兄弟之側。亦弗為也。交諸邦人之側,亦弗為也。畏父兄,其殺畏人,禮也。由色喻于禮,進耳。
什么叫“喻”呢?就是“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從“小好”曉諭、明白“大好”之所在。具體到《關雎》詩而言,詩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描寫的是“思色”之情,“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描寫的是“思色”之情急切,“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則言其甚急之情,這就是“小好”。然而,“思色”之情如此之急切,如果“交合”于父母、兄弟、朋友之側則人至死不為,為什么呢?因為禮所不允許。于是“禮”對人的約束力便凸顯出來,而這種對禮的遵守是發自人之內心的約束力,這就是“由色喻于禮”,這就叫做“喻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對照上文《孔子詩論》的話,“以色喻于禮”就是《五行》的“由色喻于禮”,“《關雎》之改”的“改”,就是《五行》的“進”,由此也便可理解《孔子詩論》“《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就是對《關雎》之君子能將對美色的愛慕之情“反納于禮”的規范之下的肯定。第14簡“其四章則喻矣”*李學勤:“其四章則喻矣”,兼指《毛傳》本的四、五兩章。第四章為“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五章為“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琴瑟、鐘鼓都是表達“禮”的器,可見,《詩論》、《五行》解詩頗有根據與合理性。就是指該君子能將“好色之愿”以符合“禮”的形式表達出來,即比擬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合乎禮的訴求行為之中。至此,“追求美色”的自然情感就納入到禮的規范之下而成為了道德情感,達到了情之“真”與情之“正”的統一。
《孔子詩論》對《關雎》“以色喻于禮”的評說代表了早期儒家對《關雎》主旨的基本看法。這種“納情入禮”的觀點,頗符合早期儒家在情與禮之關系上的基本主張。第一,早期儒家認為基于“人情”而建立的人倫秩序才能穩固。如郭店竹簡《性自命出》說:“禮作于情”,“凡人情為可悅也。茍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9]。第二,人之豐富情感需要納入禮樂制度的規范和制約之中,才是情之“真”與情之“正”的統一,才是合理的。一句話,禮既是因人之情而設,又是對人情的節制、規范和引導。如《禮記·坊記》說:“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性自命出》也說:“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這里的“道”其實是以“禮樂”為其內容的。這讓人想起《毛詩序》的著名論述: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始于情”就是“發乎情”,“近義”的“義”也就是禮義限度之所在。其實,“《詩》言志”的“志”在儒家那里也便是“情”與“義”的平衡點,也就是《詩》的“中和”精神的體現。對這一點的說明,最恰當的例子莫過于《論語·八佾》中孔子對《周南·關雎》的評價: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哀”是人之“情”,而“不淫”“不傷”便是符合禮的“節文”。雖然孔子主要是在詩樂的語境中所作的評價,但對于《詩》文本來說同樣適用。這里的評價與《孔子詩論》“《關雎》以色喻于禮”之語也是一致的。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充分看出,漢儒眼中的《關雎》乃是講夫婦之德的,且具有“風天下而正夫婦”的政教功能,而早期儒家則將《關雎》看作“以色喻于禮”的典范。二者關于《關雎》主旨的觀念和論說角度確有巨大分歧和差異。然而,如何看待這種分歧和差異呢?究其原因,是由于早期儒家與漢儒的關注域視不同。早期儒家關注禮樂秩序與社會規范、價值的重建問題,注重探討“禮之本”,因此在哲學上便關注性情問題,《詩》言人之情志,故對《詩》的詮釋注重將人之性情引導和規范于“禮”義之中。而漢儒的關注重心則在于如何規范、引導皇權專制秩序,維護其穩固性,因此,“后妃之德”之類的說法便產生了。
二、“以色喻于禮”與“風天下而正夫婦”的內在一致性
要深刻而正確的理解早期儒家與漢儒在《關雎》詩旨上的分歧,還需回到《關雎》篇本身。當作為“詩三百”之一的《關雎》被創作并以詩樂舞一體的形式應用于兩周禮樂文化之中時,其中所蘊含的兩情相悅之“情”便已經和社會禮義與倫理結合在了一起。學者已經充分注意到《關雎》中的“君子”“淑女”作為主人公乃是貴族男女,“琴瑟”“鐘鼓”乃是貴族才可享用的禮樂之器,而“采荇菜”其實也不是農事勞動,而是關乎貴族祭祀的祭品問題[10]。姚小鷗結合西周禮樂制度通過對“流之”“采之”“芼之”語意的考辨指出,《關雎》詩篇古義涉及到祭祀之禮與婚姻之禮,“《關雎》一篇所描寫的確實為周代貴族的婚姻形態”[11]。《關雎》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毛傳》曰“匹也”,即配偶。可見,《關雎》首章已道出男女戀情之追求是指向婚姻“逑和”。
《孔子詩論》“以色喻于禮”之說強調“納情入禮”,將兩情相悅之“情”規范和引導于“禮”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節制、引導和規范人情的“禮”,具體指向的是“婚禮”,因為《關雎》中的“色”就是男女愛慕之情,在早期儒家那里,“婚禮”的功用在于將生命意義上的男女之情規范化為倫理意義上的夫婦之德。因此,《孔子詩論》“以色喻于禮”的詩旨把握固然極為符合《關雎》以“求”(愛情的追求,“寤寐求之”的生命沖動)為敘事的詩章脈絡,同時也完全契合《關雎》以“逑”(齊詩魯詩中作“仇”,君子的好“匹偶”)為內在主旨的樂章精神。《關雎》本就是“求”與“逑”的統一,即生命意義與倫理意義的統一,亦即情之“真”與情之“正”的統一。“《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的樂章教化意義,從孔子開始的早期儒家便已經充分注意到。因此,早期儒家“以色喻于禮”之論體現著納情入禮、以禮節制和規范男女之情(“好色之情”)的儒學主張,體現著早期儒家對婚姻和夫婦倫理的獨特思考,與漢儒明確提出的“風天下而正夫婦”內在一致。也正因為儒家重視《關雎》蘊含的“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史記·外戚世家》談到“《詩》始《關雎》”時說:“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的教化意義,《關雎》作為“風之始”的地位才得以確立。
其實,早期儒家對男女愛慕之情是既肯定而又保持警惕的。將少男少女情竇初開之時的傾慕之情納入禮義規范下的思考,早期儒家透過婚禮婚義思想給予了充分肯定。《關雎》之為貴族婚姻之樂歌的教化意義也由此得到強調。《論語·衛靈公》中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萬章上》也說,人“知好色,則慕少艾”。正如《禮記·禮運》篇所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作為人的自然屬性和本能需求,其內在欲望沖動之動力是巨大的,不加以禮樂的規范、引導,必不得行。《孟子·滕文公下》曰:“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社會輿論和禮俗對男女愛戀之情有其約束的一面,但更是規范、引導與升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指向的禮俗就是婚禮。《禮記·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具體看《關雎》詩篇,前文已論及,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句,已經點明男女愛慕之情是指向婚姻的。而其“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則又是“以禮相求”。既得以“成男女之別”,又得以“立夫婦之義”,建立良好人倫之開端。“以色喻于禮”這一基于情之“真”與情之“正”相統一的認識而對《關雎》“詩文本”的評論,與《關雎》本為貴族婚禮之樂章的身份完全相融和一致。孔子對《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評論,我們毋寧看作孔夫子處于詩樂一體的文化語境中而做出的中肯評價。如果說該評論符合孔子的中庸中和精神,而中和精神又恰是儒家禮樂之精神,那么,居于“《風》之始”的《關雎》之于天下夫婦關系的風化意義便已經被早期儒家所凸顯。
如果說《孔子詩論》和《五行》是從情禮之關系,從《關雎》文本的內在邏輯強調了守禮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話,以《毛詩序》為代表的漢儒則是從《關雎》的歷史身份、實用功能方面正面肯定了《關雎》大義:為教化天下和規范夫婦之德提供范本。漢代四家詩對《關雎》的評價既有其時代痕跡,又是深刻承襲早期儒家夫婦倫理觀念和《詩》學觀念而形成的。
第一,“《關雎》只是君子淑女夫婦之事,與妾不妾的沒有關系”[12]。然而,毛詩的《關雎序》之所以特別強調“風天下而正夫婦”的政教義,與漢儒面對的時代課題有關。學者已經指出[12]:
如何教化君主、后妃和眾妾處理好家庭關系,成為涉及國家天下安危治亂的關鍵。所以,毛詩《關雎》意在教君主勿耽于淫樂,要尊重妻妾,勿以妻妾為玩物;教后妃不妒忌,調和后宮,更尋窈窕之淑女以為君子眾妾,防止君主和眾妾耽溺于無禮。教眾妾修德,幽閑貞專,與后妃一起輔佐君主,后宮坤寧,使君主專心政治,天下蒼生有福。
毛《詩》為了對治君主一妻多妾制可能存在的弊病,可謂用心良苦。因此,今古文經學家或從“后妃之德”,或從諷刺周康王夫婦晚朝晏起角度論說《關雎》主旨,解釋《關雎》詩句,這成為近代以來最為學者所詬病之處。然而,如果我們將四家詩所突出的“風天下而正夫婦”的風教意義和《關雎》居首以突出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的意義一并否定掉,只剩下強調男女戀歌式的解讀,其實并不符合《關雎》詩旨。因為作為西周貴族婚禮樂歌而被運用的《關雎》,贊美新娘、祝福美好婚姻是其主題,漢儒從夫婦之德角度加以肯定和強調,是有著堅實的訓詁和文本依據的,并非“無稽之談”。
第二,漢代《詩》學觀承襲早期儒家《詩》學傳統而來,深受早期儒家倫理觀念影響的。早期儒家重視人倫,其中夫婦一倫常與父子、君臣關系相提并論,并且被看作“人倫之始”,如《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易傳·序卦傳》也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婦一倫被看作社會倫理秩序和價值秩序得以確立的基礎和機樞。在出土文獻中我們也看到,在提到(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三種人倫關系的時候,也往往先論述夫婦,然后依次談父子、君臣的關系。如郭店竹簡《六德》說:
男女別生言,父子新(親)生言,君臣義生言。……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職,而讒諂蔑由作也。
男女不別,父子不新(親)。父子不新(親),君臣無義。
顯然,這里的次序并不是隨意的,而是與《序卦傳》一致,把男女(夫婦)關系作為父子、君臣關系的基礎。當然,早期儒家強調夫婦倫理與其重視父子和君臣關系并不矛盾。從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開始,早期儒家有時為了強調父子之親和君臣之義,在“五倫”的次序上會有所調整。如除了《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說外,《中庸》在談到“天下之達道五”時的順序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郭店竹簡《成之聞之》亦曰:“天登大常,以理人倫。制為君臣之義,著為父子之親,分為夫婦之辨。”不過,這些材料同樣說明,在早期儒家那里,作為“人倫之始”的夫婦一倫得到了廣泛而充分的重視。早期儒家對夫婦倫理的重視和定位,對《毛詩》有直接影響。如《毛詩·關雎》傳曰:
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如果承認《關雎》詩篇一開始便有明確的婚姻目的,如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提示的;如果承認《關雎》詩篇強調的是婚姻美滿,而非現代所謂單純的愛情沖動與激情,如四、五章“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所透露的;如果承認《關雎》的“君子”與“淑女”兩者既是婚姻的匹配,也是美德的綰合,如“窈窕”一語,既是形容體態之美,也是表彰德性之善;如果承認《關雎》所描寫的貴族男女之間兩情相悅的生命沖動體現著“自我節制”的美德,詩篇作者所崇尚的是具有中和之美的合情合理、合情合禮的生命形態和倫理精神;那么,包括毛詩在內的漢代四家詩強調《關雎》蘊涵著豐富的“夫婦之德”,可以成為“風天下而正夫婦”的道德教材的觀念,便不僅與早期儒家“以色喻于禮”《詩》學觀說內在一致,而且還是基于《關雎》詩旨和語境的合理詮釋。只不過“后妃之德”的說法有著漢儒的時代痕跡而已。
三、先秦兩漢時期《關雎》詩旨的演變脈絡
在深入理解早期儒家與漢代四家詩關于《關雎》詩旨闡釋的差異及其內在一致性之后,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早期儒家詩學派“《關雎》以色喻于禮”的觀點在兩漢是如何具體演變的?換而言之,漢代詮釋《關雎》詩旨的過程中,有哪些地方是承繼先秦詩學而來,又有哪些方面是受社會政治文化影響而做出的新解呢?
透過上文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討論可知,早期儒家注重從人情與禮義相統一的角度看待《關雎》,表現出了對《關雎》詩篇提升自然情感(“色”)、引導社會禮樂規范這一思想主旨的肯定。而根據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漢齊魯韓三家詩說,他們將《關雎》解讀為“刺詩”,其背后的根本用意則在于“以《詩》為諫”,企圖通過對包括《關雎》在內的“詩三百”的詮釋,對現實社會政治有所干預,這也與西漢今文經學作為富于批判精神而又熱衷于政治訴求和政治建樹的特質相一致。較早提出《關雎》為“刺詩”的乃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外戚世家》曰:
周之興業以姜源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這種認為婚姻尤其是帝王婚姻關系治亂興衰的觀點,得到漢代詩學家普遍認同。鑒于漢初呂后專權干政,到后來的竇太后、王太后及其外戚干政等這些歷史教訓和政治現實使漢代詩學家意識到,國家想要長治久安,帝王就必須處理好后妃與外戚問題。因此,“把《關雎》說成刺詩,從中引申出后妃之德的道理,反映了西漢經學家的政治需求。但仍將詩旨釋為夫婦關系、婚姻倫理,則不離孔子論《關雎》的要義”[13]。也就是說,從婚姻倫理和夫婦關系角度著眼解讀《關雎》,與早期儒家詩學是一致的,只不過西漢今文經學出于現實政治需要,力圖將《關雎》作為諷諫帝王及后妃謹守夫婦倫理的“諫書”,從而轉換視角認為,“后妃”作為“后夫人”陪伴君主應當有“后妃之德”才能陰陽調和,從而后宮和諧進而天下和諧。在西漢今文經學家建構“后妃之德”論的過程中,并不是一開始就將《關雎》與周康王“德缺于房”聯系在一起的。今文經學引史為鑒,引史證《詩》是經歷一個過程的。在司馬遷筆下,康王時代尚為西周盛世,曾稱贊曰:“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因此,傳習魯詩的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只是說:“至幽厲之缺,始于祍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然而,到了劉向因痛感于漢成帝專寵后妃的現實而寫成的《列女傳》中,《關雎》就成了為刺康王夫婦而作的詩篇了。其文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1]可見,為適應現實政治訴求的需要,早期儒家“以色喻于禮”的《關雎》詩旨觀在西漢今文經學的三家詩那里,工具化和歷史化的詮釋向度頗為明顯。
西漢三家詩關于《關雎》的詮釋向度對毛詩學派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雖然后者是以與三家詩爭立學官的批判姿態出現的。集中體現毛詩學派論說《關雎》的《毛詩序》,明確以“后妃之德”“風天下而正夫婦”揭示《關雎》詩旨及其意義,與西漢三家詩從夫婦之德角度解《關雎》相一致;同時,《毛詩序》特別表彰《關雎》作為“風之始”的地位,也是源自三家詩經常從“風”詩之首的角度(“四始”說)闡發《關雎》的微言大義,如《韓詩外傳·卷五》記載: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
這里孔子和子夏的對話未必真實可靠,但作為漢代“四始”說的萌芽,顯系韓詩學派的主張。又如齊詩學派的匡衡給漢成帝上疏時說:“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1]也是從《關雎》之為《詩》的首篇立說的。
上文已論及與三家詩“刺詩說”不同的是,《毛詩序》認為,《關雎》是頌美后妃有德的。毛詩的這一轉變是與《毛詩序》所提出風雅正變說相一致的。《毛詩·大序》認為產生于西周后期政治衰亂中的作品為變風變雅,而《周南》《召南》則代表“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乃是“正風”,因此不可能是“諷刺”,只能是“訟美”。相比于早期儒家及三家詩,毛詩學派著力于從統治者的角度闡發《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同于三家詩將《詩》看作“諫書”而積極干預政治和批判時政。也就是說,毛詩學派對現實政治具有更多的認同感而非批判不滿。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毛詩序》對《關雎》的解說并非完美無缺,一些說法語義含混,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上文已指出,由于刻意化用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樂”“淫”“哀”“傷”4字,反而導致整體語義不明。鄭玄也感到難以理解,以至于曾認為“哀”乃是“衷”字之誤。而“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的說法或來自于劉向《列女傳》中“《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之說,然而,劉向此說是與“刺康王”說相一致的,也就是說,既然康王夫人失德,所以希望得到淑女,匹配康王。而《毛詩序》既然不認為《關雎》是“刺詩”,所以,這里的評論也就成了無的放矢。不過,由于漢代四家詩從“風天下而正夫婦”的角度對《關雎》的詮釋可謂淵源有自,且契合詩篇文本的內在邏輯,又與早期儒家從情與禮之關系角度的解讀一脈相承而可以相互發明,因此,從根本上說,漢代詩學既有早期儒家詩學為其理論來源,又契合中國傳統社會構建和維系社會政治倫理之需要,故而漢代詩學能夠根植于社會人心而長期影響后世。
四、結語
關于《關雎》主題與主旨的討論,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的當下自有其深遠意義。我們應該認識到,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的《詩經》既是“詩”更是“經”,既具有“詩”的靈動和文學審美價值更是集中體現著中華民族價值理念的“經”。脫開經學傳統來解讀“詩三百”,將難以真正把握《詩經》作為國學經典的文化內涵。我們今天誦讀《關雎》,應該注重其蘊含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禮樂教化意義,解讀出體現于字里行間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華美學精神。我們今天誦讀《關雎》,應該懂得“風天下而正夫婦”的倫理教訓意義,懂得基于婚姻而結為夫婦,不僅是對生命意義上的愛情的肯定和接納,也是對倫理意義上的夫婦倫理責任的確認,是對愛情追求和對夫婦美善之德相“逑和”的雙重接納。我們今天誦讀《關雎》,應該從“關雎和鳴”讀出夫婦“摯而有別”的德操,從“窈窕淑女”讀出女性應有的幽閑品性與美善之德,從“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詩句讀出夫婦之間應有的“琴瑟好合”。簡言之,我們今天只有打破成見,既直接面對《詩》文本的脈絡和語境,又認真而審慎看待《詩》學史上的訓詁與詮解,才能將《詩》讀作真正的經典,并使之成為永恒的經典。
[1]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
[2]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李學勤.《詩論》說《關雎》等七篇釋義[J].齊魯學刊,2002(2):90-93.
[4] 王博.中國儒學史:先秦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饒宗頤.竹書《詩序》小箋[C]//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228-230.
[6] 李洲良.詩之興:從政教之興到詩學之興的美學嬗變[J].文學評論,2010(6):36-41.
[7]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8] 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1980.
[9]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10] 鄧安生,邢麗芳.《關雎》的性質及其教化意義[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53-57.
[11] 姚小鷗.《詩經·關雎》篇與《關雎序》[J].文藝研究,2001(6):81-87.
[12] 柯小剛.《詩經·關雎》大義發微[J].江海學刊,2014(2):13-18.
[13] 尚學鋒.從《關雎》的闡釋史看先秦兩漢詩學[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38-44.
DiscussionofPoem·ZhouNano·GuanJufrom“metaphordesiretoetiquette”to“virtuesofcouple”
WANG Guo-yu
(Da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Poem·ZhouNan·Guanjuhas always been different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early Confucianism comments the theme ofGuanJuto inform people of proper etiquette through poet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eme of des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ritual. Han Confucianism thinks thatGuanJuembodies the “virtue of empress and concubine” and has the enlightenment of exemplary significance to teach the world and correct the couple’s ways.This paper links up theConfuciuspoeticsandFiveelements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historical relevant discus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subject ofGuanJu, the comments of the early Confucianism and the Han Confucianism seem to be quite different. In fact, they are inherently consistent: informing people of proper etiquette through poet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eme of desire affirms the virtues of couple for the ethical sense, which is the sublimation and norms of men and women love for the life sense. Han Confucianism affirm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GuanJuon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the world and correcting the couple’s ways, which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uple ethical concept in early Confucianism, but also derives from the same origin with the view ofpoetryin early Confucianism. Appropriate understanding ofGuanJucan effectively interpret its implication of the ritual education and the virtues.
GuanJu; “metaphor desire to etiquette”; “virtues of couple”;Confuciuspoetics; poetics school
2017-05-09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12YJC720033)
王國雨(1978-),男,河南扶溝人,副教授,哲學博士。
I207.22
A
1671-6248(2017)04-012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