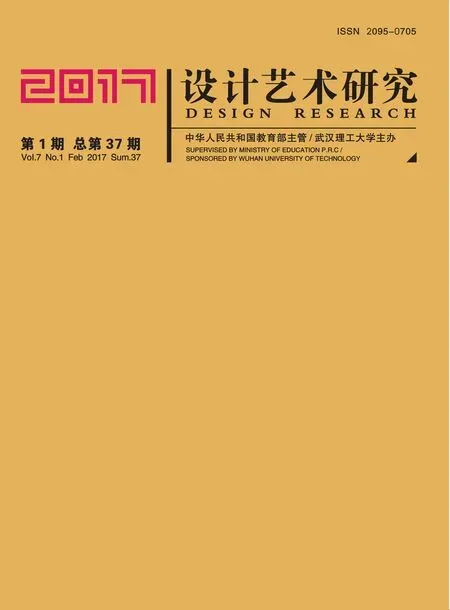新疆和中亞陶器的傳承與文化交流*
熱孜婉古麗?吾其孔ReZiWanGuLi?WuQiKong 伊明江?阿布都熱依木YiMingJiang?AbuDuReYiMu
新疆藝術學院,烏魯木齊 830049(Xinjiang Arts Institute,830049 Urumqi)
新疆和中亞陶器的傳承與文化交流*
熱孜婉古麗?吾其孔ReZiWanGuLi?WuQiKong 伊明江?阿布都熱依木YiMingJiang?AbuDuReYiMu
新疆藝術學院,烏魯木齊 830049(Xinjiang Arts Institute,830049 Urumqi)
新疆和中亞由于歷史和地理環境的原因,在文化藝術上進行著各種交流,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陶器作為新疆和中亞的一個文化載體,不僅體現著兩地文化發展與交流的層次性,而且還反映著兩地文化發展的流變性。分析從新疆和中亞階級社會形成起,到中世紀伊斯蘭教文化藝術在兩地各民族生活和文化中確立止,來探討新疆和中亞陶器文化的交流和傳承。說明在陶器文化上,由于獨特的歷史環境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兩地陶器文化的某些相似性,而發展過程中更是在相互繼承的同時,受著各種外來文明的沖擊和影響,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積累、豐富、完善、雙向交流和互動的歷史過程和發展規律。
新疆;中亞;陶器;文化交流
一、引言
在地理環境上,新疆和中亞是一個交叉地帶。從地域的文化特性上來看,生存環境緊密相連、文化藝術交流此起彼伏,是一種廣義的文化集合體和一座異彩紛呈的文化資源寶庫,它所包涵的內容極其豐富而復雜。在緩慢而長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藝術形式,可以說造就了新疆和中亞審美文化結構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相似性。
陶器作為新疆和中亞的一個文化載體,體現著兩地文化發展、交流的層次性,同時也反映著兩地文化發展的流變性。陶器在整個文化變遷運動過程之中,具有特定的歷史存在形式,從而使陶器的形態、功能、工藝技術、紋飾等,具有特定的時代意義及相應的文化痕跡與脈絡。而陶器的生產、流通、使用等環節,對于社會發展、文化、思想意識等的關系和作用而言,更具有時代文化縮影的意義。
所以,以藝術人類學的視覺與方法,應將陶器還原到其所處的社會生活、文化語境和歷史維度之中,使其背后的一張巨大的文化之網能夠得以顯現。
這誠如方李莉在《中國陶器史》中所言:“以藝術人類學的視覺介入陶器研究,對傳統器物論器論的陶器研究方法的一種創新,它要求以一種整體研究法,反對藝術品孤立于文化之外,孤立于社會之外,對陶器的研究,不應該只是一種器物或工藝美術品的研究,還應該將其研究,擴展到文化的語境中以及社會的構成與發展的領域中。”[1]
所以,在論述新疆和中亞陶器文化遺存時,應將它置于主要的古代歷史——文化區中加以考察。本文所論述的古代中亞藝術年代,從新疆和中亞階級社會形成起,到中世紀伊斯蘭教文化藝術在兩地各民族生活和文化中確立止。
二、阿契美尼德時期和古希臘時期(公元前6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世紀)
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是波斯人建立的第一個君主制王朝,又被稱為波斯第一帝國。該王朝橫跨亞、歐、非三洲,自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由波斯王居魯士到大流士皇帝一世時,疆域范圍擴大到大部分中亞地區,對中亞的經濟、文化、藝術影響很大。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間由波斯人創立的瑣羅亞斯德教,我國古代史籍稱之為“襖教”,在其統治時期,在中亞、西亞等地流行起來,之后又傳入到新疆各綠洲和草原游牧民族中。
在對中亞統治期間,波斯人把阿拉美亞文字傳到了中亞并在此普及起來。前蘇聯考古學家在花剌子模地區,也發現了刻有該文字的陶罐。即在花剌子模的科依·克雷爾干·卡拉,發現一個屬于公元前3世紀的大型陶器——酒罐,其上的銘文(可能是酒罐所有者的名字),據說也是起源于阿拉美亞的文字[2]。古代波斯人在對中亞統治期間,對中亞的文化藝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亞長時間作為阿契美尼德帝國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龐大帝國中與其他地區和民族發生經濟接觸,這些當然不能不在這一時期的文化和藝術中表現出來[3]。阿契美尼德無疑為中亞原有文化藝術注入、增添了新的文化血液,古波斯文明對新疆文化藝術的影響,早已被中外學術界所證實。
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后來被馬其頓王國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覆滅,接著中亞的文化和藝術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被稱作希臘時期。在這新的歷史條件和新的文化背景下,先前中亞的文化藝術尤其是陶器藝術,必將產生新的變化。
前蘇聯考古學家對中亞考古時,發現了大量的具有希臘陶器特征的陶器制品。這些古希臘羅馬時代中亞的陶器“制作考究,器形美觀規整,紋飾細膩典雅,器表光潔平滑,色彩鮮艷悅目,光澤柔和或艷麗”[4]。
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統治的巴克特里亞的希臘王國(大夏)(公元前256年至公元1年),對中亞影響最為深刻。巴克特里亞的文化藝術,相對于經濟來講影響更深。相對于經濟發展,波斯尤其希臘的征服和統治,給中亞文化帶來的變革和進化更加引人注目,……在希臘時代,希臘人把他們文化的幾乎所有形式,包括語言、文字、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等,以及這些形式所負載的思想觀念統統帶到了中亞,這就是一次新的文化融合[5]62-63。
在陶器方面,帕爾提亞王國(安息)陶器有綠釉陶器,器表刻有花紋和凸起的裝飾物。王治來先生在《中亞史》一文中指出:“巴克特里亞的農業在中亞是比較先進的……手工業也很發達,制陶都用陶輪,陶器的紋飾多為幾何形,或有表示豹與山羊的動物紋,可見當時的巴克特里亞文化藝術水平。”[6]35
在新疆吐魯番、和田地區出土的陶器上,如在新疆和田縣出土的帶有菩薩人像和忍冬紋的三耳人物罐(見圖1)[7]121,我們依然能看到波斯和希臘的遺風。“和田約特干遺址歷來出土遺物多為陶器、陶俑……多全裸或半裸,顯然受到希臘和印度雕塑藝術的影響……陶器上陰刻和堆貼的各種紋飾豐富多彩。……聯珠紋、忍冬紋等來自波斯……”[7]116

圖1 三耳人物罐(現存柏林)[7]121
同時,公元3世紀新疆喀什疏附縣烏帕爾村出土的,有帶西方人頭像刻有忍冬紋和葡萄葉紋的陶器碎片(見圖2)[7]120。

圖2 西方人頭像殘片[7]120
“陶器與木雕業以于闐、鄯善最擅勝場,斯坦因在約特干遺址發現的眾多陶器碎片,花紋、造型皆備極精美,其中一陶片繪有高鼻、深目、多須的男子像,帶有希臘風格,且胎質薄而堅,確乃紅陶上品。”[8]
可見,波斯文化和希臘文化這兩種特質文化在新疆和中亞的融合與交流,對當地的陶器藝術注入了新鮮的內容,而且波斯和希臘興建城市、修建道路、設置驛站,把零星分散的綠洲、河谷、沙漠和山土串聯起來,為自己的統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為日后橫穿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各種藝術形式的交流,奠定了道路保障和基礎。
三、貴霜、嚈噠與突厥時期(公元1-6世紀)
公元1-2世紀,貴霜帝國在中亞一帶開始強盛起來,這是由來自北方大月氏人建立起的王朝。王治來先生在《中亞史》中指出:“貴霜王朝與康居相接,與之關系密切。東與中國的塔里木盆地毗鄰,同天山南路綠洲諸國也有緊密聯系,并參與了他們之間的斗爭。……由于貴霜王朝弘揚佛教,當時有大量中亞的佛教徒來中國傳教。貴霜王朝對今新疆地區有很大的影響。”[6]46
隨著佛教藝術的東傳,如雕刻壁畫、語言、文字也逐漸豐富著新疆地區的文化藝術。“貴霜人在中國西域和中亞大道上設立了貿易貨棧。為了取得把中國絲織品轉賣到地中海國家的權利,貴霜帝國與帕爾提亞及羅馬帝國所屬各國的商品,除絲綢之處,還有玉石、漆器、棉織品、毛皮、鐵器等。”[9]11
貿易上的往來,促進了當時各地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相互交流,推進了各地的文化藝術的傳播。在陶器方面,“貴霜王國統治大夏時期,人們采用了以樹葉紋理、最簡單的玫瑰花形裝飾圖案,三角形符號為形式的小型沖模。用壓模在高水罐的頸部、碗的內側壁和底部壓出花紋……陶器藝術在中亞北方區域表現突出。在這里陶器是指有雕塑裝飾的陶器,公綿羊的圖形在其中占顯著地位……或者有羊頭形象裝飾手柄,或者在器皿軀干上貼上羊角頭像。另外還選擇有其他動物。這里有狗、刺猬,甚至還有猴子,雖然這種現象的出現同佛教有關”[9]136-137。
從公元3世紀初至公元3世紀末,貴霜帝國開始衰敗。游牧的嚈噠人從公元5世紀中期到公元6世紀期間統治著中亞和中國西北地區。“大約在公元5世紀20年代以后,嚈噠人便進一步征服了吐火羅、巴達赫善、克什米爾、喀布爾、健陀羅與旁遮普,向東則乘柔然衰敗之機,占據塔里木盆地的許多地方……,從此,嚈噠成了中亞強國。”[10]
嚈噠與周邊的中國、波斯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統治期間控制著絲綢之路中西之間的商道并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公元5世紀,因為中亞的主要商路經過撒馬爾罕,這里除農作物得到很快發展外,手工藝生產如陶器制造、金屬冶煉、玻璃工藝、織布等行業都得到了發展,特別是布哈拉及撒馬爾罕周邊地區。”[9]11
在西邊,波斯的薩珊王朝興盛,在經濟、文化、藝術上有了長足的發展。“無論在貴霜時期和嚈噠時期,其統治者顯然都控制這條商道來獲得巨大利益……同樣,薩珊王朝起著貿易中介的作用。薩珊王朝的銀幣,不但大量流通到嚈噠所屬的中亞境內,而且流通中國。”[11]4
在陶器制作方面,“薩珊陶器主要為釉陶和建筑用馬賽克陶磚,在造型上有仿效金銀器的把手杯,杯身較淺,常見的還有雙耳壺和系耳大罐,大罐用于儲藏食物或飲料,常有3個系耳方便穩妥地掛起。在色澤上,青釉仍然是最為流行,對淺色釉系也有追求,如淺黃、白色、淺藍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薩珊釉陶作為當時先進的制陶技術傳播到中國,對中國唐三彩產生了影響”[11]15。
在嚈噠統治中亞及中國西北地區時,各地區間經濟關系日益密切,絲綢貿易更加活躍、頻繁。同時,他們相互之間的文化藝術交流也日益發展起來。在嚈噠日益走向衰敗時,突厥作為興起于中西部的部族,在公元6世紀中后期崛起,擊敗嚈噠、柔然等游牧民族,控制中亞。“興起于阿爾泰山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在公元6世紀中后期先后擊敗柔然、嚈噠等游牧民族,其勢力范圍東起遼西、西至拜占東北及南俄草原,南到興都庫什山,成為蒙古西征之前歐亞草原上勢力最大、控制區域最廣的游牧帝國。”[12]
像希臘、貴霜、嚈噠一樣,突厥占據中亞,在絲綢之路商道上與粟特人一起進行著貿易。“公元6世紀突厥的擴張和征服,實際上是游牧民族與粟特商業民族結成利益共同體,在歐亞絲路競逐經濟利益,構建貿易網絡的經濟擴張,至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興起,唐王朝經營西域中亞之前,東西突厥,仍是牽動歐亞絲路主要國家和民族政治經濟變動的主要勢力”[12]。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各個利益集團為了不同的目的,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平臺,在這個平臺中,各國又都通過商品傳播著各自的文化。中國的絲綢、玉石、陶器傳播到了西方,反之,歐亞各國又將自己的商品帶入各地。
在這其中,陶器也作為商品又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形式,與其他商品一樣傳遞著文化信息。突厥人和粟特人在歐亞大陸上的合作,促進了東西方陶器的發展。“在古代西域,釉陶十分發達,按釉料助熔劑的不同,西域釉陶有兩類:鉛釉陶和堿釉陶……據考,隋代居工部尚書一職者,有一半非漢人,何稠(約543-622年)以擅長工藝技巧著稱于隋,其祖籍西域何國(位于今撒瑪爾罕和布哈拉之間),他以‘綠瓷’成功仿制‘琉璃’便是明證。何稠應主要通過改變釉料,才使陶瓷外表酷似玻璃,鑒于何稠的文化背景,西來的玻璃配方很可能滲透于中國瓷釉料工藝中。”[13]
在突厥和粟特的共同經濟貿易合作基礎上,新疆和中亞各國藝術有了一定的發展,其中陶器不僅作為商品,而且作為文化傳媒扮演著重要角色,傳承著陶器所承載的文化脈絡和藝術價值。
四、新疆和中亞歸屬于唐朝時期(公元6世紀中期)
公元6世紀中后期,突厥分裂為東西兩部分。公元659年,唐朝統一了東西突厥,整個西域及中亞合并于唐。也因此,西域和中亞同中國的經濟文化關系更加密切,中原文化對兩地影響也逐漸加深,在兩地設置府、州、鎮等管轄地進行管理。
“絲綢之路在唐代迅速發展成為網絡,覆蓋了中國西部地區、西域和中亞地區,當時的絲綢之路貿易以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推動了這些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使自漢代起承載著東西方文明交流使命的中國西部、西域和中亞地區,真正成為了多種文明薈萃、各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唐代中國與中亞地區各國關系非常密切,因而‘貢賜’頻繁而活躍,官方或民間的‘互市’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歷史悠久的貿易形式。”[14]
“唐朝建立之后,在突厥地設置府、州、鎮進行管理。反映在陶器方面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陶制品使用的范圍更為寬廣,陶器類別增多,如新疆溫宿縣包孜東突厥墓葬群,出土的陶器分夾砂和泥質兩種,器表多抹光,均手制……器物多附流、整、耳,增加了立體造型的美感。其二,不論大件器物還是小型器皿,在質量上要求高,小中見大,精巧而有氣魄。其三,因其他工藝品的影響和審美要求的提高,陶制品的工藝和造型也出現了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樣,如綠釉執壺,綠釉鸚鵡壺、釉綠貼塑瓶……在漢代低溫釉陶器的基礎上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使陶器工藝有了很大的發展。”[15]
綠釉是波斯、中亞陶器的特色。唐朝勢力范圍之下,新疆和中亞進行著更加廣泛而深入的文化藝術交流,雖然陶器不像絲綢一樣有重要的貿易價值,但它在絲綢之路上也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商品之一,并在不同歷史時期傳播著自身的文化發展和藝術特色。
五、伊斯蘭時期(公元6-9世紀)
公元6世紀末到9世紀,不斷受到不同政治、經濟、文化沖擊和洗禮的中亞,又受到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在滅亡波斯薩珊王朝以后,公元673年阿拉伯人帶著伊斯蘭教開始涉足和入侵中亞。最后在公元8世紀開始,徹底把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價值觀根植和傳播在了中亞。在之后長達數世紀中,新疆和中亞是個戰爭頻發、民族變遷、經濟文化大發展和大變化的年代。
在公元9世紀后,中亞阿拉伯政權先后轉移到了不同的突厥諸王朝之中,這些突厥王朝薩曼王朝、喀喇汗王朝、哥疾寧王朝、賽爾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以及日后的蒙元時期,盡管新疆和中亞在政治上跌宕起伏,但在阿拉伯帝國奠定宗教文化統一性基礎上延續著伊斯蘭文明,其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保持相對的穩定。“突厥文化進一步整合了中亞宗教文化的統一性,它不僅使伊斯蘭教得到了更加廣泛深入的傳播,而且使中亞大部分地區在語言、風俗甚至身份認可方面更為接近。”[5]191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新疆和中亞的廣泛傳播,帶來了一個嶄新的文化意識形態,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新的教義和倫理道德規范,這種文化滲透的狀態向伊斯蘭教文化轉型,這一點對兩地的各種藝術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這既是對兩地原有文化的進一步延伸、擴展,又是兩地原有文化新的質的變化。
1.阿拉伯伊斯蘭陶器
阿拉伯伊斯蘭陶器,是在原有征服地的陶器文化基礎上產生的。倭馬亞王朝早期政局動蕩,“但是倭馬亞藝術相當重要,它集各種裝飾變化之大成,衍生出隨后的大多數伊斯蘭裝飾,其中包括陶器”[16]。在陶器上,倭馬亞王朝不僅吸收和集納著拜占庭帝國的傳統堿釉系、鉛釉系中的綠、褐陶器,而且也繼承了波斯薩珊王朝的釉陶工藝。
“總體而言,倭馬亞陶器屬于前伊斯蘭陶器向伊斯蘭陶器過渡的產品,仍具有很強的薩珊波斯和拜占庭羅馬風格,但以抽象化的植物紋和簡明的幾何紋為組合的裝飾樣式,已顯示出伊斯蘭藝術的雛形。”[11]5無疑,在倭馬亞王朝,伊斯蘭陶器藝術已開始發展。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國的第二個世襲王朝,其疆域范圍從原有的征服地已延伸到中亞地區,阿拉伯帝國擴張的同時,伊斯蘭教包括在內的阿拉伯文化也在傳播中。在這一時期,“伊斯蘭文明的發展離不開這些王朝更替的命運,早在敘利亞的倭馬亞王朝邀請或驅逐各國的工匠們,這種做法也被后世政權效仿。巴格達、撒馬爾罕各地相繼成為藝術和傳承的中心”[11]3。
在經濟上,阿拔斯王朝時期的中亞經濟,尤其是手工業有了蓬勃的發展。“阿拔斯王朝中亞手工業繼續發展,手工業可以分為如下幾類:紡織業、絲織業、釀酒、制氈、制革等手工業在中亞各城鎮得到普遍發展……瓷器在中亞西部發展起來。”[17]
綜覽這時期陶器藝術,阿拔斯陶器發展了前期的成果,這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伊斯蘭陶瓷藝術風格的形成期。黃綠彩釉陶、白釉藍、綠彩陶、白釉陶、彩繪陶等類型,都是在這時期形成。如宋元時期的聯珠紋黃綠彩釉球形罐(見圖3)[18]100。

圖3 彩釉球形罐[18]100
“黃綠彩釉陶和多彩釉,以其簡單的制作方法迎合了平民的需求,并傳播到中亞、西亞,在當今的新疆仍能看到這種陶器的制作。”[11]20比如,公元10世紀中亞古代城市,也是喀喇汗王朝的重要商業城鎮訛答剌,就有黃綠釉色相間的單耳陶罐(見圖4)。

圖4 黃綠釉色相間的單耳陶罐①
自公元9世紀開始,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新疆和中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2.伊斯蘭化的突厥時期陶器
隨著阿拉伯帝國在中亞勢力的消退,這里又先后由幾個突厥王朝進行了統治。公元9-10世紀,第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王朝,幾乎征服了新疆南部地區和河中中亞地區,河中地區征服者阿里·納賽爾·本·阿里,掌控了包括了撒馬爾罕、不花剌、訛答剌、費爾干納等廣大而富裕之地。
喀喇汗王朝統治以前,中亞地區是由薩曼王朝統治的,其領地在河中,撒馬爾罕、不花剌等城市為整個王朝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中心。“薩曼王朝時期,農業、采礦業、手工業和貿易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對中亞河中和呼羅珊的居民在經濟上非常重要,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是農業生產和采礦業的進步……,陶器的生產十分流行,陶工制作的陶器細膩、光滑透亮、質量高,帶有各種裝飾,并且流行用一些語句裝飾禮用陶器的邊緣,包括《古蘭經》的段落,一些著名詩人的語句或者就是一兩句祝福的話。陶工也為窮人大量生產廉價的陶器,同時也制造金屬和玻璃器皿。”[19]54-55
比如,公元13世紀訛答剌帶有阿拉伯文的素陶罐(見圖5)。

圖5 素陶罐①
可見,自喀喇汗王朝征服新疆南部地區和中亞地區,在原有的經濟文化、手工業基礎上不斷發展。“公元11-12世紀的城市持續發展,手工業和貿易不斷擴大,喀喇汗王朝城鎮證明了公元11-12世紀繁榮的商隊貿易,大量生產的陶器和玻璃等物品也提供了城市手工業發展的清晰畫面。喀喇汗王朝制陶業的發展有自己的特點,制陶技術和用彩的范圍都發生了變化。”[9]101
比如,公元11世紀訛答剌淺釉色帶深色阿拉伯文的陶盤(見圖6)。

圖6 淺釉色陶盤①
“滿上藍釉的陶器非常受歡迎,釉下繪制復雜幾何圖形和枝蔓編織圖形的碗杯,配以優美的淡棕色和咖啡色,也很有市場,庫法體的文字也用于裝飾,但這種方式后來轉變為一種模仿庫法體難以辨認的文字裝飾風格。有的陶器下不用釉,形制和裝飾都模仿金屬器皿,十分流行。……公元11-12世紀已經廣泛使用了燒制磚,特別是在類似宮殿、清真寺、邁德賴賽(即職官學校)、陵墓和橋梁等主要建筑中……”[19]102
比如,現存于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博物館的公元10世紀帶有阿拉伯文的鉛釉陶碗(見圖7)。

圖7 鉛釉陶碗①
在喀喇汗王朝時期,由著名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編著的《突厥語大詞典》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突厥語各民族的社會文化生活,其中涉及大量陶器制作、器形等方面的信息。比如,“BOKAQ(水罐)”[20]535、“QEXIKEL(陶罐、陶瓶)”[20]629、“DOLEK(有流嘴的陶罐)”[20]505、“KENDOK(陶罐)”[20]627、“KENQEKQE(放谷物的陶罐)”[20]627、“KOZEQ(水罐)”[20]466、 “KOP(水罐)”[20]414、“IVIRIK(陶壺)”[20]637、“TOKOKA(陶壺的壺嘴、流嘴)”[20]637、 “OLMA(陶器)”[21]、 “TOYAXIQ(陶鍋)”[22]、 “YAXIMAN(小的陶嘴)”[22],等等。
另外,土爾其學者熱夏提·干尼其(Rixiat· Ganniq)在《從〈突厥語大詞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社會狀況》一書中指出:“在陶器中,把碗、盤等均稱為‘AYAK’,制作陶器的人稱為‘AYAKQI’。”[23]
雖然《突厥語大詞典》中,并沒有介紹如何制作陶器的過程,但是在詞典中明確指出“TOY”一詞泛指陶泥。可見,公元11世紀突厥民族有專門制作陶器的藝人,陶藝藝人用“TOY”一詞,并加入后綴“AXIQ”來指稱各種陶器皿。藝人制作陶器時,常常會在器表施上各種釉色,并用各種裝飾圖案來裝飾。在《突厥語大詞典》中,明確標出“SIR”是指帶有膠的漆[23]。用這種漆對陶器表面進行施釉、繪圖,具有很強烈的藝術特征。
比如,烏茲別克斯坦褐色陶碗(見圖8),以及新疆土陶菱形格彩釉花碗(見圖9)。

圖8 烏茲別克斯坦褐色陶碗②

圖9 新疆土陶菱形格彩釉花碗[18]161
從上述論述中出現的陶器詞語,可以明顯看出陶器是當時諸新疆和中亞各民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時至今日,這些陶器名稱依然在兩地廣泛使用著。
繼喀喇汗王朝,中亞地區相繼又建立了一系列政權國,如公元11世紀塞爾柱王朝至公元12-13世紀的蒙古政權,到帖木兒王朝統治下的中亞(公元14-15世紀早期),這些政權此起彼伏,對新疆和中亞的政治、經濟、文化推波助瀾,推動了兩地的文化交流。
可見,新疆和中亞的歷史和地域環境的交叉,各民族區域之間的交流,事必影響到兩地的文化交流和回授。在陶器文化上,在兩地發展過程中更是在相互繼承,并受各種外來文明的沖擊和影響,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呈現出一個動態的,不斷積累、豐富、完善、雙向交流和互動的歷史過程和發展規律。
注釋
① 圖4、圖5、圖6、圖7來源:K.BAIPAKOV,L.ERZAKOVICH.CERAMICS OF MEDIEVAL OTRAR[M]. Издателвство Онер:АЛма-Ата,1991.
② 圖8來源:National Museum of Korea.Ancient Culture of Uzbekistan[M].Seoul:ba Design,2009.
[1]方李莉.中國陶瓷史:上[M].濟南:齊魯書社,2013:5.
[2]蒙蓋特.蘇聯考古學[M].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63:239.
[3]斯塔維斯基.古代中亞藝術[M].路遠,譯.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1992:2.
[4]普加琴科娃,列穆佩.中亞古代藝術[M].陳繼周,李琪,譯.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94-95.
[5]丁篤本.中亞探險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6]王治來.中亞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李肖冰.中國新疆古代陶器圖案紋飾藝術[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
[][]社,2000.
[8]薛宗正.中國新疆古代社會生活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31.
[9]普加琴科娃,列穆佩.中亞各族文化藝術史[M].賈東海,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10]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上[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160.
[11]吳靜.波斯細密畫中的陶瓷器具研究[D].景德鎮:景德鎮陶瓷學院,2012.
[12]張爽.6世紀歐亞大陸的絲綢貿易與絲路:以突厥外交軍事活動為中心[J].社會科學輯刊,2015(6):153-158.
[13]董波.淺論早期白瓷中的西域要素[J].中原文物,2010(6):81-91.
[14]趙曉佳.中國與中亞的友好交流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1:81.
[15]張景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藝術與文化表意[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133.
[16]亞瑟?萊恩.早期阿拉伯陶瓷[M].程庸,王安娜,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14:7.
[17]趙永倫.阿拔斯王朝統治下的中亞經濟[J].興義民族師范學報,2012(1):42-46.
[18]張文閣.新疆土陶藝術[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9]阿西莫夫,博斯沃思.中亞文明史: 4:上:輝煌時代:公元750年至15世紀末:歷史、社會和經濟背景[M].華濤,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0.
[20]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辭典:1[M].維吾爾文全譯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21]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辭典:2[M].維吾爾文全譯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339.
[22]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辭典:3[M].維吾爾文全譯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49.
[23]熱夏提?干尼其.從《突厥語大詞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社會狀況[M].維吾爾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444.
(責任編輯 孫玉萍)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Pottery between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Due to geography and the forces of history, interaction in art and culture in many forms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re are countless relational ties between them. Pottery has served as a conveyor of culture and serves now as a microcosm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It exemplifies the stair-step character of their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 and refects as well the fuctuating nature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areas. Beginning with the early class-societies in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eval Islamic culture and art in the lives and cultures of the ethnic groups of these two area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and heritage of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within this realm of pottery. It then explains that it was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which gave rise to certain similarities in the “pottery culture”of these two regions a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re was a great deal that they inherited from each other. In addition, they also received many types of civilizing infuence and inpu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From a low level to a high level, from simple to complex, the art of pottery followed a rich, dynamic, continuously accumulating and perfecting, two-way interactiv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
XinJiang; Central Asia;Pottery;cultural exchange
J5
A
10.3963/j.issn.2095-0705.2017.01.004(0022-09)
2016-06-28
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國家西部項目(12EG122)。
熱孜婉古麗·吾其孔,新疆藝術學院美術系碩士生;伊明江·阿布都熱依木,新疆藝術學院美術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