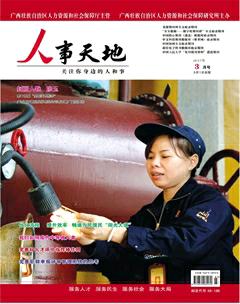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之間輪流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時,如何計算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工作年限
劉黎明
2002年1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時某在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工作。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為時某繳納社會保險。2010年7月1日時某入職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同日雙方簽訂了《聘用合同書(管理人員)》,約定合同期限從2010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時某擔(dān)任終端經(jīng)理工作。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未發(fā)放時某2012年1月1日至3月14日期間的工資。2012年3月14日時某向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提出解除勞動關(guān)系,理由系未按時足額支付工資。現(xiàn)時某主張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應(yīng)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江蘇某化妝品公司不同意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
時某向當(dāng)?shù)胤ㄔ宏愂觯?010年7月1日其在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和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的安排下與江蘇某化妝品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但工作地點(diǎn)一直在當(dāng)?shù)兀皇枪究鐓^(qū)搬遷了兩次。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和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系關(guān)聯(lián)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應(yīng)當(dāng)連續(xù)計算工作年限。為此時某向法院提供了社保繳納記錄、公證書(內(nèi)含當(dāng)?shù)厣鐣kU參保人員增減表、2010年10月12日時某關(guān)于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在某區(qū)2011年房租費(fèi)的申請簽呈)予以證實(shí),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和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對社保繳費(fèi)記錄真實(shí)性認(rèn)可;對公證書真實(shí)性和證明目的不認(rèn)可。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向當(dāng)?shù)胤ㄔ宏愂觯航K某化妝品公司和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是獨(dú)立法人,不存在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向法院陳述,2010年6月30日時某系自動離職后到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工作。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沒有支付時某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
一審法院經(jīng)審理認(rèn)為: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未足額支付時某工資,時某據(jù)此解除與江蘇某化妝品公司的勞動合同關(guān)系,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十六條用人單位應(yīng)當(dāng)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情形。現(xiàn)時某要求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訴訟請求,理由正當(dāng),應(yīng)予支持。對于補(bǔ)償金數(shù)額應(yīng)根據(jù)時某的工資標(biāo)準(zhǔn)及工作年限予以確定。關(guān)于時某的工作年限問題,根據(jù)時某在入職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后某化妝品公司仍為時某繳納社會保險的事實(shí),并結(jié)合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在某區(qū)2011年房租費(fèi)的申請簽呈中“終端運(yùn)作中心審批意見”一欄有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簽字的事實(shí),能夠認(rèn)定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存在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而時某從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到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工作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屬于勞動者非因本人原因從原用人單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單位工作,故在計算支付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工作年限時,時某主張把原用人單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計算為新用人單位工作年限,法院應(yīng)予支持。故其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計算年限應(yīng)從2002年11月開始計算。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應(yīng)按照10.5個月為標(biāo)準(zhǔn)支付時某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綜上,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江蘇某化妝品公司支付原告時某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人民幣86163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nèi)執(zhí)行。
一審判決后,被告不服,上訴至二審法院,要求依法改判。
二審法院經(jīng)審理確認(rèn)原審法院查明事實(shí)屬實(shí),并進(jìn)一步認(rèn)為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之間存在勞動法上的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guī)定,法院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實(shí)踐中,我國的一些集團(tuán)公司因經(jīng)營需要,將勞動者從一個用工單位指派、轉(zhuǎn)移到另一個用人單位。個別用人單位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用工成本最低化的目的,惡意規(guī)避法律,利用管理之便將勞動者在不同用人單位之間進(jìn)行勞動關(guān)系的分配和調(diào)動,導(dǎo)致員工并不固定和一家企業(yè)訂立勞動關(guān)系,人為造成勞動者喪失潛在利益的局面。由此如何計算員工的工作年限也顯得尤為重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3年2月1日起實(shí)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四)》(以下簡稱勞爭解釋四)的第五條開始有效扭轉(zhuǎn)實(shí)踐中存在的上述局面。本案就是勞爭解釋四出臺后司法運(yùn)用的實(shí)踐結(jié)果。
本案原告和被告爭議的焦點(diǎn)在于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之間輪流與時某訂立勞動合同時,如何計算時某解除勞動合同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工作年限。這一爭議焦點(diǎn)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jìn)行分析:一是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是否屬于勞動法上的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二是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輪流與時某訂立勞動合同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三是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輪流與時某訂立勞動合同是否損害時某的期待利益。
(一)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是否屬于勞動法上的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
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是指在法律上相互獨(dú)立,但在資金、經(jīng)營、購銷等方面存在著直接擁有或控制關(guān)系,直接或間接地同為第三者所控制或擁有、其他在利益上具有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的公司、企業(yè)、其他經(jīng)濟(jì)組織。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的關(guān)系不同于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關(guān)系,它們在公司法上屬于獨(dú)立法人,相互間自主經(jīng)營、自主管理、自主盈利,獨(dú)立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故僅從外觀上難以判斷。本案的審理思路可以歸納為從形式與實(shí)質(zhì)兩個方面進(jìn)行考量。
1.從形式上看,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一般具有相同的股東、相同的法定代表人或是相同相近的企業(yè)名稱,或者擁有同一個注冊地或者實(shí)際經(jīng)營地,在公司的員工手冊或者對外宣傳單中,會將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之間的孕育、發(fā)展歷史與變遷沿革作為企業(yè)文化加以宣傳,等等。本案從形式看,被告與第三人的企業(yè)名稱都包含有著名商標(biāo)“某某某”字樣。
2.從實(shí)質(zhì)上看,重點(diǎn)調(diào)查企業(yè)的實(shí)際控制人、兩企業(yè)是否為統(tǒng)一的經(jīng)營管理、高管是否在兩企業(yè)里兼職、勞動者工資發(fā)放主體及時間段、社保繳交主體及時間段,比如本案中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的簽呈中有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字,時某在入職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后,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仍為時某繳納社會保險,說明兩家企業(yè)在經(jīng)營管理有混同現(xiàn)象。
法院審判實(shí)踐中,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通常表現(xiàn)得極為隱蔽,即使勞動者聲稱是在兩家企業(yè)的安排下簽訂了新的勞動合同,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也僅會陳述雙方并無任何關(guān)系。從法人獨(dú)立人格說理論角度,原用人單位沒有責(zé)任承接勞動者在原用人單位的工作年限,也沒有義務(wù)代原用人單位支付經(jīng)濟(jì)補(bǔ)償。但《勞動法》不同于平等主體之間的普通民事或商事法律,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關(guān)系,勞動者對用人單位具有人身依附性,兩者地位并不平等。由此引申出法人獨(dú)立人格否認(rèn)制度在勞動法領(lǐng)域的適用。
(二)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輪流與時某訂立勞動合同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
用人單位之間對勞動者進(jìn)行調(diào)動、劃撥的目的應(yīng)當(dāng)出于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需要,符合雙方締結(jié)勞動合同的目的。也就是說,兩用人單位對勞動者進(jìn)行劃撥、調(diào)動的行為不僅應(yīng)對用人單位構(gòu)成利益最大化,同時對勞動者也應(yīng)構(gòu)成有利變更。本文擬從公司發(fā)展與個人成長兩個方面進(jìn)行考察。
就公司發(fā)展的角度而言,市場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要求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在當(dāng)今全球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和一體化的大格局下,用人單位根據(jù)企業(yè)自身的業(yè)務(wù)經(jīng)營狀況而對勞動者做出的調(diào)動、劃撥,應(yīng)當(dāng)以達(dá)成勞動力配置和諧為目的。只要這種方法符合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下企業(yè)根據(jù)自身市場配置勞動力的發(fā)展方向,法院應(yīng)當(dāng)肯定其調(diào)動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時某長達(dá)8年時間一直在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工作,在工作城市、工作場所、工作崗位不變的情況下,又與江蘇某化妝品公司簽訂勞動合同,而合同約定時某仍擔(dān)任終端經(jīng)理工作。這種情形無法反映出公司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無法體現(xiàn)出一個理智的市場經(jīng)營者應(yīng)當(dāng)做出的選擇。如果本案時某與江蘇某化妝品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是因為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在江蘇的市場規(guī)模擴(kuò)大,而時某的銷售業(yè)務(wù)能力有進(jìn)一步提升的空間,因此兩公司在與時某協(xié)商一致后擬將時某調(diào)到江蘇工作,那么這樣的調(diào)動行為即具有合理性。
就個人成長的角度而言,勞動者提供勞動從而獲得勞動價值。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價值,勞動者需要實(shí)現(xiàn)自身的提升,包括工作經(jīng)驗的增長、職務(wù)的升遷與勞動報酬的提高。首先,不同單位之間的工作調(diào)動應(yīng)征得勞動者的同意。勞動者在不同單位之間的工作調(diào)動可以分解為勞動者與舊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和勞動者與新用人單位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兩個步驟。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有關(guān)規(guī)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xié)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訂立勞動合同,應(yīng)當(dāng)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協(xié)商一致、誠實(shí)信用的原則,因此,不論是解除還是簽訂勞動合同,都應(yīng)當(dāng)征得勞動者同意。其次,不同單位之間的工作調(diào)動能夠與實(shí)現(xiàn)勞動者的個人發(fā)展相結(jié)合。勞動者隨著工作經(jīng)驗的累積,其對于工作環(huán)境、薪資待遇、職業(yè)前景均有更高的期待與要求。如果原來的用人單位沒有足夠的晉升空間或者不能滿足勞動者對于培訓(xùn)的需要,那么將勞動者推薦或指派到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中工作,使勞動者仍有升職空間,或者得到進(jìn)一步培訓(xùn)的機(jī)會。本案中時某是在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和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的安排下進(jìn)行的工作調(diào)動,這種安排無法體現(xiàn)出時某的自愿性,也不能與實(shí)現(xiàn)時某長遠(yuǎn)個人發(fā)展的愿望相結(jié)合。
(三)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輪流與時某訂立勞動合同是否損害時某的期待利益
由于勞動者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是勞動者享受本單位職工福利、用人單位辭退勞動者計發(fā)經(jīng)濟(jì)補(bǔ)償金的重要因素之一,實(shí)踐中存在某些惡意的用人單位為防止勞動者原工作年限計入新用人單位,往往采取不同手段來迫使勞動者工作年限清零。如上文所述,用人單位之間對勞動者進(jìn)行調(diào)動、劃撥的目的應(yīng)當(dāng)出于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需要,符合雙方締結(jié)勞動合同的目的,有利于勞動者的個人發(fā)展。如若這個調(diào)動、劃撥無法體現(xiàn)出上述目的,則需要特別注意是否將會損害勞動者的期待利益。實(shí)踐中筆者發(fā)現(xiàn)主要存在損害勞動者以下三種期待利益的現(xiàn)象:
一是對于在原用人單位中工作即將滿10年或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即將到期的勞動者,原用人單位采取各種手段使其變更用人單位,剝奪了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件。本案中,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損害時某的即是這種期待利益,時某在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工作已有8年,在這個時候變動用人單位,剝奪了時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件。
二是對于在原用人單位中工作即將滿10年或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即將到期的勞動者,如果勞動者能夠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那么原用人單位就喪失終止合同權(quán)利,但只要在勞動者變更用人單位并與新用人單位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后,新用人單位即享有單方終止勞動合同的權(quán)利,損害勞動者的就業(yè)權(quán)。
三是一些用人單位長期拖欠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用人單位通過各種方式使勞動者與新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guān)系,迫使勞動者能夠追索與原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報酬的仲裁時效的起算點(diǎn)提前,使勞動者喪失追索部分勞動報酬的勝訴權(quán)。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diào)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條的規(guī)定,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因拖欠勞動報酬發(fā)生爭議的,勞動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不受時效限制,但是,勞動關(guān)系終止的,應(yīng)當(dāng)自勞動關(guān)系終止之日起一年內(nèi)提出。舉例來說,2011年1月1日,勞動者甲與A公司簽訂了兩年期勞動合同,2013年1月1日甲在A公司的安排下與關(guān)聯(lián)公司B簽訂了兩年期新合同,2014年底甲追索2011年至2012年期間A公司拖欠的工資,甲與A公司的勞動合同的終止時間為2012年12月31日,甲的勝訴權(quán)已于2014年1月1日時喪失。
結(jié)合以上三個方面進(jìn)行分析,江蘇某化妝品公司與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屬于勞動法上的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兩個公司對時某工作調(diào)動的目的不具有合理性,也損害了時某的期待利益。時某從當(dāng)?shù)啬郴瘖y品公司到江蘇某化妝品公司工作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屬于勞動者非因本人原因從原用人單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單位工作,故應(yīng)當(dāng)把原用人單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計算為新用人單位工作年限。
(作者單位:萍鄉(xiāng)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