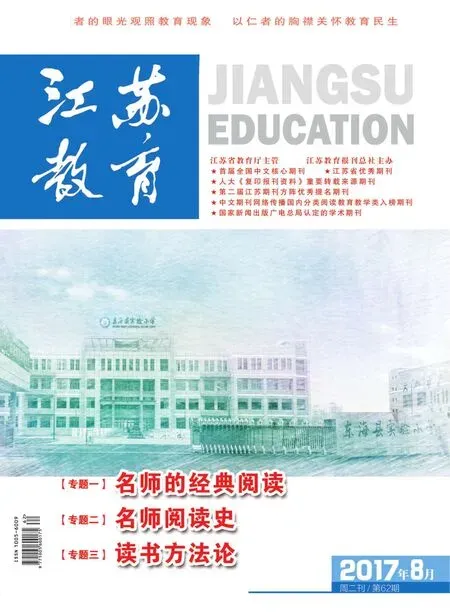青春作伴好讀書
張正耀
青春作伴好讀書
張正耀
對于教師來說,與“讀多少書”相比,“讀什么書”和“怎樣讀書”更為重要。教師要重點讀三大類書:一是哲學、邏輯類,二是文學、藝術類,三是歷史、文化類。
教師;讀什么書;怎么讀書
就某個讀者而言,讀什么書、讀多少書與怎樣讀書,是由個體的興趣、習慣、喜好而定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機構、一個部門、一級組織能夠對此做出嚴格的“規定”,因為,讀書是“私人定制”活動,甚至是個人的某種隱私。
我們提倡讀書,提倡多讀書,并不是為了自吹自擂,盲目吹噓;我們建議讀什么書,也只是限于個人經驗,而非刻板的“教條”與“定規”。讀書是生活的組成,更是生命的需要;是生活的方式,更是生命的形態。社會在發展,教育在變革,教師要想能夠接受和適應新的課題和挑戰,唯有沉下身來,安心讀書,定心教書,潛心育人。現實中有的教師確實不怎么喜愛讀書,這誠然與個人的生活理想、方式有關,但也與他們所處的生活、工作環境有關,與工作時間、強度、壓力有關,還與信息傳播渠道多元化、閱讀方式多樣化有關,畢竟讀書是一件悠閑、雅致、純凈的事情,優雅的活動只有在輕松的生活環境、安靜的心態中才會發生。這些因素,都充分說明了我們開展這一討論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與“讀多少書”相比,“讀什么書”和“怎樣讀書”似乎更為重要。有的教師確實喜歡讀書,也讀了很多書,但囫圇吞棗,食而不化,成了“兩腳書櫥”。這與對書的選擇、也與讀書的方式有很大關系。以我個人的體會,教師要重點讀這樣三大類書。
一是哲學、邏輯類。
眾所周知,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掌握了正確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我們對一切事物和現象的認知就會由謬誤而正確,由模糊而清晰,由膚淺而深刻,由一隅而全面,由低端而提升。哲學如空氣一樣,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存在于我們的生活當中,使我們須臾不能離開。我們生活在學校、社會、家庭當中,一定會對各種事物與現象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特別是對教育教學工作,也一定要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否則就不能擔負教育之責。但是,面對錯綜復雜的教育現象,面對紛繁蕪雜的教學問題,哪一個方面才是我們思考、認知的入口?又如何才能使我們既見局部又見整體,既看到表面又看到實質,既關注當前又立足長遠,既明確重點又兼顧統籌?這就要讀哲學類的書。讀哲學類書籍,可以使我們明白 “教育是什么”“教育從何處來”“教育要到哪里去”等終極性問題,可以使我們對教育的一切認知、經驗和判斷變得系統化、整體化。學校教育中,經常有一些違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違背人的認知規律的現象發生,就是因為對教育缺乏哲學思考,不能全面地而是片面、孤立地看問題。比如一些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無限延長學生學習時間,無節制地組織名目繁多的考試,出臺許多“不人性”的各種刻板的學習規定,就是片面看待“教育質量”的具體表現。有的學校和教師罔顧學生的個性發展,只抓學習質量,不抓或很少顧及學生的素養發展,不能全面發展人的素質,就是世界觀出了大的問題。
與學校教育中人文學科、自然學科所顯示的學科規律相比,哲學所揭示的是事物發展變化最普遍的規律。通過學哲學,我們就能夠掌握教育的一般性規律,既有助于我們對教育教學中特殊規律的認識,更有助于我們從整體、總體上認識和把握教育,理解社會,思考人生。以學科教學為例,有的教師“做題目”“講題目”的水平確實很高,也取得了世俗眼里的“考試成績”,但他給予學生的往往只是“術”而非“道”,是“器”而非“法”,沒有真正從學生未來發展的需要考慮,也沒有從學生自我發展的個性出發,沒有培養起適應未來社會的綜合素質,甚至都沒有能夠幫助和引導學生構建起知識體系,除了重復機械、枯燥無味的那些題目之外,什么痕跡也沒有給學生留下。遺憾的是,這種只會做題目、講題目的“教書匠”,在學校還大有市場,并受到領導肯定、學生歡迎、家長追捧,這真是教育的悲哀,也正是不學哲學、不懂哲學、不會辯證地看問題與處理問題的典型表現。
哲學作為思想方法,當然不會教會我們如何去組織教育活動,怎樣去開展學科教學,甚至怎么才能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它所提供給我們的不是什么具體的技術、手段和方法,而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是我們做好教育教學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礎。同樣的道理,邏輯學給我們帶來思維的科學、縝密、有條理、能深入。有人經常對教育教學中“不懂規律”“不講邏輯”的現象大加撻伐,殊不知,“不懂規律”“不講邏輯”首先是因為不知道“有規律”“有邏輯”,更不知道怎樣才能去 “把握規律”“掌握邏輯”。哲學、邏輯類書籍正可以幫我們解決這一難題,幫助我們抓住教育教學“規律”與“邏輯”的根本。
讀哲學、邏輯書,可以使我們“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課堂看教學”,竟至“跳出題海看知識、看能力、看發展”;讀哲學、邏輯類書,我們的雙眸會更加明亮,方向會更加明確,視野會更加開闊,認識會更加透徹,思考會更加全面,見解會更加深刻。
二是文學、藝術類。
我們所從事的是“人”的教育。“人”的存在,“人”的需求,“人”的發展,無一不要求我們始終做到“目中有人”,要樹立與明確這樣的觀點,要對“人”進行系統而完整的認識與研究,最好也是最為方便的辦法就是讀文學、藝術類書籍。因為,“文學是人學”,對人的豐富性、復雜性、靈性和創造性的全面了解,只有通過文學藝術作品才能實現。在文學藝術家筆下,人既是被說明的對象,又是說明的依據。這啟示我們,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但又是教育的依據,我們的教育活動要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的發展為本,從學生出發,從學生的需要出發;在文學藝術家筆下,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既有支配自然的偉大力量又有被自然支配的渺小和軟弱。這一切,僅靠我們對學生、對家長的直觀認識、直接了解是無法做到的。
文學藝術作品告訴我們,父母是人的創造主體,這種創造不僅指物質的創造,也指精神的撫育;教師是教育主體,承擔著教育的重任;學生是接受教育的主體,但也不是機械地接受,而是能動地反映。這三個主體的關系,不是并列的,更不是相互抵觸的,而是有機的交融,共同作用于學生主體。由此啟發我們,所謂學生的主體性、主體地位、作用,既包括他們的主觀需求,也包括他們通過學習和實踐活動對生活、社會、人生的理解和把握、發現與建構。我們必須關注活生生的“人”,學習中的“人”,發展、成長中的年輕生命。這是教育中最具有價值的要素,也是教育的根本點、出發點和歸宿點。
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教育教學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恰恰就是“人”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我們更多的時候是關注考試,不關注學習;關注“答案”,不關注思維過程;關注成績,不關注成長;關注高考、中考,不關注學科素養的培養與提高。我們不是把人當成人,而是把人降低為物,降低為工具和傀儡,這種物化的教育只會造成人的靈魂枯死。在這樣的教育生態下,人完全喪失了主體性,喪失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東西。我們的教學,要讓學生認識和發現大千世界的規律,要讓學生學會熱愛和贊美,要讓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心愿去選擇自己樂意的生活、學習方式和目標,并且能夠支配這一切。學生應該能夠在屬于自己的那一塊領地中隨心所欲地立標定界,讓他始終處于“世界的中央”,可以超越束縛,成為物質和精神的創造者,并親手塑造自己最終的形象。但可悲的是,我們的教育卻正在無情地扼殺學生身上的創造力,使他們無法感知鮮活的生活,成為受物化教育隨意支配的可憐的生物。這正是遠離文學、藝術的必然結果。
為什么有的教師教育教學行為簡單粗暴、缺乏藝術?不是他們不明白教育教學中的有關道理,而是他們的性格、稟賦中缺乏文學藝術乃至美育的全面熏陶。除了昂揚,沒有低迴;除了激越,沒有感傷;除了突進,沒有緩沖;除了直道,沒有曲徑;除了執行,沒有協商;除了沖突,沒有和解。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明白,教師作為非常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存在,同樣應有“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氣質、涵養、風度、神采,這些除了一般性教育所能給予之外,就得依靠文學藝術作品的濡染、沁入。常聽說一些極端的例子,有的學校圖書館、閱覽室長期不對學生開放,學生成天被關在教室里上課、做作業;有的教師不但自己不讀文學藝術作品,竟然還不允許學生讀文學藝術作品,無情剝奪學生接近文學藝術的機會、熱愛文學藝術、享受美的熏陶的權利,實在不可理喻。
教育,必須貼地而行,但更要飛天而舞。正是文學、藝術作品,為我們精神、靈魂的遨游插上了隱形的翅膀,使我們的教育教學有了詩的理想;正是文學、藝術作品,使我們的思維觸角伸向了無窮的遠方,使我們的教育教學充滿了溫情;也正是文學、藝術作品,使我們的教育教學充滿了美的力量。教師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廣泛、深入閱讀,可以使教育內容更形象、更感性、更多元、更有趣、更豐富、更美好。
三是歷史、文化類。
從某種意義看,歷史是現實的樣本,現實是歷史的重現。人類前行的每一個腳步,無一不昭示著探索、奮斗、艱辛、進步。讓歷史告訴未來,就是要未來的人從歷史中吸取營養,領受教訓,如此寶貴的財富,我們何不充分享用呢?對歷史的認知,能夠折射出對現實的態度。以教育史為例,我國古代教育一直忽視“人”的存在,“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人沒有自我發展的權利,也沒有自我發展的追求與空間,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成了某種政治符號的附庸,成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奴隸,人始終生活在別人的評價中,生活在某種思想意識的規范里,而沒有自我的存在方式,所以專制社會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社會,而是精神的動物世界。這種依附性,完全無視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不考慮人的獨立性、能動性,人的價值被蔑視,被踐踏,人的觀念始終沒有形成。直到近代,一些進步思想家如王夫之、戴震等才發出了人的呼喚,但他們的呼聲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因為他們無法喚醒一個裝睡或被嚴重催眠的人。晚至“五四”時代,以魯迅等人為代表,在思想文化上才形成一股肯定人的價值的思想潮流。明白了這段歷史,我們才能認識到,現在所提倡的尊重學生主體,發揮學生個性特長,讓學生全面發展、自主發展、個性發展的理念,是對教育歷史的反思與檢討、批判與回應,也是對教育現實的警醒與期盼,更是對教育未來的呼喚與向往。教育與其他任何一種社會活動一樣,正是在對歷史的不斷繼承中發展、豐富、創造起來的。
閱讀歷史、文化著作,可以讓我們回歸常識,對歷史的不尊重,就是常識缺乏的表現。歷史文化常識告訴我們,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人的發展需求也是多方面的,那我們為什么只去抓智力教育呢?人除了社會性,還有獨立性,還有差異性,但為什么我們要用同一個標準去衡量每一個學生呢?我們的課程建設、課堂教學、實踐活動,為什么不能更加豐富一些,更加注重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探究性、創造性的調動?歷史文化常識告訴我們,“讀史使人明智”,因為歷史所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個鮮活的事實,它們或正面,或反面,或多面,或立體,全面地展現了生活、社會的面貌,讓我們“知興替,明得失”,它們是我們引領學生認知世界、社會、生活的最寶貴資源,我們為什么不能獲取其中的經驗、吸取個中的教訓呢?擁有正確的歷史觀,在學生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非凡的意義。歷史文化常識還告訴我們,歷史是用來回望的,而不是用來批判和改造的,我們許多“反歷史”的認識與行為正是由于這一點。我們對歷史文化的態度往往是“批判”,我們引導學生批判古人的“愚忠愚孝”,批判古人的科學常識錯誤,批判古人的思想落后、愚昧、局限性,殊不知,那就是歷史本身。當我們和學生一起揮舞“否定”的大棒時,歷史虛無的陰影就會籠罩著我們,我們雙眼迷糊的結果是,再也看不到歷史的漸進過程,再也不能感受歷史的豐富與多樣,學生就不能建構起科學的歷史文化觀,也就不會去思考未來的自己在歷史的舞臺上準備扮演怎樣的角色,演繹怎樣的活劇。我們見到的就只能是片面的歷史,是經過“過濾”的歷史,甚至是歪曲、戲說的歷史。閱讀歷史、文化著作,毫無疑問的還有一點,對歷史文化深層結構的了解與把握,可以幫助我們進行條分縷析,形成屬于自己的判斷,豐厚自己的思想認識。
科學的教育思想、理念、觀念從何而來?從哲學、邏輯學中來,從文學、藝術中來,從歷史、文化中來。一切教育理論只不過是對它們的闡釋與推演,是它們的另一種生活、生長、生命形態,是它們的精細、精微、精確化的獨特表述。這也是我沒有建議教師們去讀教育理論書籍的真正原因。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這些話對不怎么讀書或不喜愛讀書的教師而言,豈不是白說了?所以,當務之急還是應該把我所建議的這三大類書先讀起來,讓讀書不只停留于號召與提倡上,而成為堅實的追求、扎實的行動,青春作伴好讀書,從而使我們的交流真正有意義,有價值。
G40
B
】1005-6009(2017)62-0066-03
張正耀,江蘇省興化市教育局(江蘇興化,225700)教學研究室副主任,正高級教師,江蘇省特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