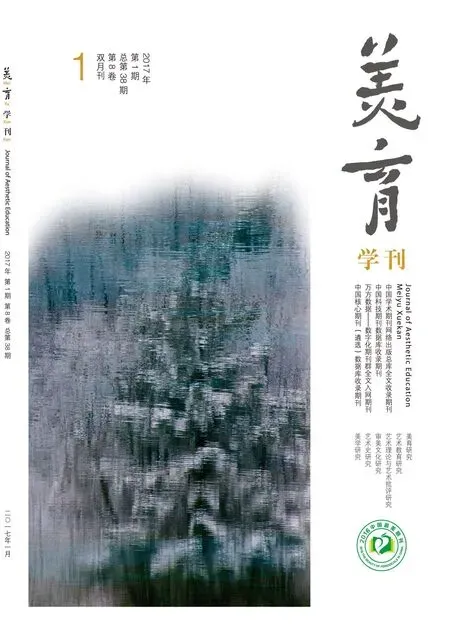古今之爭與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美學之衰落
張 穎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北京 100029)
古今之爭與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美學之衰落
張 穎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北京 100029)
在17世紀末的法國,受意大利知識界的影響,幾乎所有的飽學之士都卷入了一場規模盛大的論爭。這場論爭史稱“古今之爭”(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隨著分裂的加深和公開化,王家學院出現兩個陣營:崇古派與厚今派。這場文人戰爭牽涉諸多復雜問題,甚至卷入私人恩怨。因此,后世對之歷來褒貶不一,甚至對其研究價值亦無定論。現通過追溯古今之爭法國戰場(尤其是第一階段)的始末,闡述兩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觀點,嘗試解釋古典主義美學之衰落與這場文人戰爭的關聯,并認為它是17、18世紀交替時期法國古典主義文化衰敗的表征之一。
古今之爭;古典主義;美學;法國
在17世紀至18世紀,圍繞著古今何者更具優越性的問題,歐洲知識分子發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史稱“古今之爭”(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它最先爆發于17世紀初的意大利,主要發生在法國和英國,在其他歐洲國家也有回響。這場文人間的戰爭聲勢浩大,在17世紀末達到高潮,掀動了整個歐洲知識界。在法國,當時飽學之士幾乎都被卷入古今之爭,王家學院隨之分裂為兩個陣營:崇古派(les anciens)與厚今派(les modernes)。參與者寫詩賦文、唇槍舌劍,蔚為一時之盛。一種觀點認為,兩派都是古典主義者,只不過前者“自覺是家道中落的后嗣”,后者“自覺是青出于藍的嫡派”,從而尖銳對立;[1]另一種觀點認為,崇今派已經分裂出古典陣營,而屬于現代派,是啟蒙者的前身。至少就古典主義美學的特征——規范、嚴整、簡練、明晰、崇尚理性[2]——而言,厚今派并未有所違背,他們其實僅只反對古典題材和古代作家的獨尊地位,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古今之爭是古典主義的內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關于古今之爭的歷史,自古至今有很多種寫法。其中,伊波利特·希格(Hippolyte Rigault)的《古今之爭的歷史》(Histoiredelaquerelledesanciensetdesmodernes)*Cf. 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1856.于19世紀中葉面世。該書以史為主,以論為輔,其史料功夫細致扎實,為這段歷史的研究留下很好的文獻參考。希格把古今之爭分為兩個主戰場(英法)、三個階段,亦被后來不少研究者沿用。本文以該書提供的材料及評價為準,梳理古今之爭法國戰事的主要情況,闡述兩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觀點,從而嘗試解釋古典主義美學之衰落與這場文人戰爭的關聯。
一、法國戰況始末
根據希格的記載,古今之爭最初在意大利知識界爆發。1620年,意大利詩人、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塔索尼(Alessandro Tassoni,1565—1635)的《雜見》(Penséesdiverses)面世,引起軒然大波。塔索尼在書中做了一番古今對比,得出的結論是:今人在各個領域皆勝過古人,這些領域不單包括科學、工業、農業,還包括文學、藝術、辯才、詩歌和繪畫。[1]75據迪拉博斯基(Tiraboschi)說,該書“惹怒了當時的大部分作家,他們發現書中對荷馬的詩句與亞里士多德的看法進行了激烈的貶責,同時對文學的效用做出明確的質疑,上述種種令他們大為光火,仿佛塔索尼是在向所有學科和全體學者宣戰”[1]72。文人戰爭拉開帷幕。
很快,塔索尼的著作被讓·博杜安(Jean Baudoin,1590—1650)譯介到法國。這位譯者于1634年入選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ncaise),成為第一批“四十把交椅”之一。塔索尼作品的譯介,點燃了蟄伏在法國知識界的、與意大利類似的矛盾。1635年,博杜安的法蘭西學院同僚、黎世留手下的五人(悲劇)創作班子成員布瓦洛貝爾(Boisrobert)在法蘭西學院大會發表演講,抨擊古典文學,攻擊荷馬。這是法國厚今派第一次發動攻勢。
不過,在希格看來,首戰的爆發并非出自一個慧眼獨具、洞察先機的偉大心靈,而只是一次偶發事件,一場蝴蝶效應。布瓦洛貝爾的觀點并不出自敏銳而深刻的哲學思想,他只不過意在提出一個“簡單的趣味問題”,卻無意間點燃了一場將持續至少上百年的戰爭。[1]76-77
第二位出場的厚今派成員是德馬雷·德·圣-索爾蘭(Desmarets de Saint-Sorlin,1595—1676),他也是黎世留五人創作班子成員。這是一位中年皈依的堅定的天主教徒,曾建言國王出動一支十四萬人軍隊根除異端。與布瓦洛貝爾不同,他之所以反對因襲模仿古代詩歌,主要出自他的宗教狂熱。古代詩歌是異教詩歌,而今人應當寫作基督教詩歌。在他看來,異教詩人無論具有多高的天資,都無法像基督徒詩人那樣偉大,因為魔鬼棲居在他們身上并喚起他們的錯誤,而居住在基督徒詩人體內的卻是圣靈,圣靈將他們帶向真理[1]107。他本人踐行了這個觀念,創作出一些基督教主題詩歌,如《克洛維斯》(Cloris,1657)、《抹大拉的瑪麗亞》(Marie-Magdeleine,1669)。
崇古派領袖布瓦洛于1674年發表詩體理論著作《詩的藝術》(Artpoetique),在該書第三章里針鋒相對地批評了德馬雷。他堅決維護神話作為詩歌的主要題材。幾年后,高乃依在一場事件中發表了對崇古派有利的意見。他力主神話入詩,除了像布瓦洛那樣指出神話的審美價值,還相當機智地運用自己的創作經驗進行說理。他提出,自己在寫作詩歌時并不把那些異教神奉若神靈,而是根據異教徒的信仰來描寫他們的言語;對于那些不以基督教真理為基礎的錯誤的詩歌神性,他主張大可不必嚴厲驅逐,因為它們可以用在不嚴肅的詩歌上,比方說愛情抑或其他快事。[1]99
在古今派交戰的這一回合里,局面激烈而緊張。應該說,厚今派的德馬雷并沒有太占優勢,也沒有掀起太大風浪。1675年,德馬雷自知時日無多,在一首詩里呼喚道:“佩羅,去捍衛那正在呼喚你的法蘭西吧;/跟我一道打敗這群逆賊,/這伙敵人虛弱不堪又死不悔改,/寧肯選擇拉丁作品也不要我們的歌唱……”[1]113
德馬雷把佩羅當成自己的繼承人,而在佩羅公開加入厚今派陣營之前,另有兩位學者站出來發聲。首先一位是博烏爾斯神父(Dominique Bouhours,1628—1702)。他思維細膩而敏捷,善發新見。在其主要作品《阿里斯特與歐也尼的談話》(Entretiensd′Aristeetd′Eugene,1671)里,博烏爾斯神父為厚今派的其他人貢獻了新的思路。
表面看來,阿里斯特和歐也尼的對談彬彬有禮,不溫不火,并不像其他厚今派那樣充滿攻擊性和侵略感。不過,他們的談吐中雖盡力避免進行古今對比,但最終仍難掩今勝于古的優越之處。歐也尼說道:“希臘人和羅馬人如此珍視自己國家的榮耀,以至于人們完全沒法跟他們辯論,不然就會被翻臉,就會跟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才華的人們結下梁子。對我而言,由于我并不喜歡為自己樹敵,所以寧愿向希臘人和羅馬人讓步,并真心實意地承認,跟古希臘和古意大利的價值比起來,所有國家在英雄方面都是貧瘠的。”這段話看似恭維古人,但若細細品味,說它是對崇古派的影射之詞,說他采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恐怕也不牽強。阿里斯特也不否認希臘羅馬的精神之美,但不失時機地補充了“當今的精神之美”,它們存在于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英格蘭人以及莫斯科人那里;到處都有才識,而這其中,唯有法蘭西才具備最完美的才識(bel esprit),“這要么出于氣候方面,要么是我們的秉性對此有所推助”。他還說,一個國家的粗野或機敏,可能是此一時彼一時。“上個世紀對意大利來說是教義和禮貌的世紀……本世紀對法國而言,有如上個世紀之于意大利;人們說,世界上的全部才智和全部科學現如今皆備于我們,還說,跟法國人比起來,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是野蠻人……”[1]118-120這仿佛是在說,文明的接力棒從希臘、羅馬,到意大利,如今傳到了法國。話語間頗有些當仁不讓的意思,雖未抑古而揚今,卻著實是在頌今。
再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豐特奈爾。據說他本人“相當機智、非常有野心同時卻又極端冷漠”[1]121-122。他之所以站到厚今派陣營里,可能部分地出于年輕人出人頭地的愿望。他宣稱,在趣味方面,一切皆真,一切皆假。[1]124豐特奈爾的參戰作品主要是《死人對話新篇》(NouveauxdialoguesdesMorts,1683)。這篇對話讓蘇格拉底、蒙田等不同時代的名人匯聚一堂,擬設了他們的言論,并把作者自己的看法隱藏其中,具有強烈的諷喻色彩。比如這段對話,Erasistrate說:“我承認現代人是比我們更高明的物理學家,他們甚至認識自然,然而他們不是比我們更高明的醫生……我們看到這里天天都出現更多的死人。”Harvey回答道:“對人認識得更多,卻治愈得更差,這真是咄咄怪事。既然如此為何要耗費時間去完善人體科學呢?棄之一旁豈非更好。”[1]126這段話還觸及古今之爭的一個重要話題:科學知識的進步問題。
豐特奈爾的《死人對話新篇》是佩羅的《路易大帝的世紀》(LesiècledeLouisleGrand)的前奏。[1]1291674年,由于夏爾·佩羅的兄長皮埃爾·佩羅在攻擊古希臘詩歌時犯了兩點錯誤,被拉辛抓住后大做文章:“奉勸那些先生(按:指厚今派)不要再如此輕易地在古人作品上做決定。既然他們處心積慮要譴責歐里庇得斯,但像他那樣的人至少經得起他們的檢驗。”[1]133其實,就總體而言,崇今派陣營的古典學水平遠不及以淵博著稱的崇古派,于是在這場復雜而多反復的戰爭里,古典知識上的硬傷屢屢成為崇今派受嘲弄和批評的契機。
古今之爭的標志性事件發生在1687年1月27日。當天,法蘭西學院院士齊聚一堂,慶祝國王路易十四身體康復。崇古派領袖布瓦洛在場。聚會中程,身為國王營造總管的佩羅起身宣讀了一首詩,即《路易大帝的世紀》。它的開頭一段很有名:
美好的古代總是令人肅然起敬,
但我卻從來不相信它值得崇拜。
我看古人時并不屈膝拜倒:
他們確實偉大,但同我們一樣是人;
不必擔心有失公允,
路易的世紀足堪媲美美好的奧古斯都世紀。[1]141
這段詩常被引用。它詩意淺白,反倒具有直接的力量。為路易十四唱贊歌,本是王家學術機構的職責所在。盡管如此,在這樣的公開、重大而嚴肅的場合,借頌今為由而斷然否棄對古人的崇拜,是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古今交火,大多發生在書面上,或者屬于暗地里的小動作。這不啻為咄咄逼人的宣戰。
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在佩羅所誦讀的詩句里,列舉了不少可與古人成就相媲美的今人,獨不見布瓦洛的名字。這一公然的舉動令盛名久負的布瓦洛相當不舒服。更加令布瓦洛憤怒的是,在他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古人作品,被佩羅拿來與今人平起平坐。后來,佩羅在自己的回憶錄里不無暗爽地記載道,在自己發表這場演講期間,坐在扶手椅中的布瓦洛焦躁地晃來晃去,顯得極不耐煩、如坐針氈。布瓦洛的崇古派戰友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630—1721)回憶道,布瓦洛在演講行將結束前憤然起身離席,叫嚷著“這場演講實乃學院之恥”[1]146。不過,整個演講過程并無其他院士打斷或表示異議。更有甚者,在演講結束時,聽眾全體報以掌聲。院士們的反應加重了布瓦洛的不安:局面似乎在倒向厚今派。進展到這個階段,事情變得相當戲劇化。
布瓦洛盡管耿耿于懷,卻一直沒有做出公開正式的回應,只在幾封私人信件里說了些不怎么理智的氣話。*可能是布瓦洛的諷刺詩傷人太多,也可能出于妒忌或文人相輕等種種原因,布瓦洛在法蘭西學院里擁護者并不多。他在致Brossette的信中曾說道,學院里只有“兩三位”有良好趣味的院士。其實,學院里的崇古派除了布瓦洛和拉辛,至少還有波絮埃、費內隆、弗雷謝爾、于埃等等。布瓦洛口出此言,恐怕是氣昏了頭,或者有所夸張(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152)。不過,學院里厚今派的勢力于此可見一斑。當然,法蘭西學院的分裂已是昭彰。1687年,豐特奈爾出版《占卜史》,指出古代異教神使乃是基督教僧侶設置的騙局,抨擊了輕信古典的愚昧心靈,此書不啻為對崇古派的又一次打擊。*參見J. S. 布朗伯利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6卷 大不列顛和俄國的崛起(1688—172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組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23頁。1691年5月15日,豐特奈爾入選學院。這一事件無疑為風頭正勁的厚今派又添了一把柴。曾被布瓦洛嘲弄過的拉沃神父(abbe Lavau),在談話中將豐特奈爾與西塞羅并提,這讓崇古派相當不滿。又過去兩年,崇古派的一位重要成員入選學院,他就是以寫作《品格論》(Caractere)聞名的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ere,1645—1696)。拉布呂耶爾是布瓦洛的崇拜者,也迅速加入了辯論。
崇古派是一群信而好古的學問家,精通古希臘語、拉丁語,其中不少人是古代文獻的翻譯者,比如布瓦洛(翻譯朗吉努斯)、隆熱皮埃爾(Longepierre)、達西耶(Dacier)夫婦(翻譯賀拉斯)等。面對厚今派咄咄逼人的架勢,他們一開始并無實質性的還擊,所做的往往不外乎諷刺(梅納日[Menage])或斥罵(布瓦洛、達西耶)而已。在佩羅公開宣讀《路易大帝的世紀》后,有人匿名寫了一首拉丁文諷刺詩(據說出自梅納日之手,但他本人否認這一說法)。詩中寫道:
親愛的薩貝勒斯,你的好友佩羅
做了一首詩,取名為《世紀》,
他在里面信誓旦旦、大放厥詞。
說什么勒布倫比阿佩利斯懂得多,
說什么我們的哇哇怪叫比西塞羅說得妙,
說什么我們的拙劣詩人比瑪戎還強。
多么暗淡而無腦的《世紀》啊![1]210
佩羅把這首詩譯成法文,禮貌而強硬地指出這種辱罵“超出了文人之間所允許的自由”[1]212。他早就不無得意地預言過這個局面:“我們在愉快的爭論里樂此不疲/這爭論沒完沒了地進行下去:/我們將一直擺出各種理由,/他們將一直說著辱罵之詞。”[1]193當然事實并非完全如此,比如崇古派里的隆熱皮埃爾男爵就是例外。在他的《談談古人》(Discourssurlesanciens)里言辭是禮貌有加的。然而,除了無節制地贊美古人完美無瑕,他并未貢獻出有益的論據。在崇古派占下風、局面僵持的時刻,出現了一位引人注目的調停者德·卡利耶爾(de Callière)。他的《古今之戰的詩史》(Histoirepoetiquedelaguerredesanciensetdesmodernes,1688)*Cf. Francois de Callieres, Histoire poetique de la guerre, nouvelement declaree entre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 Geneve: Slatkine reprints,1971.以佩羅《路易大帝的世紀》演講后學院分裂為對立的兩派為由頭,由真入假,杜撰了真假一爐、古今一體的精彩故事:信息女神在巴納斯山播下警告,命令那些居住在此圣山上的最負盛名的古人和今人像法蘭西學院那樣分成兩大陣營作戰。荷馬任希臘詩歌統帥,維吉爾為拉丁詩歌統帥,狄摩西尼率領希臘演說家,西塞羅統領拉丁演說家;在今人里,統領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文壇的將領分別是高乃依、塔索、塞萬提斯。該書風趣活潑,引人入勝,廣受公眾的歡迎。其寫法后來被斯威夫特借鑒,于是有了英國戰場的標志性成果《書籍之戰》*中譯本可參見喬納森·斯威夫特《書籍之戰》,見《圖書館里的古今之戰》,李春長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年,第195-220頁。文中對崇今派的諷刺力度,幾乎讓法國崇古派里的任何一位難以望其項背。比如“作者序”里的這段話:“有種頭腦,只有一層浮沫可供撇去。有這種大腦的人需慎重收集起這種浮沫,并小心經營這點積蓄,但首先要謹防它們受到更智慧的人的攻擊,因為那會令它們全部飛散,主人卻找不來新的補給。無知的聰明是一種奶油,一夜之間膨脹而起,一只靈巧的手即可以把它攪成泡沫;然而,一旦撇去浮沫,下面露出來的只配丟去喂豬。”見上書第196頁。。故事的結尾表達了平息戰爭的愿望:阿波羅下令停止互罵,以人人封賞的方式締造了新的和平。卡利耶爾的著作受到古今兩派(除佩羅外)的一致歡迎,使得他本人在發表次年即獲得法蘭西學院的席位。這是崇古派第一次以活潑機敏的方式得到辯護。[1]213-215
崇古派的更加理性的意見發表在于埃與佩羅的通信里。佩羅曾把自己的《古今對觀》寄給于埃,請他做出坦率而無偏見的評斷。于埃回了一封長信,在必要的恭維后,毫不客氣地一一指摘書中的錯誤。比如,他認為佩羅是由于錯解了《奧德賽》里詩句的意思,才會指責荷馬把基克拉迪群島放到熱帶,于是尖刻地嘲笑并批評道:“這就好像是指責夏普蘭先生搞不清布爾日或波爾多的位置……荷馬的用語根本不是您所說的意思……”[1]218-219佩羅沒有回信。可以想象,知識硬傷令他羞赧。
法蘭西學院院士們的激烈爭執,在法國知識階層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知識人全體發生了自上而下的分裂。有些流亡海外的法國博學之士發表了意見。不少報刊也卷入進來。當時參與古今之爭的法國報刊主要有《學人雜志》(Journaldessavant)、《風流信使》(Mercuregalant)、《特雷烏回憶錄》(MemoiresdeTrevoux)等。《學人雜志》曾擁護崇古派,后保持中立。《風流信使》則與豐特奈爾、佩羅交好。耶穌會掌控下的《特雷烏回憶錄》與布瓦洛勢同水火。*關于古今之爭期間報刊上討論的情況,可參見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p. 223-233。總體上講,社會輿論傾向于同情和支持厚今派。另外,知識女性也大多站在厚今派一邊,唯有少數幾位女性例外,如賽維涅夫人、孔蒂公主等等。至于原因,受教育程度可能是重要方面。就像崇古派人士時常憤憤不平的說辭那樣,為厚今派鼓掌助威的觀眾往往缺乏古代知識,未加深究便貿然藐視古人和古典學。*參見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p. 240-241。希格還補充說,女性是天生的厚今派,因為她們既不通拉丁文亦不通希臘文,即便在女性沙龍地位較高的17世紀里,她們一般是通過閱讀古代作品的節譯本來了解古典學的。Cf. 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242.
崇古派向來不善于處理輿論。面對女性們的不支持,布瓦洛的反應乃是寫出第十首諷刺詩(Satire X)加以嘲弄。此舉大大加重了來自女性讀者的敵意。在有權勢的女性們的干預下,法蘭西學院院士的新交椅并未如布瓦洛所愿地留給德·米摩爾(de Mimeure),而是被推給了德·圣-奧萊爾(de Saint-Aulaire)。這個事件令布瓦洛氣惱不已。[1]245善于審時度勢的佩羅利用了這一戲劇性事件,在1694年發表了《為女人一辯》(Apologiedesfemmes),不失時機地揶揄布瓦洛:“難道你不知道女人們的禮貌生而伴有誠摯嗎?”這巧妙而狠辣的一擊,為佩羅的崇古派拉攏了更多的擁護者。[1]248
正是在同一年,正當崇古派的名聲跌至谷底的時候,布瓦洛終于醒悟,以他所擅長的方式發表了《有關朗吉努斯的反思》(RéflexionscritiquessurLongin,1694),不理情面地指陳佩羅曾經做出的知識錯誤。他認為造成誤判的原因是佩羅不通古文字,只能夠讀古代作品的譯本,而譯本難免有訛誤。
事態進展到難以收拾的局面時,佩羅和布瓦洛的共同朋友們開始出面調停。佩羅把自己的《為女人一辯》寄給了已屆八十高齡的大阿爾諾。這位宗教領袖彼時正在布魯塞爾流亡,但仍密切關注著法國文壇局勢。他在回信中指出,布瓦洛的諷刺并無過錯,因為它既未攻擊婚姻,亦未侮辱女性尊嚴,非但如此,那些段落反是優美的諷刺詩篇;更重要的是,諷刺詩作為一種文體,是文學性的,因此在“真”的問題上擁有某些豁免權,如果我們像對待哲學論文那樣對待它就是不合適的。大阿爾諾表達了希望二人和解的愿望。[1]2581694年8月4日,也就是大阿爾諾去世前四天,布瓦洛和佩羅握手言和,論戰至此告一段落。然而,它只是某些領域獲得了暫時的平息。戰火很快燒到英國,又在下個世紀初的法國再掀風浪:18世紀初,圍繞著《伊利亞特》譯本是否可以改寫為散文體的問題,達西耶夫人和劇作家烏達爾筆戰幾個回合,崇古派和厚今派又各自捍衛觀點,這次紛爭相對第一次的聲勢較小,最終在費內隆的干預下止息。
二、主要參戰人物及其論題
在第一部分里,我們按照古今之爭法國戰場(第一階段)的主線,簡述了這場事件的爆發、進展和(暫時)收尾。以下我們將圍繞該事件的三位主要人物,更加詳細地討論其論題和論證方法。
(一)德馬雷
德馬雷是第一位有意識、有系統地向崇古派發起挑戰的法國學者。他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為后來的厚今派提供了思路。
第一,基督教詩歌的優越性。1673年,他的詩歌《克洛維斯》再版,他增寫了一篇開場白,強調唯有基督教主題適用于英雄詩歌。他態度堅決地說:“某些作者試圖掩蓋自己的狡猾,狡辯道,正是出于對宗教的尊重,他們才不愿在詩歌中處理宗教,還說那種膽敢將虛構混同于宗教的純粹真實的做法是相當魯莽的;然而,他們妄稱尊重宗教,實為蔑視和憎恨宗教,他們難以自禁地在自己的詩歌和不信教的言語中流露出這一點。當人愛一樣東西時,必不會保持這樣的沉默;而是會帶著與這樣東西相配的重視和尊敬去談論它。”[1]97
德馬雷代表著法國崇今派中因反異教而反對古代文化的一類觀點。這類觀點與基督教的反異教傳統緊密關聯,也與當時錯綜復雜的宗教局面有關系。在同一歷史時期,基督教教會同樣堅決反對神話題材戲劇,也可歸入這個傳統。
那么,德馬雷對于非基督教題材的態度果真是寸步不讓的嗎?希格發現,其實德馬雷的立場原本留有余地,他只不過提倡基督教題材在英雄史詩里享有特權,高于異教史詩、遣興詩和愛情詩而已。后來,隨著論爭的延伸,他的觀念才推向了極端。[1]99
第二,法語的高貴性。法國人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至少可以上溯到16世紀以七星詩社為代表的民族語言運動。經過上百年的雅化過程,法語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化,并在文學、藝術、科學語言里得到應用,但并未完全取代拉丁文的至高地位。1680年,法蘭西學院內部發生了爭執,這場爭執被法語捍衛者稱作“法語聲譽”問題或“法語的無上卓越”問題[1]101。問題的焦點是:凱旋門上的銘文應該沿用拉丁文還是改用法文。大部分院士主張改用法文,比如財政大臣柯爾貝爾和夏爾·佩羅。另一派院士則不主張放棄拉丁文這種“擁有凱撒和奧古斯都之不朽性的語言”[1]102。佩羅認為,拉丁詩歌已被遺棄在深夜里,聲望和體面蕩然無存。對方一派則歌頌拉丁繆斯,用拉丁語詩句說道:人稱龍沙為“法語之父”,而他那些粗野的喧嘩刺痛了我們那敏感的耳朵;巴黎對馬萊伯吝于贊美……[1]103在布瓦洛等人的力爭下,這場爭執的結局是崇古派取得了勝利。
早在這場爭執發生的十年前,即1670年,德馬雷即發表了《論判斷希臘語、拉丁語和法語詩人》(Traitépourjugerlespoetesgrecs,latinsetfrancais),除了旗幟鮮明地主張今人詩歌高于古代詩歌外,還觸及古今之爭的另一個話題:語言問題,具體而言是法語的地位問題。因此可以說,他預見到了語言問題將是古今爭論的焦點。按德馬雷的看法,今天的法語是活的語言,它直接感染今人的心靈,由此產生出種種優點;古人的語言已經無可救藥地死去,唯留造作的虛浮。他說:“我們說著一種語言,比起那個從墳墓里拽出來的悲戚的拉丁語,它更加高貴、更加優美。我們不靠諸神,不靠變形,也不靠那些著名的作品,而往往是通過嶄新的事物來感染人們的心靈”,“龍沙只有在模仿那些古代的浮夸時,才會敗壞他那高雅的天資”,“馬萊伯的藝術教會我們優雅地歌唱,而不假裝出博學者的放誕……”在德馬雷看來,維吉爾的詩歌是貧瘠的,奧維德雖有才智卻欠缺精致[1]108-109。就其豐富、靈活、和諧而言,法語遠遠高出拉丁語和希臘語。[1]104
第三,進步觀。德馬雷的進步觀受培根和笛卡爾派思想家們的影響:雖說古代值得尊敬,但卻比不上后來的時代那樣幸福、博學、豐富、豪華,“那才是真正完熟的老境”。它就像世界之秋,擁有了豐富的果實和收獲能夠判斷和利用所有發明創造、經驗與錯誤;而古代呢,只不過是年輕而質樸的時代,就像世紀之春,只開出一些花朵。誰愿意那世界之春同我們的秋天做對照呢?那就好像是愿意把人的初季媲美于我們國王的奢華花園。[1]105-106他的基本論據是,自然乃是上帝的作品,因而是完美的;文學、藝術與科學是人的作品,所以需要一個走向完美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從不完美向更加完美的進步:“自然在任何時間都生產完美的作品:在任何時間都存在著美的身體、美的樹木、美的花朵。海洋,河流,星辰的出現與隱沒,自創世以來就同樣的美;但人的作品就另當別論了:它們一開始是不完美的,一點一點臻于完美。上帝的作品從創世以來就是完美的,而人的發明創造則不斷被糾正,根據上帝賦予他們的天賦,越往后進行糾正的人就越幸運、越完美”[1]106,“詩歌是人的一項發明,自然不曾為之提供摹本。人必須發明一些方式,把字詞以某種尺度排列成詩句,然后根據或簡單或莊重的主題做出多種多樣的詩歌,作出英雄詩歌以再現人們的偉大事跡。”[1]107這種將作者與作品分而論之的方式,其實對于證明“今勝古”而言十分便捷,在另一方面也頗合今天的世界在環境美學上的“自然全美”觀念。
第四,攻擊荷馬。法國厚今派的一個主要策略,是攻擊西方“詩歌之父”荷馬。這個慣例是由德馬雷開創的。希格說,德馬雷“猜中了現代戰略的主要原則:在侵略戰爭中,必須迅速直搗都城。在對古代的攻擊里,他給后繼者樹立了榜樣:直奔《伊利亞特》,它是整個古代的要塞和要沖”[1]109。
綜上所述,德馬雷提出了不少頗具啟發性的論點,它們在后來的辯論中被更多的人展開和深化。作為總結評價,希格認為他雖然“模糊地預見到自然力的永恒性這一觀念”,“預感到基督教文學的豐沃性,向最廣泛的崇古派下了戰書”,因而在當時稱得上“是厚今一派的真正關鍵的人物”,然而,“他缺少分寸,不知輕重,雖有些最天才、最正確的見解,卻因條理不清而有所損害,又因傲慢自大而鬧了笑話”,加之“他沒什么學識,幾乎對藝術陌生,從而無法把自己的種種觀念普遍化,僅把觀點局限在詩歌,尤其是英雄詩歌上”。正是出于上述原因,盡管他早發先聲,卻往往不被視作厚今派的第一人——人們把這項榮譽給了佩羅。[1]112
(二)佩羅
佩羅在《路易大帝的世紀》里,用自然力之永恒性挑戰崇古派的歷史衰微觀:
在這個廣袤宇宙的未可測知的圍墻里,
上千的新世界已經被發現,
還有新的太陽,當夜幕降臨時,
還有眾多星辰[1]142……
……
塑造心靈,有如塑造身體,
自然在任何時代做著同樣的努力。
它的存在永恒不變,
而它用于制造一切的這種自如之力
并不會干涸竭盡。
今天的我們所看見的當日星辰,
絕非環繞著更加璀璨的光芒;
春天里的紫紅玫瑰,
絕非多加了一層鮮艷的肉粉。
我們苗圃里的百合與茉莉
帶有耀眼的釉色,
白色的光芒并不遜于以往;
溫柔的夜鶯曾經用它的新曲
令我們的祖先迷醉,
而在黃金世紀里,
夜鶯喚醒在我們的樹林里沉睡的回聲,
兩種聲音乃是同樣的悅耳動聽。
無限的力量用同一只手
在任何時代制造出類似的天才。[1]143-144
《路易大帝的世紀》是一份宣言。他的說理著作是1797年出齊的洋洋四卷本《古今對觀》(Parallèlesdesanciensetdesmodernes)。這套書采用對話體,從科學、醫學、哲學、音樂、文學、辯術等各個方面比較了古今成就。書中既充滿風趣的機智、尖銳的意見,也不乏偏執的成見,以及輕率的話語。希格評價它“精神自由、出人意表、敢于冒險”,認為里面的辯論不僅屬于夏爾·佩羅,也來自德馬雷、豐特奈爾、皮埃爾·佩羅的觀念,因而可以代表厚今派的主要思想。[1]206
在佩羅的論證里,有三條論據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個論據基于對人類理性的信心。佩羅相信,要想判斷所有的文學問題,只要擁有自然的趣味、通常的教育、心靈的文雅就足夠了,而并不需要特殊的教育,以及更加精致的、比常人更加練達的趣味。[1]178在這一點上,佩羅顯然受到笛卡爾及其知識圈子的影響,尤其是笛卡爾“懷疑-檢驗”方法的影響。佩羅明確宣稱,希望把笛卡爾帶入哲學里的自由應用到對心靈作品的檢驗中去,擺脫文學權威的束縛,就像笛卡爾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那樣。[1]179提出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為了降低古代作品評價者的準入門檻,尤其是為崇今派確立資格。因為總體而言,崇古派里不乏古典知識的淵博之士,加之當時法國的經院式教育,給文藝批評規定了不少嚴格的規矩。然而,倘若僅以理性為準繩而做出的獨立判斷是可靠的,并足以令人信服,那么,古典學就無法享有特權,而很多不以古典學見長的厚今派人士也可以放心涉足了。
第二個論據基于對自然之永恒性的信心。創造不應以古今分高下,首創者并不更加偉大。他甚至舉例說道,第一位造船者無非模仿了貝殼類動物,如果古代創造者比今天的創造者更偉大,豈不是貝殼類動物最偉大?若論熟練程度,今人具備更充分的認識和更悠久的習慣,自當比作為初學者的古人高明。他的持論依據是,作品與作者可以分而觀之;而自然的產品是永恒不變的(樹木在今天所結的果子與古時相同,人的觀念古今同一)。乍看起來,頗有些中國人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意思。不過,有意思的是,二者的觀念正好走在相反的方向上:董仲舒的話旨在說明統治之道的綱常穩定性,從而常被保守派引以為(政治)守舊的依據;而佩羅則希望扭轉西方自古代以來的社會衰落論,把近代人提升到與古代人平等的地位,從而為近代的創新尋求根本支撐。在他看來,就像大自然年年都會出產大批量的中品和差品的葡萄酒,但也會有品質上佳者,任何時代也都有也會有平庸的普通人,卻也不乏卓越的天才。[1]179-180因此,“當我們在做古今對比時,所針對的并不是它們的純自然天賦的卓越性,那些天賦在任何時代的杰出人士身上都是相同的,都具有相同的力量,我們的古今對比僅僅針對他們的作品之美,針對他們對于藝術和科學所具有的知識,那是依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的。因為,由于科學和藝術無非是一堆反思、規范、規則,那么,詩歌作者有理由主張這堆必然隨著日積月累而增多的東西更加偉大,并走在所有時代的最前列……”[1]181
第三條論據基于對自然科學的信心。比如他認為,古人粗知七大行星和其他一些醒目的星星,今人還認識了一些衛星和眾多新發現的小星星;古人粗知靈魂的激情,但今人還了解與之相伴生的無限多的微妙病癥和狀況;從而,“我可以讓你看到我進一步把所有激情依次重新結合在一起,使你相信,在我們的作者的作品里,在他們的道德論著里,在他們的悲劇里,在他們的小說和雄辯篇章里,都存在著成千上萬的細微感觸,那是古人所不及的”[1]186。總而言之,今人相對于具備更多的幾何學、透視法、解剖學等領域的知識,加之掌握了更加完善的工具,又在技巧理論上取得了更多的進展,因此會出現比古人更加偉大的雕塑家、畫家、建筑家。佩羅在《古今對觀》結尾處充滿感慨地說:“讀一讀法國和英國出版的雜志,看一眼這些偉大王國的研究院所出版的書籍,這樣就會深信不疑地認為,自然科學在過去二十或三十年內所作出的發現,比整個古代在學術上的發現還要多。我認為自己很幸運地得以指導我們所享受的幸福,我承認這一點;縱覽過去的所有時代,目睹一切事物的誕生和進步,這是莫大的快樂,但是那些在我們的時代尚未獲得新的增長和光澤的東西則另當別論。我們的時代差不多已經達到完美的巔峰。自從過去的若干年前以來,進步的速度一直緩慢得多,看上去幾乎難以察覺——正如夏至日點臨近白晝似乎不再延長一樣——很可能沒有多少東西會使我們需要對未來的后代表示羨慕,一想到此便會有一種欣悅之感。”*轉引自約翰·伯瑞《進步的觀念》第四章“退步論:古代與現代”,范祥濤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然而,佩羅的論證并不嚴密,也不乏自相矛盾之處。在第一條論據里,一個可想而知的隱患是,知識的去精英化難免造成知識精度的下降。在第二條論據里,他把作家和作品分開討論的做法,即便論證出自然的作品持久而永恒,卻也會妨礙把這一條論據引向對古人價值的判定;況且這條原則并沒有貫徹始終。崇古派的于埃就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1]217。就這條論據而言,佩羅的方式不如德馬雷的方式明智:如前文所述,后者斷言上帝的作品(即自然)是無往而不美的,而人的作品(包括文學、藝術、科學)則有待于逐漸趨向更完美,這樣做一勞永逸、干凈利落,令反面意見的反駁無從下手;而佩羅的方式則給自己制造了麻煩。
遭到更多人指摘的是第三條論據。人們認為他把科學和藝術混為一談,把科學的進步作為藝術進步的原因。比如,希格就批評佩羅只知工巧而不懂趣味,只看質料而忽視思想[1]185-186。說到底,佩羅之所以產生如此誤解,是其用科學標準來評價藝術問題所致。希格認為,佩羅的問題在于沒有能夠區分兩種藝術:一種藝術,其臻于完美需要時間,而另一種藝術則從開端時就能夠是完美的。[1]186我們如果將前一種“art”譯作“技藝”“工藝”或“技術”,或者廣義之“藝”,希格的意思就很明白了。這種“art”的近親是科學。科學的發展過程是從無知到有知,經驗和知識的積累對于科學而言十分重要。今天的我們站在歷史的下游向上回溯,能夠看得比較明白:藝術史不是憑借經驗積累而發展的歷史,在藝術上,后發性不等于優越性,后出現的藝術不一定比先前的更高明。佩羅混淆科學與藝術的性質,放在他那個時代的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與其說是個錯誤,不如說是時代的思維特色。在17世紀的法國,盡管科學有了相當新異和突破性的進展,盡管科學的觀念,如實驗、機械論等,已經大大改變了知識精英們的思維方式,但學科領域的界線與今天相比是相當模糊的(類似地,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那么多科學藝術無所不能、璀璨有如繁星的全才,亦可部分地歸于知識分界模糊,博學者們一通而百通),科學成就也頗為有限(在《古今對觀》中,佩羅只看到了艦船相對于漁船的進步、盧浮宮相對于茅屋的進步等等,當然,這些足以令其感慨不已了)。
在談到古今詩歌對比的時候,佩羅接續了前述德馬雷與布瓦洛的爭論,即作為題材,基督教和神話兩者之中何者更應該入詩。但他更改了討論的重點。他先指出,有兩類裝飾可以為詩歌灌注生氣、美化描寫,一類是各個國度所共有的、自然的裝飾,比如情感、激情、話語等,另一類是只屬于某些地域的裝飾,如古人詩歌中的眾神,又如基督教詩歌中的魔鬼與天使,它們是人為的裝飾。后一類裝飾盡管會帶來美化效果,但它們并不屬于詩歌的本質。比方說,我們完全可以把古人詩句中的異教神置換為基督教的天使。因此,古人對神話的利用并沒有什么高明,至少不比今人使用宗教題材更為高明。既然旨在美化裝飾,故而他也同等地不反對布瓦洛所提倡的寓言入詩。
另外,布瓦洛還曾表示,把基督教人物摻入詩歌這樣的想象力游戲是大不敬的(詳見下文)。對此,佩羅有一套成熟而理智的看法:“詩歌在被用于游戲時,它是一種心智游戲;但當涉及重要題材時,它就不再是心智游戲,而等同于那些演說、頌詞、布道里的偉大雄辯術。我們不能說大衛和所羅門的詩歌是一種純粹的心智游戲,親愛的主席,您不會樂意以此稱呼《伊利亞特》或《埃涅阿斯紀》的。所以,確實存在相當嚴肅的詩歌作品,在那里放入天使和魔鬼完全不會有失體面。由于我們相信,上帝之所以把這些鬼神放入人類行為,要么是為了誘惑他們,要么是為了拯救他們,那么,鑒于我們大多數人并不懂得的種種原因,詩人難道不能夠遵循詩歌的特權把它們彰顯出來,令它們變得具體形象嗎?”[1]198-199
就總體而言,佩羅確實是一位靈活機智的辯手。當時,《古今對觀》第一卷的出版令崇古派震怒,他們紛紛指責厚今派只不過是一幫妒忌者。在《古今對觀》第二卷序言里,佩羅風趣地回應了“妒忌說”:巴黎的文人有兩種,一種文人認為古代作家盡管嫻熟精雅,卻犯了些今人沒有犯過的錯,他們贊揚同行的作品,認為它們與那些模范同樣優美,甚至往往比大部分模范更加正確;另有一些文人,他們宣稱古人不可模仿,遠不可追,從而鄙視同行的作品,一旦遇到就從言辭和文字上加以詆毀。“他們在開始時直截了當地宣布我們是無趣味、無權威的人。到了今天則又指責我們妒忌;明天大概就會說我們頑固不化了吧。”[1]193這一類俏皮話舉重若輕,有親和力,它們時常令崇古派的古板面孔顯得頗為滑稽,為厚今派贏得了不少來自女性支持者和報刊輿論支持。
不過,俏皮與機智只適合于作為錦上添花的技巧,只有在進行單方面闡述或單個回合的辯論時,它們的作用才會比較有效地發揮出來。然而,如果面臨復雜的學術問題,需要多方深入論證時,系統性、知識性的缺乏很容易暴露無遺。佩羅式的輕盈巧辯,尚需厚重的古典學知識來支撐,才可能無往不勝。尤其是,崇古派提出的一個嚴肅指責,令以佩羅為代表的厚今派不得不認真面對:“厚今派不懂希臘文,也不懂拉丁文;他們靠譯本來判斷作者;他們注定會做出糟糕的判斷。”[1]194
(三)布瓦洛
厚今派的德馬雷提出了神話應否入詩的問題。布瓦洛在其《詩的藝術》第三章里用了四十多行詩(第194行—第237行)提出反駁,力求論證神話入詩的合理性及神話題材的優越性。
古典主義美學注重文藝的教化功能,認為寫詩的目的在于勸諭人、教育人,使之樂意接受某個道理;唯有使用令人愉快而可信的內容,詩歌方可達到勸諭的效果,這就是“寓教于樂”。賀拉斯在《詩藝》里曾經指出過的這條創作原則:“詩人的愿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4]作為賀拉斯詩學的繼承者,布瓦洛也主張寫詩作文首先要講究“情理”/“理性”(“永遠只憑著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5]5。這是《詩的藝術》的總體立場。
按照這個線索,在神話題材之合法性的問題上,我們猜想布瓦洛的論證邏輯會是這樣的:詩歌應當實現教育勸服的目的,為此應當具有令人愉快的效果,而神話正是令人愉快的,所以可作為詩歌題材。然而我們發現,布瓦洛在這個部分并未怎么提到詩歌的教化目的,而是縱情談論“詩情”、詩味。他指出,神話之所以具有令人愉悅的功能,乃是由于它的虛構性。神話故事“裝飾、美化、提高、放大著一切事物”,化抽象為具象,變平凡的現實為瑰麗的想象,變“抽象的品質”為性格鮮明的“神祇”;它們令“一切都有了靈魂、智慧、實體和面容”,所以詩歌才會那樣引人入勝、令人著迷。布瓦洛沒有就此引導到“寓教于樂”的大題目上去,話語間倒更看重詩歌本身的審美價值:“若沒有這些裝飾,詩句便平淡無奇,/詩情也死滅無余,或者是奄奄一息,/詩人也不是詩人,只是羞怯的文匠,/是冰冷的史作者,寫的無味而荒唐。”[5]40-42這里似乎不見其“教”,僅見其“樂”。當然,“理性”作為一個大前提貫徹在《詩的藝術》全書里,在神話題材這個具體問題上是不言而喻、無須再提的。但布瓦洛向來不憚于重復賀拉斯說過的話。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布瓦洛在寫下這些作為反駁意見的詩行時,心情難免有些急切。他珍視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史詩傳統,衷心熱愛那些美妙的寓言故事,因此急于駁倒德馬雷,捍衛神話題材的合法性,滿腹的道理不吐不快,表達時卻略失輕重。比如這幾句詩:
并不是說我贊成在基督教題材里
作者也能狂妄地崇偶像亂拜神祇。
我是說,如果他寫非教的游戲畫圖,
也丟開古代神話,竟不敢寓言什九,
竟不讓潘神吹笛,讓巴克剪斷生命,
不敢在水晶宮里不知寫蝦將蟹兵,
不敢讓那老伽隆用他催命的渡船
同樣把牧豎、君王渡向陰陽河彼岸;
這豈非空守教條,愚蠢地自驚自警,
無一點妙文奇趣而想受讀者歡迎?
進一步他們將不許畫*參考當頁譯者小注可推知,原文此處似乎漏掉了“賢明之神”。參見布瓦洛《詩的藝術(修訂本)》,任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45頁。,
不讓那特密斯神蒙著眼、提著小稱,
不許寫戰爭之神用鐵的頭顱相觸,
不許寫光陰之神飛逝著提著漏壺;
并從一切文章里,借口于衛教為懷,
把寓言一概排除,詆之謂偶像崇拜。[5]42-45
連續的排比修辭仿佛為言辭布下鼓點密集的聲音背景,顯出責備駁斥的咄咄氣勢,布瓦洛的急切與激動溢于言表。詩中一系列的“不許”“不讓”“不敢”,是布瓦洛相當怕見的詩壇景象。進一步看,神話既然如此令人愉悅,若借以“載道”,宣揚基督教的教義,豈不方便?一百年前,意大利詩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就是這樣做的。但布瓦洛堅決反對把神話摻入基督教文學。他說:“基督教徒信仰里的那些駭人的神秘/絕對不能產生出令人愉快的東西。/福音書從各方面教人的只有一條:/人生要刻苦修行,作惡就惡有惡報;/你們膽敢拿虛構來向《圣經》里摻雜,/反使《圣經》的真理看起來好像神話。”[5]43也就是說,神話題材與基督教義相混,勢必傷害宗教的嚴肅性。布瓦洛的觀點至此似乎較清楚了:受詹森派教義影響,他主張美善分離;由基督教信仰來教人明辨是非,而充滿想象力的神話令人產生審美愉悅。
由上可見,布瓦洛堅信虛構和想象是詩歌及文學的生命,它們所帶來的愉悅感是詩歌的魅力所在,從而主張師法古代詩歌,以神話為主要題材,反對以基督教義入詩,反對以宗教教條取代審美樂趣。用今天的眼光看,布瓦洛的文藝觀似乎比德馬雷更為寬宏,至少他并未像德馬雷那樣,以“宗教正確性”作為一種專斷的美學標準*希格也在書中評判道,德馬雷混淆了宗教與文藝,后者不求“真”而求“美”;造就更偉大的詩人者,并非觀念之真,而是“情感之真、想象之美、激情之熱烈、語言之光輝”。(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108)。這個說法恐怕有些苛責前人。希格身處19世紀,那個時候的浪漫派已經標舉了“為藝術而藝術”;但在17世紀,審美尚無自主地位,因此德馬雷在標準上以宗教代審美,倒也不足為奇。不過,希格還提到德馬雷的論據在他的時代重燃。。但他對德馬雷的詰難卻不大令人信服:在西方文學史上,優秀的基督教文學并不鮮見。
布瓦洛的鮮明主張,在另一方面體現出異教詩歌與基督教詩歌在當時的激烈較量。關于基督教義可否及如何入詩,或者說可否及如何作為文學主題,這個問題十分復雜。希格認為,在基督教里,地獄比天堂更具詩性,因為唯有地獄向種種激情開放,這就是為什么撒旦乃是《失樂園》的真正主角。基督教的天堂是完美的統一體,各品級的天使異名而同類,它們只被上帝的思想激活,被上帝的意愿驅遣。說到底,在天堂里只有一個人物,那就是永恒的上帝。這個上帝是純粹心靈,其非物質性使得詩人難以下筆為之著色或施加想象力。[3]94
三、古典主義美學的內在矛盾
綜上可以看出,這場文人戰爭牽涉諸多復雜問題,甚至卷入私人恩怨。因此,后世對之歷來褒貶不一,甚至對其研究價值亦無定論*科林·麥奎蘭在《早期現代美學》第一章“古與今”中對其持肯定態度,他認為這場發生在前美學時期的論戰輔助了人們將藝術與哲學歸攏一處,從而對于我們了解美學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J. Collin McQuillan, Early Modern Aesthetics, Lond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2016, Chapter 1)。否定其價值者亦大有人在,具體可參見拙文《克朗茨的笛卡爾美學論及其命運》(待刊)。。如果我們持一種連續性的歷史觀,則無論我們相信歷史的演進道路是前進還是后退,皆會傾向于認為歷史現象或事件事出有因,至少在時間上能夠分出“前”因與“后”果。那樣的話,就古今之爭在時間鏈條中所處的位置而言,它上承古典主義美學,下啟啟蒙運動,其與二者的關聯應在可探討的范圍之內。故而筆者嘗試提出,它是17、18世紀交替時期古典主義文化衰敗的表征之一。
通過梳理這場古今之爭的過程,分析主要人物的主要論題,我們看到,這場爭論有一個總題,那就是:古與今何者更為優越?參與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論點切入這個總題。他們提出的分論題涉足宗教問題(基督教與異教)、進步問題(文學、藝術、科學的進步)、語言問題(法語與拉丁語、古希臘語)等等五花八門的領域。在討論古典傳統對西方文學史的影響時,海厄特將古今之爭的論題進一步擴展,做了如下清晰而充分的描述:“問題是這樣的:現代作家是否應該推崇和模仿古代偉大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作家?或者古典的鑒賞標準是否已被超越和取代?我們是否必須追隨古人的腳步并試圖效法他們,以達到他們的水準為最大愿望?或者我們能否自信地期待超過他們?這個問題的范圍還可以大大擴展。在科學、藝術以及整體文明上,我們取得的進步是否已經超越了希臘人和羅馬人呢?或者我們是否在某些領域領先他們,但在另一些領域落后呢?或者我們是否在所有方面都不如他們,我們是半開化的野蠻人,只是享受著真正文明人類所創作的藝術?”[6]這一連串的問題提示我們,或許可以把那場喧擾的戰爭理解為一種自我身份的焦慮,理解為當代人對當代文化之品質的矛盾性反思: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是光榮的,我們當代法國人是否同樣光榮?
這樣的反思,最深刻地糾纏著法蘭西學院的知識精英,他們肩負著知識傳承的重要責任。這個責任的首要任務,在于權衡和斷定怎樣的文化最值得推崇,最能夠為當代、為自己的民族國家帶來益處。他們面臨兩種文化:古代文化和當代文化。前者被封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完美樣板,后者擁有豐富的成果,呈現出繁榮的態勢。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進行鑒賞對照時,發現當代文化并不輸于古代文化,甚至可能在一些地方有所超越。比如佩羅說過:“古人是卓越的,這一點不可否認;但今人不遑多讓,甚至在很多地方更加出色。”可見他身為厚今派卻并不一味貶低古人,而只是更看重今人的優勝之處。按希格的話說,佩羅仰慕古人,只不過并非古人的崇拜者;他稱頌古人,但并不夸贊古人的所有作品,而是有所揀選,有所批判。[1]177,180這種對待古人的態度,在厚今派里相當有代表性。
然而,他們為何會為這樣的問題所糾纏甚至爭執不休呢?路易十四時代難道不是一個古典主義美學趣味籠罩下的大一統時代嗎?推崇并仿效古代文化,難道不正是一切古典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嗎?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古典主義美學內部發生了分裂。
夏爾·佩羅不認為古人作品都是神圣而完美的,因此斷然反對給年輕人灌輸古代文化。他說:“有那么一些人,把這種偏見灌輸給年輕人的心靈、置入他們的行為,這些身披黑色長袍、頭戴方形無邊軟帽的人,建議年輕人去讀古人作品,不單把它們說成是舉世之珍,還將之標舉為美的觀念,如果年輕人終于能夠模仿那些神圣的摹本,便送上預先備好的冠冕。他們就靠這個糊口。”[1]192夏爾·佩羅的這段話并非理論話語,但看似尋常卻很有代表性。其兄長皮埃爾也說過類似的話。1678年,皮埃爾·佩羅以書面形式說道:“我認為,我們在當下仍能看到的對古代作家的偉大反駁,僅僅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問世于一個精神既粗俗又無學識的時代;就因為有些作品確實優秀,其他同時代作品難以匹敵,它們就激起了較高的評價,這評價強烈滲透到那個時代的精神之中,它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從父輩傳給孩子,從師輩傳給學生,乃是由于,作為年輕人,孩子和學生是盲目服從的,而他們的父輩和師輩向他們信誓旦旦地說那些作品是神圣而不可模仿的。”[1]131他們所憂心的是年輕人的教育問題:應該教什么?由誰來教?換言之:應該將怎樣的文化傳承下去?這是在任何時代都至關重要的課題。或許正是在這里,透露出厚今派對古典學權威的真正不滿。
從伏爾泰《哲學詞典》里,我們可以發現他對佩羅兄弟的呼應:“我們對當代已經過分為人熟悉的偉大成果態度冷漠,古希臘人卻對微小的成就十分贊賞。這正是我們的時代對古代具有極大優越性的又一明證。法國的布瓦洛和英國的坦普爾騎士執意不承認這種優越性。這一古人和今人之爭至少在哲學領域里已經得到了解決。今天,在文明開化的國家里,沒有人再用古代哲學家的論述來教育青年了。”[7]按此說法,厚今派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至少牢牢掌握了教育的方向。
于是不少研究者指出,古今之爭的一個重要內容乃是反權威。認識到這一點,難免會將古今之爭與文藝體制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把古今之爭視作學院派里的在野派對學院權威的不滿的集中爆發,視作一場文化權力爭奪戰。不過,這樣的解釋尚欠確切,容易引起誤解,甚至可能掩蓋問題的實質。以布瓦洛為例,他在成為文壇領袖之前,也曾是與拉辛等同道一起反對沙普蘭權威的年輕人。在這種通常意義上的反權威,所關涉的是同質文化內部的權力分配問題:在野派希望奪取文化領導權和稀缺資源,取代現有權威而成為新的權威。這種代際更替并不更改文化的性質與方向。如果說厚今派確實也反權威,則這種反對與革新的訴求是更為激烈也更為根本的。他們希望棄拉丁語而起用法語,棄異教神話而起用基督教題材,用當今科學之昌明來彰顯古代文明之粗陋,這些方案都有志于把異質文化傳統扭轉為以當代法蘭西文化為主導。
換言之,需要在更深廣的意義上理解古今之爭中的反權威現象。厚今派成員的攻訐之辭,無論出于怎樣的私意,在整體上看或就客觀效果而論,都在進行著對文化方向的爭奪。這種爭奪恐怕折射出文化總體的深度病癥。那么,法國古典主義美學究竟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于竟會在其知識精英內部發生這樣嚴重的分裂和根本性的紛爭?
這里需強調的是,17世紀法國的古典主義美學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官方美學,是國家政策的附屬性產物。這種美學先天地帶有一種潛在的錯位:它在體制和內容上是古典主義的,在訴求上則是民族主義的。古典主義在內容上要求尊古、復古,在體制上要求規范化、模式化、典型化。民族主義的強國訴求,則包括著眼于當代現實的戰略考慮,比如,它需要詩歌與繪畫來歌頌國王的戰功與偉績,需要提升民族語言的地位,從而在外交上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它還需要吸納最新的科學發明,以服務于可能的國防需求,等等。可以說,這種古典主義追求的是一種旨在提高法蘭西民族文明、增強法國綜合國力的“當代法國古典”。
在這個矛盾的詞匯下,透露出兩種相當異質的指導思想:一是體制所嚴格要求的限制與管控;一是文化藝術科學創新所必須的自由意識。這兩者顯然難以長期共容,勢必發生碰撞。而此消而彼長的結果,將決定法國文化品質的歷史走向:或則管制扼殺創作,或則自由沖破規矩。正如希格曾經指出的那樣,布瓦洛之于文學界,有如路易十四之于最高法院;法王的治下一直涌動著暴力的或無聲的政治反抗,而布瓦洛的文學管控也長期面臨著一股反對力量。*參見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150。丑化路易十四形象的事情在當時并不少見,英國崇古派主力喬納森·斯威夫特就曾在一首頌揚威廉三世的詩歌里把路易十四貶低為“貪得無厭的暴君”。參見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十章“反面形象”。
所以,古今之爭中兩派的尖銳對立,或許正反映出現代文明初始階段的陣痛。我們可以從宗教文化的角度,把古今之爭看作是已然逝去、余韻猶存的古代異教文化與基督教現代之間的沖突,也可以引入一個階級視角,就像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所啟示的那樣,認為它體現了上升期的資產階級對封建文明的抵抗。新興的資產者集宗教信徒與渴望世俗成功者于一身,他們的文化精英(這一點在佩羅兄弟身上很典型)更加重視獲得文化的廣泛受眾的支持,更加有意識地針對公眾進行寫作,于是堅持使用法語,并力求語法淺白、內容通俗。進而我們難免會想到,他們的作品或許是啟蒙著作的雛形。
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的奧爾良公爵攝政時期(1715—1723年),二十歲的伏爾泰與已逾花甲之年的豐特奈爾曾在蘇利館(Hotel de Sully)沙龍暢敘。伏爾泰贊后者為路易十四時代最多才多藝之人。[8]確實,厚今派與啟蒙思想家之間,在精神特質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反叛精神,敢于向現有的權威挑戰,推崇理性,謳歌科學。不同之處在于,厚今派身處法國絕對君主制的強盛期,分化自一個高層的文化共同體,著眼于文化上的除舊布新,但所倡導的新文化仍屬于舊體制;啟蒙者們則處身絕對君主制搖搖欲墜的階段,其所謀求的思想革命更徹底地帶有政治革命訴求,立足于科學理性來鮮明而激烈地反君權、反神權。厚今派和啟蒙思想家都深知輿論造勢之道,他們較自覺地保持著集體觀念、活動的一致性,重視較廣泛受眾的反應,充分利用各種傳播渠道來為自己爭取支持。厚今派的筆戰在書信和出版物上,也出現在上流社會的沙龍里。除了這些媒介,啟蒙思想家還利用了圖書館和咖啡館等輿論陣地。
從這個角度看,古今之爭的那段歷史,或許可以解釋為古典主義美學崩潰、啟蒙美學萌芽的二項對立時期。法國17世紀的古典主義美學內蘊著自身的反對力量。它本該是一種權威化、規范化的美學,以古典美學為樣本,在各種藝術領域設定權威以作為法則的代表。而新成果的誕生,往往出自具有批判和懷疑精神的頭腦。層出不窮的新的文化成就,與笛卡爾的徹底懷疑精神走在同一條道路上。啟蒙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倚賴理性,信任人人皆生而有之的基本判斷力,就像圣·艾弗蒙(Saint Evremond,1610—1703)說的那樣:“荷馬的詩永遠會是杰作,但不能永遠是模范。它們培養成我們的判斷力,而判斷力是處理現實事物的準繩。”[9]
確實,在古今之爭的喧囂里,某些重要的東西被動搖了。就此而言,它確實稱得上啟蒙運動的先聲。從文化權威的倒掉,到神權與君主制的松動,這之間的復雜轉變,并不是古今之爭一事所能盡顯。但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古今之爭與啟蒙運動之間的相關性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歷史延續論。
[1] 呂健忠,李奭學. 西方文學史[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213.
[2] 劉意青,羅經國. 古代至十八世紀歐洲文學[M]//李賦寧. 歐洲文學史:第1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94.
[3] RIGAULT M Hippolyte.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M].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1856.
[4] 賀拉斯.詩藝[G]//亞里士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楊周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155.
[5] 布瓦洛.詩的藝術(修訂本)[M].任典,譯.第2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6] 海厄特.古典傳統:希臘—羅馬對西方文學的影響[M].王晨,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221.
[7] 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M].吳模信,沈懷杰,蔣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497.
[8] 杜蘭.伏爾泰時代[M].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23.
[9] 艾弗蒙.論對古代作家的模仿[G]//高建平,丁國旗.西方文論經典:第2卷·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456.
(責任編輯:劉 晨)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and the Decline of French Classical Aesthe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ZHANG Ying
(Literature&ArtStudiesEditorial Department,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influenced by the the quarrel between"ancients and moderns" (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As the division deepened and went public, the Royal Academy broke into two camps : those for the ancients and those for the moderns. This literary war involved many complex issues, even personal strife. Therefore, subsequent ages have disagreed about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is dispute and even about its research value. Now by tracing the whole story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at the French front (especially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views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two camps, we hope to expl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literary war and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establish it as one of the signs of the decline of French classicism at the turn of the 18thcentury.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classicism; aesthetics; France
2016-12-1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西方美學史1~2卷》(14JJD720022)的階段性成果;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研究項目《法國存在主義藝術理論研究》(14DA02)的階段性成果。
張穎(1979—),女,山東淄博人,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副編審,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近現代法國美學研究。
B83
A
2095-0012(2017)01-0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