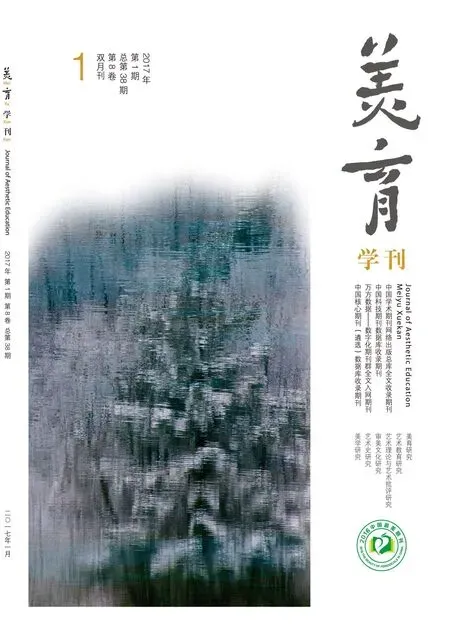中國現代“美學三慧”之人生藝術化思想比較
王廣州
(安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11)
中國現代“美學三慧”之人生藝術化思想比較
王廣州
(安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11)
朱光潛、宗白華與方東美同出一時一地,其各自的人生藝術化思想對“生”與“情”作出了富有個性的闡發,涉及人生、生活、生命與情趣、同情、情調三組相對應的主題,而且同中有異,異中見同,相映成趣。同時,三人也用各自的主張回應了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實踐論、想象論與存在論三條探討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思想的路徑。
朱光潛;宗白華;方東美;人生藝術化;比較
中國近現代以來,關于人生藝術化問題的探討者可謂甚眾,較有影響的也不下十數人。其中朱光潛與宗白華的人生藝術化思想最為純粹與顯著,而方東美的人生藝術化思想則最為獨特卻稍為隱晦。由于這三人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生成長于同一地區(安徽安慶),所以有論者化用方東美一篇論文的標題將他們稱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學三慧”。[1]3朱光潛與宗白華同年生而又同年逝,方東美較二者僅僅晚生兩年;朱光潛與方東美皆生于安慶桐城,并于1912年和1913年相繼進入由晚清桐城派大師吳汝倫創辦的桐城中學就讀,直到晚年二人分處海峽兩岸而仍有書信與詩文往來;宗白華與方東美早年都曾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方東美的重要論文《哲學三慧》首次發表于宗白華主編的《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上,并被后者高度評價。[2]173三人在青年時期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回國后不約而同地走上了美學與哲學研究的道路,方東美與宗白華曾在20世紀40年代的國立中央大學共事,朱光潛與宗白華則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北京大學共事,在相同的工作領域中思考著諸多共同的思想主題。
此三人同為從安慶走出的思想人物,行跡上有很多相似與疊合之處,這種物理事實對于有索引癖的學者來說,好像很有可以玩味和挖掘的地方。但是總體來說,這一切與其說是地域使然,不如說是時代使然。美育與人生藝術化命題的提出及其話語生產,在三人那里本身就是對時代問題的各自回應。目前關于人生藝術化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人物個案為主,因此往往著重探析各家之特點,而有意無意地忽略或無視各家之共點;實際上,在缺少比較的維度后,在分述各家之特點時反易誤入自說自話、漫無歸落的傾向中。本文意在比較三人的人生藝術化思想的具體構成,總其同而析其異,并就其思想對時代問題的回應范式揭示中國現代人生藝術化思想的三條典型路徑。
一、“生”與“情”:思想內涵之異同
“人生藝術化”,此一命題稱謂已經大致道出該命題本身的精義,似乎并無太多理論操作的余地了。所以嚴格說來,三人皆未建成某種完備的人生藝術化理論,非其不欲,誠其實難。例如宗白華在1920年就明白無誤地說:“我久已抱了一個野心,想積極地去研究這個‘科學人生觀與藝術人生觀’的問題”,但最后只是寫了一篇兩三千字的《新人生觀問題的我見》,于是“很是抱歉”,“所說的實在太簡略了”,而期之未來。[3]208不過后來也并沒有踐行,原因倒不在于缺乏他自己所謂的“科學與藝術的基礎知識”,而在于這命題本身只是個過于實在的主張而已。情形在朱光潛與方東美那里大致相近。朱光潛在《談美》的最后一章談到“人生的藝術化”問題時,也只是說要“提議約略說明藝術和人生的關系”。[4]91方東美時常將哲學與藝術視為中國與希臘文化體系的樞紐,但他還是傾向于認為哲學才是“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樞”。[5]125由此,就在三人那里形成了一個關于該命題的相同的話語存在形態,即散論式。宗白華的觀點主要散見于《青年煩悶的解救法》(1920)、《怎樣使我們的生活豐富》(1920)、《新人生觀問題的我見》(1920)、《藝術生活——藝術生活與同情》(1921)、《席勒的人文思想》(1935)、《〈美育〉等編輯后語》(1940)、《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往哪里去?》(1946)等文中;朱光潛的觀點散見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中的《談情與理》《談擺脫》及附錄的《無言之美》,《談修養》(1942)中的《談美感教育》及附錄的《消除煩悶與超脫現實》《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等文中;方東美的觀點則散見于《生命悲劇之二重奏》(1936)、《生命情調與美感》(1936)、《哲學三慧》(1937)、《詩與生命》(1973)等文中。
就存在形態而言,三人的觀點是零散分布于各個年代的作品(主要是單篇文章)中,時間跨度從十余年到三十多年不等。不過,綜觀之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三人各自的,乃至共同的某些核心主張,它們與該命題中的兩個關鍵詞“人生”和“藝術”相關,質言之,就是三人的思想都圍繞著“生”與“情”兩大主題而展開(傳統藝術觀常常落實到情感的維度),同中而又有異。首先,“生”意味著人生、生活、生命,這是三人都曾明確言說的對象,不過宗白華與朱光潛多言“人生”與“生活”,而少言“生命”。反之,方東美則主要言說“生命”,極少言說“人生”與“生活”。這一點僅從上述三人文章的標題中已可見一斑,而具體行文之中更為明顯。這三個詞在其他語言如英語或德語中一個單詞就可以表示,但是由于漢語詞匯的豐富性與含混性,它們互有聯系但是又互分互立。“生活”具有物質的意味,“人生”具有精神的意味,而“生命”則具有哲學的意味。對宗白華和朱光潛來說,無論是前者的“藝術人生觀”,還是后者的“人生的藝術化”,其要旨都在一種較高尚優雅的精神追求,但最終都還是訴諸具體現實的形而下生活本身。所以對他們二人而言,人生與生活兩個概念可以看作是一體。宗白華的這個判斷也同樣是朱光潛思想的前提:“‘生活’等于‘人生經驗的全體’。生活即是經驗。”[3]191而方東美言所必稱的“生命”具有強烈的形而上色彩。我們尤需注意的是,方東美的生命概念并不單純地指個體的生命,而是一個既包含個體生命同時又超越它的普遍生命。關于普遍生命的存在、特征以及個體生命與它的關系,方東美做了簡明的哲學設定。首先,“天為大生,萬物資始,地為廣生,萬物咸亨,合此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其次,“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是生生不已、新新相續的創造領域”,“其中生氣盎然充滿,旁通統貫,毫無窒礙,我們立足宇宙之中,與天地廣大和諧,與旁人同情感應,與物物均調浹合,所以無一處不能順此普遍生命,而與之全體同流”。[6]82-83從言說路徑看,方東美的“普遍生命”可說是黑格爾“絕對精神”概念的翻版,同時又完美地雜糅了中國上古易經與西方現代哲學家柏格森的學說,三相湊泊,賦予其豐富的哲學內涵。
其次,“情”在三人那里也各有所主,在朱光潛是“情趣”,在宗白華乃“同情”,在方東美則為“情調”。情趣、趣味、愉悅等等是人生藝術化命題的應有之義,三人之中朱光潛最為大力標舉,指出“人生藝術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它本身個體在世界之中“物我交感共鳴的結果。景物變動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在這種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們可以見出生命的造化。把這種生命流露于語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風采,就是美滿的生命史,”總而言之,“情趣愈豐富,生活也就愈美滿”。[4]92-97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朱光潛繼續推演與豐富其情趣說的邏輯內涵,在他看來,生活有情趣,便不“俗濫”,不茍且,生命便不“機械化”,反而能夠“徹底認真,不讓一塵一芥妨礙整個生命的和諧”;這種風度既藝術的,也是道德的,所以朱光潛說“我們主張人生的藝術化,就是主張對于人生的嚴肅主義。”[4]92-97有趣的是,很少關注人生藝術化之情趣愉悅維度的宗白華與方東美在偶爾言及情趣愉悅時,幾乎不約而同地持有和朱光潛相同的邏輯。例如宗白華在說當我們把世界上無論美丑的存在現象都看作藝術品一樣時,憂苦煩悶就都煙消云散了,我們的“心中就得著一種安慰,一種寧靜,一種精神界的愉樂”。[3]179不過宗白華強調“愉樂”不是“娛樂”,更“不是娛樂主義、個人主義,乃是求人格的盡量發揮,自我的充分表現,以促進人格上的進化。”[3]194所以宗白華的藝術人生觀也絕不是輕浮乃至輕佻的消費主義追求,而是著眼于生活與情緒的調節,精神與人格的完善,也許此他才較少言及情趣和愉悅,以免引起誤導。同樣,方東美在論及古希臘人“從心而欲的悲劇”精神時,認為希臘人的生命精神“著重幸福的結局、愉快的后感”。但他也指出這種幸福和愉快并不“佻巧、一味求樂”,而是要“將實際生活中所經歷的酸辛苦楚都點化了,飾之以幻美,始能超越艱難、陶鑄樂趣,以顯耀人生的勝利”。[5]26
“情”在朱光潛是情趣,是人生藝術化的目的。相較而言,“情”在宗白華主要是“同情”,是藝術人生觀的方法。在宗白華看來,情緒感覺屬于人類的主觀世界,本來就參差萬態,不易一致,而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情感完全不一致,卻又是社會的缺憾與危機”。于是宗白華首先從社會學的觀點界定同情的價值,把它作為社會結合、協作、維系與進化的動力和途徑。而藝術也就起源于“人類社會‘同情心’的向外擴張到大宇宙自然里去”,且又可以反哺社會,“真能結合人類情緒感覺的一致”,是社會的黏合劑。所以,宗白華說“藝術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是“我們拿社會同情的眼光,運用到全宇宙里,覺得全宇宙就是一個大同情的社會組織,什么星呀,月呀,云呀,水呀,禽獸呀,草木呀,都是一個同情社會中間的眷屬”,這時就會產生“極高的美感”,而整個自然與世界“就是一個純潔的高尚的美術世界”了。[3]316-319在這里宗白華把作為見之于社會界和藝術界之方法的同情看作是一種“空想”,其本質是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內省或反照”或“比例對照”(Aualogie)。[3]206同情起于空想,而能“入于創造”。所以,“所謂藝術生活者,就是現實生活以外一個空想的同情的創造的生活而已。”[3]319
“情”在方東美那里被具體化為“情調”,是生命狀態的表征。方東美自謂平生最服膺并多次引用的一句諺語是“乾坤一戲場”,此乾坤即世界、宇宙,亦即人類社會存在與活動的空間。方東美借鑒恩斯特·卡西爾的符號學說,把空間視為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符號,認為通過考察一個民族的空間觀念就可以理解其民族文化的形態、內容與性質。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生命就是存在于宇宙這個空間中的,“生命憑恃宇宙,宇宙衣被人生,宇宙定位而心靈得養,心靈緣慮而宇宙諧和,智慧之積所以稱宇宙之名理也,意緒之流所以暢人生之美感也。”這種人生美感是宇宙之中的“生命詩戲”,而又“常系于生命情調,而生命情調又規模其民族所托身之宇宙,斯三者如神之于影,影之于形,蓋交相感應,得其一即可推知其余者也。”[5]88-93據此方東美在《生命情調與美感》一文中比較了三種宇宙空間觀:古希臘宇宙為“有限之形體”,近現代西方宇宙為“無窮之系統”,它們都屬于“科學之理境”;而中國的宇宙則為“藝術之意境”。前兩者雖有有限與無窮之別,但卻都遵循科學的法則,其民族文化生活在哲學、藝術與典章制度各個層面上的最高造詣都離不開科學,所以方東美將希臘人與歐洲人的生命情調類型定格為“科學家”。而中國人則舍科學而取藝術,“體質寓于形跡,體統寄于玄象,勢用融于神思”,“播藝術之神思以經綸宇宙,故其宇宙之景象頓顯芳菲蓊勃之意境”,所以中國人的生命情調類型是持有“多系于藝術表情之神思”的宇宙觀的儒道二家,[5]101他們把宇宙感性地把握為一個空靈的藝術境界。
此外,“情”的問題還牽涉到另一對立面,即“理”。方東美在將希臘、歐洲的“科學型”與中國的“藝術型”相比較時,就已經暗含了他在《生命悲劇之二重奏》《科學哲學與人生》與《哲學三慧》中所論述的“理”與“情”的區分。具體而言,方東美認為情理本是一體而非兩截的,“情由理生,理自情出,因為情理本是不可分割的全體”,“宇宙自身便是情理的連續體,人生實質便是情理的集團。”但是人生與世界確實又是分立的,所以情境與理境也就隨之分立,“生命以情勝,宇宙以理彰。生命是有情之天下,其實質為不斷的、創進的欲望與沖動;宇宙是有法之天下,其結構為整秩的、條貫的事理與色相”,但最終“有法之天下與有情之天下是互相貫串的”[7]。這種情理如一的生命理想的典型案例,在方東美看來總能處于藝術意境中的中國人當然是一個,另外一個就是古希臘人。同樣,他們“拿藝術心眼同情地透視宇宙人生”,“情之所鐘,理必應之;理之所注,情必隨之;情理圓融,物我無間”,[5]57,81天人合德,融匯于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這樣一來,方東美對希臘民族文化特征和生命情調的判斷似乎與上述《生命情調與美感》中“科學型”(即“理”型)的觀點有所矛盾,這或許是因為他分別強調了希臘文化精神的兩個不同側面。這種生命理想的反例就是近代歐洲在經歷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后,它的“宇宙人生之美化”[5]80的精神失落了,它的文化開始走偏,情境告退而理境方滋,從天人合一走向了天人對敵和天人交戰。[6]81-82這表現為歐洲人“每好劃分主賓、離析身心、范形有別”,“理或遠注,情又內虧,實情與真理兩相剌謬,宇宙與生命彼此乖違”,“情理異趣,物我參差”,陷入虛無主義的生命悲劇。[5]32,81所以,方東美把理智稱為現代歐洲的“鬼胎”和“魔法”。[5]55,67這幾乎可謂是現代中國較具先驅性的啟蒙現代性批判。
朱光潛在他的人生藝術化思想中也參入了情理之辨。首先,朱光潛也認為人是一種有機體,情感與理性是其固有之天性,既不易拆開,也不宜浪費或壓抑,那樣只會造成精神的損耗或殘廢。但是朱光潛認為美感教育或人生的藝術化其實就是“叫人創造藝術,欣賞藝術與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尋出豐富的興趣”,故而其本質“是一種情感教育”。[8] 227-228因此,在此領域中朱光潛強調情勝于理,“有了感情,這個世界便另是一個世界,而這個人生便另是一個人生”;反之,理智的生活是狹隘、冷酷、刻薄的,如果理智暴漲橫行,那么“不特人生趣味剝削無余,而道德亦必流為下品”,所以“理勝于情的生活和文化都不是理想的”,“我們試想生活中無美術、無宗教(我是指宗教的狂熱情感與堅決信仰)、無愛情,還有什么意義?”[8] 47-49顯然,朱光潛在對情與理的褒貶抑揚上與方東美的均衡二者的態度有所不同,不過這只是表面現象,因為朱光潛是站在美育與人生藝術化的立場上講他的話的,重情自有其可辯護性。而方東美是在另一個更宏大的文化語境中發言的,是想從古代思想歷史中尋找一種可以補缺時弊的文化理想形態,理路與朱光潛有所不同,這種態度上的差異也就可以存而不究。
二、時態與型范:思想氣質之異同
上文提到朱、宗、方三人的人生藝術化思想是他們對時代問題的各自回應之產物。從時間看,宗白華的思考最早,始于1920年,而朱光潛次之,始于20年代末期,方東美最遲,始于30年代中后期。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在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沖擊之后,又繼以軍閥混戰,國民革命失敗,而日本不斷挑釁,最終悍然入侵,如此混亂的時局導致文化方面尤其是青年們人心惶惶、精神失落而苦悶,一派頹頓。面對此種時代病與青春病,宗白華與朱光潛的反應最為直接,就是以人生藝術化的方案來為青年除煩、解悶,進而為時代與國族把脈、找路。
為此,宗白華在1920年三四月份一氣寫了《青年煩悶的解救法》《怎樣使我們的生活豐富》《新人生觀問題的我見》三篇文章。希望青年們嘗試建立“藝術的人生觀”,首先運用“唯美的眼光”,把社會與生活中的各種無論美丑的現象都當作一種藝術品去看待,這樣就能在平凡乃至丑陋中見出美,心中得到安慰、寧靜和愉悅,一切憂愁與苦悶、無聊與煩惱就都排遣掉了。但這還只是消極的、靜觀的一步,僅僅豐富了對外經驗,還要以積極奮勇的行動在世界中遍歷一切既有與變數,把生活當作藝術品去創造,這樣人生的內在經驗也豐富了。在這一取徑上,朱光潛和宗白華是極為相似的,他在《談情與理》《談擺脫》《談美感教育》《消除煩悶與超脫現實》《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等文章中以朋友身份與青年娓娓交談。朱光潛也要求人生的藝術化要在欣賞與創造兩個層面形成合力,首先是藝術式地欣賞,從人生與生活中得到情趣與享受;其次他尤其強調人生本身就是廣義的藝術,會生活的人就是藝術家,每個人的生活與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而完整、和諧、本色的生活或生命史就是一種令人驚嘆的藝術杰作。[4]92-95朱光潛把這稱為人生藝術化的另一層含義,即人生的嚴肅主義,從而與情趣主義完美合璧。
在那個風聲鶴唳、刀兵四起的時代中期冀用人生藝術化的方法來解除苦悶、調劑生活、創造生命,這種務虛的路子看起來顯然是極為不合時宜的,宗白華與朱光潛對此其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宗白華在1935年的《席勒的人文思想》一文中認為席勒美育思想的主旨就是“將生活變為藝術”,以實現其文化理想,但是“這個理想在現在看來似乎迂闊不近時勢”。[2]115而在《談美》的“開場話”中,朱光潛也承認在那個危急存亡的年代中,“談美!這話太突如其來了!”[4]7談美,甚至主張人生藝術化,看起來這實在太違時太矯情了。相反,時局已然如此,朱光潛認為“現在談美,正因為時機實在是太緊迫了”,“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人心凈化,先要求人生美化。”[4]7較之朱光潛,宗白華則稍顯謹慎與猶疑,不過他也說“徒然提倡實用,不注重精神人格的培養,在這國家危急的時候,流弊也很大。”[2]261而精神人格培養的重要途徑就是美育或人生藝術化,所以“向著這個理想去努力,也不是不可能的,況且古代也不是沒有實現過。”[2]115如此,他們二人才抱一種“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的心態,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勉開人生藝術化之言路。
與宗、朱人生藝術化思想的逆勢“早熟”形成有趣對照,我們可以稍稍提及他們的同代人梁漱溟人生藝術化思想的“晚出”。梁漱溟早在1927年就做過以“人心與人生”為主題的講演,30年代又在山東講過一次,但是由于“九一八”事件和“七七事變”,中國的形勢日益嚴峻,所以他認為“懂人生問題這種沒有時間性的研究寫作之業”就“延宕下來”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這一“延宕”就是近半個世紀,直達1984年才出版同名著作,在其中梁漱溟的人生藝術化思想才得以呈現。[9]梁漱溟人生藝術化思想的晚出,當然是應景的、入世的,而宗、朱二人思想的早熟同樣是另一種應景與入世,區別在于策略的不同。
方東美身處同樣的時態之中,不像宗、朱那樣對當時國家民族命運與社會人心道德耿耿于懷,他一直保持一種冷靜的哲學家的心境,其思考與寫作超越了一時一地的國家與民族問題,直入一種類似于梁漱溟所謂的“沒有時間性的研究寫作之業”中去。這個沒有時間性,也沒有空間性的“業”就是感性文化狀態中的人的生命理想。*由于方東美的論述范圍幾乎囊括了人類東西方文化的歷史與現實,所以僅就人類的范圍而言,他的論題可以說是沒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方東美的人生藝術化思想是他的文化哲學的有機構件,也是他的“宇宙藍圖建筑術”的一個方法。他的“哲學三慧”(古希臘、近現代歐洲與古代中國)其實是文化三型,不過我們看到其中的西方世界是古今完整的,而中國只是半截中國,有古而無今,這表明方東美在無意識中認為從文化上看中國沒有現代史。方東美所以探討文化類型與生命理想問題,實是出于對人自身的憂慮。
方東美認為當時的工業化時代“是一個突變的時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科學與技術支配了人的社會生活,以致人類“幾乎無一處不成問題”,都成了“問題人物”,[10]于是宇宙與人生也就不能相合相應,人類再也“尋不著安身立命之所”,[5]28“與他們的住所捍格不入,備感疏離。”[6]65所以方東美懷著一種濃烈的文化鄉愁向古希臘和古代中國尋求智慧與資源,在那里他發現了理想的生命模式:人類與宇宙的普遍生命渾然一體,浩然同流,生機無限,“足以陶鑄眾美,超拔俗流,進而振奮雄奇才情,高標美妙價值,據以放曠慧眼,摒除偏執,創造浩蕩詩境,邁往真、善、美、純與不朽的遠景。”[6]382此時方東美的“宇宙藍圖建筑術”已經完全實現,此時的人已經進入生命的最高境界,是方東美念茲在茲的“大人”了,這個人同時也是真人、善人和美人。
合而觀之,我們看到在朱光潛與宗白華的人生藝術化思想中都同時包含藝術式的欣賞與藝術式的創造,朱光潛更多的是強調把人生與生活當作藝術品一樣去創造,使之成器,故而其人生藝術化思想是人間的,具實踐論氣質;宗白華更多的是強調唯美的、空想的靜觀態度,故而其人生藝術化思想是藝境的,具想象論氣質。而方東美從文化類型出發,以和諧圓融的生命情調修復現代性社會狀況下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感受,形成美感境界,故而其人生藝術化思想是宇宙的,具存在論氣質。
三、結 語
中國現代的人生藝術化思想的園地中,朱光潛、宗白華與方東美可算是三朵美麗的花,朱光潛熱烈,宗白華雅潔,方東美素淡。他們的人生藝術化思想追求不俗,而又氣質各異。其中朱光潛與宗白華的人生藝術化思想是顯學,論述已豐;而方東美的人生藝術化思想則通常不為人所論及,至多到他的生命美學而止步,我們捅破層紙,把它納入到這個人生藝術化學術史來探討,并打破一般的獨立個案研究的模式,與朱、宗的思想相比較,形成以三人為模范的三種人生藝術化的言說路徑,從而為中國現代的人生藝術化思想研究提供一點討論。
[1] 陳繼法.朱光潛的美學——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M].臺北:臺灣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2]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3]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4]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2.
[5] 方東美.生生之德[M].北京:中華書局,2013.
[6] 蔣國保,周亞洲.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方東美新儒學論著輯要[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7] 方東美.科學哲學與人生[M].北京:中華書局,2013:22-24.
[8]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2.
[9] 王廣州.從藝術到禮樂:論梁漱溟的審美教育思想[J].齊魯師范學院學報,2011(6):11-16.
[10] 方東美.方東美先生演講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3:174,192.
(責任編輯:紫 嫣)
A Comparis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 Three Sages in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on Artistic Life
WANG Guang-zho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Zhu Guangqian, Zong Baihua and Fang Dongmei, three contemporary aesthetes of a same place, came up with differing views of artistic life that touched on aspects such as life, tastes, compassion and sentiments. Yet their differences were not without similarities. The three of them dealt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ir epochs each in his own fashion, resulting in three approaches to exploring ideas of modern Chinese artistic life — the practical, the imaginative and the existential.
Zhu Guangqian; Zong Baihua; Fang Dongmei; artistic life; comparison
2016-11-20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德國古典哲學時期的“在家”問題研究》(15YJC720023)、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點項目《散文與在家:黑格爾美學中的現代性問題研究》(SK2015A381)的階段性成果。
王廣州(1976—),男,江蘇東海人,文學博士,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
B83-0
A
2095-0012(2017)01-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