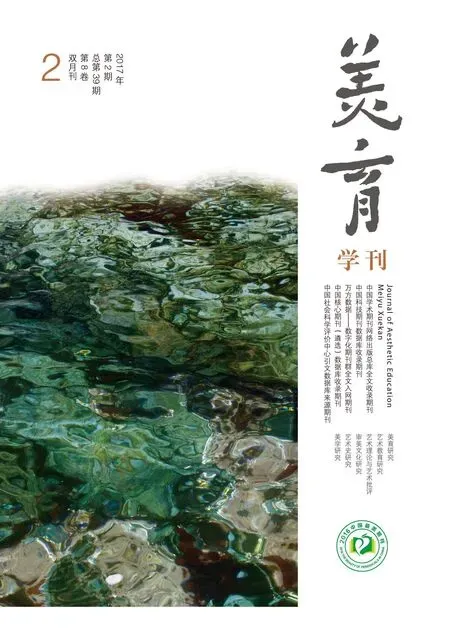“道”的文化闡釋
黃衛星,張玉能
(1.中國科學院 自動化研究所,北京 100190;2.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
“道”的文化闡釋
黃衛星1,張玉能2
(1.中國科學院 自動化研究所,北京 100190;2.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道”字的形義及其演變顯示,其本義似應為“路”,現代漢語中主要衍生出“道路”“道德”“道理”“道義”“道家”“道學”“道統”“人道”“道白”“正道”“道教”等詞匯。從哲學上來看,“道”的本義引申為“途徑”“方法”,再引申為“思想體系”“規律”“原則”“學說”“道理”等;在中國哲學史上道家是與儒家相輔相成的主要思想流派,道家的“道”及其體系影響了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而且在世界上也影響深廣,特別是對西方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說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從倫理學上來看,“道德”“人道”“道義”等概念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和社會導向;中國倫理學史上的宋明理學的“道學”和“道統”曾經對封建社會的穩態發展起著意識形態的鞏固和僵化作用。從美學上來看,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美學思想在“道法自然”的原則下,形成了崇尚自然、追求審美自由境界的美學思想,從先秦時代開始,特別是魏晉時代以后一直影響到中國文學藝術實踐,不斷興起超越政治和道德的功利目的的文藝思潮,與儒家美學思想的政治道德功利目的相抗衡,促進著中國古代文藝的審美自由境界的拓展,尤其是對中國古代的音樂和書法藝術以及唐詩宋詞元曲的繁榮發展起著重要的推進作用。道教是中國古代本土產生的宗教形態,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在朝廷還是民間都發生過重要影響。
道;道路;道德;道理;道家;道教;道學
文字是承載和傳播文化的符號,是人類話語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工具和產品。透過每一個字及其所組成的詞語的形聲義的演變及其闡釋,我們就可以了解這種文字所承載和傳播的文化的具體內涵、獨特特征、變化發展。因此,我們選取一些中華文化關鍵詞來進行一些文字和詞語的詮釋,從一個側面來理解和闡釋中華文化。
一、“道”字的形和義
“道”字的形義及其演變顯示,其本義似應為“路”,現代漢語中主要衍生出“道路”“道德”“道理”“道義”“道家”“道學”“道統”“人道”“道白”“正道”“道教”等詞匯。
關于“道”字的本義,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如是說:《說文》:道,所行道也。從辵,從首。一達謂之道。古文道從首寸。段玉裁曰:“《毛傳》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申為道理,亦為引道。”舜徽按:道之為言蹈也,謂人所踐蹈也。余詳寸部導篆下。[1]李恩江:《常用字詳解字典》說:“道,從辵,首聲,形聲。”下面列出10個義項:道路、通道,量詞,方向、方法、道理,道德,思想體系,道教的,說,以為,等等。[2]顧建平《漢字圖解字典》說:“道,會意字。金文從首(頭),從行,表示供人行走的道路。篆書從辵(像路和腳),從首,亦表示供人走的路。本義是路。”[3]李格非主編的《漢語大字典(簡編本)》列舉了39個義項,主要有:道路,路程,取道,水道,古代棋局上的格道,圍棋局上下的交叉點,門類,行輩,輩分,方位,方法,技藝,宇宙萬物的本原、本體,事理、規律,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舊指好的政治局面或政治措施,道德、道義,道家,道教或道士,說、講述,施行、實行,知道,正直,表示存在,料想、以為,量詞、助詞,等等。[4]宗福邦、陳世鐃、肖海波主編的《故訓匯纂》中列舉了307個義項,主要有:路,道路,說,言,言說,行,行輩,行列,理,道理,天地自然之理,天下之達理,事物當然之理,禮,禮義,禮樂,治也,治理,仁義,德之欽,先王之大道,先王之遺道,直,才藝,道藝,方,術,法術,仙道,自然之道,中和之道,通,德之本,教之本,法之本,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始,萬物之奧,形而上者謂之道,無,虛無,無為,無用而生謂之道,率性之謂道,循性行之是謂道,自然能生天地者,道長,方術之人,謂之,道德教化也,引也,導,導引,行也,通也,開通,達,由,從,順,動也,等等。[5]
根據這些字書,我們可以確定“道”字的本義就是“路”“道路”。“道”字由“路”“道路”分別引申為“途徑”“方法”,再引申為“原理”“規律”“道理”“道德”等等,還引申為“政治主張”“思想體系”,就有“道家”“道教”等,也有所謂“好的政治局面或政治措施”;又從“水道”“河道”引申出“疏通”“引導”“教導”“開導”,由此進而引申出“治理”,如此等等。《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主要列舉了如下的義項:道路,水流通行的途徑,道德,技藝、技術,學術或宗教的思想體系,等等。[6]
二、哲學上的“道”
從哲學上來看,“道”的本義“道路”引申為“途徑”“方法”,再引申為“思想體系”“規律”“原則”“學說”“道理”等等;在中國哲學史上道家是與儒家相輔相成的主要思想流派,道家的“道”及其體系影響了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而且在世界上也影響深廣,特別是對西方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說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道”這個哲學范疇在中國出現得很早,據傳是西周(公元前1036—前771)周公所著而被后世奉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經典《周易》中就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陰一陽謂之道。”(《易傳·系辭》)[7]377,588《周易》作為占卜之書,雖然有了一些中國哲學思想的雛形,但是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哲學范疇及其體系。“道”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的正式規范范疇,應該歸功于老子(約公元前571至公元前471)。老子《道德經》中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7]652老子把“道”作為萬事萬物的存在的本原,所以他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7]654從老子的描述來看,“道”是一種先天地而生的、無形、非物質、不可言說,卻無處不在的東西,這種東西只能是一種人類抽象思維所設想的“無”,因此,把這種精神性的東西(無)作為世界萬事萬物的本原,就應該是一種本體論上的唯心主義。因為這種唯心主義把“道”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實存,所以它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老子的“道”有一點類似于德國古典哲學集大成者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理念)。而且,老子的“道”在生成萬事萬物時,是一種相反相成、相輔相成、相互轉化、不停變化的過程,因而又是充滿了素樸辯證法的過程。老子的辯證法比起黑格爾的“正—反—合”的過程更加符合事物的復雜生成變化的實際狀況。老子的“道”本體論和素樸辯證法與《周易》的“形而上者謂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的生命哲學,對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儒家創始人孔夫子以及儒家的后繼者幾乎都把“道”作為存在之本,不過,老子強調的是“道法自然”,而儒家的“道”更多的是倫理之本。孔子所說的“志于道,據于德”(《論語·述而》)、“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就是指“倫理之道”,即道德和仁政的基本規律和原理。因此,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分別有“天道、人道、地道”,不過,中國思想家很少談“神道”,這大概與老子的“道本體”的非宗教性有關。在西方的宗教思想比較濃厚的文化傳統中,“神道”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基督教中,道就是永恒的上帝。“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中國的“道”的范疇,特別是老子的“道”,不僅影響了中國傳統哲學,而且影響到西方哲學,西方人把中國的“道”翻譯為“Tao”,尤其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晚期引進了老子的“道”,提出了“天地人神”的“四重性”的“詩意的棲居”。他認為,由于傳統的形而上學哲學世界觀,導致了現代的科學、技術、生產,以及暴君、壟斷和集權專制,也就是忘卻了存在,破壞了人與人的世界的統一,人失去了人性,物失去了物性,因而非詩意的居住導致了世界幽暗、萬物消失的可怕景象。人們在消耗著語言和踐踏語言,卻言不及義,思的詩意也被遮蓋了。詩意的遮蓋導致了邏輯、計算、測量的瘋狂肆虐。因而可以說,技術的白晝是世界的黑夜。人已是極度貧乏,出現了種種的存在危機。有了危機就需要拯救。在這貧乏而黑暗的時代,為了人的真正的存在,為了人詩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就必須召喚詩人、傾聽詩人。為什么呢?因為詩人最深切地意識到了時代的貧困,最早發現了時代的神性的遠逝。詩人似乎處在與人、神圣者和短暫者之間,他猶如“在”的信使,神圣者的信使給我們帶來了在的到來和神圣者到來的消息,給我們帶來了存在的顯現和真理的敞亮,能使世界詩化、詩意化。所以,海德格爾勸告世人:“我們這些人必須學會傾聽詩人的言說。”詩人言說的就是詩、藝術,使世界詩化,敞亮了真理,就使人達到詩意的存在,詩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和平、自由、幸福,人有人性,物有物性,萬物同一,具有了天地人神四重性,達到了原始的同一。[8]這種原始的天地人神的統一就是海德格爾從老子的“道”中領悟出來的真正的、本真的“存在”(包括“此在”“思想”“言說”)。
三、倫理學上的“道”
從倫理學上來看,“道德”“人道”“道義”等概念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和社會導向;中國倫理學史上宋明理學的“道學”和“道統”曾經對封建社會的穩態發展起著意識形態的鞏固和僵化作用。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特別是儒家哲學思想,主要關注人、人性、人生等問題,因而與倫理學(廣義的,包括道德和政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往往被稱為“倫理型”哲學思想。《孟子·盡心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莊子·知北游》篇:“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管子·內業篇》:“道也者,……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形勢解篇》:“道者,所以便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正,事君則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文子·道德篇》:“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老子》:“道常無為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管子·君臣上篇》:“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荀子·正名篇》:“道也者,治之經理者。”[7]654-655這些都說明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把“道”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傾向,主要是一種人類本體論或者社會本體論(人生論、政治學、倫理學)的范疇,而主要不是自然本體論(宇宙論)的范疇。因此,在天道、地道、人道三者之中,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最為注重人道,也就是講究人之為人的道理,所以“道”的倫理學含義就被凸顯出來。
“人道”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其哲學含義和倫理學含義是相通的。首先,“人道”是指“人之為人的”基本的規定、原理、途徑、方法之類。《周易·說卦傳》:“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禮記·喪服四制篇》:“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禮記·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道”:“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其次,“人道”即人倫,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次序、等級等的規則、規定。《莊子·寓言篇》:“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成玄英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禮記·喪服小記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再次,“人道”指人間的規律和法則,道家認為“人道”低于“天道”,“天道”是“無為”而“人道”缺失“有為而累”。《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余。”《莊子·在宥篇》:“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7]18由此可見,“人道”在儒家和道家學說中的不同地位。道家把天道看得高于人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656而儒家則主要看重人道。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他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說的“道”主要是指“人道”,即指:人的思想志向或者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然而,道家也還是比古希臘哲學家的自然本體論更加重視人類本體論的“道”。所以,老子說:“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這里的“道”就是指“人道”,即“治理天下”的規律或者方法。當然,老子的“人道”也是要遵循自然規律的,這樣的話,跑馬就可以用于耕種,否則戰馬就只能征戰荒郊,甚至在野外生馬駒。[9]
“道德”一詞是現代漢語中的一個詞,其詞義并不是古漢語“道”和“德”的合取,而是偏重于“德”,指的是:合乎一定準則和規范的行為,或者制約人們共同生活和行為的準則和規范之意識形態。“道義”的含義則是合取了“道德”和“正義”的意思。這些都是“道”字在中國傳統倫理型思想影響下逐步形成的詞語,反映了中國社會和思想意識對于倫理(道德和政治)的重視。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就是強調道德、道義、人道的高度重要性。
儒家講求倫理道德。相傳為孔子得意門生曾子所著述的《禮記·大學》這樣寫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10]儒家就是這樣把道德修養放在了治理家族和家庭,以及治理國家、天下太平的根本基礎之上。自從宋代程顥、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大力提倡以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為了中國人世代相傳的倫理信條。
儒家這種重視倫理道德的思想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形勢下開始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代,儒、道、佛三家競爭激烈。佛家思想流于空想,耽于來世,不務現實大業,并不符合時勢要求,也不符合統治階級的意愿,唐武宗滅佛以后,元氣大傷,以后從未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主要在民間流行。道家思想“無為而治”“小國寡民”不適合于開國以后欲鞏固封建統治的統治者的意愿,卻善于方術技巧小道,成為民間宗教——道教的依據和一部分失意士大夫和隱逸之士的精神寄托。宋朝以后,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相繼退出朝廷,隱入山林。儒家思想則成為封建統治的靈魂和主流意識形態。北宋程顥、程頤以儒家思想為主,吸取了道佛兩家思想的某些方面,創立了理學,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從宋代到明代幾百年間,理學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潮。大概因為理學主要發揚“孔孟之道”,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正宗“道統”,故而又被《宋史》稱為“道學”。理學,以創建者命名稱為程朱理學,以流行時代稱為宋明理學。理學或道學的中心思想是“存天理,滅人欲”,講究心性修養,故而又被稱為心性之學或性理之學。所謂“天理”就是封建倫理,主要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也包括忠、孝、節、義等道德觀念和倫理信條。這種心性之學或性理之學對中國封建社會宋元明清幾百年的超穩定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以封建倫理思想的一整套僵化的“道學”和“道統”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治國理政方略,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統治。比如,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貽害過許多封建社會中的婦女;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就被戴震批判為“以理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封建禮教以及神權、王權、族權、夫權等被魯迅等痛斥為“吃人”的制度和縛人的“封建繩索”。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倫理,倡導科學和民主(賽先生和德先生),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當然,注重個人人格修養和修身養性,充分發揮道德和政治等意識形態的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治理各級社會組織的功能,仍然是一種值得我們今天批判繼承的文化傳統。
四、美學上的“道家”
從美學上來看,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美學思想在“道法自然”的原則下,形成了崇尚自然、追求審美自由境界的美學思想,從先秦時代開始,特別是魏晉時代以后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學藝術實踐,不斷興起超越政治和道德的功利目的的文藝思潮與儒家美學思想的政治道德功利目的相抗衡,促進著中國古代文藝的審美自由境界的拓展,尤其是對中國古代的音樂和書法藝術以及唐詩宋詞元曲的繁榮發展起著重要的推進作用。
老子無疑是道家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創始人,他的《道德經》五千言為整個道家哲學和美學思想奠定了基礎和基調,然而真正使道家美學思想系統化的卻是莊子,他才是道家美學思想的真正代表者。道家美學思想的總根是“道”本體論,其脈絡是“道法自然”“無為”“返璞歸真”,與儒家美學思想的“里仁為美”“興觀群怨”“美善相樂”相反相成、相輔相成,形成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儒道互補的總體格局。道家美學思想的總體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其一,以道為本,道法自然,突出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自然性。正因為如此,老子才在禮崩樂壞的時代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他還指出美的相對性:“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同時他還極力否定那些違反自然本性的東西:“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11]29-30莊子秉承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認為美在自然,他說:“天地有大美而無言”,“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莊子·知北游》)。他否認那些非自然的美,所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莊子·山木》);他也主張美的相對性:“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子·齊物》)莊子也認為各種人為的審美與藝術活動有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發展,主張“擢亂六律,鑠絕竽瑟”,“滅文章、散五采”(《莊子·胠篋》)[11]32-34實際上,道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美和審美及其藝術,而是以自然之美來批判中國古代從原始氏族社會進入階級對立的文明社會大量存在的美與真、善分裂對立,以及以丑為美和追求感官享樂的所謂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其二,以“無為”“虛靜”“逍遙游”為審美境界,彰顯了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超越功利性和精神自由性。道家認為,世俗人們所追求的聲色犬馬之類的感官享受或欲望權勢的恣意妄為,儒家欺世盜名的“仁、義、禮、智、信”之類偽善的實現,都不是真正的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真正的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應該是:顯現“法自然”而“無為”的“道”、超越人間利害得失而達至“虛靜”、不受任何外物所奴役的絕對自由的精神“逍遙游”境界。老子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11]30莊子說:“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莊子·刻意》)[12]226這些都表明道家把超功利的自然無為作為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本質。《莊子·逍遙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12]8道家主張人們要達到這種審美自由境界必須首先澡雪精神,無為、虛靜,就像是“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的“天樂”(《莊子·天道》);又如削木為鐻的梓慶那樣“齊以靜心”,即“坐忘”“心齋”“以天合天”(《莊子·達生》);好像痀僂者承蜩那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莊子·達生》);如同庖丁解牛那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由“技”進“道”;猶如宋史真畫者那樣“解衣般礴”。[11]36-38這些論述和這種超越盡管有些神秘玄虛,充滿了主觀空想和虛幻精神,不免有消極避世之嫌,但是這種超越功利的“無為”“虛靜”和“逍遙游”卻最為恰切地揭示了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本質和特征。其三,以情感之“真”為要務,追求“返璞歸真”的審美本真狀態。道家不像儒家那樣把美當作善的象征,講求“美善相樂”和“比德之說”,而是把“真”作為最高的價值取向。不過,道家的“真”也不是西方美學所謂的科學上的“規律性”,而是情感的真誠和動人。《莊子·漁父》中的漁父答孔子之問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在道家看來,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就應該是那種具有真情實感、能夠動人的自然本真狀態。也正因為如此,老子認為“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第四十一章)。莊子認為“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強調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忘言”。[11]30-41由此可見,道家美學思想更加重視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自然性、超功利性、情感感染性,與重視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社會性、功利性、倫理教化性的儒家美學思想相互作用、互相補充,制約了中國古代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對立統一和繁榮發展。
不過,道家美學思想更多地注重和突出文學藝術的美的規律,形成和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自然天真、含蓄凝練、自由抒情的審美特征。道家美學思想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的自覺意識,這比較鮮明地表現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意識的自覺化,建安文學的繁榮、山水田園詩的興起、完整的文論著作如《典論論文》《文賦》《詩品》《文心雕龍》等不斷涌現、《文選》的編輯出版等等,都是這種文藝和美學的自覺意識的鮮明標志。道家美學思想的真誠動人、抒情至上的觀點,無疑也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的抒情性高于敘事性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大大加速了繼承詩經和楚辭傳統的抒情詩歌的高度繁榮發展,形成了漢賦以后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曲的世界文藝高峰,使得中華民族的文藝的詩詞、歌賦、戲曲等情感瑰寶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獨領風騷。道家美學思想的素樸自然、無為虛靜、情真意切的美學追求,鑄就了中國文學藝術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鏡花水月”“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十四詩品》),“為情造文”“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文心雕龍》),“綺麗不足珍”“垂衣貴清真”(李白)的自然清新、含蓄凝練、情真感人的美學風貌。正是儒道互補的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形成了既重自然天真、無為虛靜、逍遙自由,又重里仁為美、倫理教化、美善相樂的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總體上的“向內求善”的倫理型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滲透了“返璞歸真”“虛壹而靜”“凝神觀照”的審美自由型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二者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綻放出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的璀璨花朵和殷實成果。
五、宗教上的“道教”
道教是中國古代本土產生的主要宗教形態,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在朝廷還是民間都發生過重要影響。
道教由張道陵張天師創立于東漢,興盛于南北朝,故而又叫“天師道”,主要有全真派和正一派等派別。道教崇奉“道”,視“道”為化生宇宙萬物的本原,故名“道教”。它奉玉清教主元始天尊為鼻祖,軒轅黃帝(前2717至前2599)為始祖,老子(老聃,尊稱“太上老君”)為教祖,以《道德經》(即《老子》)、《正一經》和《太平洞經》為主要經典,奉三清(指道教所尊的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境。也指居于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為最高的神。因此,道教也被稱為:黃老、道家。道教觀宮幾乎遍布中國各大名山,湖北的武當山、江西的龍虎山、安徽的齊云山、四川的青城山被稱為四大道教名山。洛陽上清宮是道教第一所國家級道觀。其他著名觀宮主要有:北京白云觀,武當、終南重陽宮,山西永樂宮,西安八仙宮,成都青羊宮,嶗山上清宮,香港蓬瀛仙館,武漢大道觀,龍虎山天師府,等等。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核心內容是神仙信仰,修煉途徑是丹道法術,終極目標為得道成仙、自然和諧、國家太平、社會安定、家庭和睦,修道積德者能夠長生不老、幸福快樂是它的祈求。它根源于中國本土,充分反映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文化積淀,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魯迅曾深刻指出:“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1918年8月20日魯迅致許壽裳)。[13]英國漢學家李約瑟也認為:“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爛掉了的大樹。”[14]178道教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軍事謀略、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國民性格、倫理道德、思維方式、民風民俗、民間信仰等方面,也廣泛影響了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的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它是東方科學智慧之源,它是宗教卻大力促進了科技發展,也是全球最珍愛生命和尊重女性的宗教。
從政治經濟上來看,道教曾經深刻地影響到封建王朝的政權鞏固和經濟發展。歷史上的興盛朝代,如漢朝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在治國方針上大多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儒道互補的策略。唐代的興隆與確立道教為國教有一定的關系,李唐王朝利用與老子李聃同姓宣揚皇權神授,因而尊奉道教,以利政權鞏固。高祖李淵的《先老后釋詔》規定:“全國以道教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太宗李世民再度強調尊崇道教,高宗李治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李隆基親自注釋《道德經》供人學習,命名《老子》為《道德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庚桑子》為《洞靈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科舉考試增設老、莊、文、列四子科,道教之盛達到極致。武宗李炎更是滅佛崇道,使道教廣為傳播。道教“道法自然”“無為而治”“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思想,使得朝廷能夠在改朝換代之初適當輕徭薄賦,垂拱而治,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恢復發展生產,經濟出現繁榮之勢,太平盛世就順勢而成。與此同時,道教流傳民間,給鋌而走險的農民提供了一種思想武器和組織形式,因此,漢末黃巾起義、南北朝李弘起義、元末白蓮教起義、清末義和團運動,幾乎都借用道教教義,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揭竿而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宣傳了道教的治國理政的天道理念和無為方針。因此,道教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特別是促進了大唐帝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
從科學技術上來看,道教以它特殊的方式推進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指出:“道教具有征服自然的精神。”[15]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指出:“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和藥物學都起源于道家。”[14]175道教術數之學利用數學的某些規律,形成了以《奇門遁甲》為代表的象數之術,對數學規律的探索和運用有一定促進,道教的占卦、算命、相面等方術在研究和運用光學、磁學、聲學、天文學等知識方面也有許多特殊貢獻;道教法師的煉丹術、命相術、風水術、占卜術等都與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相關:道士煉制外丹促進了火藥發明,占卜算命、風水符箓等推動了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的發明。道教煉丹師的實踐探究大力促進了冶煉技術及其相關的物理、化學的發展,道教法術師和道士修煉“御風而行”的羽化升天功夫有力推動了機械制造的進步;道教的煉丹術還促成了釀酒、制藥、制造水泥、顏料、豆腐等工藝技術副產品,相傳淮南王煉丹催生了豆腐制造;道教的煉丹術通過絲綢之路西傳到歐洲,豐富了歐洲人的化學知識,促進了現代化學的產生和發展。道教追求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修身養生、練習太極、煉丹成仙,極大地促進了中醫藥學、中國傳統養生學,葛洪、陶弘景、孫思邈、劉守真、傅山、劉一明等中醫藥家都是道術高明的修煉者。中醫藥學和養生學的治未病、天人同構、自然無為、陰陽調和、形神共養、統籌兼顧、丹道修真、服藥煉氣、積德行善、建功立業等思想觀念,都與道教的“尊道貴德,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道承負”“性命雙修,反樸歸真”“清靜寡欲,自然無為”“我命在我,不在天地”等基本教義一脈相通。道教在中國傳統的生理學、經絡學、解剖學、藥物學、性醫學(房中術)、心理學等方面建樹豐碩。養生學的服食(食療)、行氣、辟谷、導引、調息等方術以及內丹學等等,都已經被現代科學證實為有效可行,源自張三豐等道教大師的各種強身健體的太極拳、太極劍、形意拳、八卦掌、五禽戲、八段錦、按摩術等武術氣功,都已成為中國特色的醫藥學、養生學、康復學、武術學、精神治療學的寶貴遺產,并且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和深度傳播。
從學術上來看,道家和道教所衍生的學術思想、學術流派、學術思潮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近代,乃至現代的學術發展。郭沫若認為:“道家思想可以說壟斷了二千年來的中國學術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僅存了一個招牌。”[16]道教大力傳承發揚道家思想,在東漢確立以后先后在中國學術史上產生了魏晉玄學、隋唐重玄學和宋元明清內丹學,是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舉足輕重、不可忽視的學術流派。道教崇奉和宣揚的道家哲學思想,如無中生有、道生萬物的宇宙本體論和陰陽轉化、循環運動的素樸辯證法,在形成中國古代傳統世界觀和方法論思想觀念過程中實乃不可或缺。由此,中華傳統文化的儒道互補成為中華民族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發展的基本規律和趨勢。宋朝理學早期代表周敦頤、張載,理學創立者程顥、程頤,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學術思想與老莊思想、高道陳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道教的宇宙圖式論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從而構建了程朱理學的“天理”體系和“存天理,滅人欲”的基本信條。明朝王陽明的心學也是比擬道家和道教的“良知”說和內丹學,充分融合道教玄學理論和修養方法逐步完善而成。作為本土滋生的宗教,道教始終與外來的佛教不斷斗爭、相互影響,綿延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佛教在東漢初傳時期曾經被視為黃老道教的一個支派,南北朝時佛教借助老莊玄學的勢力和影響得以廣為傳播,也形成了佛道之爭。佛教禪宗之所以能夠最終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以道家思想和道教方法來修正佛教基本教義和修行方式,祛除印度佛教一些繁瑣教義和嚴酷方法,適應了中國廣大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精神寄托和自我解脫的需求,道教的一些神仙方術也滲透浸染到密宗等佛教門派的修行方法之中。這樣佛道兩教相互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儒道互補和儒佛道融合的格局。
從文學藝術上來看,道教所滲透的道家思想和老莊風格塑鑄了中國文藝獨有的恬淡、無欲、隱逸、逍遙之美,熏染了中國文藝追求意境、超越寫實、飄逸神奇的藝術風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深深銘刻著道教和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異方術、逍遙精神、貴生倫理的印跡,浸潤著道家和道教的自然天成情懷、奇妙浪漫情調、標新立異審美,尋找到了一股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精神源泉。南北朝以來的《搜神記》《酉陽雜俎》《聊齋志異》等志怪小說的靈感似乎來源于道家和道教,《枕中記》《太平廣記》等唐宋傳奇中的道家思想和道教元素溢于言表;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情感渲染形成了唐詩的古奧華麗風格,李白等詩人的仙風道骨、瀟灑曠達,山水田園詩的隱逸超脫、優悠逍遙,無不流露出道教的影響和韻味;道教的語詞和樂曲給宋詞提煉出大量的詞牌樂譜,如《漁家傲》《如夢令》《鵲橋仙》《憶江南》《憶秦娥》等等,蘇軾等的詩詞風流倜儻、無為灑脫,都流淌著道家風韻和道教格調;元代清新隱逸、幽怨狂放的小令,神仙飛升、神奇夢境的戲曲,以道家和道教的方式宣泄了異族統治下的冤情憂憤;道教神學思想浸潤了“三言二拍”《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明清小說,“智者形象道士化”成為明清小說的不二法門。道教文學形式的衍生,比如李白的游仙詩、明朝盛行的青詞,以及《封神演義》《西游記》《聊齋志異》等神魔小說,都與道教的興旺發達密不可分;這類道教文學形式甚至影響到當代流行的以丹道為主題的修真小說、玄幻小說、盜墓小說、仙俠小說等等。中國藝術追求寫意、神似、自然的風格和神韻的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情趣,似乎都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美學思想的精彩表現。中國繪畫書法藝術史上不乏深受道家思想和道教教義影響的藝術大師,例如王羲之、顧愷之、吳道子、趙孟、黃公望、祝枝山、徐渭、朱耷、鄭板橋等等。京劇、越劇、豫劇、黃梅戲等中國傳統戲曲都充分利用、融合、移植道教音樂的曲調、唱腔,道教音樂幾乎全面促進了中國傳統音樂戲曲的繁榮發展。道家和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風水堪輿道術在中國傳統建筑(包括宮殿、民宅、陵墓)的選址、布局和建造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風水學說和風水先生的職業,除去其中的某些封建迷信和故弄玄虛的成分,對于今天的環境科學和建筑科學都有許多借鑒的遺產,可以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道教所宣揚的道家思想和信仰極其強有力地塑造了中國國民性格,在民族心理、倫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周作人認為:“平常講中國宗教的人,總說有儒釋道三教,其實儒教的綱常早已崩壞,佛教也只剩了輪回因果幾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還流行民間,支配國民思想的已經完全是道教的勢力了。照事實看來,中國人的確都是道教徒。”(《鄉村與道教思想》)[17]許地山也說過:“從我國人日常生活的習慣和宗教的信仰看來,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們簡直可以說支配中國一般人的理想與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家思想與道教》)[18]道教對“道”的信仰達到了唯道是求的真誠,這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中國官民一齊刻苦修煉,為求得道升天而知行合一,不懈奮斗;道教的樂生貴生、灑脫逍遙、無欲無爭的精神,培育了中國人民務實求真、愛生樂活、安貧樂道的品德;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剛、反者道之動的素樸辯證法思維,塑造了中國人民寬宏大量、內斂含蓄、無為而無不為的性格;道教陰陽協調、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決定了中國人民順應自然、審時度勢、反樸歸真的志趣;道教崇尚“知常容,容乃公”的準則,造就了謙讓包容、兼收并蓄、寬厚開放的民族素質,不僅促成了恢弘漢唐氣象,還促使中華文明綿延不息。道教不僅“尊道貴德”,而且也講“忠孝仁義”,以德進修,以道成仙,勸人為善,深刻影響了中國人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道教尊崇始祖軒轅黃帝,形成了海內外華人尊黃帝、認祖宗、大一統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道教廣泛吸收、改造民間神話傳說,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道教神仙譜系和民間信仰。例如,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關公忠義、媽祖顯靈、慈航真人變身觀音、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玉皇大帝封神榜、王母娘娘瑤池會等等。道教信仰的許多方面深深積淀在中國的傳統民俗里,影響著信仰習俗、祖宗崇拜、節日習俗、娛樂習俗和方術活動。例如,本命年拜太歲,祭祀先人燒紙錢,春節祭灶王、貼對聯、放鞭炮、接財神、拜天公、鬧元宵,這些習俗都與道教信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有許多是值得我們批判繼承的東西。
道教廣泛流傳于東亞、東南亞,影響深厚:道教深深滲透于日本的神道教、天皇信仰、民間信仰,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韓國天道教、20世紀20年代創立的越南高臺教都是在道教基礎上形成的,道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信徒也有很多而且分布社會各個階層,成為一種重要的民間宗教勢力。道教經典《道德經》的歐美各國文字譯本多達近500種,《道德經》歐美文字譯本發行量排名第二,僅次于《圣經》。《老子》《莊子》等道家思想不僅給康德、尼采、黑格爾、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巨大啟迪,而且也使萊布尼茨、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受益匪淺,還賦予卡夫卡、托爾斯泰等文學家想象和靈感,同樣獲得了里根、梅德韋杰夫等政治家的青睞和眷顧。道教文化的內丹養生、星相占卜、風水堪輿、醫藥療法、房中之術等等已經風靡全球,太極拳、太極劍、形意拳等以柔克剛的武術運動在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為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海外已有1.5億多人習練太極拳強身健體。道教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給世界各國環保主義者許多有益的啟示和思考,道教文明將惠及全球全人類。
[1] 張舜徽.張舜徽集·說文解字約注:第3冊[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426.
[2] 李恩江.常用字詳解字典[K].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185.
[3] 顧建平.漢字圖解字典[K].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890.
[4] 李格非.漢語大字典(簡編本)[K].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6:1744.
[5] 宗福邦,陳世鐃,肖海波.故訓匯纂[G].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299-2302.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K].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80-282.
[7]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K].臺北:水牛出版社,1993.
[8] 張玉能.西方文論教程[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342.
[9] 崔仲平.老子道德經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50-51.
[10] 大學·中庸[M].北京:中華書局,2006:4-5.
[11] 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冊[G].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 孟慶祥.莊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13] 魯迅.魯迅文集導讀本·第23卷·文藝書簡:上[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7.
[1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2.
[16] 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人民出版,1954:162.
[17] 周作人.談虎集[M].上海:上海書店,343-344.
[18] 許地山.道教史[M].劉仲宇,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1.
(責任編輯:紫 嫣)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ao"
HUANG Wei-xing1, ZHANG Yu-neng
(1.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he morphological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道" Tao points to its original meaning of "路" which means a road and from which a host of other words are derived in modern Chinese, such as "way", "moral", "truth", "justice", "Taoism", "Confucianism", "humanity", "spoken parts in an opera", "the right way", "doctrines and principles" and etc.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ao" is first extended to "way"and "method" and then to "ideology", "law", "principle", "theory", "truth" and so 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are two opposing and yet complementary schools of thought. The Tao of Taoism and its system have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China, but also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Heidegger. From the ethical point of view, "morality", "humanity" and "justice" are norms and orientations which all mankind is subject to.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Neo Confucianism, an orthodoxy ideology in Song Dynasty, 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eventual rigidity of the feudal society. From the view of aesthetics, Taoist aesthetic thoughts, typified by Lao Tzu and Chuang-tzu and holding "imitation of nature" as the acme of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mergence of an aesthetics that advocates nature and seeks aesthetic freedom. Since the pre-Qin era, especially after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aesthetics has influenc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actice in China, bringing about artistic movements that transcend political, moral and other utilitarian concerns characteristic of the rival Confucian aesthetics and expanding the horizons of aesthetic freedom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especially in ancient Chinese music, calligraphy,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drama in Yuan Dynasty. As an indigenous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Taoism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feudal China, whether in the court or in society at large.
Tao; road; moral; truth; Taoist School; Taoism; orthodoxy Confucianism
2016-12-14
2014年財政部中央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項目《漢字數字化技術產業應用項目——漢字數字化文化體驗館第一期工程》(2014-126)和2015年科技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公共數字文化全國共享服務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示范》(2015BAK25B00)的研究成果。
黃衛星(1974—),女,湖北蘄春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博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博士后,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和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文化傳播、文化軟實力、文化創意產業等研究;張玉能(1943—),男,江蘇南京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美學、西方美學、西方文論、文藝學等研究。
B83
A
2095-0012(2017)02-0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