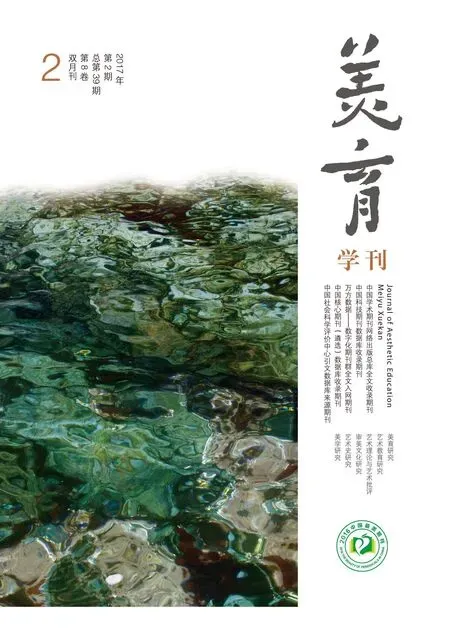按自然本身來欣賞
——西方當代自然美學到環境美學的轉折與發展
聶春華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303)
?
按自然本身來欣賞
——西方當代自然美學到環境美學的轉折與發展
聶春華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303)
按自然本身來欣賞,即掙脫傳統自然美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藝術欣賞范式,按照自然審美欣賞自身的特點去為它尋找新的合法依據,是20世紀后半期西方傳統自然美學向環境美學轉折的根本訴求;無論是環境美學中的認知派還是非認知派,這兩種最重要途徑的共同目標都是試圖挑戰傳統美學的藝術欣賞范式并確立自然審美欣賞自身的特質;在對傳統自然美學觀構成挑戰的同時,它們自身的知識形態的建構也預示了美學未來發展的某些重要可能。
自然美學;環境美學;科學認知主義;審美參與
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和美學理論自身的變革促成了西方當代傳統自然美學向環境美學的蛻變,如果用一個主題來概括這種蛻變,那么“按照自然本身來欣賞”,即從藝術欣賞的舊范式中掙脫出來,按照自然本身的性質和特征來欣賞自然,按照自然欣賞本身的性質和特征來構建自然的欣賞理論,構成了環境美學有別于傳統自然美學最鮮明的口號。
一、按照自然本身來欣賞的兩種途徑
環境美學的興起可以追溯自羅納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20世紀60年代一篇極富前瞻性的論文《當代美學及其對自然美的忽視》,他在這篇論文中提出的觀點啟發了后來環境美學中認知主義和非認知主義兩種最重要的途徑,而這兩種途徑毫無例外都對傳統自然美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藝術欣賞范式不滿,并尋求適合于自然本身的審美欣賞方式。在這篇論文中,赫伯恩認為藝術作品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是其帶有“框架”,如繪畫或雕塑都有其物理邊界;而自然則是“無框架”的,在自然欣賞中各種不可控制的聲音或視覺等因素會不斷地進入,并試圖整合進我們的整體經驗中。因為自然審美欣賞可以不受這些“框架”的束縛,因此更容易實現一種開放性的和參與性的欣賞模式;赫伯恩強調“框架”的缺失并不意味著自然界的審美缺陷,它實際上構成一種和藝術欣賞不同的但同樣值得嚴肅對待的審美經驗的來源,因此我們需要按照自然本身之所是而不是根據藝術來認識自然真實的審美本質。
赫伯恩上述觀點對環境美學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直接啟發了環境美學中兩種最重要的途徑:一種是以阿諾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為代表的環境美學非認知派,把身心參與、感知想象和情感涉入等非認知因素作為環境欣賞的核心,這種途徑與赫伯恩所說的自然有助于形成開放性的和參與性的欣賞模式有很密切的關系;第二種是以艾倫·卡爾松(Allen Carlson)為代表的環境美學認知派,強調環境欣賞需要接受來自自然科學知識的引導,這種途徑直接來源于赫伯恩所說的自然審美欣賞是嚴肅的而且必須認識自然的真實本質的觀點。*Ronald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in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eds.),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Broadview Press, 2004:47.關于赫伯恩的環境美學思想及其對卡爾松和伯林特等人影響的具體論述,見拙作《羅納德·赫伯恩與環境美學的興起和發展》,載《哲學動態》,2015年第2期。
卡爾松繼承了赫伯恩要認識自然真實本質的觀點,認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自然是環境并且它是自然的,而且要把這種認識作為我們審美欣賞的核心。這樣我們就會按其所是并依據其性質來審美地欣賞自然”[1]51。按其所是并依據其性質來欣賞自然,這在卡爾松看來就是要正確認識自然并把對自然的欣賞建立在這種認識之上,能夠充當這種知識的只有關于自然的科學知識,比如應該把鯨魚當做哺乳動物而不是魚來欣賞。他通常通過自然欣賞與藝術欣賞之間的類比來強化科學知識的合法地位,因為在藝術中嚴肅的、適當的審美欣賞往往是通過藝術史傳統和藝術批評這些知識在認知層面上加以塑造的,比如缺少立體主義的藝術史知識我們很難正確理解《亞威農少女》那種破碎畫風的意義,卡爾松認為在自然中嚴肅的、適當的審美欣賞也必須通過自然史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在認知層面上加以塑造。日本學者齊藤百合子(Yuriko Saito)與卡爾松一樣,強調科學知識能夠提供最負“責任”的自然審美欣賞,她說:“嘗試按其所是來理解自然,也就是不涉及人類存在和介入來理解自然。我相信,這樣的嘗試構成了自然科學與其他話語(通常是本地的民間傳說和神話)的基礎。我認為帶有這種考慮的自然審美欣賞為我們提供了最負責任的按照自然本身而來的欣賞。如果需要一個更好的術語,我稱之為自然的科學欣賞。”[2]146瑪西婭·伊頓(Marcia Eaton)則從另一角度呼應了卡爾松的立場,她強調想象和虛構在審美上雖有積極的意義,但如果不和科學知識結合則有可能淪為主觀臆斷并對自然造成傷害,比如濕地和沼澤常常因被想象為丑陋之地而失去了保護,因此想象和虛構“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生態學知識基礎上并與之相協調,還要接受生態學知識的指導而變得充實”[2]177。
赫伯恩關于自然欣賞具有開放性和參與性特點的論述啟發了環境美學的非認知派途徑。比如阿諾德·伯林特的審美參與理論,強調自然具有開放性的結構特征,可以引發欣賞者對自然產生全方位的、多感官參與和沉浸的審美體驗。艾米麗·布雷迪(Emily Brady)直接說卡爾松那種“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模式是錯誤的,以科學知識作為自然審美欣賞的導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提出另一種非科學基礎上的途徑,這種途徑在指導審美欣賞時以感知和想象為中心”[2]156。比如欣賞波浪的曲線,我們只依賴于感知和想象,卻不必知道波浪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她主張一種非科學認知立場的審美感知和想象論。諾埃爾·卡洛爾(No?l Carroll)也認為存在一種非科學的自然審美欣賞立場,這種立場他稱之為“情感喚起”(emotional arousal)模式,就如同在雷鳴般的瀑布前被其宏偉所感動那樣,卡洛爾認為這種被喚起的感動并不需要科學范疇的指導。此外,雪莉·福斯特(Cheryl Foster)提出自然環境具有一種“環繞維度”(ambient dimension)的審美價值,這種審美價值具有尚未知識化、理論化的形式,“它暗示一種被環繞,或被融合的包圍、參與的可察覺感,但這種環繞的所有形式拒絕語言的表達”[2]206。這表明雪莉·福斯特在自然審美欣賞問題上同樣具有非科學認知主義的立場,她傾向于把環繞的、被包圍的、參與的感覺視為自然審美欣賞的核心。
環境美學的認知派和非認知派是在環境美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兩種最重要的途徑,前者強調自然欣賞中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后者則賦予參與、想象、直覺等因素更重要的地位。實際上,無論是強調自然科學知識,還是強調想象、情感和直覺等體驗,環境美學都有意地將自然欣賞和藝術欣賞區別開來,從自然欣賞自身的特點去為它尋找新的合法依據,這是20世紀后半葉傳統自然美學能夠向環境美學轉折的根本原因。
二、對“如畫性”藝術欣賞范式的挑戰
環境美學所要挑戰的這種藝術欣賞范式是什么?確切地說,環境美學并非要否定藝術欣賞的既定慣例和特征,而是要反對那種以藝術欣賞范式主宰自然審美欣賞的習慣。
藝術欣賞是以視覺和聽覺為主要感知方式的。西方傳統藝術作品的框架、作者意圖、欣賞方式等都要求隔離和集中欣賞者的注意力,導致藝術欣賞活動中欣賞者的感知結構越來越被化約為視覺和聽覺的專利。自18世紀康德的無利害美學觀誕生以后,這種感知結構被一再強化,導致其他感知要素,如觸覺、嗅覺、味覺等,被視為和審美愉悅無關甚至是妨礙獲得審美愉悅的因素。這種藝術欣賞方式也導致遠距離靜觀成為其突出的表現特征。西方傳統的藝術作品經常掛在博物館、藝術館、畫廊的墻壁和展臺上,有些作品甚至懸掛在天花板甚至屋頂上,這種遠距離的靜觀欣賞方式阻止了我們和藝術品的實質性接觸,因此在感官感知中將觀照對象的物質性降到了最低,使之成為視覺或聽覺體驗中的純粹意象。傳統美學關于自然審美欣賞的思考主要受這種藝術欣賞范式的主導,更傾向于將自然視為某種審美靜觀的對象,用遠距離的特定的視角或者固定的觀景點去欣賞自然,這實際上是用藝術欣賞那種帶“框架”的方式去欣賞自然,而自然那種“無框架”的性質則被忽視掉了。
傳統自然美學的這種遠距離靜觀模式排他性地把視、聽兩種知覺作為審美的專屬感覺,因此對其他感知感覺構成了壓制性的作用,看似自由的審美活動其實成為“有選擇的欣賞”,正如齊藤百合子所說:“這種對視覺設計的排他性強調造成了我們有選擇地欣賞,使我們只欣賞那些與視覺有聯系的興奮、有趣、享樂或愉快的部分。”[2]143這種排他性的感知方式最終促成無利害靜觀美學形成了一種壓制性的話語模式,即按照藝術欣賞范式來感知和欣賞自然。“如畫性”(picturesque)這個概念集中體現了這種自然欣賞模式。卡爾松說:“這個術語按字面理解也就是‘像畫一般的’,并暗指一種欣賞的模式,通過這種模式自然界被分成不同的風景,每種風景都指向一種由藝術確立的理想,尤其是風景繪畫。”[1]45這種模式幾乎主宰了西方18世紀的自然審美欣賞,而經過這種模式過濾的自然,實際上是按照藝術欣賞范式來切割過的自然。傳統美學意義上的自然風景變成了在視、聽知覺中展開的“二維”景觀,而欣賞者也變成了靜態的、脫節的和隔離的旁觀者。
環境美學要消解傳統美學中的藝術欣賞范式并確立自然審美欣賞自身的特質,就必須觸及這種排他性的感知結構以及作為其延伸的如畫性觀念。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環境美學的認知派還是非認知派,都試圖挑戰傳統美學這種藝術欣賞范式的霸權。這種挑戰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問題上:
(一)身體化審美問題的凸顯
環境美學要顛覆傳統美學那種遠距離靜觀方式,其結果必然是走向身體的在場和諸感知的聯合。在這方面伯林特的審美參與理論是最典型的,他吸取實用主義哲學的經驗論和現象學的知覺理論,主張環境審美是身體在場的審美,并涉及所有感官感覺的聯合合作。所謂身體在場,意味著不再像遠距離的靜觀模式那樣將身體的實質性接觸排除在審美場之外,在場即意味著欣賞者與欣賞對象之間距離的消失。傳統美學那種遠距離的靜觀模式,帶來的是剝離物質性的意象和沉思,其本質是非物質和非肉體的。在伯林特看來,審美過程即意味著通過各種感知和環境交流溝通,審美的反饋將直接作用于人的體驗并給人帶來實質性的影響,物體的質感、空氣的濕度、水流的溫度等等,會或隱或顯地改變身體的內在系統和適應性,重塑身體在環境中的感知活動和習慣。環境感知的豐富性會不斷挑戰欣賞者的審美接受,造成引人注目的不可預知的感知驚奇,正是通過這種持續性的身體重塑行為,欣賞者不斷調整自身感知的限度,最終實現感知者與被感知者的和諧。身體在場同時也意味著審美是多感知的體驗,欣賞者不僅要看、要聽,還要通過各種感官來感受,用手、用腳去感受土地的質感,用皮膚去感受風和陽光的觸摸,用呼吸和嗅覺體味空氣的濕度,不再是視、聽知覺主導審美過程,各種感知感覺都參與了進來。伯林特因此強調了身體各種感覺樣式的全面統一,并實現了對傳統美學那種等級化的感知結構的顛覆。
(二)審美相關性問題的凸顯
對于卡爾松的科學認知主義來說,強調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才是根本性的,在這方面他把能否視知識與審美相關作為科學認知主義和傳統美學的區別。在他看來,關于審美相關性問題,傳統美學提供了一個相當保守的回答,即認為凡是感官感覺以外的東西很少是與審美相關的,這一貧乏的答案基于現代美學最基本的兩種哲學主張:無利害與形式主義的教條。就前者而言,它“典型地涉及一種特殊的態度或心靈狀態,根據此態度或狀態觀賞者對欣賞對象保持淡漠或維持一定距離。這種態度或狀態因此給予一種審美相關性的標準,其特征在于規定一種欣賞的模式,在其中無論是欣賞者還是對象都是孤立的,都與整個世界相分離。因此,恰當的審美欣賞與不在對象本身中呈現的東西相分離,外在于對象的知識也就被視為和這種欣賞無關”;而形式主義“根據形狀、線條和顏色的形式關系提供一種關于藝術的本質主義分析,這些形式關系典型地宣稱能喚起欣賞者的一種特殊的情感。而且,形式主義對藝術中的這種本質性的形式維度與其他維度進行了嚴格的區分。藝術和它的欣賞被限制在它自身的世界中,只與它自身的情感有關,而和整個世界無關。從這個外在世界中欣賞者不能帶給欣賞對象任何東西。恰當的審美欣賞再次與不在對象本身中呈現的東西相分離,外在于對象的知識也再次被視為和這種欣賞無關”[1]130。在這種無利害學說和形式主義的支持下,傳統美學對審美相關性問題采取了純粹主義的回答,凡是不在對象本身中呈現的東西都被視為與恰當的審美欣賞無關,這就把關于對象的諸多思想、意象、聯想和知識排除在了審美欣賞之外。卡爾松對審美相關性問題的重視,目的是為自然審美欣賞中的科學知識正名。為了追尋自然欣賞對象的真實本性,卡爾松認為由自然學家、生態學家、地質學家和自然歷史學家等提供的知識都與自然審美欣賞有關。
三、類比與置換
我們把類比和置換視為環境美學認知派和非認知派建構自身知識形態的不同方法,其中涉及的是環境美學中最基本的關于藝術和自然關系的看法。無論是認知派還是非認知派,實際面對的都是自18世紀以來漸趨僵化的傳統美學范式,它基本上是以德國古典哲學為知識框架,以藝術欣賞作為其理論研究的核心典范,這一學科形態迄今還主宰著美學領域大部分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的生產。在傳統美學中,自然欣賞往往構成了這種以藝術欣賞范式為核心的學科體系最難解決的問題,環境美學直接面對的就是傳統美學中這個最難解決的問題,而它能在20世紀興起,借助的也就是要為自然審美欣賞的合法性正名。正是這種學理背景的存在,對環境美學基本問題的解答就不僅涉及我們對自然審美欣賞的重新理解,也必然要對既有的美學學科形態構成根本性的挑戰并涉及美學未來發展的可能。
以柏林特為代表的非認知派其實并沒有把藝術欣賞和自然欣賞視為兩種不同性質的審美欣賞,在挑戰傳統無利害靜觀美學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提出一種替代性的理論,這種理論能夠代替無利害的靜觀美學對藝術和自然作出統一的解釋。伯林特的參與美學并非來自其環境美學研究,而是來自他早年的審美經驗現象學和藝術參與思想,因此他提出的審美參與這個概念始終貫穿在他關于藝術欣賞和自然欣賞的全部研究中,這個概念針對的主要是占主導地位的無利害靜觀范式而不是藝術欣賞范式。伯林特說:“為何把環境作為一種美學的范式?這當然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即使環境美學有其獨有的特征,有理由把它擴展到其他的藝術中去么?至少可以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任何模式的價值在于其啟發性和說明性的力量。把環境的審美經驗作為標準,我們就會舍棄無利害的美學并支持一種參與的美學。參與的思想不僅可以用來解釋像建筑和舞蹈那樣讓人感到棘手的藝術經驗,它還使我們重新思考與其他藝術共有的欣賞經驗。在繪畫、音樂、戲劇和雕塑這樣的藝術中,我們開始意識到無利害美學通過把欣賞限制在陳腐的窠臼中而把我們的欣賞狹隘化了。雖然這些藝術形式仍有各自的力量,但這些力量受到限制并帶有局限。參與的思想使這些藝術進入一種開放性中,超越了通常主客之分的局限,鼓勵我們在一種審美的情境中建立相互參與的關系,這種關系使藝術品和感知者在一個整體中結合起來。”[1]157-158這段話很清楚地顯示了伯林特參與美學的思路,即通過置換的方式用審美參與理論代替無利害靜觀理論。在傳統美學范式中,如果說占主導地位的解釋模式是無利害美學觀,那么在伯林特的參與美學中,審美參與成為了解釋自然和藝術的共同范式。伯林特因此將其參與美學打造成為和傳統美學一樣具有普遍解釋力但立足點不同的普遍美學。
以卡爾松為代表的認知派則普遍把區分自然欣賞與藝術欣賞作為立論的前提。基于對藝術欣賞范式獨占作用的質疑,從赫伯恩到卡爾松都強調需要按照自然本身而不是根據藝術來認識自然真實的審美本質,這是卡爾松科學認知主義路線的根本出發點。但卡爾松也并非把自然欣賞與藝術欣賞截然對立起來,而是用兩者之間的“類比”模式代替了傳統美學用藝術欣賞“同化”自然欣賞的舊模式。在卡爾松看來,既然藝術欣賞離不開藝術史等背景知識,那么自然欣賞也需要強調知識在審美判斷上發揮的作用,而在這里發揮作用的當然不是藝術史知識,而是自然的科學知識。卡爾松的科學認知主義路線在拋棄藝術范式同化作用的同時也弱化了自然與藝術之間的統一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他那里沒有對涵蓋自然與藝術的普遍美學的渴求。與伯林特的參與美學對普遍美學的顯豁追求不同,在卡爾松這里對普遍美學的追求是通過結構上的相似而隱晦地表現出來的。既然藝術欣賞和自然欣賞能夠通過類比的方式聯系在一起,那么其實也預先設定了兩者之間存在某種結構上的相似,而這種相似性正是隱含在卡爾松科學認知主義路線中的普遍性追求。因此,雖然自然欣賞需要依賴自然科學知識,藝術欣賞需要仰仗藝術史知識,但兩種審美欣賞在結構上的相似性預示了卡爾松意義上的普遍美學是需要根據科學知識來定義的,科學知識(無論是藝術史知識還是自然知識)是一個能夠容納自然和藝術在內的更大的美學的普遍性的保證。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認知派還是非認知派,它們在對傳統的無利害美學觀構成挑戰和解構的同時,其自身知識形態的建構也預示了美學未來發展的幾種可能。那么,審美參與或科學知識能否成為未來新美學的生發點,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美學自身的發展。雖然每種美學立場都可能暗藏著它對美學普遍性的追求,但我仍然將更寬泛意義上的普遍美學視為時間和空間流變中的未完成態。美學上的理論總是隨著人類審美經驗的擴展而發生變革的,人類的審美經驗不斷發生變化,因此所謂美學的普遍性追求總是指向遙遠的未來。19世紀的美學可能無法理解立體派、達達主義、波普藝術那種對它們來說有些怪異的審美經驗,但20世紀的美學卻無法不把這些藝術領域產生的變化作為自己需要嚴肅思考的對象了。20世紀環境的惡化與環境危機的出現,促使人們更多地將目光放在環境上,而環境藝術、大地藝術、景觀藝術的出現又不斷拓展人們藝術體驗的界限,環境美學的出現其實是人類審美經驗變化發展的產物,它的出現也預示著傳統以藝術體驗為核心而建構的美學體系隨著人類審美經驗的擴展而產生變革。因此美學的普遍性既然是以涵蓋人類審美經驗的整體作為自身的訴求,那么人類審美經驗的變化發展也決定了它不會有一個最終的模式。美學是不斷發展的,其普遍性也只具有暫時的意義,對于美學普遍性的理解同樣也是發展和變化的。
正是在此意義上,普遍美學只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它是美學的邏輯終點而不可能真正達到,但其意義就在于對這種普遍性的追求可以成為美學自身不斷變革的動力,成為美學不斷適應變化的審美經驗而拓展自身的最終目標。由此看,無論是伯林特的審美參與理論,還是卡爾松的科學認知主義途徑,或是其他環境美學家的觀點,它們在為自然審美欣賞本身確立合法性的時候為我們貢獻了未來美學的幾種可能形態,但同時也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語境和限定,它們的意義在于為我們重新解釋不斷變化的審美經驗并接近最終的普遍美學提供了新的模式,但若是把這些模式固定為美學最終的形態則剝奪了審美經驗這種變化的本性,并讓美學的普遍性最終失去了它得以存在的意義和它所能激發的那種變革動力。
[1] CARLSON A. 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M]. Britain: Routledge Press, 2000.
[2] CARLSON A, BERLEANT A.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M]. Canada:Broadview Press, 2004.
(責任編輯:紫 嫣)
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 Turn and Development from Natural Aesthetics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NIE Chun-hua
(Chinese Departr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303, China)
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 which means being free from the dominant appreciating paradigms in traditional natural aesthetics and seeking a new legitimate basis according to nature′s own featur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urn from natural aesthetics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Whether it is the cognitive or non-cognitive approach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ey share the goal of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appreciating paradigms and establishing the features of natural aesthetics. While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ppreciating paradig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own forms of knowledge also indicates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natural 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ognitive approach; aesthetic engagement
2016-12-17
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環境美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研究》(13CZX083)、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環境美學史研究》子課題《明代環境美學研究》(13&ZD072)、廣東第二師范學院教授專項《當代環境美學的歷史圖景與實踐價值研究》(2015ARF23)的階段性成果。
聶春華(1978—),男,廣東韶關人,博士,廣東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美學和文藝學研究。
B83
A
2095-0012(2017)02-0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