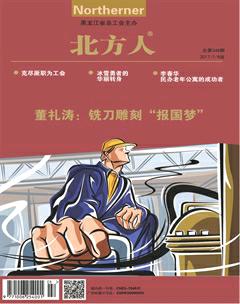媽媽用自己的飯菜送你去山川湖海
倪一寧
大學期間去臺灣交流,回家那晚,一桌人吃飯,我半年未見韭菜炒蛋黃桂花糖醋小排,幾次立起身來,頻頻夾菜,吃到興頭上,親戚問我:“好吃吧?在外面,是不是特別想念媽媽的手藝家常的味道?”
只要點個頭就能蒙混過關的問題,我偏偏擱下筷子,頑固地搖頭:“不不不,挺想家的,但不想我媽做的菜。”
如果你也有一個可以理直氣壯喊“哎喲下班了累死了”的媽媽,你就一定見識過傍晚六點兵荒馬亂的廚房:擇了一半的芹菜攤在案板上,活蝦被悶在黑色袋子里,時不時動兩下,熱鍋上噼里啪啦炸響的,是酸辣土豆絲,我媽邊燒菜邊收拾,右手拿著鏟子,左腳踩著抹布,低頭那兩下工夫,就把濺到地板上的油漬擦去了。難吃歸難吃,童年的我還是無數次拿著一包薯片,無限期待地守在廚房門口,也無數次被我媽差遣——“去幫我切兩根蔥好伐”“水水水”“你能不能不要吃零食了,待會飯么不要吃,你健康一點兒好不好啦”。
好的呀,那你菜燒得好一點兒啊。我捏著空空的薯片袋子,對著她的背影扁了扁嘴。
其實我們嘗試過很多改良方案。有一兩年,是請了個阿姨在家燒菜,但我們到底經不住她重油重鹽的攻勢。奶奶偶爾來小住,會燉了紅燒肉烤了玉米烙在家等,但花樣換來換去,都是爸爸愛吃的菜式。再后來,我建議集體訂外賣,被我媽迅速否決,她就像晚清朝廷一樣,既拒絕外援,也不肯改革,既想捍衛圍著桌子吃熱菜的傳統,又無力支撐時局,幸好只要大門一關,她也是我們這個小小政權的老佛爺。
碰上長假回家時,我也樂意下廚房。跟我媽開辟鴻蒙的氣勢不同,我謹遵食譜教誨,連放多少面粉,都要放到小托盤上稱一稱。但我做菜的次數仍然屈指可數,一則耗時太長,效率太低。二則我每次都會被刀背磕到,被烤箱燙到,我爸看著端出來的蛋撻,和我哭哭啼啼展示的小小疤痕,常有吃人血饅頭之感。
在臺灣半年,有時碰到咬一口就能有一汪油的雞排,我也會想起我媽的拿手菜。這次回來,廚房里仍然兵荒馬亂,不時響起“水水水”“給我遞蠶豆過來”“哎呀你不要擋著我呀待會焦掉了怎么辦”,不像做菜,倒像修長城,分秒必爭,眾志成城。她看到我手里托著個車厘子的盤子,又蹙起眉頭:“你怎么一直這樣的,正餐不吃,零食不停。”
我嬉皮笑臉地抱住她:“我開開胃呀,等你的響油鱔絲。”
是在臉貼到她的羊絨衫的瞬間,我突然意識到,無聲無息地,她也妥協了。我媽現在做菜手藝越來越精湛了,飯桌上常提的是股票和折扣,很少再說單位里的人事變動。她穿暖色調的大衣,而我小時候,印象中的媽媽,是衣柜里一色黑白灰職業裝的人。
不進則退,她選擇了退守廚房。
萬青有句著名的歌詞,問“是誰來自山川湖海,卻囿于晝夜、廚房與愛”,說到底,志短只因情長,能把人困在廚房的,從來也只是愛。童年里的媽媽,頻繁出差,莫名其妙地走了大半個中國,導致我小學時學唱《魯冰花》,唱到“閃閃的淚光魯冰花”時,共鳴到落淚。后來我媽的山川湖海,成了寧波新寄來的帶魚,山上剛挖到的竹筍,哦,還有我的行蹤。她成了上班時關心創業板走勢,下班后替我熬烏骨雞湯的人,看著她熟稔地捏起鍋蓋的側影,我也覺得沒必要再細問,提前回家做飯等我們的時候,心底會不會有一點兒凄惶。
要怎么問呢?所有的媽媽們,好像都不擅長邀功,不擅長自我標榜為家庭犧牲,她們寂寞又專注地打理廚房,烤出一籠又一籠噴香的面包,目送你去更邈遠的山川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