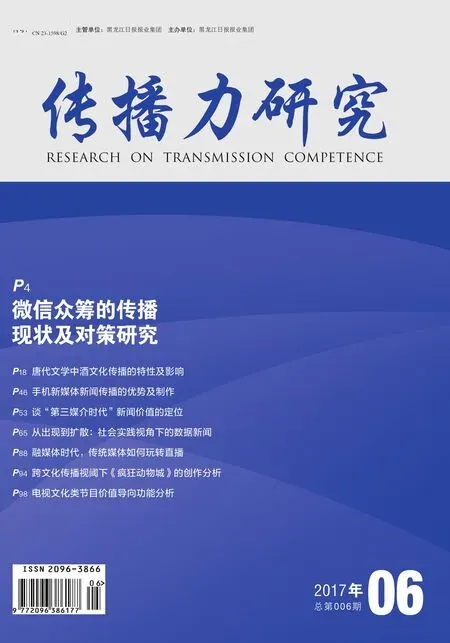“祛魅”:大眾媒介建構(gòu)下的審美
——基于阿多諾文化工業(yè)視域
文/胡濤
審美,是外在的客觀世界給人內(nèi)在的主觀感受營造的一種愉悅之感,或者對其進行的評判。在大眾媒體塑造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中,審美可以說是岌岌可危,物化與異化,扭曲與變形,斷代與消解,公眾受到了來自良莠不齊的文化沖擊。結(jié)合時代呈現(xiàn)的審美之殤,筆者選擇審美作為研究的主題,從人的社會化過程來看,人對美的追求可以折射出關(guān)于“人性”本質(zhì)的思考。由此及彼,社會大眾的審美意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對于美的認知。從理論層面,阿多諾對文化工業(yè)的批判,訴說了美的支離破碎與人的聊無慰藉,宣告了沉淪已久的理性的喪失。從這個角度來說,恰好契合對當(dāng)下媒介建構(gòu)的審美主題進行反思。
一、文化工業(yè)濫觴與審美
(一)機械復(fù)制的“同一性” 與“欺騙性”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而言,文化范式促進了信息的交換,即:對內(nèi)的規(guī)勸和對外的宣揚。在媒介時代環(huán)境下,我們創(chuàng)造了文化,反過來文化又塑造了我們,我們逐漸進入一個由文化控制的社會。在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里,很明顯就能體會到工業(yè)文化控制了人們的生活,人活著的每一天如同機器一番,進行簡單的重復(fù)。而這樣的同質(zhì)化生活方式,使得人們無法抉擇,只能選擇馴服和接受。從文化層面上而言,也就是人們越來越傾向于一致了。當(dāng)然,阿多諾認為文化藝術(shù)的發(fā)展不應(yīng)該以總體性和同一性為目標(biāo),這無疑是一種倒退。他強調(diào)文化藝術(shù)發(fā)展要把握住自己的獨特本質(zhì),堅持差異性的原則,只有這樣才可以沖破這層虛假束縛,追求人個性的解放。
“文化工業(yè)不斷在向消費者許諾,又不斷在欺騙消費者。”大眾媒介不斷給我們建構(gòu)和制造神話,構(gòu)建我們對生活的期許,反過來又欺騙我們,這種欺騙通過媒介對文化的塑造來完成。文化工業(yè)不但沒有帶來意義的升華,還造成了壓抑和背棄的諾言。心靈和自我在商業(yè)環(huán)境下和媒體的意識形態(tài)下不斷被扭曲和操控,思想的疆域不但沒被重新開拓,反而深受到技術(shù)的桎梏。依托傳媒技術(shù)的發(fā)展,媒體塑造的“擬態(tài)環(huán)境”逐漸折射了人的本性——個性的缺失,物化的思想。
(二)審美的“祛魅”也是一種坍塌
“祛魅”一詞來源于德國社會學(xué)家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宗教倫理的論述當(dāng)中。“世界的祛魅”是指宗教發(fā)展中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在此獲得了邏輯結(jié)論,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來獲得拯救的做法,都當(dāng)做迷信和罪惡加以摒棄。①因此,在韋伯看來,“祛魅”實際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從而借宗教改革使人獲得救贖,那層神秘的面紗便昭然若揭,同時也隨之世俗化。古為今用,審美形式的“祛魅”驅(qū)趕了帶有神秘色彩的神話,使得審美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放棄了對原有魅力的崇拜,失去了原有內(nèi)在的,神圣的,本質(zhì)的美的價值,審美也就蛻變了固有的形式。實際上,審美形式上的“祛魅”可以說是一個追求世俗化和功利性化的過程,從當(dāng)下媒介塑造的文化環(huán)境來看,其實質(zhì)是價值理性逐漸被工具理性所替代的過程。自文化工業(yè)濫觴,賦予同一性的美喪失了對真正美感的追求,公眾處于媒介建構(gòu)下的審美病態(tài)中。因此,它使得審美陷入了一種極端貧困的狀態(tài),以致公眾越來越習(xí)慣沉浸和囿于媒介傳達的視覺感,畫面感的體驗之中。
二、大眾媒介建構(gòu)下的審美之殤
(一)人的異化與物化
如今消費社會的文化浪潮已經(jīng)席卷全球,消費作為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不斷生產(chǎn)和傳播人的欲望。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指出“消費社會的特點: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號的基礎(chǔ)上,否定真相”。思想上的潰敗和人的物化已經(jīng)愈演愈烈,人們不屑談?wù)撨^往的美德,認為那是陳詞濫調(diào)。所以,我們不難得出當(dāng)下這樣一種消費現(xiàn)象:在消費的過程中,獲得欲望滿足的同時也迷失了自己,也就不會驚嘆追名逐譽儼然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
外在的容貌美,面具美成了一種追求美學(xué)的病態(tài),對美的界定是來源于內(nèi)在和外在的事物并作用于人的感覺。媒介利用新聞報道,公關(guān),品牌戰(zhàn)略等多樣化渠道,大肆渲染和傳播媒介眼中的“光環(huán)”美。譬如在影視制作唯好萊塢模式是從,在對身體美的塑造和包裝上。媒介在廣告,影視劇等當(dāng)中給大眾營造一種審美范式,以此內(nèi)化為社會層面的審美形式,受眾就會以此作為標(biāo)準(zhǔn)來粉飾自己,所以,外形美麗成為了一種自我身份認同和社會隱形的規(guī)則。當(dāng)然,筆者在此并不是反對時尚,而是揭露用病態(tài)的審美來標(biāo)榜自己和社會。因此,它失去了理想的高貴性和嚴肅性,僅僅是外在粉飾的虛榮,不是對內(nèi)在精神自由的追求,可以說這是一個審美危機的時代。
(二)傳播技術(shù)與藝術(shù)的祛魅
阿多諾對文化工業(yè)技術(shù)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之所以這么說,鑒于科技的進步和發(fā)展,人類對物質(zhì)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滿足,越是長期處在舒適區(qū),人們內(nèi)心對于精神的釋放和尋求新鮮事物的壓抑會變得越來越激烈。當(dāng)?shù)竭_相應(yīng)的水平時,勢必造成人的精神需求變得異常空虛和墮落,對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會降低。我們在享受科技帶來豐厚福利的同時也徒增了憂愁,如今數(shù)字化時代的到來,人們受制于技術(shù)的羈絆,生活上越來越依賴于媒介,由于媒介的“同一性”和機械復(fù)制,人類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與日俱增,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從“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向和“技術(shù)理性所轉(zhuǎn)變。正是由于這一傳播技術(shù)的進步,媒介營造的審美逐漸讓人變成它的工具,不但沒有提供美的理性,反而造成了對藝術(shù)的破壞。阿多諾指出一旦被技術(shù)操控,將會是對美的摧毀,對藝術(shù)的需求如同本雅明描繪的“機械復(fù)制”而已。
(三)話語的消解與意識的操控
在新媒體、自媒體出現(xiàn)之后,政治的管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zhì)疑。這主要表現(xiàn)在:政治的媒介化。現(xiàn)在的政治傳播方式、運作方式都離不開媒介,也就是說媒介作為政治的表演工具和宣傳工具,一方面,受到宣傳影響的民眾越來越關(guān)心政客們的非政治性事件,如丑聞、緋聞、家庭生活等;另一方面,政客們也需要表演。特別是在新媒體出現(xiàn)之后,越來越重視政治行為的表演。所以說政治化的媒體就好似在制作、演出一場荒謬可笑的戲一樣。根據(jù)議程設(shè)置的理論,媒介通過提供的信息和安排的相關(guān)議題來左右人們的思考方式,雖然無法決定人們怎么想,但是卻可以影響人的想什么。政治化的媒介,通過媒體對議題的報道,試圖把政治意識變成意識形態(tài)傳遞給大眾,通過表演和偽裝“修飾”話語權(quán)威性,因此這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公眾話語權(quán)的消解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
三、重構(gòu)審美的意義
(一)還原審美的精神性
從阿多諾對美學(xué)的認知上面,可以得知美學(xué)在現(xiàn)代意義上,主要還在于精神性和自律性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這是現(xiàn)代美學(xué)的一個基本特征。談到現(xiàn)代美學(xué),往往會對比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tǒng)美學(xué),在對傳統(tǒng)美學(xué)的認識上,他認為黑格爾與康德是最后兩位對藝術(shù)能夠系統(tǒng)論述美學(xué)的哲學(xué)家。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能夠在傳統(tǒng)美學(xué)當(dāng)中,接受來自于藝術(shù)家們普遍認同的藝術(shù)規(guī)范,也就是一種潛在的范式。因此這種規(guī)范本身是凌駕于其所創(chuàng)造出的藝術(shù)作品本身的,傳統(tǒng)美學(xué)追求的目標(biāo)是掌握藝術(shù)所特有的表達形式。但從阿多諾的文化工業(yè)視角對美的看法,認為美學(xué)是一種精神性和自律性的標(biāo)志。結(jié)合當(dāng)下時代環(huán)境來看,我們認為的現(xiàn)代美是什么呢?是黑格爾的那種藝術(shù)性終結(jié),還是阿多諾所思考的精神性與自律?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時代所呼吁的審美意識在筆者看來其實就是要求一種祛魅的過程,也就是重構(gòu)當(dāng)下美學(xué)的意義和本質(zhì),約束我們的精神,形成自律。重新建構(gòu)現(xiàn)代美學(xué)的意義。而美學(xué)的建立也在乎兩個層面:一是理性和精神,用藝術(shù)呈現(xiàn)原本的內(nèi)容,以及需要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和狀態(tài);另一方面需要藝術(shù)具有一種批判的力量,媒介宣揚一種所謂工具理性時,往往帶有欺騙性。這就是需要人們自覺識別和判斷,在“物化”和“異化”中,獨立思索,以藝術(shù)的方式去表達真正的自我和實現(xiàn)身份的認同。
(二)美的否定性創(chuàng)造
在阿多諾對“同一性”和“欺騙性”批判當(dāng)中,可以審視出公眾已經(jīng)進入了被媒介審美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之中,充滿了各種魅惑和期待。但在當(dāng)今現(xiàn)代社會資本的鐵蹄之下,人如果要不斷擺脫物化和異化,實現(xiàn)自我的精神救贖,就必須在現(xiàn)存的基礎(chǔ)上充分實現(xiàn)自我的否定性創(chuàng)造,在阿多諾看來就是要在對現(xiàn)實進行批判和否定的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尋找。換個角度而言,即便在技術(shù)理性化和價值理性的支配下,否定的辯證法才是美獲得自我表達的最好方式,雖然有相當(dāng)一部分是對藝術(shù)的思考,但是通過以反向的思考方式來揭示虛偽的現(xiàn)實,阿多諾就是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了否定。而這種否定性,在筆者看來是一種哲學(xué)意義上的現(xiàn)代審美。不但剖析生活,否定性思考,尋求新的意義。
時觀社會的拜金之風(fēng)盛行,經(jīng)濟的發(fā)展富足了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卻奴役了精神世界。前面談到傳播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人們提供了生活便利的同時,也消解了話語和操控了意識形態(tài)。雖然,人類對物質(zhì)的需求得到了釋放,但是這種物欲如同無法填補的深淵巨壑一樣,無法逃離虛假的現(xiàn)實。各種各樣的媒介時時刻刻都在渲染一種,身份標(biāo)識,價值判斷,引誘人們憧憬媒介所描繪的生活愿景,因此工具理性在價值理性面前不堪一擊。其中要實現(xiàn)這一方式和手段是:批判和破除工具理性壓制的藝術(shù),因為藝術(shù)是一種世俗的救贖。只有這樣一種對審美的祛除和否定,才能從媒介對美學(xué)意義的建構(gòu)中,實現(xiàn)真正的啟蒙價值,獲得真實的精神思考。
四、結(jié)論
本文通過對阿多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解讀,考慮媒介乃至整個社會當(dāng)前的情形之后,闡述了其對我們當(dāng)今社會審美的意義和思考。并以此揭露在文化工業(yè)赤裸裸的誘惑下,悲天憫人的情懷逐漸被物質(zhì)化所取代,藝術(shù)商品的功利化侵入人的想象性思維,品茗鮮味,蠶食靈魂已蒼然淪落為深諳世俗的交往規(guī)則。對于虛假帶來的刺激感和獵奇心態(tài),逐漸喪失自己的獨立思考,隨之而來的審美觀念也是病態(tài)化和扭曲化。在阿多諾思考下的文化工業(yè)理論,審美的再生應(yīng)該在于精神性和自律性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這也正是這個時代所亟待解決的問題。
注釋:
①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阿多諾.美學(xué)理論[M].王柯平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姚文放.審美文化批判[M].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
[3]周憲.審美現(xiàn)代性與日常生活批判[J].哲學(xué)研究,2000.
[4]趙勇著.整合與顛覆:大眾文化的辯證法—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大眾文化理論[M].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
[5]李勇.媒介時代的審美問題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6]李西建.美學(xué)與現(xiàn)代性問題的研究現(xiàn)狀及前景[J].哲學(xué)動態(tài),2002.
[7]支云杰.祛魅與復(fù)魅_阿多諾藝術(shù)形式問題探究[M],天津師范大學(xué)出版,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