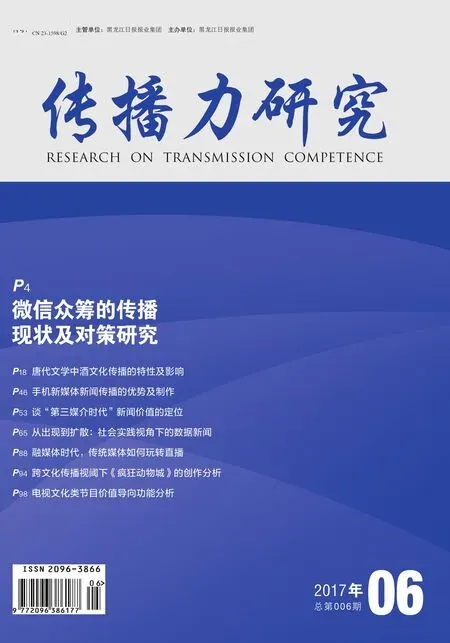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公民記者”現象的利與弊
文/許琳
新媒體時代的到來,讓“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記者”成為了現實,記者這一定義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很多新聞事件不是媒體記者率先發布,例如2011年的“溫州動車事件”、2015年的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件等,受眾最快獲取信息的渠道是新媒體,而發布第一手信息的,也同樣并非專業記者,而是位于事發地的普通公民。新媒體的興起和快捷的網絡傳播賦予了普通公民一種嶄新的角色:“公民記者”。
所謂“公民記者”,是指在新聞事件的報道和傳播中發揮記者作用,卻非專業新聞傳播者的普通公眾。他們與專業記者共同在新聞發生的最前線活躍,利用網絡發言迅速方便的特點,第一時間發現、報道、更新新聞訊息。
那么,新媒體時代,“公民記者”現象在新聞傳播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有哪些利與弊,對新聞傳播又有著哪些影響呢?
利:及時發布信息,彌補記者不在現場的缺憾
《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7)》指出,中國的網民總數到去年年底達到了7.31億,其中有95.1%的網民是通過移動終端上網,也就是說,7.31億網民中有6.95億是移動互聯網網民。
目前用戶最多、影響力最大的媒體就是網絡。網絡媒體視信息接收終端而定分為互聯用戶和手機用戶兩大類,而這兩類用戶從年齡、職業分布到性別比等各方面都有較大的重合。新媒體促成了現階段信息開放的社會環境,像記者一樣拍照寫稿發布信息,已經不再作為記者的“專利”,而是每個受眾也同樣能夠做到的事情。網絡新聞傳播具有方便快捷的特點,用戶通過評論、轉發,能夠更有效的促使新聞內容的傳播效果和互動性的增強。
因此,一部分人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臨時自發地成為了“新聞報道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公民記者”。他們涉及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對突發事件進行報道,彌補記者不在現場的缺憾。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蘆山發生7級地震,最早發布第一條地震消息的不是傳統媒體,而是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消息發布時間距離地震發生僅5秒,成為災難救援的另一條生命線。
2005年7月7日,倫敦遭受恐怖襲擊,事件發生的突然性導致了傳統媒體普遍缺席。因此,當天報紙報道時,大多采用的都是受眾提供的手機照片,拍攝的內容是在地鐵爆炸的現場,人們爭相逃跑的畫面。普通公眾所提供的影像資料,彌補了傳統媒體記者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缺位,這些資料也起到了記錄歷史瞬間的作用。
除了對突發事件的報道,一些專業的“公民記者”能夠發表關于本專業方面較為獨到深刻的見解,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今年初,在維也納舉辦的世界肺癌大會上,公布了萬眾矚目的肺癌靶向藥物奧希替尼的首個三期臨床試驗數據結果。這樣的專業會議國內沒有記者參加,卻有與會專家在搜狐公眾平臺發布了內容詳實專業的新聞稿件。文章開頭指出了維也納世界肺癌大會公布的肺癌靶向藥物,奧希替尼的首個三期臨床試驗數據。指出了奧希替尼的小名一般性稱呼AZD9291,以及在中國市場的推廣價值和中國患者的期待性,簡明扼要地指出了該信息對中國肺癌治療的重要價值。
文章從寫作上并不比記者遜色,而作者較強的專業背景讓讀者更多地了解了這一新藥的具體作用。由此可見,對于某些專業性較強的新聞,由專家或業內資深人士發表自己的意見或看法,往往會更有深度,更具權威性。
弊:信息準確性存疑,觀點難免偏頗
“公民記者”雖能在第一時間對突發事件進行記錄并傳播,但由于主觀因素較多,一般難以做到準確、全面,很難最大化保證新聞的公正客觀。例如,某條信息可能只是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記錄,卻因為信息內容存在著一定的價值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傳播效果和社會影響。而“公民記者”不受記者的行為規范和職業道德的約束,很多情況下可能不顧及事實的真相,聞風即動,捕風捉影。這些信息通過新媒體快速傳播,就有可能成為一種社會事件的“放大鏡”和社會情緒的“發泄口”,混淆視聽,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
更有甚者,通過自媒體,來刻意散布某些虛假、不實消息以達到個人的不良目的。因此,在發生重大事件時,尤其是某些突發事件發生的前提下,新媒體上的新聞內容大多雜亂無章,因而導致了群眾的猜疑、議論,甚至有可能出現社會恐慌。
近年來,由于食品安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因此也使得許多違法分子刻意散布與食品安全有關的謠言,以造成群眾對食品安全的恐慌。以“塑料紫菜”為例,今年2月,有一段將紫菜泡水撕扯的視頻在網絡上大面積流傳,以“事實證據”證明該品牌的紫菜是“塑料做的”。而接下來,在短短一周內,就出現了20多個不同版本的‘塑料紫菜’視頻的爆發式傳播。 “塑料紫菜”謠言在網絡上呈幾何式擴散,視頻中涉及的某品牌紫菜被迫在黑龍江、廣西、甘肅等地多家超市下架。短時間內,謠言沖擊波從消費者、超市一路傳遞到經銷商和加工廠,最終影響了相關的養殖戶,導致整個產業鏈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原料收購價格腰斬,造成大量紫菜滯銷。
為維護群眾、企業的合法權益,公安部迅速部署相關地區成立專案組,對涉案謠言視頻進行偵查,抓獲拍攝謠言視頻實施敲詐勒索人員5名,制造“塑料紫菜”謠言人員5名,傳播謠言信息人員8名,“塑料紫菜”謠言快速散播的趨勢才得以遏制。
由此可見,在現有的公民素養之下,網絡民間輿論場的過度開放導致進入其中的“公民記者”魚龍混雜,新聞真實性無法保證。此外,“公民記者”在法律上的尷尬境地使其合法性也備受質疑。凡此種種,不能不令人對“公民記者”持謹慎態度。
思考:新媒體時代,更需要傳統媒體發出權威客觀的聲音
綜上分析,新媒體時代“公民記者”現象有利有弊。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公民記者”各自的初衷不一,進入新聞傳播領域可能是由于興趣使然,或者單純熱衷于新聞事件,但也有可能是受到個人利益的驅使。我們需要意識到,公民記者是沒有受到專業培訓的徹底“外行”,不僅沒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也缺乏職業新聞人的素養,信息的發布有臨時性、偶然性、碎片化特點,重視言論自由勝過身為“記者”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往往有著天然的主觀立場和個人動機,個人傾向性嚴重,無法保證信息的客觀公正。
正因為此,我們應該深思,新媒體時代如何對“公民記者”的參與式新聞進行引導,通過對其有效的引導,避免這一類新聞在傳播中出現不規范行為,降低參與式新聞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何在與公眾的互動與交流中提高新聞的品質,從而適應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傳播的變革。
筆者認為,在當前新媒體大發展時期,在這個信息過剩的時代,更需要專業媒體發出權威客觀的聲音。
在新媒體時代,記者應該秉承新聞專業主義的精神,將熱點新聞和事件背后的本質傳播給公眾。追求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不帶個人偏見報道真實信息;不受任何利益控制;堅持公共性原則不變,這也是“公民記者”與職業記者之間的區別所在。
例如今年上半年中關村二小的校園事件,當時三方都從自己的角度闡述自己的訴求和觀點,學校從他的角度做了回應,被欺凌的學生家長發表了自己的訴求和觀點。后來新華社、人民日報都進行了比較專業、客觀、公正的報道,還原了事實。由此可見,越是在噪音、雜音較多的時代,更需要傳統媒體以專業的眼光,對雜亂無序的信息進行整合分析,核實消息來源,去偽存真,加強對輿論關注的引導,保證報道的客觀性和權威性,遏制謠言,成為新媒體時代新的“把關人”。
[1]蔡雯.人人都是記者 “——參與式新聞”的影響與作用[J].對外傳播,2010,3.
[2]余冰珺.反思“公民記者”[J].傳媒觀察,2012,8.
[3]夏瓊,林憶夏.社交媒體語境下“全民記者”的概念誤讀[J].新聞實踐,2012,3.
[4]吳飛.新聞專業主義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