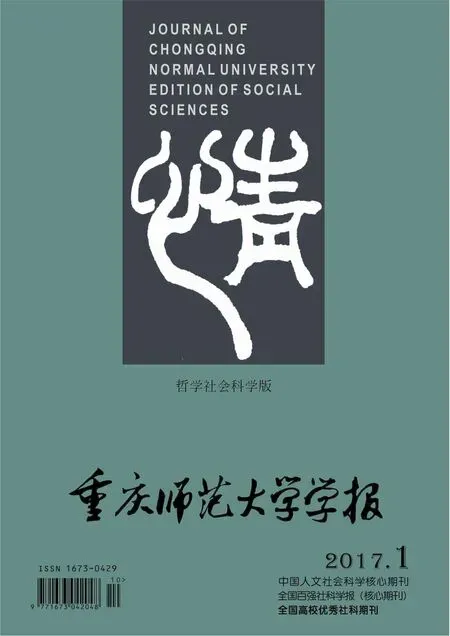棒球棍、青痣、井
——《奇鳥行狀錄》意象淺析
楊 曉 蓮 沈 榮
(1.四川外國語大學 中文系,重慶 400031;2.南通智聯外語培訓中心,江蘇南通 226000)
棒球棍、青痣、井
——《奇鳥行狀錄》意象淺析
楊 曉 蓮1沈 榮2
(1.四川外國語大學 中文系,重慶 400031;2.南通智聯外語培訓中心,江蘇南通 226000)
《奇鳥行狀錄》是村上春樹創作生涯的轉折點,從這部作品開始,村上小說由前期所關注的內心世界轉為更開闊的社會問題。本文通過深入分析《奇鳥行狀錄》的三個核心意象——棒球棍、青痣和井,與作品抗擊暴力的主題相掛鉤,最后回到日本現代社會中不斷傳承的暴力體系的分析,以及作品對于侵華戰爭責任的反思,討論作者通過這三個意象所要表達的主題:抗擊暴力、銘記歷史、反思戰爭責任。
村上春樹;《奇鳥行狀錄》;棒球棍;青痣;井
村上春樹是當代世界文壇享有極高聲譽的作家、翻譯家和學者。他的《奇鳥行狀錄》于1996年獲得第47屆讀賣文學獎。2009年獲得了具有“諾貝爾文學獎風向標”之稱的耶路撒冷文學獎。哈佛大學教授杰·魯賓(Jay Rubin)評價該作品是“村上春樹創作的轉折點,也許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偉大的作品”[1]185。在小說中,“作者完全走出寂寞而溫馨的心靈花園,開始闖入波譎云詭的廣闊沙場”[2]。《奇鳥行狀錄》“是一部正面描寫日本軍隊在亞洲大陸暴虐罪行的小說,作為戰后出生的作家,這是村上在對同代及下一代人講述戰爭之于血肉之軀的恐怖”[3]。這是一部得以窺見日本黑暗、殘暴的過去的作品,對于認清當今日本社會國家體制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奇鳥行狀錄》是村上傾注較多心血的作品。村上曾坦言:“那個故事在等待我來寫,我所做的不外乎把它順利地解放出來。”[4]《奇鳥行狀錄》由橫、縱兩條情節線構成。橫線是主人公“我”——岡田亨尋找突然下落不明的妻子,其中牽涉到以妻子兄長綿谷升為代表的日本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邪惡。縱線是間宮中尉對于諾門坎戰爭的回憶 ,以及因與赤坂肉豆蔻、肉桂母子相識從而陸續浮出水面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的往事等,這部分較為集中地表現了戰爭背景下的暴力。在小說中,橫線縱線交錯展開,表現了作品抗爭暴力的主題。
目前學界對《奇鳥行狀錄》的研究主要還停留在戰爭和歷史方面,而作品的意象還沒有被充分研究。所以,本文試圖探究與小說抗爭暴力主題緊密相關的三個核心意象:棒球棍、青痣和井,來分析作者通過這三個意象所要表達的主題:對于日本戰爭責任的反思,對于歷史的銘記以及對于暴力的抗爭。
一、棒球棍意象——承載暴力和抗擊暴力
棒球棍是《奇鳥行狀錄》這部作品的重要意象,它一方面既是暴力行為的承載物,也是打擊暴力的武器。
在小說中出現過兩根重要的棒球棍,一根由“我”從一位民歌手處獲得,他不明不白地對“我”發起攻擊,“我”從其手中奪得并保留了下來,作為最終對決的武器;另一根出現在縱向情節中,肉豆蔻的父親是一名臉上長有青痣的獸醫,他曾親眼目睹日本兵用棒球棍將一名中國人打死,而本該已死的中國人卻死死抱住獸醫不放,想要將其拖入尸坑。
此外,小說中還多次出現過與棒球棍有關的暗示,如鄰家女孩笠原May在院中曬太陽時身邊放著的一根球棍,照她的話說只是因為握在手中安心;再如,“我”準備擺脫所處的險惡環境,意欲逃至所謂庇護所的希臘時,卻被一個帶著棒球帽的大塊頭“猛地抓住胸口一掄”[5]357;而在縱向情節中,被處決的中國人更是身套棒球服,這些暗示都不禁讓人聯想到棒球棍與“打”這一動作的關聯。
棒球棍作為一種體育器具,由于其獨特的長水滴型設計,給人良好的握感,方便持有者做出“打擊”的動作。然而小說中的棒球棍卻全部用于打人。第二部第17章中,“我”追隨曾有一面之緣的流浪歌手時卻被其用棒球棍偷襲,“我”奪過球棍反擊后仍“欲罷不能”,而被“我”毆打的人竟然“嗆著自己的口水笑得嗤嗤有聲”[5]389,仿佛暴力這件事情是可以傳染的。“我”在打完人后下意識地將棒球棍帶走,晚上睡覺時“右手依然攥得緊緊的作格斗狀”[5]390,這種反應意味著暴力是融于人類基因之中的。棒球棍擔當的雖然只是“打擊”這一動作,實際上還承載了人類對于暴力行為的放縱,甚至是渴望。
在縱線情節中,臉上長有青痣的獸醫目睹日本兵處死四名從“滿洲國軍官學校”逃跑的中國學生,四人穿著帶有編號的棒球服,其中三人被刺刀刺死,“五臟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5]609,唯獨最后一人被下令用棒球棍打死,因為他在逃跑前用球棍打死了日本教官。在這短短的行刑過程中出現了三種刑具:槍、刺刀和棒球棍。槍是現代戰爭中的武器,刺刀和球棍在一定意義上則屬于冷兵器。棒球是日本社會中極其流行的一項競技體育,美國有常春藤體育聯盟,日本則有甲子園。這是一項幾乎融入日本人血液中的體育運動,不難將其與大和民族的某些精神內核聯系在一起。如同武士道精神要通過武士刀這樣一種外化的兵器實體表現出來一樣,人類內心深處的暴力傾向也被灌注到棒球棍中。棒球棍選手在擊球區的預備動作是下半身半蹲,上身右轉面向前準備擊球,這與武士手握武士刀的動作是極其相似的。“傍晚強烈的陽光把球棍粗大的影子長長地投在地面”[5]612,這時的球棍分明就是砍刀,只不過比起寄托武士精神的刀,這幅球棍表面已布滿凹痕,沾有皮肉毛發。人們內心的暴力通過用棒球棍打人這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棒球棍是承載暴力的工具。
棒球棍表面上看只是一件打人的兇器,作者在其中還加入了是非觀的思考——打人是暴力,抵制暴力卻也需用暴力,所以在《奇鳥行狀錄》的第三部高潮部分,棒球棍成為了打擊暴力的武器。“我”把從民歌手中奪來的棒球棍帶下枯井,像“進球區的棒球手雙手緊緊握住棍柄”,“用棍頭輕輕叩擊井壁以測其硬度”[5]469,之后“我”發現可以由“井”進入妻子被囚禁的房間,最終的決斗眼看就要到來。此時的棒球棍儼然由承載暴力的兇器變成了打擊暴力的武器。作者的善惡觀也由此得以窺見:有惡就要抗爭。但外化為棒球棍這件冷兵器的抗爭精神,有可能成為一發不可收的暴力,也有可能使斗士在打擊暴力的斗爭中勝利。
作品中描寫“我”與惡斗爭的情節頗耐人尋味:對方“那一團不知是什么的東西”使用的是匕首,“我”使用的則是棒球棍,雙方就這樣在黑暗中進行一場日本武士對決似的戰斗。在黑暗中,“我”能傷及對方,對方亦可刺到“我”的情節也頗具東方武打對決的特色,很明顯作者在追求的不是昆汀電影式的暴力美學,不是把滴著血的肉翻出來給讀者看,但讀者分明能夠透過紙頁聞到血腥味兒、暴力味兒和死味兒。最終棒球棍擊中了“那個東西”,勝過了更具殺傷力的匕首,這是一種暴力抗擊另一種暴力的勝利。
暴力已經融入了人類的基因,作者通過棒球棍這一暴力的外化物從施加暴力到打擊暴力角色的轉換,豐富了整部作品抗擊暴力主題的內涵。
二、青痣意象——銘記歷史的印記
青痣是《奇鳥行狀錄》中非常值得思考的意象。作品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比如讓這塊青痣隱隱發燙、作痛、低燒,甚至讓它活起來,試圖喚醒人們對于遺忘過去的屈辱感和與邪惡作斗爭的命運感。
小說中有兩個主要人物的臉上長出了一模一樣的痣。在橫線情節中,“我”在妻子失蹤后下到井中思考與妻子的相識相知,并發現自己可以透過井壁到達妻子被囚禁的賓館房間,升井后發現自己的右臉長出了一塊嬰兒手掌大小的青痣。“我”帶著這塊青痣與惡進行決斗,獲得勝利后青痣消失不見。在縱線情節中,肉豆蔻向“我”講述其祖父——一位右臉長有一塊青痣的獸醫的見聞。他見證了日本侵華戰爭中在侵入“戰前的滿洲”即中國東北地區發生的暴力。但是面對暴力的演進,獸醫感受到的“寒氣”卻永遠沒有從其體內散去。
青痣在作品中主要有兩個象征意義:銘記歷史的印記和區分庸人與斗士的標記。
青痣是屈辱感具體化的意象,每個人犯下罪孽后都會背負上一份屈辱感。證件照攝像師也只能用粉將青痣暫時蓋住,使其顯得不那么明顯;“我”曾妄圖逃往理想中的樂園希臘以重新開始生活,但帶著這樣一份屈辱是行不通的;鄰家女孩笠原May年輕時因為自己的貪玩和一時的惡意造成戀人去世,她也一直帶著眼角的疤痕活在懺悔之中。“我”觸及她的傷疤以及她仔細舔舐“我”的痣,都是接受這份屈辱感的表現。作者通過這樣一大塊青痣的形式將這份屈辱感烙在臉上,體現了不忘屈辱與堅定斗爭的決心。
村上通過青痣與歷史的關聯,以青痣代表屈辱感,探討了何為真實的歷史。“我”在第一次升井后,加納馬耳他問“我”身體是否發生了變化,“我”曾打趣道:“要是背后長出翅膀,估計再不情愿也還是察覺得到的。”[5]316但加納馬耳他告誡道:“了解自身狀況并不那么容易。……人無法以自己的眼睛直接看自己的臉,只能借助鏡子,看鏡里的反映,而我們只是經驗性地相信映在鏡中的圖像是正確的。”[5]316“自己的臉”指本民族的歷史,“自己的眼睛”指本民族對于歷史的審視。大多數日本人和“我”一樣,認為只有“長出翅膀”這樣的大變化才能被注意到。部分日本人在戰后開始正視自己的過去,但同時各種否認戰爭責任的呼聲也甚囂塵上,歷史修正主義和鼓吹“國家正史”的民族主義開始泛濫,使得一個國家在自身身份認同問題上存在著巨大分歧。“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村上在《奇鳥行狀錄》中表現出對歷史的濃厚興趣,因而自己構建了這樣一部“擰發條鳥編年史”(《奇鳥行狀錄》的日文原題為「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ねじまき’意為‘擰發條’,‘クロニクル’(chronicle)意為‘編年史’,直譯應為《擰發條鳥編年史》),以橫縱線交替的形式筑成一部歷史體驗錄:從間宮中尉那里,“我”得知了曖昧不清的諾門坎戰爭,從赤坂肉豆蔻、肉桂母子處,“我”得知了發生在中國東北的血腥事件。棒球棍、青痣和井意象將“我”與歷史的塵埃聯系在一起,使“我”感受到應該銘記歷史,承擔起對歷史的責任,正視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從這種源自過去,迎面走來,并傳承給我們的東西中理解自己”[6]。
無論臉上長出的青痣是何物,它起到的起碼是區別作用——區分臉上有痣的人和沒有痣的人。作品中有多處關于有痣與無痣之人的對比。在橫線情節中,路上的行人會以“那位有痣的大阿哥”稱呼“我”;干洗店的老板看了一眼我臉上的痣,丟下一句“夠你受的”;拍證件照的攝像師對“我”的臉又是打光又是蓋粉;美容師看了一眼鏡中的“我”,便“活像看著一碗滿滿敷著一層芹菜梗的蓋澆飯”[5]463。但是“我并不覺得它難看亦不覺其污穢”,并且“意識到必須接受它”。在縱線情節中,臉上有青痣的獸醫見證了日本兵在蘇軍即將攻進中國東北之際槍殺動物園中動物,以及處死中國逃犯的情景,他自始至終帶著這塊青痣經歷了惡行,卻無從逃脫這徹頭徹尾的惡;而“我”卻帶著這塊青痣與惡進行斗爭,最終奪回妻子。作者通過多對共時和歷時的對比,用痣將庸人與斗士區別開。一方面,庸人經歷惡卻不以為意;另一方面,斗士能夠敏銳地感受到現實和歷史的使命感,帶著一份屈辱進行斗爭。
這一塊嬰兒手掌大小的痣將上世紀30年代的滿洲、外蒙和80年代的日本聯系起來。在第二部第28章中有大段關于獸醫對于“命運形成宿命式達觀”的描述:“小時候他非常憎惡他人沒有自己獨有的這塊痣。……若是能用小刀把那個部位一下子削掉該有多好。但隨著長大,他漸漸找到了將臉上的痣作為無法去掉的自身的一部分,作為必須接受之物來靜靜予以接受的方法。”[5]602獸醫認為世界是被命運的巨大力量統治著的,他雖然認為自己不是一般的宿命論者,但他也不曾實際感到自己有生以來單獨決定過什么,于是獸醫看著動物被殘忍射殺,看著中國逃犯被以極端的方式殺害。命運感使得獸醫被動地接受著自己身處的歷史,他感到無能為力,覺得人們不過是被有著“自由意志”外形的歷史欺騙而已,因此獸醫始終都沒有擺脫這股強大命運感的束縛。
而與之產生鮮明對比的“我”并不覺得它難看亦不覺其污穢。“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須接受它。”[5]463雖然兩人都接受了臉上的痣,但“我”帶有很強的戰斗性:“我”能夠一眼認清綿谷升虛偽表面下潛藏的惡,看出惡的流動和傳承。“我”完全是一個斗士的形象,不同于村上小說其他主人公遭遇離奇事件而表現出的“卷入感”和無奈,比如《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的精算師和讀夢者,以及《1Q84》中的青豆和天吾,《奇鳥行狀錄》中的岡田亨主動靠著自己的毅力和決心與惡勢力斗爭。
作者圍繞青痣意象展開有關情節的寫作時主要運用的手法是對比:遺忘過去和銘記歷史,斗士抗爭和庸人妥協等,以此呼喚要銘記歷史。
三、井意象——自然和諧的象征
小說中出現過兩口重要的井。在橫線情節中,一口井位于“我”家附近的空宅內;在縱線情節中,另一口井出現在間宮中尉的回憶中。“我”家附近有一幢不斷發生怪事的空宅,院里有一口枯井。妻子失蹤后,“我”下到井中回憶與妻子的往事,體驗到了瀕臨死亡的感受,并發現自己可以透過井壁進入妻子被囚禁的208號房間。在第一次升井后,“我”的臉上多了一塊嬰兒手掌大小的青痣,之后多次下井進入208號房間探尋妻子失蹤的真相。最終,臉上長著青痣的“我”帶著棒球棍下井,與“那個不知道是什么”的東西對決,救出了傷痕累累的妻子,之后“我”所身處的枯井竟然重新涌出地下水將我淹沒。而在諾門坎戰役中,間宮中尉當時與同伴潛入滿蒙邊境執行機密任務,被抓到后投入荒漠中的一口枯井中,體驗到了瀕臨死亡的感受。
作品中有關井的情節錯綜復雜,異常抽象,既是能否出水的井這一自然之和諧的象征,又是囚籠或者殺人兇器的井這一靈肉分離器的象征。井意象將主人公現實身處的東京與1938年外蒙的諾門坎聯系在一起,又與棒球棍意象,青痣意象建立聯系,完整地將《奇鳥行狀錄》抗爭暴力的主題包含在內。
井是一個可怕的場所,以至于“投井”成為了一種殺人方式;干枯的井則是一個深入黑暗的囚籠,一個開放的地牢,一個殺人兇器。在小說第一部,間宮中尉被外蒙兵逼入枯井中,他在談話中如是回憶:“面對這劈頭蓋臉的光明,我幾乎透不過氣來。……我甚至忘卻了恐懼、疼痛以至絕望,只顧目瞪口呆地坐在輝煌的光芒中。”[5]186“……整個人就像被一股巨力徹底摧毀了,我想不成什么更做不成什么,連自身的存在都感覺不出,仿佛成了干癟的殘骸或一個空殼。”[5]187“……我還不止一次夢見自己在井底或者腐朽下去,有時甚至以為那才是真正的現實,而眼下日復一日的人生倒是夢幻。”[5]191在橫線情節中,“我”的妻子莫名失蹤,“我”便下到井中思考種種與妻相識相知的往事。當鄰家女孩笠原May將“我”得以憑借升井的繩梯拉走并將井蓋死死蓋住后,“我”在井下也體驗到了瀕死感,“我”感到“身體便如被剝制成標本的動物,里面空空如也”[5]281。而這樣一種瀕死體驗還具象化為一塊青痣長在“我”的臉上,時時刻刻起著提醒作用。
從以上橫線和縱線中有關“井”的情節可以看出,井是“通往潛意識的通道”[1]189,人在井下成了類似于純精神的存在。間宮中尉在井下被每日只有短短幾十秒的光照所感召,成為了一具空殼,生命的內核被焚毀一盡;“我”在井下追憶了從前與妻子的生活,回想從與妻子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出現的無以言表的奇怪之處,回想妻子墮胎的往事。井深入大地,使得井底之人能夠赤裸裸地直面自己的內心世界,拷問自己的靈魂,使得靈魂擺脫束縛,得以剝離出肉體。 “井”在給予瀕死體驗的同時成為了一個靈肉分離器:透過井壁的“我”已經不是現實的“我”,更多的是一種想要救出妻子的決心的意念集合體,“我”進入的也不是現實中關押妻子的房間,對決的邪惡也不僅僅是綿谷升本人。井將“我”的靈魂和肉體分離,使“我”能夠直面自己的內心世界,找回妻子。“我”首次下井時,感到:“身體如被剝制成標本的動物,里面空空如也。……這委實不可思議,我繼而感覺的分明類似一種達觀。”[5]281“動物被剝制成標本”是瀕死體驗,而感受到的“達觀”是“我”直面內心世界后的一種釋然。“我”在現實中尋找妻子,在井下則探尋自己的內心,井為這兩種探尋提供了媒介。
村上通過將歷史與現實聯系,將死亡感受與拷問內心相聯系,實則還是要表現須銘記歷史的主題。在《奇鳥行狀錄》第一、二部付梓之際,村上曾實地考察過諾門坎戰場,他回憶到:“站在那曾經激戰的戰場遺址上時,我清楚地感受到了那里漂浮的死亡氣息。……深夜突然睜開雙眼,發現房間在劇烈搖晃,到了無法走路的地步。開始以為是地震,在黑暗中爬行,打開門來到走廊,發現外面一片寂靜,我才發現搖晃的并非這個房間或是世界——是我本人。”[1]174村上來到曾經充斥著死亡的戰場,感受到了內心的震顫。死亡的存在迫使作者直面歷史黑暗和殘暴的深處,并引發作者對于戰爭以及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暴力的思考。間宮中尉體驗到了戰爭的暴力而“我”因為妻子被莫名奪走也慢慢感受到身邊無處不在的暴力。井連接了兩個時空,并讓“我”醞釀與暴力抗爭并且奪回妻子的決心。
水是生命的源頭,是自然慷慨賜予的產物。但井作為水源在作品中絕大部分情況卻處于干枯狀態。笠原家能夠使用清澈甘甜的地下水,而僅一墻之隔的宮脅家卻只有一口枯井,給人以“滅頂式無感覺的感覺”[5]77,使得宮脅家怪事不斷;靈媒加納馬耳他曾去水源最好的地方修行,為了喝到最好的水,她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我”和妻子例行拜訪算命先生本田,得到了要注意“水流”和“水脈”的告誡,并得知“該上之時,瞄準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該下之時,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5]60;“我”從房產經理人處得知宮脅家的那口枯井“戰前還出水來著,不出水是戰后”[5]428;而在最終對決中打敗邪惡后,“我”坐在井底淹沒在涌出的井水中。
以上情節表明,井下無水便怪事叢生,惡被打敗后井中便有了水。有水之井是自然和諧的象征。水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人類除去了惡,自然才能和諧,才能繼續慷慨地給予人類生命的源泉。在第二部結尾部分,“我”在游泳時感覺自己置身于巨大的井中,意識到“這是世界上所有井中的一口,我是世界上所有我中的一個”[5]404。在現實與意識的邊緣,“我”又進入了妻子被囚禁的房間,接收到了妻子向“我”求救的信號,明確了“至少有我值得等待又值得尋求的東西”。在水中,“我”順應了自然的召喚,決定奪回妻子。
在小說結尾部分,“我”通過想象自己在水中從而進入了房間:“想象自己在游泳池往來爬游的光景,我忘掉速度,只管靜靜地緩緩地游動不止。……如此游了一會,漸覺身體竟如乘緩風,自然隨波逐流。[5]654由此可見,“水”和“井”在主人公抗擊暴力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在與惡對決勝利后,原本干枯的井底竟然重新涌出了水,“水再過五六分鐘就將堵住我的嘴和鼻孔,隨即灌滿兩個肺葉。……我的肺拼命要吸入新空氣,但這里已沒有空氣,有的只是溫吞吞的水”[5]697。井讓“我”體驗到死亡感和暴力,將“我”剝離成一個空殼之后,當“我”戰勝邪惡后又再次用水將這具空殼灌滿。“我”以為水即將把自己淹死,其實新涌出的水是一種洗禮:嬰兒在母體中靠灌滿肺部的羊水獲得氧氣,“我”在接受洗禮之后也重獲新生,這是自然在對個體注入新的生命。
井通過給予“我”的瀕死體驗,產生靈肉分離作用,使“我”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同時井也作為自然和諧的象征,在“我”抗擊暴力的過程中給予啟示,在勝利后給予“我”自然的洗禮。井意象與作品主題層層掛鉤,是整部作品中最為復雜且內涵豐富的意象。
結 語
本文所選取的三個核心意象和《奇鳥行狀錄》打擊暴力、銘記歷史和反思戰爭的歷史都息息相關。棒球棍是暴力的承載者同時也是暴力的打擊者,在實施暴力與打擊暴力角色相轉換的同時,作者融入了一定善惡觀的思考;青痣是銘記歷史的印記,作品中的歷史便是黑暗而殘暴的戰爭,這塊青紫色的痣便是黑暗歷史具象化的展現;井是供人探索內心世界的媒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水井與枯井的區別象征了自然和諧與否。
棒球棍、青痣與井三者之間也互相聯系:主人公下井體驗到了瀕死感后,臉上便出現了青痣,而青痣作為貼于外表的一份屈辱感與命運感又使我想起過往黑暗的歷史,驅使著“我”用棒球棍打擊暴力。在小說的高潮部分,這三個意象最終得以重合:臉上長著青痣的“我”,雙膝夾著棒球棍坐在井底,最終奪回妻子。井作為一個有自然靈性的地方,讓“我”找回了自己,帶“我”到達妻子被禁之處得以抗爭暴力。這時,武器、抗爭的決心和媒介缺一不可,都是“我”得以最終取得勝利必不可少的條件。
對于現代中日兩國關系來說,戰爭遺留問題、封閉性社會體系等問題是繞不開的話題。村上作為一名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家,在《奇鳥行狀錄》中對于不斷傳承的暴力體系,以及對于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與反思,都與戰后的一些日本作家形成鮮明反差。正如王向遠指出:“這種情況表明,日本文學界對戰爭的責任,對侵略戰爭尤其是侵華戰爭的罪惡,還遠遠沒有形成普遍的悔罪意識,對侵略戰爭的普遍的正確的認識還沒有形成。”[7]村上春樹通過《奇鳥行狀錄》,揭示出日本現代社會殘暴的、封閉的暴力系統,批判了本質上毫無變化的日本社會體制。
[1] 杰·魯賓.洗耳傾聽:村上春樹的世界[M].馮濤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 林少華. 追問暴力:從“小資”到斗士[J].《奇鳥行狀錄》序.2009,(8).
[3] ヅエイ·ルビン.村上春樹『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の翻訳に對して[J].群像.2003,(12).
[4]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0④ 『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1、2』“解題”[M].講講談社,2003.
[5] 村上春樹.奇鳥行狀錄[M].林少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6]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修訂譯本)[M].洪漢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7] 王向遠.戰后日本文壇對侵華戰爭及戰爭責任的認識[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5)
[責任編輯:左福生]
The Baseball Bat, the Green Mole and the Well: an Analysis on Core Imageries ofTheWind-upBirdChronicle
Yang Xiaolian Shen R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48, China)
TheWind-upBirdChronicleis the turning point of Haruki Murakami as a writer, from which Haruki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of significance than to human’s inner world of mind in the earlier stage. In this thesis, the three core items, namely the baseball bat, the green mole and the well, all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novel’s theme of combating against violence, are deeply analyzed. In the end, the continuous violence system in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and the author’s pondering on Japanese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are contained in this thesis. All in all,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re combating against violence, bearing in mind the past and pondering upo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ggressive war.
Haruki Murakami;theWind-upBirdChronicle; the baseball bat; the green mole; the Well
2016-11-02
楊曉蓮(1964-)女,四川省岳池縣人,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 沈榮(1994-)男,江蘇省南通人,南通市智聯外語培訓中心國外部教師,主要從事雅思托福寫作教學。
II3
A
1673—0429(2017)01—00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