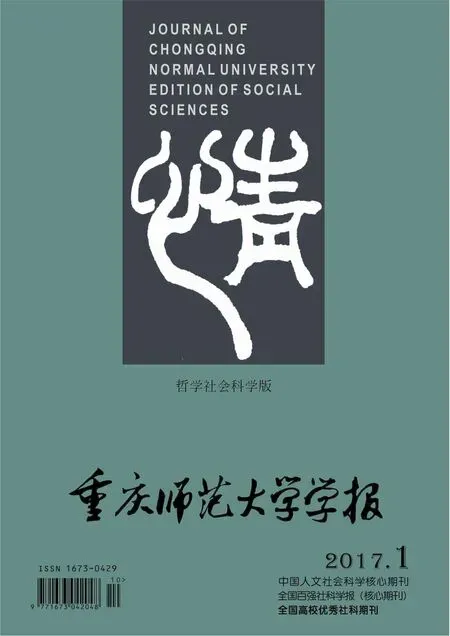從弗雷格的“涵義”到康德的“先驗形式”
——試論語言現象統一的必然性基礎
肖 福 平
(西華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39)
從弗雷格的“涵義”到康德的“先驗形式”
——試論語言現象統一的必然性基礎
肖 福 平
(西華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39)
在語言現象的經驗中,我們常常將這種現象的存在統一視為其自身固有品質的表現而具有客觀性的存在地位;弗雷格的語言分析注意到了語言現象經驗中的相關常識論,提出了一種去心理主義的“涵義”觀,并希望以此確立語言現象存在與統一的客觀思想模式;弗雷格的“涵義”論揭示了語言現象經驗的共同性基礎,但這樣的“揭示”并沒有為“共同性基礎”確立真正的源泉,我們只有從“涵義”思想的改造與回歸先驗哲學的進程中方可探知語言現象存在與統一的必然性基礎,即語言現象世界的呈現與統一性特征決定于理性存在的先驗形式,決定于純粹理性世界的語言存在原因。
語言;理性;涵義;先驗形式
如果遵循康德哲學的先驗論思想建構,我們就可以說:純粹直觀形式源自理性世界并決定表象世界的存在,表象存在的純粹理性原因應該擁有一種先驗形式的存在地位,所有關于表象呈現得以進行的直觀形式和所有知識概念得以形成的知性形式都應該具有先驗形式及其統一的源泉。換言之,自然世界的統一性源于理性存在的統一性,外在世界的差異性源于直觀表象的差異性,外在對象的知識性區分源于知性概念的區別特征。至此,自然過程的統一與表象不可離開理性世界的先驗認知形式,一旦這樣的形式被貫徹到語言現象與自然物的經驗中,它就不僅僅屬于先驗的存在,而且要造成關于這種純粹形式存在的經驗現實,或許我們對于這種先驗形式的說明無法獲取有效的經驗證明,但我們卻無法去懷疑經驗現實與先驗形式的合乎一致,否則,經驗的現實就不會如此存在了。語言存在的現象世界就在這樣的經驗現實之中,語言現象的區分與統一、語言現象的經驗發生與意義獲取都要建立在先驗語言形式存在的必然性基礎之上。
一、語言現象經驗中的“指稱”與“涵義”
在語言現象經驗的現實過程中,我們會面臨語音的意義系統、文字的意義系統、句子的意義系統、篇章結構的意義系統,以及與此相關的宏觀或微觀層面的語言現象的意義系統,那么,作為個體或系統的語言現象為何具有了意義體系的存在呢?或許,我們在這樣的問題上會選取一種常識性的答案:語言現象表達了“什么”,而且是表達了客觀自然對象的“什么”,盡管這樣的“什么”還沒有直接地排除觀念或思想內容的“什么”,但觀念與思想只是作為一個中間的環節,其最終的決定還是指向了自然對象的“什么”,于是,語言現象作為意義系統的存在決定于客觀的自然世界,即自然對象的世界為我們提供了解決一切語言現象之意義的來源之所,源于這樣的常識性答案,我們所經驗的語言現象,如“古樹”,就成為了一種意義的載體,成為了語言現象中的一種意義單位,于是,與之關聯的各個方面,如發音的經驗過程、書寫的經驗過程、記憶和思考的經驗過程,等等,都無一例外地朝向作為自然物的“古樹”,并接受其意義確立的地位。然而,在這樣的常識性答案中,我們卻無法找到語言現象的意義單位與自然物之間的必然聯系,不論是語言符號的意義賦予,還是自然物的意義決定,兩者的聯系和統一缺乏一種必然性基礎,即使在同一種自然語言現象里,一種符號或表述形式與一種自然客體或狀態間的對應聯系也非必然,更不用說那些存在于不同自然語言現象里的情況了。在我們的語言里,“古樹”作為語言現象的意義載體(表意符號)對于自然對象的“古樹”而言不是唯一的,具有相同意義載體的語言現象總是變化地存在著,并且只是慣例性地指向自然對象的“古樹”,任何必然性關系的確立對于自然物而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理由去斷言:是客觀自然對象建立了由其自身到語言現象的必然聯系和意義的賦予。如果這樣的斷言不容置疑,語言現象及其意義體系的存在就會完全地歸屬于自然世界的創造,成為自然決定的語言現象,顯然,這樣的結果有違于我們的語言現象經驗實際。倘如我們將這樣的情況擴大到多種自然語言之間,語言現象與自然對象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更加難以確定。所以,在面臨某種自然對象與某種語言現象之間的關系存在時,它應該是一種被規定的、外在的、慣例性的和偶然性的關系。同語言現象的存在情況一樣,自然對象的存在也是變化不定的。在兩種流變的現象里,如果雙方在認知層面的關系確立沒有問題,那任何一方的意義賦予就僅僅是一種相互配置的規定結果,一種外在經驗過程的偶然性對應關系的產生,既然是如此對應關系的產生,那它所涉及的就只能是一種經驗意義上的相對關系。于是,這種關系下的意義源泉或有效性根本不涉及雙方本身是什么的問題,也不涉及誰先誰后、誰主誰次的問題。或者說,我們可以擁有關于語言現象和自然現象的經驗,也可以擁有關于兩者對應關系的經驗,但我們并未在經驗的對象那里獲取任何關于“語言現象的意義決定于自然物”的必然性根據,為此,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如果整體的世界或全部的世界里只有語言現象和自然物,那么,語言現象該是什么呢?自然物又該是什么呢?兩者的關系與意義決定又如何呢?對于這樣問題也許只有上帝才會知道。長期以來,一些語言哲學或語言學的研究者不斷地探尋這樣的問題,希望能在語言現象的符號與自然物對象之間構建一種整齊的、一一對應的關系,并試圖通過發現某種標準的語言現象工具來實現關于自然世界的無歧義描述,如果這樣的標準工具存在,那關于自然世界的圖式應該就是某種使用語言現象的編碼圖式,那關于自然世界的邏輯形式應該就是某種關于語言現象的邏輯形式,反之亦然。在弗雷格看來,要獲取這種語言編碼圖式或邏輯形式的表達,數學研究的方法可以借鑒,即它們的表達形式相當于數學的函數式f(x),一種具有所有真值可能性但又不具備真值現實的函數形式。在這里,f(x)的真值現實體現在語言現象的層面(自然語言),體現在有關專名、概念詞、句子等的使用過程中,尤其以句子的形式最為典型,如果以“那棵古樹長在深山里”為例,那我們可以說,關于語言現象的函數式f(x)成為了具有真值表達的句子,任選項x(自變量)以專名或概念詞的形式同謂詞f結合在了一起,那么,在我們取得具有真值判定結果的語言現象的句子時,我們是否可以在語言現象之內來完成這樣的真值判定呢?當然,語言現象不能提供這樣的標準,具體而言,我們不能從句子的“古樹”、“長在深山里”來判定句子的真值,句子的真值存在應該不同于語言現象的層次。弗雷格認為,作為語言現象的句子之真值是建立在意義(Meaning)層面之上的,而意義層面則相當于語言現象所指稱的對象世界,所以,句子的真值最終決定于語言現象所指稱的對象(objects),其結果又回到了上文所討論的常識性答案之上。顯然,弗雷格沒有滿足于如此的分析結果,因為他知道,從語言現象的層面到其意義的層面不能僅僅是一種外在對應配置的關系,更涉及一種決定這種對應關系的本原體存在。因此,在提出“意義”概念的同時,他又提出了“涵義”(Sense)的概念。許多學者將它直接解釋為“思想”,或者,句子的涵義就是句子思想,其過程可以表示為:句子→思想→真值,至于說“涵義”究竟是什么,弗雷格在《論涵義和意義》一文中并未提供明確的定義或說明,只是到了《思想》(1918)一文,“涵義”的討論才被加以了關注。如果說“涵義”就是思想,那思想就是我們“能借以考慮真的東西”[1]112。或者說,“涵義”的存在帶來了關于語言現象的意義呈現和真值判斷,只有依靠這樣的“涵義”,語言現象的不同表達單位才會成為意義的載體,自然世界的對象才會進入語言現象的意義層面,建立語言現象與自然世界的對應聯系才會具備作為第三方存在的決定根據。當然,“涵義”在弗雷格的分析里只是作為了某種衡量“真”的標準或工具,只是作為了某種客觀思想的存在而區別于語言現象和自然物,于是,它遠非“真”的本身,遠非思想的承載者本身(弗雷格并不承認任何關于思想的承載者),或者說,一旦發生了關于“真”之判定的思想借用情況,思想的標準就不應該扮演一種終極的角色,而只可被視為某種結果的應用,那么,產生這種思想結果的原因根據又該是什么呢?
二、語言現象統一的必然性與“涵義”啟示
在論及“涵義”或思想時,弗雷格已經觸及到了語言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的必然聯系問題。由于兩種現象之間的必然聯系遠非現象自身可以提供或加以決定的,于是,他在語言現象和自然現象之間提出了“涵義”的存在,其實質就是要指出:不論是語言對象層面的現象,還是自然對象層面的現象,它們都是關于“涵義”或思想的呈現,都是關于“涵義”或思想作用的成果,至此,“涵義”或許在這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換言之,“涵義”在現象間的聯系過程中或許提供著某種必然性的基礎。倘如“涵義”的作者要將它確立為沒有任何承載者的客觀思想存在,或將它確立為某種“既不是外界的事物,也不是表象”[1]127的存在,那“涵義”就應該歸屬于它自身所是的存在,并且在本質上區別于語言現象或自然對象的系列。同時,“涵義”的存在也應該成為語言現象與自然世界之規定和聯系的真正源泉,所有關于語言現象和自然世界知識及意義的斷言都應該源于“涵義”之“真”的標準,當然,這樣的“涵義”已經超越了它的弗雷格之意。如果我們能夠對“涵義”的問題進行拓展,而不僅僅是弗雷格的“思想”之路,那“涵義”的自身所是就會突破“思想”作為判斷標準的地位而凸現自身作為世界統一的根據地位。也可以說,只有當“涵義”突破弗雷格的“客觀思想”之域而擁有世界統一的根據時,它方可稱得上“考慮真的東西”的標準,而且,這樣的標準也不可能屬于外在世界的東西或類似于某種被動的鏡面之物。在“涵義”被弗雷格賦予“考慮真的東西”之時,它就應該具有“真”的標準或“真”的模式。由此下去,“涵義”簡直就成為了“真”的源泉,一切關于語言現象與自然現象的存在和聯系判定就成為了“涵義”存在及其統一的經驗必然,于是,關于“涵義”的定義應該是一個可以加以說明的問題。然而,令人有點困惑的是:在弗雷格提出了“涵義”問題,并指出了“涵義”就是無需任何承載者的“思想”、就是“借以考慮真的東西”之后,他并沒有將“涵義”的討論聯系到一個更為基礎、更為純粹的地位上進行,也沒有將“涵義”與“意義”作為同樣重要的語言現象分析層面來加以討論。不論是在“句子→句子的思想→句子的真值”的過程,還是在“專名→思想的一部分→對象”的過程,或者在“概念詞→思想的一部份→概念”的過程,弗雷格分析的起點是“句子”“專名”或“概念詞”,即起始于語言現象的存在。而分析的完成則要建立在后兩個步驟或層面上,第一個步驟歸屬于他的“涵義”,第二個步驟歸屬于他的“意義”,兩個步驟的分析將會使我們產生關于語言現象的“涵義”和“意義”理論建構的期待,并以此揭示語言現象與自然世界聯系的必然基礎。但是,在相關的兩篇重要論文《論涵義和意義》與《思想》里,我們未能發現“涵義”理論的建立,即使在《思想》中提及“涵義”之時,作者也是出于討論“意義”的需要來進行的。可以說,文章中只有一個中心,即“意義”中心。實際上,語言現象分析的兩個步驟或層面就是圍繞“意義”來進行的,“意義”層面的“真”“對象”“概念詞”成為了作者反復提及和論證的問題。其中,“對象”(object)更是起到了“真值”決定的最后環節,“邏輯的基本關系是一個對象處于一個概念之下的關系:概念之間的所有關系都可以劃歸為這種關系”[2]122。于是,語言現象(句子、專名等)意義的決定又回到了自然世界(對象)上,回到了兩者聯系的現實經驗層面,而關于兩者聯系統一的某種必然性基礎并未通過“涵義”問題的提出而獲得解決,或者說,在“涵義”面對語言現象與自然現象的對應中,“涵義”作為意義可能的“思想”未能確立自身的必然性地位。顯然,要將“涵義”建立為某種公共的、客觀的、無需任何承載者的“思想”模式或標準就是要確立某種先驗的形而上的智性存在,并使之能夠提供一切關于語言現象與自然對象聯系的必然性基礎,即某種理性世界的“高級而純粹”的基礎。然而,對于弗雷格這樣的語言分析哲學家而言,確立這樣的基礎存在就等于添加無必要的“實體”,就等于做出了無必要的“本體論”承諾,這樣的“添加”或“承諾”不僅無助于語言分析的過程,更是有悖于解構本體存在的語言分析宗旨。所以,“‘涵義’是什么”盡管成為了弗雷格所關注的問題,并且被明確地加以提出,但關于該問題的答案卻并未被提供,更不要說關于“涵義”理論的建立了。
既然如此,“涵義”在語言現象(句子)的分析中出現又能為我們揭示什么呢?不可否認,在從語言現象到其意義層面的聯系里,即:句子→思想→真值,作為思想層面的“涵義”僅僅是一個“中介”,而不是一個“中心”,這樣的“中介”只能揭示作者在進行語言現象的“涵義與意義”的分析中意識到了某種“第三方”存在的問題,即某種關于語言現象與自然世界如此存在和統一的原因根據問題,所以,“涵義”更多地表明“意識”發生和呈現的“給定方式”[3]66,而非“意識”的內容建構。其次,“涵義”的出現與康德的影響不無關系。弗雷格在創建自己的語言哲學王國時潛心研究過萊布尼茨和康德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后者的先驗哲學與邏輯思想,應該說,弗雷格深受萊布尼茨的“普遍語言”論和康德的先驗邏輯(純粹形式邏輯)論的啟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地追尋某種理想的語言形式存在,這樣的理想語言形式不僅要成為全部語言現象的普遍邏輯形式,而且要等同于全部自然現象存在的普遍邏輯形式。那么,這樣的理想語言形式不可能由自然語言(語言現象)提供,更不可能由自然現象提供,它必須建立在某種具備客觀性和必然性基礎的存在之上,而這樣的基礎應該聯系于康德的先驗邏輯及其先驗形式的存在,盡管弗雷格的語言哲學理論使用了“涵義”或“客觀思想”而沒有認可康德的先驗形式存在。再者,不論是“涵義”也好,還是“客觀思想”也好,它們僅僅是作為了一種語言現象分析中所涉及的意義判定“依據”而提出,至于說該“依據”的出處、形成和有效性地位,弗雷格對此并未提供實質性的添加,以至于語言現象的任何真值決定完全可以繞開“涵義”的環節而回到“經驗對象”的最終存在上來,所以,當語言哲學發展到了羅素和維特根斯坦那里,“涵義”就成為了一種多余而被斷然地加以了拒絕。至此,在語言現象世界及其與自然世界的統一問題上,弗雷格的“涵義”并未帶來關于這種統一的任何必然性基礎。弗雷格的語言哲學分析所指向的是關于語言現象和自然現象的事實,以及兩者聯系的經驗事實,而非追問這種“事實”存在的必然性基礎。結果,人們經歷“涵義”后所獲得的仍然是語言現象意義決定于自然現象的答案,并且,語言現象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仍然缺少同一性的基礎和源泉,那么,兩者可以體現同一性關系的基礎和聯系的源泉又會在哪里呢?
在我們面對語言哲學的分析過程時,我們不可離開語言現象的存在事實,只有基于這樣的“事實”,我們才開始了關于語言現象的句法分析、意義索源、真值決定,等等。從此,語言現象作為知識的對象體系才逐漸地被建立和完善起來,其構成的所有部分才成為了意義顯現和規范的載體,并最終取得具備真值結果的語言現象的表現形式。當然,語言現象的“事實”不論是作為知識體系的存在,還是作為意義載體的存在,它都決不會是一個可以“自在”或“自顯”的對象,或者說,語言現象的經驗“事實”不是關于其自身作為經驗對象存在的表現結果,而應該是被“理性主體”所構建的“第二自然”結果,所以,任何從語言現象的“事實”中去尋找這種“事實”的根據都將是沒有結果的。在語言現象的世界中,人們盡管可以把經驗紛繁的語言個體對象,以及將自然因果關系體現到紛繁語言現象的聯系之中,但語言現象的對象地位始終未能離開“理性主體”的決定與構建過程,不論這樣的“構建”是否已經完成,也不論這樣的“構建”多么地遠離我們而具有自然對象的屬性,一旦語言現象的“事實”存在無可爭議,作為“理性主體”的存在地位就應該明白無誤地加以確立,否則,關于語言現象的一切經驗與知識性構建就會變得什么也不是,更不用說去獲得語言現象、自然世界、語言與世界的聯系與統一。可以說,在弗雷格的“涵義”或“思想”之外,作為“第三方”的存在就應該明確為創造了語言現象的理性主體,理性主體的存在為現象世界,包括語言現象,提供著最后的源泉或根據,哲學家康德將這樣的源泉或根據稱之為理性存在的先驗形式,那么,不論是關于自然世界的存在與統一,還是關于語言現象的存在與統一,它們所依照的并非某種外在的“客觀”對象,而是理性存在的先驗形式基礎。
在康德的先驗哲學思想里,理性的先驗形式就是一種“自明”的存在,只要我們面對了現象世界的呈現,我們就必然地面對了作為現象基礎的“自明”存在,盡管這樣的“面對自明”還不是經驗意義上的發生。在我們經驗語言現象、認識語言現象和聯系語言現象的過程中,我們實際上是在面對語言現象的事實,面對語言現象作為認知對象的事實,而不是面對語言的存在。因為語言存在不僅僅涉及語言現象經驗過程的事實,更涉及如此語言現象產生的理性主體原因根據。于是,語言存在關系到語言現象的事實,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這樣的事實,或者說,所有依據語言現象經驗和語言現象內容的知識,如語音知識、語法知識、語義知識、語用知識,等等,它們可以作為語言經驗的認知成果,也可以作為語言現象存在的事實說明,但它們卻無法作為對語言存在的完全經驗的證實。在常識性的理解中,語言的存在慣例性地被歸屬為了語言現象的事實,以至于語言現象被視為了語言存在的全部,被視為了語言存在的最后家園,然而,這樣的“家園”并未因為語言學家們的辛勤勞作而可靠起來,人們對于這種家園的最后的希冀總會缺少允諾。因此,語言存在問題的揭示既是一個語言現象經驗的過程,又是一個回歸其自身所在的過程,前者為人們展現語言現象的知識,后者為人們確立語言現象形成的純粹基礎,即作為理性之先驗語言形式的基礎。
三、語言存在的現象世界與理性的先驗“家園”
在語言存在問題探究的先驗哲學視野下,我們唯有確立語言現象的先驗理性形式根據,關于語言現象的知識才會是可能的、才會是真正屬于我們而成為認知的對象世界。或者說,我們之所以能夠認知語言現象、擁有語言存在的經驗現實,只是因為我們作為了理性的存在、擁有了關于語言存在的先驗形式原因。不管理性存在的先驗語言形式如何地具備其自身的純粹性特征,也不管它是否可以被加以描述或指稱、以及是否可以等同于語言現象的經驗特征,它的存在應該是產生語言現象和認知語言現象的前提。只有基于這樣的前提,所有關于語言現象的經驗現實方可真正地成為理性存在的現實,并呈現為合乎理性之先驗形式規定的現象特征,否則,語言現象就會什么也不是,更不用說那些關于語言現象的常識性答案了。所以,語言的存在源自于自然世界或自然語言現象的結論只能是作為一種語言“物化”的假象,其真正的“家園”還是理性存在的先驗語言形式。依據語言存在的理性“家園”,先驗語言形式在理性存在過程中的地位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加以說明:其一,關于語言現象的創造,其二,關于語言現象的認知可能。
第一個方面強調理性之先驗語言形式并非就是語言現象的事實,先驗語言形式因為自身的純粹性而區別于任何經驗過程的語言現象,即:它帶來了語言現象存在的系列,但它又不在這樣的現象系列之中,一切關于現象世界的自然因果律或時空特征的描述對于它而言都是沒有意義的,“如果理性有與現象相關的原因性,那么,理性就是這樣的一種能力,結果的經驗性序列的感性條件才首先開始了”[4]465。它應該是一個純粹理性世界的智性源泉、一種可能提供所有語言現象之根據的理性能力,這樣的純粹源泉和能力因為理性存在的“自明”而被加以確立,并因為理性的“實踐性”而創造語言現象的經驗世界。所以,語言現象中的成分表現、要素關聯、意義決定、整體統一,等等,它們無一不是在貫徹理性的先驗語言形式的規定。倘如我們依據先驗哲學的基本思想將這樣的先驗語言形式標識為純粹的理念形式、純粹的知性概念形式和純粹的感性形式,那么,對于作為有限理性存在的人類而言,先驗語言形式就成為了語言存在中的絕對之在和自由之在,就成為了某種純粹的可能性原因。這樣純粹的“語言”之因不應該內在于自身而不外顯,它必然地跟隨著理性實踐的召喚而規定著語言經驗過程中的創造,其結果就是帶來語言現象的產生、變化和發展,當然,這樣的結果決不是關于語言存在的純粹理念形式、純粹知性形式和純粹感性形式的經驗對象化,或者說,語言現象的經驗過程無法延伸到語言存在的純粹世界,對于先驗語言形式存在的“認知”永遠是一個人類無法實現的美好愿望,否則,語言的存在又會被等同于語言現象而脫離于理性的家園,從而違背語言現象的可認知限制,并引起語言現象何以被認知的無窮困境。因此,在說明語言現象的產生原因時,我們其實是在面對自身存在過程的創造,即面對理性存在的語言現象的創造,不論該創造的結果(語言現象)是否完備,也不論它處于何種階段,它的產生出現總是要合乎其先驗形式的規定,任何逃逸這種規定的語言現象都將是不可能的。那么,語言現象的表現特征,如關聯性、規律性、統一性、真假性等,都只能是作為理性存在之先驗語言形式的現實體現和反映。顯然,在我們經驗語言現象之時,我們常常說某個語言現象的個體或單位表達了某個概念或某種意義,即使這樣的概念或意義僅僅屬于心理經驗的層面,語言現象的表達可能性和現實性只有在語言現象作為理性存在的先驗形式的實踐成果(先驗語言形式條件下的創造成果)時才能存在,否則,語言現象對于概念或意義的表達就會缺失必然性的統一基礎,只有源于先驗語言形式之規定的理性統一與創造能力,語言現象的經驗過程才能通達概念與意義的層面,才能回到語言存在的純粹根據、回到語言現象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所以,不論語言現象在“自然語言”的定義中如何變得遠離理性主體,以及如何變得“客觀”而對立于認知主體,語言現象終歸還要秉承理性的先驗形式規定而作為理性存在的創造性成果。
第二個方面強調先驗語言形式基礎作為語言現象認知可能與現實的根本前提,即作為理性存在的人類所擁有的語言現象知識,如語音的知識、符號的知識、語法的知識,以及關于語言知識系統的劃分知識等等,都只能是作為合乎其先驗形式規定的經驗發生與判定結果。就語音的知識而言,它可以被展開為如何發音的知識、如何標記語音的知識、如何形成語音組合規律的知識等等,不論是作為具備自然物理性質的聲音,還是作為描寫這種“聲音”所使用的符號系統,它們都在語言行為者的經驗中奠基于理性主體的先驗語言形式,并使之本質地區別于一切外在的過程和內容。在這樣的語音知識里,不管我們是在模仿什么,還是在書寫什么,以及在發現什么,我們總會說“知道”,總會在經驗的意義上明白語音的定義、語音的符號和語音的規律等等,語音的知識就是關于這種“知道”與“明白”的內容。至于說語音的方方面面何以被認知,這與語音的方方面面是否成為了經驗的直觀對象相關,即一定要表現為某種關于空間中的占據和時間里的持存,只有如此,理性的純粹時空形式才會具備經驗對象的映照,作為語音的方方面面才能被呈現或表象,才能進入關于語音的先驗綜合過程而取得關于語音的概念與知識。所以,在語音的認知過程中,與其說我們在認知語音的知識,不如說我們在展示自己認知語音的固有先驗語音模式。當然,這里的先驗語音模式歸屬于上文的先驗語言形式,它既涉及先驗的感性模式,又涉及先驗的知性模式和理性模式,而且,它就是本文所關注的那個語言現象得以被經驗和被創造的先驗模式。于是,形成任何語言現象的知識并非是我們認識了某種異己或外在的對象,而是我們認識了語言現象的存在基礎與先驗語言形式的相通性和一致性。而且,只有具備了這樣的相通性和一致性,關于語言現象的知識在我們人類這里才具備了形成和統一的前提,作為“第二自然”的語言現象才會在“是什么”的意義上取得真正普遍性地位的判定。在語言現象作為理性存在過程或人的存在過程的必然現實之時,從語言現象回歸其先驗形式之路應該是相通的,語言現象“也是通過純粹理性產生”[5]184,任何的否定則會導致語言現象存在的消失(沒有“相通”就無法承認語言現象“直觀”的發生),這樣的結果有悖于語言現象經驗過程的現實。 顯然,我們可以盡情地享受“語言(現象)是什么”的無窮經驗過程,享受語言現象世界的宏大、奇妙、有序、變換與意義, 但我們卻一點也不能享受那些無法被直觀、無法作為我們的經驗對象的語言存在(倘如我們還可以稱之為語言存在的話)。所以,語言現象與其先驗形式的相通無疑為我們呈現了這樣的情形:語言現象一定是作為我們經驗直觀對象的存在,其如此呈現的根據必然聯系于理性之先驗語言形式的存在。盡管語言現象的“是什么”判斷總是被限制在經驗直觀的世界之中發生,但這樣的限制卻絲毫不會影響相通性的存在,從經驗直觀到其純粹直觀形式、從純粹直觀形式到其純粹知性形式,以及純粹理性形式的進程都應該是相通的。不僅如此,語言現象與其先驗形式既是相通的,又是一致的,語言現象與其先驗理性形式的一致性區別于它作為知識存在的一致性。我們擁有關于語言現象的知識,可我們并不擁有關于先驗語言形式的知識,所以,這里的“一致”體現為語言現象對于其先驗形式規定和要求的完全貫徹、合乎與響應,體現為語言現象無一例外地歸屬于理性之先驗語言形式的存在結果,體現為現象世界的語言知識統一緣起于純粹理性的形式統一的關系存在。總之,只有我們立于了兩者之間的“相通性”和“一致性”關系,關于語言現象的知識才具備了真正的意義存在,即語言的現象關系和呈現事實在于擁有其決定根據或理性的先驗形式存在。在理性存在的世界里,語言現象的知識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一切關于語言現象的分析與綜合,一切關于語言現象的思想與探尋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從現象到本質的“返回”,一種關于語言存在的尋根之旅,其主體只能是理性的存在或人類自身。所以,任何關于語言存在問題的澄清必然聯系到關于理性存在或人的問題的澄清,那種將語言存在問題僅僅歸屬于語言現象問題的研究只能導致語言實踐的結果凸顯而忽略關于這種結果的理性根據或原因追問,并且,這種研究所能取得的成果除了作為一種有限的、相對的和暫時的認識成果之外,它無法帶來關于語言存在探尋的真正統一性和全面性基礎,只要我們置身于語言現象的世界里,只要我們將語言現象視為語言存在的全部,那語言存在模式或決定根據就會變得紛繁復雜,處于流變之中而難以確定,更不用說去尋覓語言存在的統一性原因。所以,縱使有無數的語言研究者能夠提出無數的語言學理論和規律發現,操控語言存在之路對于他們而言依然是那么遙遠和困難,除非他們能夠回歸語言存在的理性世界。
總之,在語言現象及其統一的必然性基礎問題上,如果我們可以從弗雷格的“涵義”思想中獲得其拓展和通向康德的先驗分析之路,我們就可以說:“涵義”作為一種在語言哲學中被討論的“客觀思想”已經具備了將語言現象及其意義源泉聯系于語言行為者的可能趨勢,只是弗雷格因為自己的“心理主義”考慮而要將這樣的“涵義”客觀化。在“涵義”被弗雷格闡釋為“客觀思想”時,他是無法回避“涵義”作為語言現象存在的產生性模式的,這樣的產生性模式不可能因為它的客觀與普遍性地位賦予就能同語言行為者的主體性世界區分開來。只要我們將“涵義”及其產生性模式回歸到它應該所是的位置,這樣的“位置”只能屬于語言行為者的世界。如果我們將語言現象及其統一的必然性基礎同“涵義”及其“客觀思想”聯系起來,那“涵義”的“客觀”與“普遍”之意就應該是語言行為者作為理性主體存在所共同擁有的語言存在模式,即理性的先驗語言形式。不論是涉及語言現象經驗的感性階段,還是涉及其知性階段,作為先驗形式存在的語言基礎總是在提供著一種產生語言表象世界中的統一性和區分性特征的純粹理性原因,所有關于語言現象世界的區分、綜合與統一在于理性主體的先驗語言形式。簡而言之,同自然世界的情形一樣,語言現象世界的統一性源于理性存在的統一性,其具體語言現象內容的差異性源于直觀表象的差異性,其定義的區別性特征源于知性概念的區別特征。至此,先驗認識論提供著這樣的前提:自然過程的表象與統一不可離開我們所具有的先驗認知模式,一旦這樣的模式被貫徹到語言現象與自然物的經驗中,它就不僅僅屬于理性的先驗存在形式,而且帶來了關于這種純粹形式存在的經驗現實。當然,語言存在的現象世界就在這樣的經驗現實之中,語言現象世界的區分與統一、經驗直觀與概念綜合同樣要源于理性的先驗語言認知模式或先驗語言形式的存在。
[1] 弗雷格. 弗雷格哲學論著選集[G]. 王路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 王路. 邏輯與哲學[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肖福平,肖紹明.走進語言哲學[M].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
[4]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t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33.
[5] Heidegger.TheEssenceofHumanFreedom[M]. trans. Ted Sadler. London, 2002.
[責任編輯:劉力]
On Necessary Foundation of Language Phenomenon and Its Unity
Xiao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language phenomenon, we often take the phenomenon and its unity as its inherent quality, and has the status of objectivity; Frege’s language analysis notes the relevant knowledge in his language philosophy theor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sense” for getting rid of psychologism, and hope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model of language phenomenon’s existence and unity; Frege’s concept of “sense” reveals the common basis for experiencing language phenomenon, but such “reveal” has not establish the real source for “common basis”, only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se” and the returning to the thought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can we ascertain the necessary basis of the being and the unity, i.e. the whole world of phenomenon and its unity has been decided by the rational being and its form a priori, including pure language form a priori.
language; reason; sense; transcendental form
2016-09-20
肖福平(1962-),男,重慶璧山人,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和語言哲學研究。
IH0-0
A
1673—0429(2017)01—007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