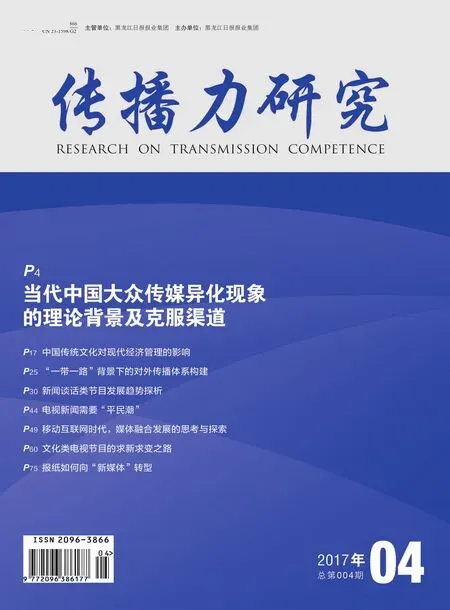對“平庸之惡”背后的群體思維的解讀及當下的思考
文/王爽
1960年,納粹的頭號戰犯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成功捕獲,阿倫特在當時接受《紐約客》雜志的邀請,以雜志特約記者的身份去現場報道。在去往以色列之前,阿倫特曾提前閱讀了警方公開公布的3000多頁的卷宗。最后發現,被阿倫特認定為窮兇極惡的艾希曼不過是一個滿口陳詞濫調、微不足道的小丑式人物而已。
隨后,阿倫特在其1963年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了“平庸的邪惡”這一概念:做出惡舉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惡之徒,哪怕是平日連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驅趕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體中,成為大環境運轉的一員,就很容易因為選擇“服從”而做出連他自己都難以想象的事情。
從群體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一個人之所以會犯罪,并非是由于這個人的性格中有及其極端的成分,而他也可能是極其溫和、順從的人。當群體中達成一致訴求的需要足夠強大時,謹慎的思考和合理的決策就會喪失,使得一些成員甚至會為了維護群體和諧而去壓制群體的異見,這是美國心理學家厄文·賈尼斯率先提出的關于群體思維的定義。
受群體思維的影響,群體的和諧一致成為群體所追求的特征之一,多數群體成員傾向于既簡單又明白、贊成票居多的解決方案。雖然追求一致是群體討論的目標之一,但當個體間的不同觀點甚至是理性的聲音被完全忽視,非理性的聲音占據主導便可能形成集體的惡行。據此可以看出,“平庸之惡”思想的實質是群體思維作用的一種表現形式。
一、群體思維的產生條件
(一)高水平的群體凝聚力
群體凝聚力對于群體思維的發生是必要而非充分的。艾希曼是個惡名昭彰的納粹罪犯,負責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然而在審判之中,他并不承認自己的罪責,他真誠地信奉著納粹組織的思想,堅定地相信組織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因此在執行命令時,也毫不猶豫。納粹組織的群體凝聚力可以被稱為是較高水平的,當這種高凝聚力在其他的共同作用下,會有極大的可能性產生群體性的思維模式。在納粹組織中,高水平的群體凝聚力為殘忍的群體思維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責任分攤心理
責任分散效應也被稱為旁觀者效應,它被認為是心理學中一項被基本證實的群體效應。當從事某種社會行為時,集體行動帶給個體的道德壓力、法律風險要遠遠低于個體單獨行動,當然這里的集體行為也包括集體不作為。屠殺作為一種反良知的惡劣行為,由于人本能地趨利避害,大部分的普通個體擁有合理的自我判斷。但在群體面前,個人產生的“法小責眾”的想法,讓他們面對屠殺變得理直氣壯,增強了對自我“惡”的行為的信心而不去懼怕個人行為后果。
(三)命令式的領導方式
勒龐認為有群體的地方就有領袖,他是核心,是各色人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希特勒對于軍隊的領導方式毫無疑問是命令式或稱之為強制性的,艾希曼殺害猶太人在他的個人陳述中僅僅是因為要執行命令,他堅信希特勒對他的領導,并認為這是對于國家人民有益而正義的事情。這種命令式的領導風格不鼓勵來自其他成員的不同觀點,不遵從正常的討論程序,容易嚴重阻礙群體成員的認知過程和道德判斷能力,也是群體思維產生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
二、現代媒體環境下對“平庸之惡”的思考
在新媒體技術出現之前,受眾和媒介的關系一直處在一種偏向傳遞的形式,而非雙向互動。新媒體的出現顛覆了一切,徹底改變了受眾主要依靠接受媒體信息而無法傳遞聲音的傳統模式,兩者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而在這種互動中可能產生的消極效應便是“平庸的惡”的產生。
在網絡如此普及化的今天,網絡的匿名性和快速傳播的特性也使得很多網民在網絡上盲目跟風,形成沒有事實依據的群體性輿論傳播。在新媒體發展的今天,一次次的輿論暴力事件不斷地驗證著“邪惡的凱旋僅僅需要的是善良的袖手旁觀”這句話。網絡群體的“一邊倒”現象,對當事人造成重大傷害時,保有理性的人成為沉默的螺旋亦是一種對“惡”的助勢。在警惕自己造成“平庸之惡”的同時,更要勇于站出來反對被群體思維控制的不正確觀點,發出自己的聲音。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2](法)古斯塔夫·勒龐.戴光年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11.
[3]蔣露今.新媒體語境下的“烏合之眾"[J].今傳媒,2013年第3期.
[4]陳力丹,陳俊妮.論組織內傳播[J]. 新聞與傳播評論,2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