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
陶悅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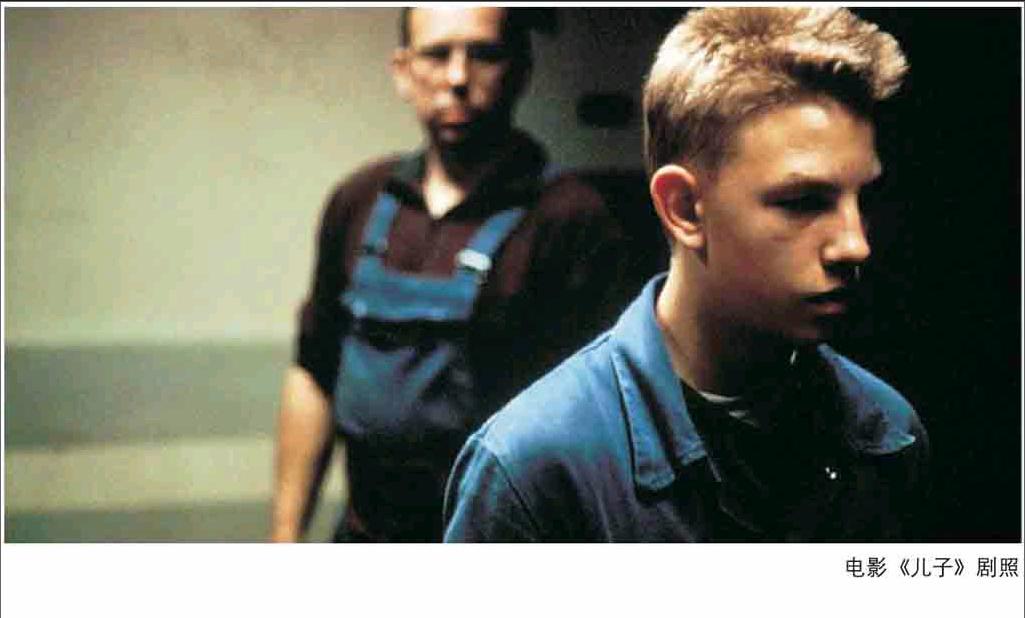
【摘要】 朗吉努斯在其《論崇高》中,將奧德修斯去往冥府向埃阿斯的鬼魂道歉,而后者沉默以對的場景,稱作是整部《奧德賽》中最為崇高的部分。這雖然是朗吉努斯從古典修辭學角度所做出的評價,但崇高作為一個現代概念,“埃阿斯式沉默”所表現出的與人性有關的隔絕與斷裂,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本文選取《兒子》《趣味游戲》《四月三周又兩天》《八月》和《清水里的刀子》五部中外電影,通過對其中特殊沉默場景的分析,討論當代電影中埃阿斯式沉默的表現、效果以及在當下探討崇高的意義。
【關鍵詞】 當代電影;崇高;埃阿斯式沉默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我這樣說,他沒有回答,卻同其他故去的死者的魂靈一起走向昏暗。他本可抑怒和我作交談,我也愿意。”[1]216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奧德修斯經女巫指點通過冥土回家,在地府中,他遇見了昔日戰友埃阿斯的鬼魂。埃阿斯身為僅次于阿喀琉斯的希臘英雄,因與奧德修斯的一場爭執而自殺,未能死于戰場。奧德修斯為此深感愧疚,他向那魂靈哀悼并且道歉,然而埃阿斯的回應卻是什么也不說,跟隨著其他鬼魂一道走入深淵。
古希臘作家朗吉努斯在其著作《論崇高》中對此評價:“不形之于言,卻比任何談吐來得高尚。”[2]84在他看來,埃阿斯的沉默與奧德修斯一系列精妙的修辭形成極其強烈的對比,后者站在勝者和生者的立場,使用大量辭藻來表明悔意,然而埃阿斯卻沉默應對,以無言瓦解修辭,因而形成了崇高的風格,他也由此肯定了荷馬的偉大。
這是朗吉努斯從古典修辭學角度出發所做出的評價,整部《論崇高》也旨在探討語言的崇高風格,以期對這種特殊審美感知的生成機制及手段做出解釋。但在全書完成之初它并未受到重視,直到中世紀后才被翻譯成各種文字。書中關于崇高的探討,極大影響了后世歐洲美學的發展,因而使之成為一個重要的現代概念。這種效果“延后”的原因在于,與智者派、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修辭學派不同的是,這些當時的修辭學理論基本都指向一種對情感和注意力的操控,認為修辭術可教,而朗吉努斯所討論的崇高卻是不可教的,更多是指向一種失控狀態,即人在突破感性與知性臨界點時的不確定性,而這種對不確定性的關注顯然與現代的思考方式更為接近。由此,本題中“崇高”含義,并非現代漢語中崇高的含義,而應是一種臨界狀態的感受,對這種感受的把握能夠帶來什么,就是“埃阿斯式沉默”在今天被討論的意義。
埃阿斯身為荷馬詩中的偉大英雄,與奧德修斯爭奪阿喀琉斯死后的遺甲,由于奧德修斯使用詭計導致他未能勝利,因而飲恨自殺。如奧德修斯所說,埃阿斯的鬼魂“本可抑怒”和他作交談,但卻最終含怒不語,走向昏暗。在這個場景中,埃阿斯的沉默所展現的是對自身不強大的承認,這種失落感傳達出了人生中無可談論又無可奈何的隔絕與斷裂。面對奧德修斯,他已是失敗者,作為一縷幽魂,他意識到了人之為人的局限與節制。因此,他的沉默是一種壓倒性的情緒,可以喚起人們心中的挫折感,引發一種超越性的思考與行動,因而也就指向了崇高。
在電影中,同樣存在大量沉默場景,但并非都能構成埃阿斯式的崇高。康德在其《判斷力批判》中特別區分美與崇高,認為后者是“自然表象中感性之物由以被評判為適合于對之作可能的超感性運用”[3]106,即由理性運作的對經驗的否定,而非想象力與知性的游戲。其表現在于克服感知性尺度時,因對經驗把握失敗而導致的失落與挫敗感,是一種對于自我的否定,因而成為康德意義上的反思判斷。在康德之后,后康德主義批判這種將感性與超感性區分的做法,認為二者從來都是交織在一起且使得主體參與其中的。尼采在《崇高者》一篇中更寫道:“這就是靈魂的秘密,惟當英雄離棄靈魂,方能在夢中接近。”[4]150其意指康德所謂的否定性克服已經失效。但無論以何種觀點來看,本文所要在電影中尋找的埃阿斯式沉默,必然不是從經驗出發而引起的一系列情感表達,而恰恰在于對經驗把控能力喪失后的考察。
當代電影中的哪些沉默情節設置構成了此種崇高、這樣的安排又能起到什么樣的效果,以及在當下探討崇高有什么意義,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以下選取《兒子》《趣味游戲》《四月三周又兩天》《八月》和《清水里的刀子》五部中外電影進行分析。
一、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
沉默(silence)概念的涵蓋面非常廣,它指噪音或聲音完全喪失的安靜狀態,推展開來也可以是一種無人說話的尷尬處境,或是某人拒絕談論某事或回答某些問題的舉動,以及其他任何溝通上的缺失,在這一點上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日常言語和音樂。[5]1420沉默的行為或是現象在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已引起許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與關注,如諾爾·諾依曼的《沉默的螺旋》從政治學傳播學的角度研究群體意見與沉默現象,喬治·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基于文學發展,針對語言文化的衰落對政治暴行深入反思。而在我國,學者們多從語用學出發探討沉默的功能,在各種文本中進行話輪研究,按照萊文遜(Levinson S.C.)在《語用學》一書中的做法,將其分為話輪間沉默、話輪內沉默和話輪沉默。
從電影史來看,由于技術的限制,早期電影是既沒有色彩也沒有聲音的。1895年6月,盧米埃爾兄弟拍攝影片《代表們的登陸》(Départ en voiture,1895),在放映時演員拉格蘭奇站在銀幕后將自己的臺詞重復了一遍,被電影史家喬治·薩杜爾(George Sadoul,1904-1967)稱為“有聲電影第一次天真的嘗試”[6]7。三十多年后,導演阿蘭·克勞思蘭德(Alan Crosland,1894-1936)拍攝制作的影片《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1927)正式上映,在其中插入了歌曲與對白,標志著電影制作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有聲電影的出現,宣告了“沉默”作為固有屬性的瓦解,也因此在人聲、音響、配樂等范疇方面出現的沉默狀態,給觀眾帶來了新的體驗與解讀路徑。貝拉·巴拉茲在其《電影美學》的“聲音”章節中談到沉默:“在影片里,沉默可以成為一種非常動人的效果,可以起多種多樣的作用,因為沉默固然意味著不說話,但它并不排斥各種各樣的表情和手勢。一個無聲的眼色可以傳達無限深情,無聲的人反而更有表現力,因為一個默默無言的人的面部表情能夠說明他沉默的原因,使我們感覺到他的威嚴、他的氣勢或他的緊張心情。在影片里,沉默絲毫不會中斷動作的發展,而這類無聲的動作甚至會造成一個生動的局面。”[7]218-219在這里,有聲片中的沉默被認為是使得其他細節被增加關注的原因,將對影片情節發展引起新的緊張與新的意義。
沉默是有聲片中對于有聲狀態的人為暫停,但同時也是對這種狀態的補充。在敘事意義上,沉默能夠體現影片的復雜性與開放性,而在觀影體驗上,沉默場景則能強化觀眾對于影片時間感的捕捉。從這一點來看,電影中的沉默場景似乎是為觀眾提供了一個想象與回憶的空間,而在這空間之中又必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種沉默的可能。本文中所要討論的就是基于電影情節同時延伸到某種特殊情感判斷的沉默場景,通過對埃阿斯式沉默在影片中的效果分析,發掘其在當下討論崇高時所能夠起到的作用。
在達內兄弟的電影《兒子》(Le fils,2002)中,木匠奧利維的兒子在五年前被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的少年所殺。五年后,當奧利維在自己的木工學習班中重遇這個殺人犯時,已經完成了官方贖罪程序的少年似乎并沒有將他認出。但奧利維沒有忘記,這場重逢勾起了他內心中壓抑已久的情緒,使他無法保持冷靜。在上課過程中,奧利維從不喊出弗朗西斯的名字,課程結束時也唯獨不與這個男孩握手道別。但同時,他卻又一次次地偷偷跟蹤弗朗西斯回家,他的眼神無時無刻不追隨著這個讓他痛失愛子的少年。奧利維的這些怪異扭曲行為一直持續到了影片臨近末尾處,當弗朗西斯說出“你能當我的監護人嗎?因為你教我做木工,還關心我”時,他再也無法忍受,將那個具有毀滅性的秘密告訴了面前的人。
“你殺死的那個男孩,是我的兒子。”奧利維的話一出口,弗朗西斯立刻選擇了逃跑,奧利維在他身后追趕,靠著年齡和身型的優勢將弗朗西斯制服在地。他用雙腿壓住少年的胸膛,他的雙手緊緊地扣住了身下人的脖頸。時間在這里被無限拉長,特寫鏡頭從奧利維的雙手移到了他的臉旁便不再變動,鏡頭中的他不斷喘息,額頭上的汗滴落到眼鏡片上。之后鏡頭又切換到中景,奧利維松開了手,從弗朗西斯身上離開。
影片的最后,奧利維在木廠前將木料搬上拖車,沒過多久弗朗西斯走到了他的身邊,拿過剩下的木塊將其安放到了車上。奧利維看著他,沒有說一句話。
奧利維沒有掐死弗朗西斯,甚至在后者回到他的身邊時默許了其幫忙搬運木料的行為,整部影片就在奧利維的沉默中戛然而止。這似乎是觀眾喜聞樂見的場景——少年殺人犯被寬恕并且被接納,但這是寬恕嗎?
探究奧利維最終的沉默指向,需要追溯到他的前一個行為,即在追逐中他將弗朗西斯制服卻并沒有將其殺死,而這樣的行為又使得我們不免回到影片的最初,追問奧利維為何不在認出弗朗西斯的時候即刻動手。
一個父親在盛怒之下向殺害兒子的兇手復仇也是常常會被展現在熒幕上的題材,這其中的悲苦與壓抑,或許是觀眾想要看到的。但奧利維卻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傷害弗朗西斯的想法,只有在后者得知真相逃跑,而他立刻起身去追時,才讓我們看到了一絲他想要復仇的沖動,但這沖動也很快消失在了他松開的雙手上。與之相反的,奧利維更多向觀眾展現的是他與自身的不停斗爭,那些扭曲又怪異的行為,故意冷落與偷偷跟隨,甚至讓弗朗西斯感受到了如同父親般的關心與陪伴。而奧利維又何嘗不是?他曾偷過弗朗西斯的鑰匙潛入其房間,看那孩子抽的煙,躺那孩子睡的床,如果說這是他在弗朗西斯身上投注了對兒子的思念是太過牽強的,那么至少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似乎也不是恨,而只是少年的飄零。
所以奧利維的沉默不是寬恕,而是一種不確定。他自己也無法明白自己的欲望是復仇還是原諒,他不知道應該選擇哪一個。奧利維甚至要比從前跟蹤弗朗西斯時更加掙扎,因為一切都已經說開了,而孩子又走回了他的身邊,那么接下來到底應該怎么做?在奧利維將弗朗西斯壓倒在地的時刻,他意識到了后者在殺害兒子時的那種情緒,于是他最終強迫自己從沖動中抽離,將手松開。這是成年人的冷靜與自省,但同時又是生命中的斷裂,因為奧利維還是放不下。他的沉默帶著對于自身的不確定,他意識到即使殺了對方也無法改變的事實,所以沒有動手。
達內兄弟一貫的紀錄片式拍攝手法,筆直地盯住角色本身,對其心理活動的刻畫到了冷酷無情的地步,而這種內心的洶涌都隱藏到了奧利維的沉默之下。
哈內克的反暴力之作《趣味游戲》(Funny Games,1997)講述了一個以游戲來進行恐怖殺戮的荒誕故事,全片沒有直接描述血腥場面卻令人不寒而栗,做到了讓暴戾無因又使人心悸不已。影片中,主角一家來到鄉村湖區度假,遇到了兩個態度友好又需要幫助的年輕人,女主人不疑有他地將二人迎進家中,卻不想換來的是一場毫無憐憫的囚禁凌虐游戲。整場殺戮在主角一家的別墅中完成,兩個年輕人先后打死了主角家的寵物狗、敲碎男主人的膝蓋、強迫女主人在所有人面前脫衣,緊接著提出開啟一場死亡游戲的單方面決定,游戲的主題則為“明天到來之前主角一家全都會死”。在“游戲”過程中,年輕人們輕佻又無謂的態度與主角一家崩潰無力的神情形成強烈對比,導演將這種暴力無限制地放大,讓兩個白衣惡魔將全家人的尊嚴與信仰打碎。最后,男主人與兒子被開槍射殺,女主人則被捆綁后丟入湖底。明日到來,無人生還。
全片劇情緊湊,通過施虐者的暴力循環,讓觀眾始終處于一種焦慮與不適的狀態。但在這循環之中,仍存在一處長達180秒的停頓,兩名殺手在開槍射死這家人的兒子以后暫時離開,攝像機給了別墅客廳一個全景且保持不變,鏡頭中出現了受傷倒地的男主人的雙腳、被捆住手腳的女主人的上半身、躺在血泊中的男孩尸體,以及不斷切換賽車畫面的電視機。
此刻影片中的畫面仿佛靜止,只有電視機變化的亮度與節目聲音能提醒時間的存在。女主人于1分17秒后起身,蹦跳著來到電視機前將它關閉,至此影片中所有聲音全部消失,女主人就跪在電視機旁一言不發,全程沒有朝死去的兒子看過一眼。
這場沉默為女主人同時也是觀眾劃出了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之中,女主人或許是在從過度崩潰的情緒中尋求平靜,或許是在思考接下來該如何逃離,但更為可能的狀況,她只是被嚇壞了而已。過度疊加的暴行使得她的身心承受能力都達到了即將瓦解的狀態,在這樣的臨界點上,她的所有情感已經被剝奪,腦中一片空白。她從靜坐到起身去關掉電視的過程中都不曾看過兒子一眼,而那卻恰恰是這短短幾步中必然需要面對的事情,但她沒有看。她從兒子的尸體旁跳過,最后背對著血泊中的小孩跪坐沉默,她不知如何面對也想不明白之前所發生的一切,于她而言實在是過于瘋狂與恐怖。
對于觀眾來說,這樣長時間的沉默是十分難熬的,但同時也得到了喘息的機會。一般來說,兒子被槍殺后應該會有特寫鏡頭,不論是給誰,但本片導演卻將機位固定,讓觀眾始終處在被動的客觀視角去觀察女主人的精神狀態,實際上也是被強迫著去反思暴力本身以及在觀影時希望從暴力中獲得樂趣的行為。
“我的目的是在觀眾眼前呈現真正的暴力,讓他們發現自己是如何成為施虐者的共犯……進而成為煽動下的受害者。”[8]162導演哈內克還原了暴力的本質,試圖想讓觀眾明白的是:暴力不是娛樂與消遣,而是一種無法承受的痛,無論是發生在誰的身上。
羅馬尼亞影片《四月三周又兩天》(4 luni, 3 saptam?ni si 2 zile,2007)講述了在蘇聯解體前夕的1987年,當時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羅馬尼亞將墮胎定義為非法行為。影片女主角為了幫助自己的大學室友兼好友秘密墮胎,通過其他朋友介紹,聯系到了愿意冒險做手術的醫生,并且籌集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手術費用。但就在做手術前,醫生卻認為錢的數目遠遠不夠他去冒坐牢的風險,于是提出用兩名女學生的身體來做交換。面對脆弱的好友,沒有選擇的主人公同意了這個要求,在廉價旅館中承受侵犯之后,主人公的好友才得以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流產。
由于事先與男友有約,女主人公中途暫時離開了旅館,在到達目的地以后,她向男友問出了糾纏著內心的一個問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你會怎么辦?”男友的反應顯得有些無措,他起初回避了問題的重點,堅持認為他已足夠小心,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而后在女主人公的再三逼問下,他才回答道:“也許……我會娶你。”
主人公回到旅館時,好友腹中的胎兒已經流出,她用白毛巾包裹住將成型的血肉后沖下旅館,在穿過一條又一條黑暗的街道之后,將其丟棄在了路邊的垃圾桶中。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與好友無聲地對坐于旅館的餐廳中,侍者端上一份由各類動物內臟所組成的菜肴,好友面無表情地將它吃下,而主人公沉默地看著她。遠處傳來某個婚禮現場的喧鬧聲。
在被醫生侵犯之后,女主人公赤裸著下身沖進旅館的浴室,用力搓洗自己。在中途離開去往男友家的公車上,她靠在窗前,無聲地流下眼淚。在抱起胎兒的尸體下樓后,她害怕又緊張地穿梭于暗巷之中,急促而壓抑地喘息著。
盡管無助且惶恐,主人公卻獨自承擔著這一切瀕臨崩潰的局面,她或許恨過好友,卻更多牽掛。然而當她最終回到旅館,看著好友毫不排斥地吃下那些帶著血絲的動物內臟時,她突然感受到了所有行為的荒誕性。男友在家中給出的那個回答也在此刻顯得諷刺無比,因為好友無動于衷吃下動物器官的模樣,或許就會是她的將來。影片最后,伴隨著遠處婚禮現場的喧鬧聲,餐廳窗外偶有車燈一閃而過,女主人公轉頭看向攝影機鏡頭,電影就結束在這里。
一鏡到底的中景,逐漸擴展的裂痕,強烈的無力感在主人公1分04秒的沉默中蔓延開來,最后的疑問被隱于突然降臨的黑幕之后——事情何以會壞到這個地步?
在大陸影片《八月》(2016)中,剛結束小升初考試的曉雷正享受著沒有作業的暑假。他的父親是電影廠的一名剪輯師,平日無事時會帶著他去游泳館學游泳、去田埂間捉蛐蛐、去電影院看免費電影……就像每個炎熱又自由的夏天一樣,影片中充斥著九十年代初內蒙小城里反復的家庭生活與大把的閑工夫,而曉雷就用他少年的眼睛觀察著這個司空見慣的世界。
然而這個夏天又似乎有些不同,電視新聞中不斷播報的國有單位改制新聞,宣告著鐵飯碗的打破,曉雷父親所在的電影廠也受到了改制的沖擊,面臨著解散重組的局面。家屬院中的大人們看似平靜,心卻如同這夏日般燥熱起來,曉雷仍舊百無聊賴地耗著,直到父親為了生活遠走他鄉,他才真實地感覺到時間過去了,一切都在改變著。
在影片的后半段,電影廠舉辦了改制前的最后一次員工運動會,男女老少都參與到了拔河項目中,這時突然響起一條廣播,說廠里的卡車啟動不了了需要大伙去推,眾人聽了立刻就放下了手里的長繩,沒有任何的遲疑。曉雷站在人群之后,安靜地看他們往廠門口跑去,他知道自己的父親并沒有在這其中,而是坐在電影廠的暗房里剪輯最后一條片子。曉雷看著,沒有向前也沒有說話,接著在卡車成功發動的時刻,選擇了一條小岔路,走開了。
國家政策的改變真正能夠影響什么,曉雷或許不會懂。但父親與他不再能夠以員工及家屬的身份免費看電影、廠里原先畫海報的工人轉行去街上刻字、與父親關系極好的導演云叔離開了小城……這些都讓他隱隱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變化。究竟是什么他說不出,但看不清前路的現實卻是片中每一個人都在經歷的,對未知的迷茫與自身的不確定化成了曉雷沉默的背影,他沒有向前融入推車的人群之中,反而是選擇了條岔路離開,這種無法向他人甚至自己言說的失落感,沖破了一整個時代來到我們的眼前。
《清水里的刀子》(2016)改編自回民作家石舒清的同名短篇小說。在影片中,穆斯林老人馬子善的老伴去世了,他的大兒子準備將陪伴老人十多年的牛殺了來祭祀自己的母親。馬子善老人起初不同意,因為家中實在已經不寬裕,老牛還能用來分擔一些農活,但大兒子希望能讓生前活得辛苦的母親不再受虧待,因此執意殺牛。老人最終同意了,且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對牛細心照料,可就在祭祀儀式的前幾天,牛開始不吃不喝。
這讓老人想起了穆斯林的民間傳說,牛作為“大牲”,如果其死是被用作正途,那么牛在死之前就會預知自己的命運,它將在喝水的盆中看到一把屬于它的刀子,由此不再吃喝,以期保持一個完全潔凈的身體來迎接死亡。牛與老人一樣已經接近暮年,它的行為促使老人生發出了自身對于死亡的感悟。為了清凈內心的污濁,清清白白地離開人世間,老人在祭祀儀式之前將妻子生前向鄰里欠下的五塊錢還上了,隨后他牽著牛去田野間散步,在那里看見了老伴的靈魂在田里耕作。
整部電影從老人妻子的葬禮開始,以牛之死作為結局,所有敘事都圍繞著這兩個死亡主題流動。在影片最后,殺牛祭禮即將開始,馬子善老人提出要去一趟集市,兒子說:“大,今兒你不能走啊”,老人沒有回答。
“牛知其死,他貴而為人,卻不能知道。”[9]355在原作中,作者說這是令馬子善最為傷痛的地方。然而在影片中,老人的沉默或許還含有更深的斷裂。他從牛不再吃喝的行為中體悟到了死亡,并且已如牛一般潔凈自己,按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來說,不論是對牛還是自身的死亡,他都理應能夠從容面對,且看透這世間的生死循環。然而就在牛要被宰殺的時候,老人卻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辦法做到坦然面對。逝去的老伴,還有即將死去的老牛,都是如此,他的心中還是不舍。
對于兒子的挽留,老人沒有作答,沉默許久后還是去了集市,直至日落才歸。老人回家后,先去牛棚轉了一圈,隨后才打開院門,可見其心。
二、斷裂之下的崇高及意義
崇高一詞雖最早出現于古希臘作家之筆,但作為直到近現代才受到重視并引發討論的一個概念,在現代美學研究中常被認為是美以外的最重要的審美范疇。然而在現實語境和具體判斷中,卻總會出現對于崇高很難避免卻又十分普遍的誤讀。
以電影為例,在抗美援朝題材影片《英雄兒女》(1964)中,志愿軍士兵王成在戰斗中喊出了“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的口號,在王成壯烈犧牲之后全軍開展了向他學習的運動。在這里,王成的英勇行為被認定為崇高,而在現代漢語語境中,崇高似乎也包含了這樣高大正面的形象。如此,以無所畏懼、英勇赴死的姿態煽動觀眾情緒的英雄片和戰爭片不勝枚舉,大眾也傾向于同意將其稱作崇高。但這究竟是道德上的高尚還是美學意義上的崇高,顯然是混淆的。
與朗吉努斯評價《奧德賽》極為相似的,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其美學著作中曾談到《約伯記》(The Book of Job),他認為其中對于恐怖與不確定性的描述是極為崇高的部分:“它包裹在無盡的黑暗之中,不是比最生動的描寫、最清晰的畫作所能表現的意象更令人敬畏、更令人震驚、更為恐怖嗎?當畫家們清晰地展現這些古怪的、恐怖的觀念時,我認為幾乎所有人都失敗了。”[10]55由此,美學意義上的崇高并不是現代日常漢語中所表達的高大宏偉之意或是僅僅將其視為某種高尚的品德,而應是一種與恐懼有關的、主體去把握自身不確定性時的狀態。
奧利維的掙扎、女主人的崩潰、女大學生的無力承受、曉雷的失落、老人的無奈……如上一節中所述,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其崇高表現幾乎都不是高大正面的,而恰恰是基于一種痛苦,這種痛苦表現在沉默者突破自身感知性尺度時的不確定。在這種不確定之中,主體面對的不是豐富的經驗或經驗的正面生成,而是經驗所帶來的意識到自身無能的某種失落與挫敗,是人生中無法談論又無可奈何的斷裂與隔絕。而在《英雄兒女》中,觀眾所能感受到的王成并不懼怕死亡,他是為了心中信仰而慷慨赴死。如果僅是從這一層面來理解人物且止于此,那么王成所完成的就只是一個合目的的道德行為,因而與審美上的崇高無關。
崇高不是純粹的激情,也并非帶善的宣教。對好的道德行為的贊嘆并不能使我們得到相應的道德提升,反而會因無法把握其實質而成為教條主義。要真正地理解道德行為,只有回到其原初情境之中,回到那個感知性尺度被突破的臨界狀態,當我們感受到其中的恐懼與艱難甚至是無法自持時,才能夠接近道德。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如果觀眾只是在觀看一個悲慘壯烈的故事或是角色,而不親自去感受那個臨界狀態,是不可能體會到真正的崇高的。因為簡單的觀看只能是被知性中的概念,固定了想象界限,從而放棄運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將一切都訴諸情感,而情感稍縱即逝,無法保持一種可靠的生命力。
這種回到原初情境又追回自身的自反行為,在評判崇高中是被必然要求的。康德在這一點上強調了反思空間的重要性,即在這個空間之中,我們不要急于行動,而是要去思考行動的可能性,去認識到自身理性的力量從而克服經驗帶來的失落,最后才達到崇高并由此展開自由的不受情緒支配的行動。但在后康德主義者看來,這樣的一種空間到了現代已經幾乎不可見了,感性與超感性、主體與客體總是交織在一起無法區分開來,人們在被恐懼或痛苦壓倒時沒法再去克服,而是深陷其中,這也是現代人體會崇高變得越來越困難的原因。
但反思的能力與行為總是不可缺少的。由此,電影或許是能夠人為提供這樣一個空間的較為合適的載體,而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更可作為崇高體驗的途徑之一。當電影人物突然陷入沉默,觀眾在這無聲的時刻才能開啟自由想象的空間。也正因如此,我們甚至要呼吁多一些這樣的沉默時刻,而且是讓觀眾“難熬”的沉默。
在這沉默所提供的空間之中,觀眾從體會角色心境轉換到感受自身的能力,同時影片中的空白又迫使其不能訴諸情緒而是尋求理性的幫助去思考問題。真正的崇高能讓我們感受到自身擁有突破的能力,卻同時不會狂熱或是狂妄地認為能憑一己之力完全達到預想。在無法把握經驗的情況下去尋求自身理性的幫助,實際上是對經驗的一種否定,而就是在這樣的否定中,真正的崇高者在行動時往往就展現出了安靜甚至表面上的無動于衷。所以,當奧德修斯用了大量修辭來表達自己的悔意與哀思后,埃阿斯沒有拒絕也沒有接受,他只是沉默。恰恰是這種狀態讓我們不能在理性之外找到附著點,不能去依靠感情來理解他的沉默,而只能去直面生和死之間永遠的鴻溝。如果埃阿斯回應了奧德修斯,那么這鴻溝就被填平了,也就失去了崇高的指向。現代人體會崇高尤為艱難,而通過對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的感知,反思背后隱藏的驚心動魄的情感,在斷裂中反思人性喧囂,才是可行的方式。
當然,這里還是存在“過度解讀”或是誤讀電影文本的質疑,需要明確的是,本文討論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并非將關注點置于沉默的解讀,而是在解讀沉默時所發現的超越性的可能。
三、小結
古希臘作家朗吉努斯在其《論崇高》中,將奧德修斯去往冥府向埃阿斯的鬼魂道歉,而后者沉默以對的場景,稱作是整部《奧德賽》中最為崇高的部分。這雖是朗吉努斯從古典修辭學角度出發所做出的評價,但由于其中的崇高指向一種失控狀態,即人在突破感性與知性臨界點時的不確定性,而這種對不確定性的關注又顯然與現代人的思考方式更為接近,因此也就成為了一個極為現代的美學概念,“埃阿斯式沉默”也有了在當下討論的意義。
在電影中,同樣存在大量沉默場景,但并非都能構成埃阿斯式的崇高。本文以朗吉努斯的《論崇高》為切入點,通過選取的五部中外電影:《兒子》《趣味游戲》《四月三周又兩天》《八月》和《清水里的刀子》來對其中的“埃阿斯式沉默”進行分析,討論當代電影中這類特殊沉默場景的表現、效果以及在當下以此來探討崇高的意義。
對于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的討論,是基于電影情節同時延伸到某種特殊情感判斷的過程,在分析后可以發現,它必然不是從經驗出發而引起的一系列情感表達,而恰恰在于對經驗把控能力喪失后的考察。這種臨界狀態的感受,以及對這種感受的把握能夠帶來什么的討論,就是當代電影中的“埃阿斯式沉默”所能夠帶來的超越性的可能。
參考文獻:
[1](古希臘)荷馬.奧德賽[M].王煥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2]繆靈珠.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3](德)康德.判斷力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德)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OUP Oxford.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陳曉云.電影學導論[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
[7](匈牙利)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M].何力,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78.
[8](法)米榭·席俄塔,菲利普·胡耶.哈內克論哈內克[M].周伶芝,張懿德,劉慈仁,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9]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M].魯迅文學獎·寧夏作家自選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10](英)埃德蒙·伯克.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M].郭飛,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