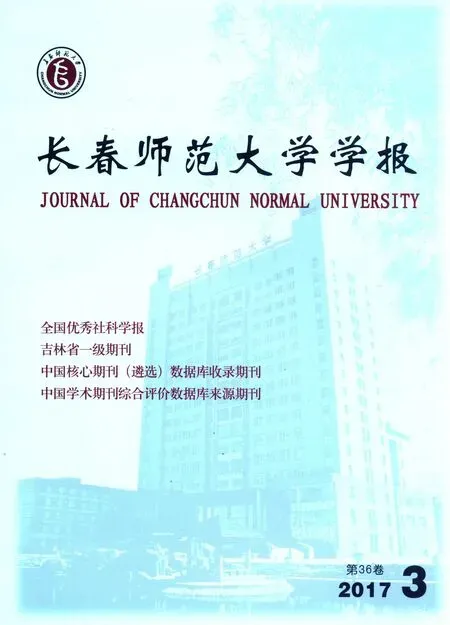對(duì)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的思考
——兼評(píng)鄒德文所著《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
李無(wú)未
(廈門(mén)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福建 廈門(mén) 361005)
對(duì)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的思考
——兼評(píng)鄒德文所著《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
李無(wú)未
(廈門(mén)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福建 廈門(mén) 361005)
目前對(duì)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的研究已經(jīng)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對(duì)漢語(yǔ)東北方言語(yǔ)音史研究文獻(xiàn)的挖掘已經(jīng)找到了一條可以行進(jìn)的路線,且已經(jīng)形成較為完備的基本認(rèn)識(shí)理論與方法,對(duì)東北方言語(yǔ)音的研究也由部分的認(rèn)識(shí)向整體性認(rèn)識(shí)拓展。但是,漢語(yǔ)東北方言語(yǔ)音史研究還僅僅是一個(gè)起始,清代東北方音史文獻(xiàn)形態(tài)所呈現(xiàn)出非線性、非均衡的特征,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分布零散而隱秘,語(yǔ)種多樣化,亟待挖掘與整理。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面臨著多重理論“范式”選擇,對(duì)“語(yǔ)言異質(zhì)化”理論、詞匯擴(kuò)散理論、語(yǔ)言演化尺度理論、語(yǔ)言類(lèi)型學(xué)理論、語(yǔ)言地理類(lèi)型學(xué)理論等的研究,需要超越現(xiàn)有的研究“范式”,才能帶來(lái)意想不到的收獲。
東北方言;語(yǔ)音史;創(chuàng)新研究;《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
一、東北方言史研究的新生機(jī)
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長(zhǎng)期以來(lái)過(guò)于忽視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的研究,以致漢語(yǔ)東北方言史面貌始終處于蒙昧混沌狀態(tài)。近些年來(lái),在學(xué)者們的努力下,情況開(kāi)始有所改變,比如在漢語(yǔ)東北方言語(yǔ)音史方面,鄒德文教授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2009)以其系統(tǒng)、全面而著稱于世。在漢語(yǔ)東北方言詞匯史方面,有學(xué)者通過(guò)《車(chē)王府曲本》《同文類(lèi)解》《奉天通志》等文獻(xiàn)挖掘資料,如李光杰教授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清代東北方言詞匯研究》(2012)以其文獻(xiàn)涉及面廣泛而贏得學(xué)術(shù)界的普遍贊譽(yù)。中國(guó)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的部分面貌因以上研究而顯露出來(lái),給中國(guó)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領(lǐng)域帶來(lái)了嶄新的氣象。
但我們也看到,中國(guó)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的各個(gè)分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發(fā)展并不平衡,距離達(dá)到整體性研究的目標(biāo)還相當(dāng)遠(yuǎn)。比如,漢語(yǔ)東北方言語(yǔ)法史、漢語(yǔ)東北方言語(yǔ)用史研究等還不能令人滿意,至少還沒(méi)有出現(xiàn)像《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清代東北方言詞匯研究》那樣有重要學(xué)術(shù)分量的專(zhuān)著,更沒(méi)有學(xué)者去建構(gòu)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理論系統(tǒng)范疇。這些情況表明,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還處于起始階段,還不能說(shuō)是已經(jīng)成熟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認(rèn)為,這個(gè)起始已經(jīng)孕育著新的學(xué)術(shù)生機(jī),代表了未來(lái)的漢語(yǔ)東北方言史學(xué)術(shù)走向,非常值得我們珍視。為什么?其一,對(duì)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文獻(xiàn)的挖掘,已經(jīng)找到了一條可以行進(jìn)的路線。其二,對(duì)漢語(yǔ)東北方言史文獻(xiàn)的研究已經(jīng)形成較為完備的基本認(rèn)識(shí)理論與方法。其三,由部分地認(rèn)識(shí)漢語(yǔ)東北方言史向整體性認(rèn)識(shí)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拓展,已經(jīng)打下了良好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其四,從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各個(gè)分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不平衡出發(fā),向縮小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各個(gè)分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差距的目標(biāo)挺進(jìn),越來(lái)越接近漢語(yǔ)東北方言史研究平衡發(fā)展的理想境地。
二、《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個(gè)案的典型價(jià)值
鄒德文教授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經(jīng)過(guò)四年的修訂,已經(jīng)達(dá)到了預(yù)期的目標(biāo)。我們?cè)谧YR它問(wèn)世的同時(shí),也希望通過(guò)對(duì)它成書(shū)過(guò)程的描述來(lái)進(jìn)一步引伸思考研究漢語(yǔ)東北方言史時(shí)需要認(rèn)真對(duì)待的一些問(wèn)題。
(一)《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選題和立意玄妙之處何在?
鄒德文教授博士學(xué)位論文為何要以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作為選題?鄒德文教授對(duì)此有過(guò)說(shuō)明:
如果說(shuō)漢語(yǔ)語(yǔ)音史是一座大廈,那么,方言語(yǔ)音史就是支撐這座大廈的強(qiáng)勁立柱……(研究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一是可以填補(bǔ)東北方言史空白,二是可以為完善漢語(yǔ)語(yǔ)音史的修撰提供素材,三是可以為現(xiàn)代漢語(yǔ)普通話語(yǔ)音的研究和正音工作提供重要的材料和結(jié)論,四是可以證明普通話基礎(chǔ)語(yǔ)音系統(tǒng)的來(lái)源。
本書(shū)填補(bǔ)了中國(guó)東北方言史研究中的一項(xiàng)空白,這是可以肯定的。在《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之前,確實(shí)沒(méi)有同類(lèi)的著作出現(xiàn),這也曾是東北方言史學(xué)者們最為心痛的死穴。《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的問(wèn)世,結(jié)束了這個(gè)讓人不愉快的歷史。作為東北方言史領(lǐng)域的同行,能不歡欣鼓舞嗎?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個(gè)認(rèn)識(shí)層面,似乎過(guò)于膚淺。東北方言語(yǔ)音史研究與漢語(yǔ)通語(yǔ)語(yǔ)音史研究密切相關(guān),而漢語(yǔ)通語(yǔ)語(yǔ)音史研究又是漢語(yǔ)語(yǔ)音史的核心,更是摸清漢語(yǔ)普通話語(yǔ)音史形成的關(guān)鍵。所以,《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的價(jià)值就非同小可了,其意圖也十分明確,還有更大的目標(biāo)在后面。
(二)發(fā)掘和研究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文獻(xiàn)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guó)東北方言史研究難如人意,而且處于蒙昧、混沌狀態(tài)。每個(gè)學(xué)者都可以捫心自問(wèn),誰(shuí)不想改變這種蒙昧混、沌狀態(tài)?誰(shuí)不想去做一個(gè)“敢為天下先”的拓荒牛?
其實(shí),先賢學(xué)者也曾為此而殫精竭力,比如林燾就曾發(fā)表《北京官話溯源》(1987)、《北京官話區(qū)的劃分》(1987)等論文,提出了“北京官話區(qū)”新概念。他認(rèn)為,從東北地區(qū)經(jīng)過(guò)河北省東北部的圍場(chǎng)、承德一帶直到北京市區(qū)的這一片相當(dāng)廣大的區(qū)域內(nèi),各方言的聲韻系統(tǒng)十分接近,調(diào)類(lèi)完全相同,調(diào)值極其相似,這個(gè)區(qū)域應(yīng)該劃歸為一個(gè)北京官話區(qū)。這等于說(shuō),東北官話語(yǔ)音只是北京官話語(yǔ)音的一個(gè)組成部分,東北官話語(yǔ)音概念并不成立。后來(lái)的學(xué)者,比如錢(qián)曾怡、耿振生等教授也贊同此說(shuō)。在筆者看來(lái),這個(gè)觀點(diǎn)還需要重新思考。僅僅通過(guò)現(xiàn)實(shí)語(yǔ)音面貌描寫(xiě)就下定論,還難以得到歷史文獻(xiàn)上的直接證據(jù)支持。我們理解先生們的無(wú)奈——文獻(xiàn)太少,又非常分散,進(jìn)行大規(guī)模文獻(xiàn)發(fā)掘需要更多的時(shí)間。最主要的是,文獻(xiàn)幾乎無(wú)處可追尋。沒(méi)有了文獻(xiàn)的支撐,東北方言史研究的大廈還能樹(shù)立起來(lái)嗎?只能是空想的東北方言史研究樓閣,或者曰東北方言史研究海市蜃樓。
鄒德文教授接受過(guò)嚴(yán)格的歷史文獻(xiàn)學(xué)和漢語(yǔ)音韻學(xué)、漢語(yǔ)方言學(xué)“正統(tǒng)”學(xué)術(shù)訓(xùn)練,進(jìn)行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史研究時(shí)不畏艱難、打破常規(guī),向傳統(tǒng)等韻圖、韻書(shū)及域外文獻(xiàn)要資料,曲徑通幽,化腐朽為神奇,居然從無(wú)路的蠻荒之地中踏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通暢之路,由此奠定了牢固的東北方言史研究基礎(chǔ),他想不成為“敢為天下先”的拓荒牛都很難。
(三)《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該如何處理文獻(xiàn)中的“音位”“音值”問(wèn)題?
中國(guó)傳統(tǒng)韻書(shū)等韻圖語(yǔ)音材料,按照現(xiàn)代語(yǔ)音學(xué)觀念,就是“剪不斷,理還亂”,或多個(gè)音系疊加,或語(yǔ)音現(xiàn)象糾葛,混沌一團(tuán),難解難分。鄒德文教授根據(jù)其語(yǔ)音大勢(shì)趨向,采用楊耐思先生所述的“剝離法”,提取最典型的東北方言語(yǔ)音特征,大大提升了這些文獻(xiàn)的東北方音史價(jià)值,對(duì)《黃鐘通韻》《音韻逢源》語(yǔ)音研究就是如此。但有一個(gè)問(wèn)題,就是一般人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韻書(shū)等韻圖語(yǔ)音材料,無(wú)論你如何“翻云覆雨”、“玩于股掌”之間,都無(wú)法改變它與生俱來(lái)的先天缺憾,即只能求得音類(lèi),卻不能求得音值。為從傳統(tǒng)韻書(shū)等韻圖音類(lèi)過(guò)渡到東北方音音值,需要在觀念上有一個(gè)轉(zhuǎn)變,即充分利用求得的清代東北方音音類(lèi),把它看作清代東北方音音位,由音位向音值過(guò)渡,就非常好辦了。薛鳳生先生曾在《語(yǔ)言科學(xué)》上發(fā)表《音韻學(xué)二題》一文,強(qiáng)調(diào)漢語(yǔ)音系研究與音位學(xué)的關(guān)系,認(rèn)為推論漢語(yǔ)音系必須重視音位對(duì)比,嚴(yán)格的音位對(duì)比是構(gòu)成音系的必要條件。這與他的中國(guó)音韻學(xué)的傳統(tǒng)是音位學(xué)的,韻書(shū)不是記發(fā)音而是記錄音位對(duì)比的音系,韻書(shū)的性質(zhì)本質(zhì)上是音位性的觀點(diǎn)相一致。理解到這一點(diǎn),就可以解決傳統(tǒng)韻書(shū)等韻圖不能求得音值的問(wèn)題。域外文獻(xiàn),尤其是朝鮮、日本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漢語(yǔ)教科書(shū)語(yǔ)音材料,因?yàn)檫\(yùn)用表明音值標(biāo)音標(biāo)記,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把它納入到研究中來(lái),如虎添翼,更可以做到精確標(biāo)音,證明傳統(tǒng)韻書(shū)等韻圖音位的可靠性。毫無(wú)疑問(wèn),這種處理文獻(xiàn)的理論與方法,跨越了語(yǔ)音文獻(xiàn)混沌的鴻溝,實(shí)現(xiàn)了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文獻(xiàn)使用的最大效能,這是遠(yuǎn)遠(yuǎn)超出前人的。
(四)《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是“發(fā)現(xiàn)”還是“發(fā)明”?
現(xiàn)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爭(zhēng)搶發(fā)表出土文研究資料的現(xiàn)象甚囂塵上,文獻(xiàn)中心主義盛行。由此,引出了是不是沒(méi)有占有第一手資料就居于二流學(xué)者地位的討論。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文獻(xiàn)發(fā)現(xiàn)”比“文獻(xiàn)發(fā)明”更重要,學(xué)術(shù)界的文獻(xiàn)囤積居奇現(xiàn)象十分普遍。其實(shí),有關(guān)這個(gè)問(wèn)題的討論,很早就有人進(jìn)行。日本著名學(xué)者吉川幸次郎曾留學(xué)中國(guó),他在《我的留學(xué)記》(2008)中提到,黃侃對(duì)他說(shuō)過(guò):“中國(guó)的學(xué)問(wèn)不在于發(fā)現(xiàn),而在于發(fā)明。”吉川幸次郎立刻想到,當(dāng)時(shí)在日本,人們是把羅振玉、王國(guó)維的學(xué)問(wèn)當(dāng)作權(quán)威來(lái)看待的。羅王之學(xué)無(wú)疑是以發(fā)現(xiàn)為主,傾向于資料主義。但要從發(fā)明來(lái)說(shuō),他們未必如此。發(fā)明是對(duì)重要的文獻(xiàn)踏踏實(shí)實(shí)地用功去細(xì)讀,去發(fā)掘其中的某種東西。從人們熟知的文獻(xiàn)中發(fā)掘新問(wèn)題更難,更見(jiàn)功力。錢(qián)穆后學(xué)嚴(yán)耕望也有如此主張,他在《治史三書(shū)》(2011)中強(qiáng)調(diào),以正史為基礎(chǔ),由舊史料推陳出新,“不要愁著沒(méi)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聚小為大”;“于細(xì)微之處見(jiàn)發(fā)明”。我們不去評(píng)論羅王之學(xué)是否為發(fā)現(xiàn)或?yàn)榘l(fā)明問(wèn)題,也不去認(rèn)定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何者為優(yōu)的問(wèn)題,從《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來(lái)看,“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相得益彰卻不是虛妄之辭。
可以肯定的是,《黃鐘通韻》《音韻逢源》是傳統(tǒng)等韻圖、韻書(shū)。前人如趙蔭棠、永島榮一郎,今人如應(yīng)裕康、巖田憲幸、耿振生、陳雪竹、陳喬等均有研究,想要超越他們,就得“從夾縫中”求新知,發(fā)明新觀點(diǎn)。如此,何其難也?鄒德文教授所理出的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特征就可以證明,其“發(fā)明”的功力不可小覷。
《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的“發(fā)現(xiàn)”在于使用了中國(guó)學(xué)者幾乎不知道的日本明治漢語(yǔ)東北方言教科書(shū)文獻(xiàn),比如《支那語(yǔ)講義》。本來(lái)這是日本培養(yǎng)“中國(guó)通”的漢語(yǔ)東北方言教科書(shū),具有侵略中國(guó)的目的。認(rèn)識(shí)到它的本質(zhì)之后,還要看到它的另一種學(xué)術(shù)意義——既是日本文化侵略中國(guó)的罪證,也是研究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假名標(biāo)記就十分珍貴。這個(gè)“發(fā)現(xiàn)”非常重要,因?yàn)樗梢詮浹a(bǔ)《黃鐘通韻》《音韻逢源》文獻(xiàn)語(yǔ)音音值研究的不足。等于說(shuō),提升了《支那語(yǔ)講義》作為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真實(shí)記錄的罕見(jiàn)的漢語(yǔ)方音史價(jià)值。《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的原創(chuàng)性就在于如黃侃先生所說(shuō)的有“發(fā)現(xiàn)”也有“發(fā)明”。
(五)《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還有后續(xù)探討空間嗎?
衡量一個(gè)研究課題結(jié)項(xiàng)后是否具有內(nèi)在旺盛的學(xué)術(shù)生命力,不在于它所貢獻(xiàn)的成果本身是否完美無(wú)缺,而在于它是否還有延展性的研究空間。筆者認(rèn)為,《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的延展性空間很大。比如移民與東北方言形成問(wèn)題。從大的方面來(lái)看,就移民對(duì)社會(huì)的影響,已有學(xué)者進(jìn)行探討,如葛劍雄等《中國(guó)移民史》(1997)、張士尊《清代東北移民與社會(huì)變遷:1644-1911》(2003)、范立君《近代東北移民與社會(huì)變遷:1860-1931》(2005)。但是,個(gè)案研究稍顯不足,如東北移民的“語(yǔ)言接觸”問(wèn)題研究就是個(gè)難點(diǎn)。對(duì)清代之前的東北方言語(yǔ)音史、清代之后的東北方言語(yǔ)音史、東北方言語(yǔ)音制度史、東北方言區(qū)域語(yǔ)音教育史等都可以進(jìn)行探討,而且大有可為。比如歷史上朝鮮確立了一套嚴(yán)格的漢語(yǔ)“質(zhì)正”制度,通事譯官學(xué)習(xí)明清漢語(yǔ)官話,就曾以東北官話語(yǔ)音為標(biāo)準(zhǔn),糾正朝鮮漢語(yǔ)學(xué)習(xí)者的語(yǔ)音學(xué)習(xí)錯(cuò)誤,這在《朝鮮王朝實(shí)錄》中有明確的記載。如《實(shí)錄》世宗74卷,18年(1436丙辰/(正統(tǒng))1年)8月15日(戊寅)2:
議政府據(jù)禮曹呈啟:“國(guó)家能通漢語(yǔ)者少,實(shí)為可慮。擇講肄官及生徒年少聰敏者,號(hào)稱義州迎送官,至遼東留止之時(shí),或質(zhì)問(wèn)經(jīng)書(shū),或傳習(xí)語(yǔ)音。仍給麻布十匹、人蔘五斤,以資其行。”從之。
這是朝鮮國(guó)王支持朝鮮漢語(yǔ)學(xué)習(xí)者去遼東進(jìn)行漢語(yǔ)語(yǔ)音“質(zhì)正”活動(dòng)的直接證據(jù),目的是培養(yǎng)懂得漢語(yǔ)遼東語(yǔ)音的通事譯官。
《實(shí)錄》成宗200卷,18年(1487丁未/(成化)23年)2月2日(壬申)條:
壬申,御經(jīng)筵。講訖,侍講官李昌臣啟曰:“臣曾以圣節(jié)使質(zhì)正官赴京,聞前進(jìn)士邵奎以親老居遼東,回來(lái)時(shí)尋問(wèn)之,該通經(jīng)史,精審字訓(xùn)矣。世宗朝遣申叔舟、成三問(wèn)等到遼東,就黃瓚質(zhì)正語(yǔ)音字訓(xùn),成《洪武正韻》及《四聲通考》等書(shū)。故我國(guó)之人,賴之粗知漢訓(xùn)矣。今須擇年少能文如申從濩輩,往就邵奎質(zhì)正字訓(xùn)書(shū)籍,則似有利益。但正朝節(jié)日之行,人馬數(shù)多,不可久留;如唐人解送時(shí)入送,則可以久留質(zhì)正矣。”上問(wèn)左右,僉啟曰:“遣文臣質(zhì)正,祖宗朝古事,今可行也。”
這段文獻(xiàn)給我們提供了如下線索:世宗時(shí),申叔舟、成三問(wèn)等到遼東,向黃瓚質(zhì)正語(yǔ)音字訓(xùn),完成了《洪武正韻》及《四聲通考》等韻書(shū),這對(duì)我們考訂《洪武正韻》及《四聲通考》對(duì)音譯音語(yǔ)音系統(tǒng)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黃瓚,一作黃璜,明朝遼寧開(kāi)原人。黃瓚對(duì)《洪武正韻》及《四聲通考》進(jìn)行“質(zhì)正”,表明遼東語(yǔ)音潛在的巨大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邵奎居于遼東,申從濩等到遼東邵奎處“久留”質(zhì)正“字訓(xùn)書(shū)籍”,所學(xué)肯定也與掌握遼東官話語(yǔ)音標(biāo)準(zhǔn)有關(guān)。
由此看來(lái),《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后續(xù)延展性空間巨大,這也正是它的學(xué)術(shù)魅力之所在。
三、重建清代東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
《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文獻(xiàn)發(fā)掘固然很難,但筆者認(rèn)為,難度更大的還是如何重建清代東北方音史問(wèn)題。
“重建”是什么?“重建”的英文是reconstitution。它本來(lái)和生命科學(xué)概念相關(guān),有的學(xué)者打個(gè)比喻:正如病毒的核酸和蛋白質(zhì)可構(gòu)成病毒粒子那樣,從破壞細(xì)胞所得的部分可再組建細(xì)胞,就是重建。另外,“重建”也指各類(lèi)組織的重新構(gòu)成。語(yǔ)言學(xué)中的“重建”,借用了自然科學(xué)的術(shù)語(yǔ)。它的基本思想來(lái)源于歷史比較語(yǔ)言學(xué)理論,所關(guān)心的主要是對(duì)語(yǔ)言譜系的梳理和對(duì)史前語(yǔ)言的構(gòu)擬,構(gòu)擬就是“重建”。“重建”所使用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就是歷史比較方法。那么,什么是歷史比較方法?梅耶在《歷史語(yǔ)言學(xué)中的比較方法》中說(shuō):“進(jìn)行比較工作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從比較中揭示普遍的規(guī)律;另一種是從中找出歷史的情況。”由此可見(jiàn),語(yǔ)言比較是前提,可在語(yǔ)言比較過(guò)程中尋求語(yǔ)言規(guī)律。
重建清代東北方音史,也是進(jìn)行語(yǔ)言比較以及在語(yǔ)言比較過(guò)程中尋求語(yǔ)言規(guī)律的工作。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進(jìn)行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比較以及在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比較過(guò)程中尋求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規(guī)律的工作。
但如何才能進(jìn)行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比較并尋求語(yǔ)音規(guī)律呢?我們?nèi)绻亚宕鷸|北方音史研究初始階段看作一個(gè)“無(wú)序”的混沌物質(zhì)狀態(tài)體的話,那么,進(jìn)行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比較并尋求語(yǔ)音規(guī)律的過(guò)程就是一個(gè)從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混沌物質(zhì)狀態(tài)體中撥開(kāi)云霧、層層深入從而重建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秩序的過(guò)程。向混沌求清代東北方音史“新知”,必然會(huì)由“無(wú)序”到“有序”。
把重建清代東北方音史工作和混沌現(xiàn)象研究等同起來(lái),就要認(rèn)識(shí)到它和混沌現(xiàn)象研究類(lèi)似的地方。混沌物質(zhì)狀態(tài)所呈現(xiàn)的是非線性、非均衡的復(fù)雜性特征,清代東北方音史文獻(xiàn)形態(tài)所呈現(xiàn)的也是非線性、非均衡的復(fù)雜性特征。比如,和它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分布零散而隱秘,語(yǔ)種多樣,往往沉睡于圖書(shū)館和檔案庫(kù)中。學(xué)者們要做的工作就是拂去歷史霧霾,使這些文獻(xiàn)得以重見(jiàn)天日。挖掘與整理的過(guò)程,就是化混沌為清晰可辨的過(guò)程。這是就清代東北方音史文獻(xiàn)挖掘而言的。
但是,這種文獻(xiàn)挖掘并不等于“重建”,只是化文獻(xiàn)混沌為文獻(xiàn)清晰可辨的第一步工作。“重建”清代東北方音史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將文獻(xiàn)轉(zhuǎn)化為清代東北方音史的面貌和規(guī)律,并對(duì)成因加以解釋的過(guò)程。其實(shí),這也是將混沌的、呈現(xiàn)非線性的、非均衡的、隨機(jī)無(wú)序的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推進(jìn)到呈現(xiàn)線性、均衡、確定性的狀態(tài),從而使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工作進(jìn)入有序境地。
按照這個(gè)研究工作步驟,《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尋求文獻(xiàn)研究依據(jù),比如從《黃鐘通韻》《音韻逢源》、朝鮮漢字音、日本東北方言教科書(shū)中尋求語(yǔ)音資料,就是將混沌而呈現(xiàn)非線性、非均衡、隨機(jī)無(wú)序的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文獻(xiàn)整理推進(jìn)到呈現(xiàn)線性、均衡、確定性的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文獻(xiàn)整理,使該領(lǐng)域的工作進(jìn)入到有序境地。“重建”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系統(tǒng),所得出的結(jié)論與解釋性結(jié)果,比如聲母韻母聲調(diào),以及變化規(guī)律等等,則是按照一般學(xué)者“重建”時(shí)所采用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即運(yùn)用歷史比較方法將研究結(jié)果推進(jìn)到呈現(xiàn)線性、均衡、確定性的有序境地的過(guò)程。毫無(wú)疑問(wèn),符合一般的歷史比較語(yǔ)言學(xué)的原則和方法。向混沌求新知,獲得了一個(gè)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
“重建”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系統(tǒng),以歷史比較方法為基本操作程序,貫徹的是建立“共同語(yǔ)”規(guī)則。梅耶說(shuō):“就系屬已經(jīng)確定,并且按照一定方法研究過(guò)的各族語(yǔ)言來(lái)說(shuō),對(duì)它們進(jìn)行比較,就是在它們之間構(gòu)擬出一種原始的“共同語(yǔ)”(langue commune initiale)。《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于此無(wú)異。構(gòu)擬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系統(tǒng),也是為建立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系統(tǒng)服務(wù)的。《黃鐘通韻》《音韻逢源》、朝鮮漢字音、日本東北方言教科書(shū)存在各自的語(yǔ)音系統(tǒng),但都不能完全代表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系統(tǒng)。如此,進(jìn)行它們之間語(yǔ)音系統(tǒng)比較的工作,尋求語(yǔ)音對(duì)應(yīng)規(guī)律,拿出能夠說(shuō)明各自語(yǔ)音系統(tǒng)并清楚解釋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系統(tǒng)分化和變化規(guī)律的手段來(lái),就達(dá)到了基本研究目的。
怎樣去認(rèn)識(shí)鄒德文教授研究的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系統(tǒng)?筆者認(rèn)為,還是要回到梅耶的觀點(diǎn)上來(lái),即“構(gòu)擬只能給我們一個(gè)不完備的,而且毫無(wú)疑問(wèn)是極不完備的關(guān)于共同語(yǔ)的概念”;“任何構(gòu)擬都不能得出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的共同語(yǔ)”;“比較方法只能得出一個(gè)相近的系統(tǒng),可以作為建立一個(gè)語(yǔ)系的歷史基礎(chǔ),而不能得出一種真正的語(yǔ)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達(dá)方式”。按照這個(gè)理論去理解,鄒德文教授所構(gòu)擬的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系統(tǒng)是一個(gè)理想的有關(guān)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的構(gòu)擬系統(tǒng),而且只能給我們一個(gè)不完備的關(guān)于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共同語(yǔ)的概念。它可以作為我們建立一個(gè)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的歷史基礎(chǔ),卻無(wú)法代替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系統(tǒng)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達(dá)方式。
這是我們理性的、實(shí)事求是的、頭腦清醒的科學(xué)態(tài)度,也是無(wú)法苛求鄒德文教授有關(guān)清代東北方言“共同語(yǔ)”語(yǔ)音研究工作的一個(gè)重要方面。
從已有的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著作中能引發(fā)的有關(guān)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的后續(xù)思考究竟有多少,這確實(shí)是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課題存在的巨大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之所在。現(xiàn)代學(xué)者對(duì)歷史比較語(yǔ)言學(xué)“重建”理論責(zé)難不少,清代東北方音史研究就面臨著多重理論“范式”選擇,像“語(yǔ)言異質(zhì)化”理論、詞匯擴(kuò)散理論、語(yǔ)言演化尺度理論、語(yǔ)言類(lèi)型學(xué)理論、語(yǔ)言地理類(lèi)型學(xué)理論等等,可謂花樣翻新,讓人目不暇接。超越現(xiàn)有的研究“范式”必然帶來(lái)意想不到的收獲,向混沌求新知,一定還會(huì)有更多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毫無(wú)疑問(wèn),學(xué)術(shù)界在無(wú)限地期待著。
[1]鄒德文.清代東北方言語(yǔ)音研究[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3.
[2]李光杰.清代東北方言詞匯研究[D].廈門(mén):廈門(mén)大學(xué),2012.
[3]林燾.北京官話溯源[J].中國(guó)語(yǔ)文,1987(3).
[4]林燾.北京官話區(qū)的劃分[J].方言,1987(3).
[5]薛鳳生.音韻學(xué)二題[J].語(yǔ)言科學(xué),2009(4).
[6]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xué)記[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8.
[7]嚴(yán)耕望.治史三書(sh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李無(wú)未,張輝.朝鮮朝漢語(yǔ)官話質(zhì)正制度考論——以《朝鮮王朝實(shí)錄》為依據(jù)[J].古漢語(yǔ)研究,2014(1).
[9]岑麒祥.國(guó)外語(yǔ)言學(xué)論文選譯[M].北京:語(yǔ)文出版社,1992.
2016-09-26
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東亞珍藏明清漢語(yǔ)文獻(xiàn)發(fā)掘與研究”(12&ZD178);國(guó)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清及民國(guó)東北方言與北京官話語(yǔ)音關(guān)系研究”(12BYY065)。
李無(wú)未(1960-),男,廈門(mén)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從事漢語(yǔ)史及漢語(yǔ)語(yǔ)言學(xué)史、域外漢語(yǔ)教科書(shū)研究。
H17
A
2095-7602(2017)03-007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