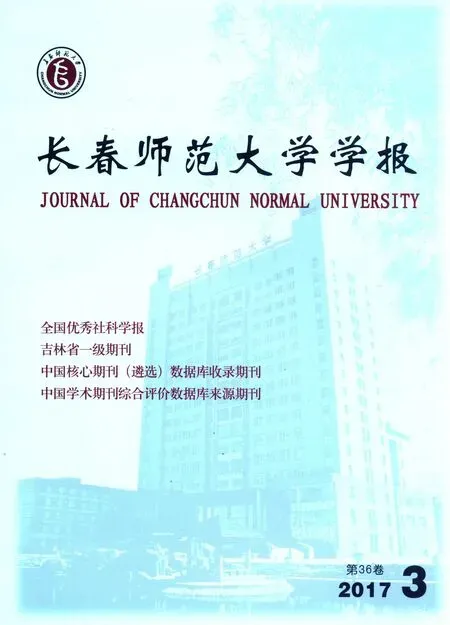“走出去”的文學倫理學批評
郝運慧
(北京交通大學 語言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44)
“走出去”的文學倫理學批評
郝運慧
(北京交通大學 語言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44)
文學倫理學批評誕生于西方文論“倫理轉(zhuǎn)向”的全球語境和反撥國內(nèi)外國文學批評領(lǐng)域泛理論的浪潮之中。經(jīng)過十余年的發(fā)展,它已形成了較有體系的理論框架和批評話語,并指導了大量的批評實踐。難能可貴的是,它作為本土誕生的理論已在國際上取得了諸多同行的肯定和認可,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反撥了中國文論在國際上的“失語癥”,為中國文論“走出去”和參與國際話語權(quán)的競爭起到了積極作用。
文學倫理學批評;走出去;話語權(quán)
20世紀的歐美文學界,文學批評理論與文學理論批評空前繁榮,以法國和美國為中心的兩大文學理論陣營于爭鳴中共同譜寫了文學理論的多聲部合唱。法國學派的哲學思辨和理論建構(gòu)、美國學派的文化轉(zhuǎn)向和問題意識主宰了20世紀歐美文學批評理論的主旋律。20世紀中晚期,具有族裔背景的文學批評理論家,如斯皮瓦克、薩義德和近來的齊澤克等人更是集理論思辨和文化意識于一身,取得了開拓性的成就。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20世紀的文學理論爭鳴中,全無中國背景和中國聲音。中國文論“失語癥”直接導致中國文論國際地位的缺乏和話語權(quán)的喪失。包括季羨林在內(nèi)的諸多學者都意識到了在國際文論界“中國聲音”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學者王寧近年來在多篇文章中探討了中國文論的國際化戰(zhàn)略及有效途徑,他指出:“中國的文學理論家不能只是被動地等待被別人‘發(fā)現(xiàn)’,而應該更為積極主動地去與居于國際文學理論前沿的歐美文論家進行交流和對話,從而掙得一些基本的話語權(quán)”[1]58。
進入新世紀,這一現(xiàn)象開始有所轉(zhuǎn)機。2010年,華裔文藝理論家李澤厚的《美學四講》被《諾頓理論與批評文選》收錄。這一事件“預示著曾長期為歐美理論家所把持的國際文學和文化理論界也開始認識到西方中心主義的缺陷了,他們需要聽到來自西方世界以外的理論家的聲音,盡管這些聲音中依然夾雜著不少西方的影響,但卻帶有更多的來自非西方國家的經(jīng)驗、本土特色和文化精神”[1]60。我們可以預見,被視為中國文論“走出去”主要障礙的西方中心主義正在被逐漸打破,中國文論“走出去”的國際環(huán)境正在好轉(zhuǎn)。進入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立足本土,兼收并蓄,以積極的文化自覺意識,成為中國文論“走出去”的又一成功典范。
一、“倫理學轉(zhuǎn)向”與中國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勃興
20世紀歐美文學界理論的繁榮一方面彰顯了理論家們思辨的高度和灼見的深度,另一方面也將理論的發(fā)展帶入了智性的狂歡和縹緲的游戲之境地,使得文學批評在某種程度上“僅僅是為了在語言的歡樂宮中尋求快感,越來越走向精英化、專業(yè)化和私人化的文學批評逐漸被驅(qū)逐至公共生活的邊緣”[2]。此種演變的直接后果就是剝離了文學中的倫理之維,使得文學與倫理漸行漸遠。基于此,批評家們開始在文學批評中重新審視社會問題和共同體價值,“倫理學轉(zhuǎn)向”成為北美文學批評界的一個顯著趨勢。而且,“此次的倫理轉(zhuǎn)向不是回到19世紀的文學批評傳統(tǒng),而是對形式主義的反駁和對文學作為一種認知方式的重新定位”[3],并“被賦予新的內(nèi)涵和承載了新的使命”[4]。
作為對國際社會文學批評倫理回歸的呼應以及對國內(nèi)外國文學批評“理論空洞化”的反撥,以聶珍釗為首的一批國內(nèi)學者開創(chuàng)了文學倫理學批評學派,第一次明確地將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批評文學的方法提了出來,強調(diào):“目前是中國的文學批評出現(xiàn)倫理道德價值缺位的時候,我們的文學批評更應負起道德責任,以實現(xiàn)文學倫理道德價值的回歸。而文學倫理學批評就是達到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5]。自2004年起,聶珍釗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深入地闡述了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起源、學理、方法論、批評的對象和內(nèi)容、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的差異;同時結(jié)合外國文學研究中的經(jīng)典文本,展示了這一批評方法應用的范例,論證了這一方法的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此外,劉建軍、鄒建軍、李定清、張杰、龍云等一批學者對這一新生的批評方法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多維的建構(gòu)與完善。近十年中,在這一方法指導下的文學批評實踐大量涌現(xiàn),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的繁榮不僅驗證了這一批評方法廣泛的適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倫理學轉(zhuǎn)向”與時代精神的契合。可以說,經(jīng)過十余年的發(fā)展,文學倫理學批評已得到了國內(nèi)外學者的廣泛關(guān)注與應用,逐漸發(fā)展成為一門熱學。
在筆者看來,文學倫理學批評十余年的發(fā)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起止于聶珍釗先生的兩篇標志性文章——《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和《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shù)語》。倫理意識、倫理禁忌、倫理環(huán)境、倫理選擇、倫理身份、倫理結(jié)等關(guān)于這一方法論的核心概念的提出與闡釋標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理論體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對于文學倫理學第一階段的發(fā)展情況,修樹新、田俊武等人的綜述性文章對此作了全面的總結(jié),既包括歷時的流變梳理,也包括共時的問題剖析。其特別指出文學倫理學批評在某些理論問題上還有待進一步厘清,如倫理和道德、倫理批評和道德批評、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和西方文學倫理學等關(guān)鍵概念需要得到進一步辨析。同時,對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性質(zhì)進行了界定,表明其作為批評話語的立場,并強調(diào)了其作為方法論的兼容性和適用性。第二階段主要圍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價值判斷展開,深入探討了文學的價值問題與社會功用。聶珍釗先生指出,“文學經(jīng)典的價值在于其倫理價值,其藝術(shù)審美只是實現(xiàn)其倫理價值的形式或途徑”;文學的功能在于教誨而不在于審美,倫理價值是文學最基本的價值。聶珍釗先生以倫理批評為核心對文學的價值和功能的論證也遭遇了不同的聲音,倫理與審美之爭成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第二發(fā)展階段的重要特征,而這樣的爭辯為文學倫理學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建構(gòu)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走出去”的文學倫理學批評
與文論在西方學界的消熱不同,西方文論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界依然熱度不減,國內(nèi)學者每年產(chǎn)出大量的理論著述,但影響力十分有限。王寧指出“后理論時代”的來臨對我們中國的文學理論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在這樣一個沒有主流的‘后理論時代’,各民族的文學理論都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中國的文學理論應該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有所作為,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應該勇于以積極的姿態(tài)走向世界,與占據(jù)國際主流的各種西方理論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并建構(gòu)出具有相對普適意義的自己的理論話語”[6]。可見,“走出去”與加強對話性是文學倫理學批評當下的主要任務之一。學術(shù)期刊、學術(shù)平臺等依托主體的建設將有效助推當下所面臨任務的解決。
作為中國學術(shù)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國際性學術(shù)期刊建設是實現(xiàn)中國文論走向國際并加強對話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目前中國的學術(shù)期刊在同國際接軌方面還存在著巨大差距,尤以人文學科為甚。中國國際期刊的缺失,導致了中國立場和中國價值在國際學術(shù)界的“失語”。2014年,聶珍釗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連續(xù)發(fā)文強調(diào)中國學術(shù)期刊要積極參與國際話語權(quán)競爭,并呼吁努力建設一批有國際話語權(quán)的學術(shù)期刊。聶珍釗和王寧的呼吁既顯示了國家和時代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學術(shù)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說,作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發(fā)源地和主要陣地的《外國文學研究》被收錄為A&HCI來源期刊,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載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在人文科學領(lǐng)域的國際學術(shù)影響力。
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中國特有的聲音能夠活躍在國際文學批評的舞臺,也得益于其他實體機構(gòu)的建設和國際學術(shù)會議平臺的搭建。2011年至今,《外國文學研究》雜志聯(lián)合國內(nèi)外其他學術(shù)機構(gòu),已成功舉辦五屆“文學倫理學批評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其中,在2012年成立了“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IAELC)。這一國際學術(shù)組織的成立,對進一步加強國內(nèi)外從事文學倫理學研究的學者的合作意義重大。2014年,“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中心”成立。這些實體機構(gòu)的建立和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的召開彰顯了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新興的批評方法的活力,不斷推動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的新局面、新高潮和新高度。
另外,“文學倫理學批評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日益興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2015年于韓國首爾和釜山共同舉辦的“第五屆文學倫理學批評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來自2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200余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此次會議進一步加強了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的國際視野,是一次“中國學術(shù)走出去的學術(shù)盛宴”[7],標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已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此外,2015年5月,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舉辦“批評理論學術(shù)年會”,會議專設主題探討了“中國崛起背景下的文學新象與批評理論建構(gòu)”。歐洲科學院院士鄧·阿貝勒在點評中對聶珍釗教授開創(chuàng)新學說并積極參與世界學術(shù)對話表示贊賞,并指出文學倫理學批評為文學批評向德育和審美功能的回歸提供了動力,與西方的主流話語形成互動與互補的關(guān)系。阿貝勒還認為,文學倫理學批評必將為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接納和應用,并在中西學者的共建中進一步系統(tǒng)化[8]。著名敘事學家安斯加爾·紐寧認為,倫理批評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在西方日漸式微,但在中國學術(shù)界得以興盛。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無論在理論體系、術(shù)語概念還是批評實踐上,取得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復興了倫理批評,這也是中國學者對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貢獻。
三、結(jié)語
在中外文學史上,文學與倫理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文學的倫理批評是不可避免的。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植根于中國當下歷史語境的一種文學批評方法論,吸收了中西倫理和倫理批評的要旨,是在西方文論倫理轉(zhuǎn)向的國際背景下衍生的變體。它由中國學者提出,在國內(nèi)逐步走向繁榮,當屬中國當代文論的一個分支。另外,從事文學倫理學研究人員多有外語學科背景,其學科領(lǐng)域特點和語言上的優(yōu)勢使這一方法論很快實現(xiàn)了“走出去”的局面,并正在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得到更多國際同行的認可。
學者張江主張中國的文學理論“融入世界,與西方平等對話”[9]37,但是“對話的前提必須是,我們的理論與西方相比要有異質(zhì)性,有獨特價值”[10]。作為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的創(chuàng)始人,聶珍釗先生指出:“同西方的倫理批評相比,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有其鮮明特點,即它將倫理批評轉(zhuǎn)變?yōu)榕u文學的特定方法,從而使它能夠有效地解決具體的文學問題;它用文學倫理學批評概念取代倫理批評的概念,建立了自己的批評話語;它通過范例分析,對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正是由于這些特點,文學倫理學批評才有別于西方的倫理批評而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新的批評方法”[9]37。由此可見,保持了自身異質(zhì)性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可以被“用于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和國際性的理論爭鳴,使得長期以來已經(jīng)‘西化’的文論術(shù)語首先變得混雜,進而彰顯其不同于西方理論話語的特點,最后才能形成自己的獨特范疇和話語體系”[11]。
[1]王寧.再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國際化戰(zhàn)略及路徑[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2]陳后亮.倫理學轉(zhuǎn)向[J].外國文學,2014(4):116
[3]楊革新.文學研究的倫理轉(zhuǎn)向與美國倫理批評的復興[J].外國文學研究,2013(6):16
[4]劉英.回歸抑或轉(zhuǎn)向: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美國文學倫理學批評[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90
[5]聶珍釗.關(guān)于文學倫理學批評[J].外國文學研究,2005(1):11.
[6]王寧.“后理論時代”西方文論的有效性和出路[J].中國文學批評,2015(4):67.
[7]黃暉.文學倫理學批評與國際學術(shù)話語的新構(gòu)建:“第五屆文學倫理學批評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J].外國文學研究,2015(6):166.
[8]夏延華.讓批評理論與世界同步——首屆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批評理論學術(shù)年會”側(cè)記[J].外國文學研究,2015(6):171-172.
[9]張江.當代西方文論的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J].中國社會科學,2014(5):37.
[10]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在中國[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35.
[11]王寧.“后理論時代”中國文論的國際化走向和理論構(gòu)建[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85.
2016-09-2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費人文社會科學專項基金項目“尼采哲學視角下麥爾維爾小說研究”(2015jbwj002)。
郝運慧(1980-),男,副教授,博士,從事英美文學研究。
I06
A
2095-7602(2017)03-01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