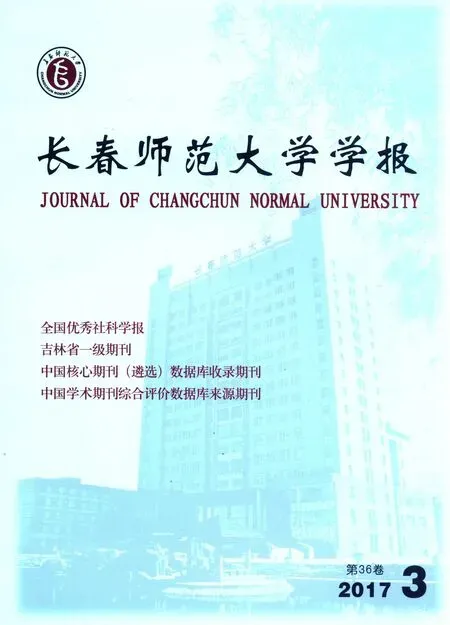陳鴻璧與張昭漢關系考
李 想,劉 釗
(長春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2)
陳鴻璧與張昭漢關系考
李 想,劉 釗
(長春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2)
清末民初女翻譯家陳鴻璧與南社成員張昭漢是20世紀初年第一代知識女性。本文以她們的交往為考察對象,試圖廓清二者的關系,探討她們共同從事女權革命、開展女子教育、翻譯文學作品的經歷,反映一代知識女性的啟蒙思想傾向與文學追求。
陳鴻璧;張昭漢;女權;翻譯文學
清末民初是第一代知識女性覺醒的文學時期,誕生了女性小說家、女政論家、女翻譯家和南社女作家四大女性文學群體,標志著女性文學創作的重要轉型。女性文學創作從閨閣走出來,走向了社會生活領域。她們接受了新式教育,是女界啟蒙的受益者,積極從事女子教育,呼吁女權,在文學創作中承擔啟蒙女界的職責。女翻譯家陳鴻璧雖然沒有參加革命文學社團南社,但她與南社女成員張昭漢有著密切的聯系。二人的生活道路、人生經歷十分相似,共同開辦女校、翻譯小說,都表現出積極倡導和實踐女權的思想,表現出20世紀初第一代知識女性的思想追求。
一、接受新式教育,投身教育事業
陳鴻璧和張昭漢年齡相仿,都是20世紀接受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女性。陳鴻璧(1884-1966),原名陳碧珍,廣東新會人,近代女翻譯家、教育家、實業家,早年積極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和實業運動,與張昭漢的經歷十分相似,都有接受新式教育的經歷,也一樣是同盟會會員。陳鴻璧家境優越,曾入上海中西女塾和圣若瑟學校兩所教會學校學習。當時,教會學校非常重視訓練學生的外語寫作和閱讀能力。陳鴻璧通日、英、法文,且達到較高程度。同時,其家學淵源深厚,一家人均通英語,父親陳兆桐有翻譯西書的經驗,可以對陳鴻璧的翻譯實踐進行指導[1]。這為陳鴻璧翻譯文學作品、傳播西方先進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清末啟蒙思想家將開啟民智作為拯救國家的途徑,興辦女學為女界啟蒙的首要途徑。著名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啟蒙思想家梁啟超認識到了婦女在國家存亡中的歷史地位,深知若想要國家強大,必須由興女學開始。著名革命家陳天華在其撰寫的《警世鐘》中也提到,女子應入女學堂,擔救國重任。陳鴻璧與張昭漢是興女學的受益者。她們接受了新式教育,視野開闊、思想先進,又積極地從事教育,自覺地擔負起救國、啟蒙的責任。
陳鴻璧關注幼兒教育事業,辛亥革命后積極響應孫中山聯合女界以普及教育的號召,于1912年和表妹唐關素梅創立上海幼稚園,專門收粵籍幼兒。學校很快擴大規模,增設小學,又創辦了旅滬廣東小學。1917年,陳鴻璧在上海民立女子中學和育賢女學任教,教書之余擔任廣州《七十二行商報》《長沙日報》通訊員。陳鴻璧不僅親自開展教育活動,還翻譯外國的教育理論書籍。1926年5月,她翻譯了美國馬爾騰的《思想之偉能》
(又名《人皆王者》);1926年6月,翻譯了英國細拉的《兒童之訓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該書是國內兒童教育中急需的書籍,應用性強,出版后很受歡迎,于1931年10月、1933年3月分別又再版發行。1927年,自撰《幼稚教育之歷史》《上海立案私立廣東幼稚園情況》,使她累積了幼兒教育與實踐經驗,掌握了系統理論知識,成為幼兒教育的專家。陳鴻璧“雖風雨疾病而不稍息,迨民國十年又出其余力倡辦女學,造福吾儕,語曰誨人不倦”[2]。1924年7月,她在南京參與了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屆年會,作為女子教育組的一員對女子教育問題進行了提案,提出女子中學應加入兒童學這一科目,且在對外語的教學上應更注重培養翻譯人才。
張昭漢(1883-1965),女,字默君,名寶螭,號涵秋,湖南湘江人,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革命家、文學家、教育家。她先后畢業于上海務本女校和上海圣約翰女子書院兩所女子學校。1918年,她奉教育部委派,赴歐、美調查職業教育,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系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考察學習,周游英、法、意、瑞士、比利時、埃及、印度等處,于1919年11月11日歸國,著有《歐美教育考察錄》《戰后之歐美女子教育》。張昭漢于1909年加入南社,是第200號南社成員,在南社中與呂碧城齊名。她在幼時就顯現出與眾不同的文學造詣,7歲作《寶螭戲墨》,8歲帶領親友放足,并作《放足詩》。她從小受其父張通典的民主革命思想影響,思想進步,又與父親一道加入同盟會。自1906年入會后,她開始從事反清活動,辛亥革命后曾在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任秘書、內務司司長等要職。張昭漢一生熱愛文學,重視教育,倡導婦女平權,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婦女解放的思想。
陳鴻璧曾與張昭漢同在神州女界協濟社創辦的神州女學任教,張昭漢任校長,陳鴻璧任教務主任。神州女學設有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專修科,依據學生的知識結構水平和年齡進行分班教育,規定入學者須身家清白,8歲至11歲以下可以簡單識字者可入初等小學,12歲到17歲基礎較好者可入高等小學,26歲以內有中西學學習基礎者可入專修科學習。張昭漢主張發展個性與智行并重的教育理念,在教育方針上倡導男女平權、愛國互助的教育方針。她們開辦學校、倡導女權、為婦女傳授知識和技能,在當時覺醒的知識女性群體中比較具有代表性。她們深知女權運動不是一蹴而就便可成功的,更不是對政治權利的盲目追隨。與張昭漢相比,陳鴻璧對婦女政治權利的追求態度不是很積極,而是更加重視女子的受教育權以及女子經濟獨立問題,倡導婦女自食其力解決吃飯問題。
二、積極倡導女權,爭取政治平等權利
法國大革命后,正義、自由、平等思想席卷歐洲,在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下女權運動興起。隨著產業革命的推動,歐洲婦女自我意識覺醒的程度大幅提高,經濟獨立意識增強,參與社會工作中的人數增加。1900年“女權”這一概念傳入中國[3],賦予知識女性獻身民族國家的權利。陳鴻璧、張昭漢等從小受西學影響的一代知識女性,熟悉西方歷史和政治環境,對國內婦女被壓迫、被歧視、被剝削和被利用的生存狀態感同身受,自然容易走上宣傳女權、啟蒙女界的道路。
1907年11月9日,陳鴻璧作為育賢女塾代表參與民立上海女中學堂第一次女界保務會并進行演說。1911年11月,陳鴻璧與張昭漢、唐群英創立“上海女界協贊會”,最初以為革命事業募集軍餉為目的,后改組為“神州女子同和協濟社”。這個婦女團體主張女子參政,以養成女國民為宗旨,提出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實業,提出創設女子完全法政學堂,為參政做準備。“神州女子共和協濟社”曾上書孫中山大總統,要求參政。
同年,張昭漢組織成立女子后援會和上海婦女北伐敢死隊并任隊長,通過軍事參與,駁斥了傳統社會中只有男人才能參與軍事、保家衛國的觀念,證明婦女有能力承擔家庭以外的社會責任。敢死隊的成立為進一步推進男女平權、保障婦女的政治權利打下堅實基礎,足見張昭漢的政治抱負。1912年1月15日《民立報》以《女敢死隊入京》為題,報道了張昭漢等人赴京拜謁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事實,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婦女公開向政府要求政治權利的行動。
1912年2月,陳鴻璧與張昭漢參與了《中華民國女界代表上參議院書》和《女子參會上孫中山書》的聯名上書。同年秋天,“神州女子同和協濟社”創辦了《神州女報》,張昭漢任經理。張昭漢在《神州女報發刊詞》中言明了《神州女報》的辦刊目的,即鼓吹平權和參政之理。《神州女報》成為民國初期政治激進的一份報刊,陳鴻璧的《蘇州光復之真相》等作品均發表在《神州女報》上。
為幫助解決南京政府遷至北京后的資金問題,1912年5月19日張昭漢自發地組織成立國民捐勸導會,到會有500余人,婦女占多數。會上,張昭漢、陳鴻璧、呂碧城等發表演說,號召婦女參盡國民義務,為政府排憂。7月3日,陳鴻璧參與了邑廟萃秀堂的宣講會,號召婦女踴躍捐款。《神州女報》于1912年12月第5期以《國民捐勸導會之成立》為題進行報道。同年,國際婦女參政聯合會會長嘉德夫人環球考察經香港至上海,陳鴻璧等神州女界協濟社的社員們共同到嘉德夫人住所進行拜會。嘉德夫人指出“中國女界程度之高尚,性情之摯誠,為歐美人所傾服,將來女子參政之成績,必以中華為最完美”[4]。
1912年,以唐群英為首的激進派公然與政府對峙,為男女平權及女子參政問題大鬧臨時參議院和國民黨成立大會。陳鴻璧也參與了唐群英等參政激進派的活動。陳鴻璧作為清末知識女性群體中的先覺者,立足于文化啟蒙,如在辛亥革命時期任《神州日報》主編。武昌起義后,陳鴻璧與張昭漢共同創辦了日刊《蘇州大漢報》,陳鴻璧任總編輯,張昭漢任社長。其宗旨是倡導大同、鼓舞士氣。1912年1月23日出版的《婦女時報》第5期有題為《<大漢報>主筆陳鴻璧女士》之肖像畫[5]。
1912年3月16日,神州女界協濟社成立,陳鴻璧任實業部長,張昭漢任社長。其間,陳鴻璧身體力行,主張提高婦女勞動技能,認為婦女應通過自己的勞動達到經濟獨立,不再依附男子,積極倡導婦女走實業救國的道路,主張引導婦女在經濟上實現自救。作為女權運動的追隨者,陳鴻璧與張昭漢一同參與女權活動,注重引導婦女在經濟上實現自救。10月,陳鴻璧作為發起人之一,在北京創辦了《女子白話旬報》,后改名為《女子白話報》,次年5月停刊,主要以普及女界知識、達到男女平權為目的,通過淺近的語言傳達深刻的理論思想。
陳鴻璧認為婦女適合從事農業或者畜牧業的勞動,她在上海創設女界蓄植試驗所,利用良田十畝,種植農作物和蓄養牛羊家禽。陳鴻璧在1912年第4期的《神州女報》上發表了以《神州女界協濟社經營女界蓄植試驗所》為題的文章,介紹了陳鴻璧養蠶以興實業的舉措。可見,陳鴻璧對農業、畜牧業、家庭養殖業都進行了嘗試,身體力行地探索婦女經濟獨立的途徑。
此外,陳鴻璧積極配合興辦女子商業,在上海創設愛華公司,專銷國貨。她曾組織生產綢絲,用來制作愛國女子帽子,用國貨沖擊洋貨。張昭漢更加追求婦女的政治權,陳鴻璧比較關注婦女自食其力的經濟權。陳鴻璧對張昭漢充滿崇敬,曾經專門撰文評述張昭漢,不乏對張昭漢革命生涯的肯定,認為張昭漢從小就有崇高理想,是女界中具有革命思想之大家。此外,她還對婦女活動進行過總結,1912年《神州女報》1~2期有其撰述的《光復時代女性活動史》,宣傳婦女解放和民族解放。
三、共同翻譯小說,率先從事文學啟蒙
1905年前后,陳鴻璧開始翻譯活動。1907年7月,她入小說林社下設的宏文館學習,成績優異。1906年11月,她翻譯英國維多夫人的《印雪簃譯叢:探案錄之一》,由小說林社總發行所出版兼發行。1907年,她在晚清四大小說期刊之一的《小說林》雜志上連載三部長篇翻譯小說,分別是英國佳漢的科學小說《電冠》、法國寶嘉爾奧的偵探小說《第一百十三案》和佚名歷史小說《蘇格蘭獨立記》。在眾多的小說林社的女譯員中,翻譯作品最多的非陳鴻璧莫屬。從《小說林》創刊開始到終結的12期內,每期都有陳鴻璧的翻譯作品發表。《小說林》刊載的長篇翻譯作品僅有9部,陳鴻璧的翻譯作品就占了三分之一,可見其翻譯功力深厚,為《小說林》做出重要貢獻。小說林社曾出過《第一百十三案》和《蘇格蘭獨立記》的單行本,足見其受歡迎程度。
《小說林》宗旨是“輸進歐美文學精神,提高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作為《小說林》的創辦者之一,徐念慈對陳鴻璧的翻譯活動予以大力支持,曾請黃人寫了一副對聯,對陳鴻璧的翻譯才能表示贊賞:“錦心巧織梵蒼文,便教跨虎淪凡,當夸視西山寫韻;仙爪窮鎪歐墨影,雅擬騎麟晉謁,試縱譚東海揚塵。”[6]陳鴻璧依托《小說林》雜志和小說林社的扶持,成為當時譯壇上一名活躍的女譯者,其翻譯活動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
清末民初的社會環境中,女性的文學活動離不開男性知識分子的指導和幫助。陳鴻璧憑借自己的才華,贏得了男性知識分子提供的文學翻譯與創作的平臺。
陳鴻璧多部翻譯小說由小說林社、上海廣智書局、群益書局爭相發表,是一位兼具翻譯水平與一定市場接受度的翻譯家。1911年7月,陳鴻璧與張昭漢共同翻譯了美國白乃杰的奇情小說《盜面》,后由廣智書局、群益書局和千頃堂同時發行。同年,她們還合譯了英國查克的偵探小說《裴乃杰》和《裴乃杰奇案之一》(或譯為《裴乃杰奇案》),亦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發行。她倆的翻譯“蟹行書換雕龍技,文字醇醇接古悲。蜃氣已看幻樓閣,犀光時與照蛟螭。天方慘儋吾滋疚,道在孤微世豈知。為語雞林傳萬本,暫憑鉛槧警頑疾。”[7]小說得到如此好評,表明她們的翻譯已日漸成熟。陳鴻璧形成了自己的小說翻譯風格,她的譯文通俗易懂,與林紓相比較忠實于原著,特別是在人物的心理描寫上頗具匠心。
張昭漢在與陳鴻璧合譯兩部文學作品之后很少再從事文學翻譯,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詩歌創作方面。張昭漢于1911年譯述了英國沈威廉的科學小說《尸光記》等作品,其余作品均屬于革命性或詩文性質的文學作品。張昭漢的詩結構工整,用詞多有典故,也能在其基礎上自出機杼,其作品主要有《默君詩草》《正氣呼天集》《白華草堂詩集》等。陳鴻璧與張昭漢作為國內較早覺醒的知識女性,依托報刊雜志等媒介,用翻譯和文學創作開啟醒民救國的大門。
陳鴻璧、張昭漢是清末民初第一代覺醒的知識女性,她們從事文學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啟蒙女界。南社是清末規模較大的具有反帝反清性質的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團體,由陳去病、柳亞子和高旭等人于1909年11月在蘇州發起,其宗旨在于激勵民族氣節,用文學服務革命事業。南社以詩歌創作為主,聚集了許多行為品性高尚且有較高文學造詣的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很多南社成員也是同盟會會員,這決定了南社的文學表現較為激進。南社活動的14年間,成員發展壯大到1000余人,女成員有60人左右。陳鴻璧雖然沒有與張昭漢一樣加入南社,但她在女子教育、政治追求方面都與張昭漢不分伯仲。陳鴻璧與張昭漢密切關系,人生經歷相似,政治追求相同,一同開展教育、辦報、翻譯等啟蒙女界的實踐。陳鴻璧沒有參加南社大概是她以翻譯小說為主,不以詩歌創作見長的緣故。
[1]欒偉平.清末民初女翻譯家陳鴻璧的家世[A].秋瑾、徐自華、吳芝瑛、呂碧城暨近代女性文學高層論壇[C].2015.
[2]葉茷如.陳鴻璧先生[N].廣東女學校學生自治年會報,1922-01-15.
[3]劉釗.中國女性文學理論建構的范疇與方法[J].社會科學戰線,2015(12):155.
[4]何黎萍.西方浪潮影響下的民國婦女權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296-299.
[5]郭延禮.自西徂東:先哲的文化之旅[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231.
[6]欒偉平.小說林社研究:上冊[M].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41.
[7]傅熊湘.傅熊湘集[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3.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or CHEN Hong-bi and ZHANG Zhao-han
LI Xiang, LIU Zhao
(Changchun Normal Uni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32, China)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e female translator CHEN Hong-bi and the member of the Nanshe ZHANG Zhao-han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wome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The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ir interaction, tries to distinguish their relation, including the feminist revolution they participated in , the carrying out of education on women and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literature works. All of these reflect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tendency and literature pursui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women.
Chong Hongbi; Zhang Zhaohan ; feminist ; translated literature
2016-09-21
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末民初婦女報刊文學的社會性別研究”(2016B278)。
李想(1990-),女,碩士研究生,從事近代文學研究;劉釗(1965-),女,教授,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性別研究。
I206
A
2095-7602(2017)03-01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