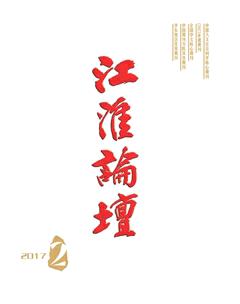傳承與啟蒙
方頠瑋
摘要:晚清小說既是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傳承,更承載著開啟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啟蒙功用。晚清文化語境與小說現代性生成有密切的關系;小說理論的現代取向展現出晚清小說獨特的現代性特征;不同文化視域研究者的闡釋,使晚清小說現代話語呈現出獨特性和豐富性。這一切均來自于對晚清啟蒙內涵的不同理解,這對呈現晚清小說現代意義的多重性,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晚清小說;跨文化視域;現代性;現代話語;啟蒙內涵
中圖分類號:I0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2-0180-006
晚清小說生成于19世紀后半葉,繁榮于世紀之交,在短期內以不可思議的爆發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康有為有詩為證:“我游上海考書肆,群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如小說何。”又說:“方今大地此學盛,欲爭六藝為七岑。”[1]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小說地位有所提升,功用也多樣化起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眼中,小說的價值取向是多方位的,在跨文化視域下小說研究也呈現出不同的現代話語。晚清小說的發展,對“五四”以后現代小說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對晚清小說的不同認知,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由古代轉向現代所經歷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它同樣折射出晚清小說不同的現代意蘊。
一、晚清文化語境與小說現代性
晚清小說興盛這段時期(1),是古代向現代的歷史過渡期,中國由閉關鎖國到中西接觸,引發了多樣并且復雜的文化反響,這為小說現代性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獨特且多元的思想土壤。
從小說自身發展歷史來看,晚清小說的敘事模式有了很大的變化[2],它使小說具有現代性品格。這基于內外因素的合力。從外部來說,西方小說的引入,中國小說深受影響而產生變化,尤其是形式的變化較多。周作人就曾經提出:“新小說與舊小說的區別,思想固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3]形式變化使小說以新的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從國內來說,在中國文學結構中小說的地位由文化邊緣移向中心,可以說,后一種變化的產生是基于前者。晚清小說的變化,在幾十年中生成自身獨立的現代品格。
公共媒介為小說現代性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語境。晚清小說的繁榮,離不開國內現代印刷業的發達和現代新聞事業的發展。在中國,最早發表文學作品的刊物《瀛寰瑣記》創刊于同治十一年(1872),主要刊載以詩文為主的文學作品,間或刊登翻譯小說。二十年后的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出現了以刊登小說為主的期刊《海上奇書》,由此在小說的創作與接受之間,出現了公共媒介。
晚清新小說的繁榮,還得益于跨文化譯介與出版為其奠定現代地位。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在日本創刊《新小說》,是最早專載小說的期刊,并提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促使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達到了峰值。關于晚清小說的繁榮盛況,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描述:“書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文學類一共收翻譯小說近四百種,創作約一百二十種,出版期最近是宣統三年(1911)。雜志《小說林》所刊東海覺我《丁未年(1907)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就一年著譯統計,有一百二十余種。《東西學書錄》(1899)只收三種,《譯書經眼錄》(1905)較多,然亦不過三十種。梁啟超《西學書目》(1897)不收小說,《新學書目提要》(通雅書局,1904)只存文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平圖書館,1933)所收創作,亦只與《譯書經眼錄》數量相等。實則當時成冊的小說,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種以上,約三倍于涵芬樓所藏。”[4]可見晚清小說出版盛況印證了小說數目之大,種類之繁多。這不僅使晚清小說具備了無可厚非的研究價值,也為從不同層面研究晚清小說提供了豐富的切入點。
晚清政治現代性訴求與小說現代性亦有密切的關系。梁啟超極力強調小說與改良社會的關系,雖然之前“此風未盛,大雅君子猶吐棄不屑厝意”。[5]但是此刊物的創辦,可稱“空前之作也”。對小說的提倡,也體現出一定的藝術傾向性。梁啟超所倡導的“小說界革命”,是為了推動中國的資產階級政治革新,它促使小說正式進入學者的研究視界,這不僅影響了近代小說的創作,也代表著戊戌變法以來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里,近代學者關于晚清小說的研究立場。戊戌變法前后,梁啟超和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嚴復、夏曾佑等人一起,非常重視和贊揚小說。對小說的褒揚以及提倡,對晚清小說理論的探討,這對小說創作的繁榮、翻譯小說的興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大大改變了小說自古以來不列九流不入四庫的卑下地位。
另外傳教士小說的輸入、翻譯小說的興起,以及傅蘭雅小說競賽的展開都影響了晚清小說的創作高潮,也促成了最早的中國現代小說的出現,這些都為小說現代性提供了現代文化土壤。
二、小說理論的現代取向與晚清小說現代性
處于新語境中的晚清小說被注入新的活力,促成了小說理論的現代取向。
小說理論的現代取向首先表現為在小說中建構現代政治話語,它促使現代白話小說的繁盛。梁啟超受英法日等國小說影響,指出“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將“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1898)論小說的重要性:“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6]新小說主要采用白話敘述,是因為晚清時期,文言主要用于上層社會的精神交流,白話更容易為百姓所接受。白話既然可以爭取民眾,就自然成為建構現代政治話語最合適的語言,小說中的意識形態功用需要依賴白話才能被凸顯與強化。如此,語言的功用性和審美性在晚清小說的書寫中被隔離開來。因為,文言美于白話,為了政治因素,小說之美只好降至次要地位。雖然有人強調,“小說者,文學之傾于美的方面之一種也”(2)但是政治功用仍是當時保證小說生命與價值的護身符。可見,小說之于梁啟超,與其說為文學作品,更多的卻是政治工具。他看中的是白話小說的教化作用,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梁啟超就提出:“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于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7]梁啟超看中的是小說有著一種“不可思議之力”,能夠支配人的心理,對社會、人心起到教化作用,進而改變社會現狀,這遠勝于傳統的“大圣鴻哲數萬言”。可見,梁啟超將小說作為傳播自己政治理念的媒介,希望喚醒以及教化更多的群眾,目的是以白話小說來爭取話語權的擴散,自然也就成了建構現代政治話語的載體。
小說理論的現代取向還表現為對西學的濃厚興趣,體現出現代性小說話語取代傳統敘事話語的趨向。甲午戰后,屢遭外力挫敗的知識分子,轉心欽慕西學。在這股西化的熱潮中,康梁所倡導的“小說界革命”是以翻譯、介紹西洋小說為起點的。利用西洋小說的眼光來反觀中國傳統小說或者利用傳統詩文小說的寫法來翻譯西方小說,推進了文學運動的深入以及近代小說理論的成熟。康梁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前文所提及的突出小說的覺世新民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對舊小說的批判。當時所引進的小說,又多與歐美、日本的政治小說相關,那些知識分子也借此有了變革現實、改良群治的經驗依據。當然,觀念的轉變不代表傳統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的消失,這反而突出了近代小說發展中所面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文本的政治性與文學性,文字的俗與雅。但梁啟超等人看中的是白話小說的通俗易懂,有不可思議之力來支配人道。因此必須以白話小說現代話語取代傳統敘事話語。
小說理論現代取向亦表現在小說價值功能的選擇。晚清小說理論的形成是基于小說的政治教化作用,小說作為藝術的獨立價值,小說中所承載的作家創作能動性以及人性關懷被刻意忽略。這個時期,小說的作者基本也是理論家,在他們的創作實踐和理論表述中,對藝術的直覺囿于上述理論建構出的慣性思維,一如既往地注重小說的教化功能。因此,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以及趣味性自然被近代學者邊緣化。因時勢導致的研究趨勢所迫,作家與固定的讀者群皆無單純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心思。這體現在對西方小說的價值取向上:以中化西、將西方小說的價值局限在認識世界、教育民眾的范圍內。或者從科技、創新的角度來推崇西方的科幻、偵探等小說。因此,晚清知識分子與其說是對小說的提倡,不如說是賦予小說一種話語功用力量。晚清小說折射出的中西文化沖撞,以及知識分子在小說中改良群治的思想訴求,與19世紀的西方現代文明密切相關,這注定晚清小說在誕生之初就已具備了現代性意義。
小說理論現代取向的另一個方面,是兩種現代性的交織,即在回歸傳統,懷疑、反思西方文明和啟蒙的相互矛盾中互相激發,期盼將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結合起來,以取得小說的現代話語權。一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和懷疑。民國初年,時政敗壞,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方文明與價值觀遭人懷疑,自然激發起國內知識分子反思晚清以來被看作楷模的西方文明的破綻,從而引發對本土文明回歸的自覺。二是現代啟蒙文化的建構及其取向。戰爭與民族的雙重危機,使得知識分子憂心于在尋找出路的年代,如何實現自己救亡與振興民族的抱負。當時,儒家傳統和復辟帝制時的復古論調準確無誤的建立起了聯系,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舉的大旗則正是“打倒孔家店”,反傳統。兩種現代性的交織體現出傳承與啟蒙的復雜關系。只有觀照民國初年的政治危機,參照當時的守舊、復古等對立語境,才能很好地理解新文化運動,雖然被定義為一場文化思想啟蒙運動,但是一開始就被政治化,我們只有將它作為帶著意識形態和政治色彩的概念才能使其獲得整體意義。因此晚清小說在五四的視野里,達不到當時學者關于政治、社會改革的期待值,并且由于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使晚清小說除去政治小說以外,其他文類小說在五四學者眼中不具備存在價值。晚清小說對藝術性的追求,對現代性問題的探究,以及對吸收了西方表現技法的敘事模式的創新,都被置于邊緣。五四學者的態度奠定了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研究史中的地位,這一地位中所包含的回歸傳統與啟蒙的矛盾、所包含的政治話語隱含著晚清小說所特有的現代性。
三、跨文化視域中晚清小說的現代話語及其成因
國內外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多各取所需,導致在不同文化視域中,晚清小說所呈現的現代性話語是不同的,這就構成晚清小說現代話語的多重性。
晚清小說的現代話語體現在政治場域對文學話語的闡釋。無論是康、梁所推行的小說的政治功用,還是五四以來晚清小說研究的政治取向,注定他們研究晚清小說和創作時聚焦于吻合政治場域的文學話語,晚清小說被賦予文以載道的重任。五四后漫長的幾十年里,同樣由于意識形態原因,晚清小說研究的其他方面被邊緣化,致使晚清小說缺乏被全面的認知。與以往從政教視野闡釋文學的不同在于,這一時期對晚清小說政治場域的文學話語解讀,卻具有文學現代性的表征。一是文化現代性的企求使他們站在政治現代化的立場,希冀從晚清小說活動提煉出政治現代性的主張。二是從國民觀念的視角,希望以小說作為文化生態建構的手段,并且能夠欲新一國之民。三是要求文學內涵借鑒西方文學的意識形態話語。
晚清小說的現代話語還體現在以西方文論為軸心的闡釋。英語世界晚清小說研究從興起之初,就在一個較為成熟的西方理論背景下進行闡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將晚清小說置于一個“客體”的地位。這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美興起的新批評理論有關,它極大地影響了海外學者對晚清作品的研讀,他們傾向于在意識形態氛圍濃郁的中國學術圈外另辟路徑,以發現他們所欣賞的文本內涵。在《夏志清論中國文學》中,對《老殘游記》首先側重于小說的藝術及其意義發現。他指出《老殘游記》有無可置疑的文本內部力量和藝術成就,“卻還沒有人用比較嚴密的批評方法去分析、討論。”[8]247因此,他將晚清小說作為一個獨立自在的“客體”,意在孤立小說中的要義和辭彩,進而專門對小說的藝術風格進行分析。其次,他對《老殘游記》的關注,重點不再是作者對社會貪官酷吏的政治批判,而是注重挖掘劉鶚內心最深切的悲痛:“劉鶚相信這些哭者多情善感,以見其靈性的深邃。他們大半皆變一己之哀而為人類之哭。”[8]250再次,夏志清以返回文學本體的姿態觀照小說文本的功能和力量。他將劉鶚與杜甫對比:“提及杜甫,乃用以闡明劉鶚的記述手法。”[8]251這一記述手法是立足于文學本體,將作者的個人情感與藝術力量融為一體,使小說呈現的不再僅是對于封建社會現實的揭露,更重要的是小說本身千回百轉的文化審美面貌所代表的各種不同功用。夏志清所發現的文本內在的豐富力量,是對晚清小說現代性意義的新發現。
第二,將晚清小說置放在文學史的框架內加以審視,特別是從敘事技巧的創新角度去發現晚清小說的發展脈絡。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論及晚清小說敘事技巧的創新,對小說文本中的西方藝術經驗,從理論上概括出文學史意義。立足這樣的視角,西方學者能夠超越政治,見證世紀之交中國小說千回百轉的面貌,試圖重新挖掘小說的各種實際功用,從文學現代性的走向還原小說的純文學性,在小說的自然存在中探詢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面貌,凸顯小說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將“文學的歷史”與“文學現代性”這一對矛盾命題放在一起,一方面,通過小說挖掘包含在記憶與遺忘夾縫中的客觀過往來呈現文學的歷史,另一方面,通過小說敘事技巧及其審美性,呈現創作個體及其強烈的主體意識。這一做法,恰恰能夠顯示出晚清小說現代性的原貌。
第三,通過文學與歷史互動研究模式,呈現晚清小說現代話語的豐富性。王德威以“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提出了“被壓抑的現代性” [9]。后來他以小說為依據,提出的“想象中國的方法”,成為近代到當代文學與歷史互動研究的新思路。文學與歷史互動研究模式,與20世紀新歷史主義理論以及尼采等人的觀點有關。他認為任何歷史記載或者單一的文學研究視角都不足以還原晚清歷史的全部真相,正如尼采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中描述的那樣:“歷史知識從一個永不枯竭的源頭向他流來,奇怪的片段匯聚在一起,記憶敞開了它所有的大門,卻總敞的不夠寬”[10]。也就是說,很難有任何歷史記錄下任何時代的所有事件。王德威從中受到啟發,認為小說是最能反映精神事件和歷史經驗的文體,超越歷史文本的只能是文學文本。于是,他從文本著手,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小說,直面瞬息萬變的歷史所帶來的挑戰。他想通過小說,重新書寫記憶與遺忘的夾縫間客觀存在的歷史。王德威建構的文學與歷史互動研究模式,能夠呈現晚清小說的另類面貌和尚未發掘的豐富蘊含,發現小說內藏的多彩現代話語。
第四,運用跨文化的研究立場和方法,闡釋晚清小說現代話語的獨特性。與國內學者相比,西方學者超越了國內從實用論視點發現的現代性內涵,但同他們原來所倡導的現代性或純文學觀相比,也發生了大面積的位移。例如包括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在內的一系列論著中,沒有掩飾自己對梁啟超、魯迅等人小說可以載道觀點的排斥,但這種排斥與純文學觀念亦有較大距離。也就是說,利用西方文論的思維來理解或研究晚清小說,本身就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最終也需要回到意識形態層面。從另一角度看,以這種思維來理解文學現代性,重在強調個人的主體意識,強調文本字里行間所透露的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這也透露出在西方話語邏輯下,以個人權力為核心的政治價值的意識形態,它與審美性關系不大。但不能否認的是,西方晚清小說的研究成果,向我們呈現出小說被賦予的強大現代使命,向我們突出了當時引導社會文化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現代主流權力意識。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引發的意識形態取向,呈現了晚清小說文學現代性與西方本土不同的獨特景觀,同時基于不同的研究立場,他們還呈現出主流意識形態掩蓋不了的晚清現代性的眾聲喧嘩。這些形態各異的闡釋,恰恰呈現出晚清小說現代話語的獨特性和豐富性。
第五,以人文主義情懷觀照晚清小說,將晚清小說置于世界文學之林,呈現出審美——文化張力的現代話語。首先,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將審美或者抽象意識介入晚清小說文本時,不僅是對當時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哲學的或者現實的話語之如鏡照影的再現,更是根據現下的既定語境生發更多的蘊含,這類話語是一個審美——文化的張力結構,反映的是現代性與晚清社會的二元對立。而這一張力結構呈現的每一種面貌都關乎以個人為主體的現代立場。其次,西方學者的知識譜系促使他們在研究晚清小說過程中,擴展了晚清小說乃至中國文學的研究范疇。在西方學者眼里,晚清小說發生在中華帝國晚期這個宏大的歷史地理空間,這個空間處于不斷風云突變的世界背景之中,這樣,西方學者在無形之中為晚清小說建構了一個新的歷史地理框架,不僅將晚清小說拉入中國文學的主流,也使晚清小說因其特有的審美現代性置身于世界文學之林。這一將晚清小說置放在世界地理坐標上的做法,使其具有了審美——文化、現代性——社會性結構的現代文學話語。
隨著西方理論的介入,國內學者也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晚清小說中的文字、文本與文化之間的關系,例如性別政治、文化生產等西方文論所觸動的文學議題,這些議題啟發或推動國內學者對小說的文學性有著更廣義的理解和觀察,從文類到現象,從運動到思潮。這些討論已然超出國內五四文學研究的典律,使得晚清小說研究有了更廣闊的時空坐標和研究維度。
西方研究路向,與國內看法一起,構成跨文化視域中晚清小說研究的現代話語。這些觀點及其語境也是不同文化視域中晚清小說現代話語生成的原因。
四、中西比較:啟蒙內涵與晚清小說現代性
世紀之交的晚清小說體現著近代以來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結果,是近代啟蒙思潮的產物。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激進的反傳統傾向,似乎都與啟蒙思潮相關。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啟蒙為現代性的根本。國內學者與西方學者對啟蒙內涵的理解存在著差異,這直接影響到對晚清文學作品價值的發現和對現代性的理解。
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知識分子并沒有將自身行為界定成符合西方啟蒙運動的范式。但是隨著啟蒙理念的常識化,啟蒙成就了近代知識分子對于現代性的想象,他們將晚清至五四時期的一系列改革運動定義為啟蒙運動。晚清時期,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在既定的啟蒙理念之下,知識分子倡導理性治國,這符合西方啟蒙運動的理性化脈絡。將西方國家看成是中國改革應該效仿的模板,恰恰證明了西方對中國啟蒙的影響。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繼續傳承啟蒙觀念,但由于世界大戰造成西方文明深重的危機,此時的知識分子萌生了不同于19世紀西方現代文明的新構想。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打開了另外一個關乎啟蒙的思考和想象空間。對于五四知識分子來說,啟蒙的意義不在于像歐洲啟蒙運動那樣,有著一貫的原則和整體性規劃,以啟蒙精神為凝聚點,而在于因為個人不同的政治抱負,賦予啟蒙不同的意識形態話語。啟蒙運動被這群知識分子建構成一個多重論辯和實踐的空間,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等不同的思潮和派別競相登場,釋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這不僅使得啟蒙具有豐富的內涵,也生成了多種不同的現代性。1949年以后,啟蒙話語被新民主主義思潮所替代。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一系列啟蒙思潮主要是對美國現代化理論的挪用。對此,國內學者褒貶不一,許紀霖在《啟蒙的命運》一文中,這樣形容新啟蒙主義和美國現代化理論之間的關系:“啟蒙派避開了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這類敏感的意識形態概念,他們借助當時在中國紅極一時的現代化理論,將西方的資本主義敘述為一種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術參數加以量化的現代性指標,或理解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三大特征,從而使這一具體語境中的歷史訴求具有了超歷史的普遍主義性質。”[11]陷入超歷史的普世主義的新啟蒙,既說明中西對啟蒙的理解有差異,也說明啟蒙在本土化過程中,會發生種種變異。國內學者以變異的啟蒙內涵觀照晚清小說,自然在取向和方法上與英語世界學者產生差異。因此,對啟蒙的不同理解也就帶來對晚清小說現代性的多重闡釋。
晚清、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其行動方式和形式與歐洲啟蒙運動的區別是顯著的。西方的啟蒙運動是指人類逃脫自身不成熟狀態的文化,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制度性的,體現著整體的啟蒙精神。人類不成熟的狀態是服從命令,并且利用這種思維形式應用到軍事紀律、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威中去。成熟與不成熟是中國先覺者和歐洲啟蒙主義者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差別。首先體現在對傳統或外來思維的態度和運用上。真正的啟蒙是需要人能隨時自主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思維模式和主觀意識,需要一再沖破僵化體系的藩籬,擺脫約定俗成的制度規訓,要將理性自由化,公開化。將近代知識分子與歐洲啟蒙運動的上述公式聯系起來看,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并沒有能夠做到自如地運用理性來思維,為了在啟蒙中找到自身的政治意涵,以西方學說為途徑,一味的信奉,自認找到能夠一勞永逸的掙脫儒家思想束縛的玉律,這樣,使得歐洲中心主義又一次表現出其支配性。啟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逐漸悖離本來的含義。其次,當時知識分子對歐洲啟蒙含義的挪用和位移,使啟蒙詞義具備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進而遮蔽了啟蒙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內涵。到了后現代時期,西方學者利用后現代視野去看待現代社會中的啟蒙問題時,會發現人的自主形象被破壞無余,取而代之的是經濟權力的支配,和被無限代入的政治因素。
所以,無論是晚清小說的興起與近代政治改革之間的關聯,還是國內外對待晚清小說研究的不同視野,都可以被認為是對啟蒙內涵的不同選擇和運用。比較中西研究晚清小說的差異,現代性更代表著雙方在研究過程中的一種差異的精髓,一種對于親身經歷或者目睹由前現代向現代轉型過程中關于現代文明的觀感和對于現代文明的態度。西方晚清小說研究也許可以更好地揭示出西方現代性視野下的中國文學,但是并未完全領悟中國文化的啟蒙意義,因而也未體現出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啟蒙意義的全部理解,更未明白中國近代文學在文學現代性中到底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而且,在西方學者觀照中國研究界的時候,由于一直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民族家國觀念的擺布而小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能動性。殊不知,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自我能動性就是一種現代理性的呈現。中國知識分子在對西方文化的接受過程中,不僅利用西方理論來創作小說,也利用西方理論來研究小說,只是沒有能夠完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西方的啟蒙意義以及對于人類理性的運用沒能做到真正的理解,也未能根據中國實際加以把握和運用,因此在創作或者研究的過程中難免依舊囿于自身的觀點和思想而難以突破。
晚清小說特定的時代背景注定了它不平凡的身份。無論晚清小說的綜合價值被定位于什么水平,它確實是對中國文學傳統的一種傳承,更是承載著開啟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啟蒙功用。由于理論背景的差異性,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不同文化視域中的晚清小說,其研究成果對現代性的呈現也就不同,這凸顯了晚清小說本身現代性內涵的豐富多彩。無論是國內知識分子還是西方學者,或許出發點大不一樣,但是都從不同層面展示了晚清小說的現代話語,這對呈現晚清小說現代意義的多重性,推進晚清小說研究,無疑是必要的。
注釋:
(1)“晚清小說”概念與西方學者以“中國中心”觀念里的“中華帝國晚期”概念相關,“中華帝國晚期”涵蓋明清至民國前的歷史時期,所以“晚清小說”不僅是時間的概念。此處參見[美]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1頁。
(2)1907年2月,《小說林》在上海創刊。在《小說林》第1期,黃人撰《小說林發刊辭》,對當時小說的繁榮發表新評價,既批判舊時對小說太輕視,又不滿當時對小說太重視。并不強調小說教育人群﹑改造社會的作用,而指出“小說者﹐文學之傾于美的方面之一種也”。
參考文獻:
[1]康有為.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詩以速之[M]// 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08.
[2]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38.
[3]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J].新青年,1918,5(1).
[4]阿英.晚清小說史·序言[M].香港:太平書局,1966:1.
[5]《新小說》介紹 [N].《新民叢報》,1902-11-14(20).
[6]阿英.晚清小說史[M].香港:太平書局,1966:2.
[7]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897—1916)[G].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12.
[8]C.T.Hsia. C. 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9][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M].宋偉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0][德]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M].陳濤,周輝榮,譯.劉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
[11]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J].二十一世紀,1998,(12):4.
(責任編輯 清 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