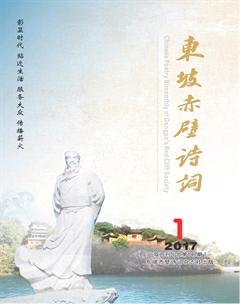檻外談詩(二)
夏元明
中國人向來有門戶之見,喜歡站在自己的角度,排斥異己。比如武術(shù),甲派瞧不起乙派,丙派又不以甲乙為然,此常常成為影響自身發(fā)展進步的重要因素。這種囿于成見的作風(fēng),在詩歌領(lǐng)域也同樣存在。比如新舊詩,喜歡舊詩的人,對新詩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認為那不過是說白話,完全沒有詩味。而操新詩者,則對舊詩多有鄙薄,每每斥之為“平仄游戲”,迂腐而已。這種現(xiàn)象生活中常有發(fā)現(xiàn)。廢名就曾經(jīng)記錄過一段掌故,說是他在武漢求學(xué)的時候,教國文的老師將胡適的《蝴蝶》書于黑板,譏之曰:“北大教授居然寫出這種狗屁詩來!”言下大為憤慨。而廢名則認為,《蝴蝶》一詩雖然算不得十分好,但也說不上壞,作為一首詩,它還是稱職的。而今觀之,這首詩真正不足倒不在于詩意,而是新得不夠,脫不了舊詩的影子,是典型的“放腳體”。如果論詩意,這首詩還是有得一說。題目為“蝴蝶”,則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與蝴蝶有關(guān)的典故。典故分雅俗,雅的是“莊周夢蝶”,俗的是“梁祝悲劇”。梁山伯、祝英臺的故事,在民間可謂家喻戶曉,吾鄉(xiāng)方言,“蝴蝶”不叫蝴蝶,徑稱為“梁山伯”,可見這個故事有多么深入人心。胡適以“蝴蝶”為題,與舊詩中常見的詠物有別,也許可以稱之為借物抒情、托物言志。胡沒有用舊典,但與梁、祝故事暗相契合。因為胡適所詠也是愛情悲劇,或者還不僅限于愛情。所謂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多么情投意合,自由自在。可是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一個忽飛還,也就是分離,分離造成悲劇。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自然“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這分明是一個愛情故事,因為蝴蝶在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常常就是愛情的象征。聯(lián)系詩人自己的經(jīng)歷,出國前已經(jīng)有了老婆,那就是江冬秀。但到了美國,又有美國女子對他產(chǎn)生了愛慕。胡適在一首詞里就記載了這件事,其結(jié)尾云:“君為我拾葚,我替君簪花。”說的是他們一起到郊外游玩,你為我撿拾桑葚,我則將野花插在你的發(fā)間,多么親密、親愛!可是這兩個跨國戀人卻不能自由結(jié)合在一起,因為之間夾著一個江冬秀。想起老家的那一個,眼前的一個也只能舍棄,這就是“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如此說來,這首詩還是“言之有物”的,感慨不可謂不深。如果再加以引申,聯(lián)系到胡適倡導(dǎo)白話文,不僅響應(yīng)者寥寥,而且連自己最好的朋友也為之質(zhì)疑和反對,內(nèi)心的孤獨只怕不亞于失戀。如果這個聯(lián)想不算突兀,那么,這首詩就不僅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其間更有深意藏焉。如此說來,像汪曾祺“胡適不懂詩”的批評,是不是略過?更別說廢名那位偏激的老師!當(dāng)然,胡適的詩歌語言也過于平白了,這也影響了他的詩意表達。但我要說的是新舊詩固然不同,但要之不在語言形式,而在于詩之本身。有詩意,白話也行,沒有詩意,就是平仄、對仗無懈可擊又如何?相互之間,在一些表象問題上爭執(zhí)不已,壁壘森嚴,大可不必。
再說詩歌語言。喜歡舊詩的人常常批評新詩淺白,或者語言歐化,弄得人一頭霧水,看不明白,此當(dāng)為新詩的主要罪狀。其實說到歐化,我倒是同意廢名的看法,舊詩文中本來就有很“歐化”的句子,并非來自國外的影響。比如《論語》中,“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難道還不夠“歐化”?以至翻譯成英語,連語序都不必調(diào)整。再如《詩經(jīng)·七月》:“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主語一直到最后才出現(xiàn),不是歐化得可以?然而,這正是地道的漢語,是我們的祖先留下的。我們不批評古詩文中的“歐化”語句,偏偏對新詩的句子說三道四,豈不有失公允?再說淺白,舊詩中寫得好的詩大多倒是淺白的,比如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一點典故沒用,一點別扭的句子沒有,怎么沒人指責(zé)其“淺白”?李煜的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也很明白曉暢,可從來沒見人批評說不好。所以,這種雙重尺度,恰恰證明了自己的“門戶之見”。新詩有很多語言其實是很典雅的,耐人尋味,并不一味淺俗。比如卞之琳的《無題(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過你一絲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見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轉(zhuǎn)千回都不跟你講,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載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樓去!
南村外一夜里開齊了杏花。
何等的優(yōu)美!“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南村外一夜里開齊了杏花”,該要引起人多少美麗的遐想!像這樣的詩,它就是詩,與新舊無關(guān),真正懂詩的人決不因為它是白話寫成的,就不喜歡它。但有些人偏要說這樣的詩晦澀難懂,可我要說句得罪人的話,是你自己不愿意懂,或根本不配懂,怎么怪得了詩人!
新舊詩其實還有許多相通之處。我們讀新詩,見到其中含有舊詩的影子,往往喜之曰“借鑒傳統(tǒng)”。比如張棗《鏡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古典的味道很濃。其實讀舊詩,也偶爾能發(fā)現(xiàn)新詩的筆法,讀之也平添欣喜。比如《西洲曲》:“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蓮心徹底紅”就很有新詩的味道,通透直接,直抵事物的本質(zhì)。舊詩每講溫柔敦厚,可這里的句子卻酣暢淋漓,半點也不做作。這里透露的氣息是新詩的熱情奔放,是一種自由個性的伸展。與之異曲同工的有龔自珍的《題盆中蘭花》,居然寫出了“一寸春心紅到死”的詩句!紅到死,又比徹底紅進了一步,真是敢于創(chuàng)造。龔自珍不僅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文學(xué)上也是一員猛將,決不因襲陳套。這樣的詩人理所當(dāng)然值得人敬重!龔氏還有一首《夢中作四絕句(之二)》也是我所喜歡的:“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如潮!”花影如潮,古往今來誰人這樣寫過?太過癮了!
廢名在《新詩問答》中有幾句話值得深思。他說:“我覺得中國以往的詩的文學(xué),內(nèi)容總有變化,雖然總有變化,自然而然的總還是‘舊詩。以前談詩的人,也并不是不感覺到有一個變化,但他們總以為這是一種‘衰的現(xiàn)象,他們大約以為愈古的愈好。我想這個態(tài)度是不合理的。他們不能理會到這是詩的內(nèi)容的變化,這變化是一定的,這正是時代的精神。”廢名的意思是說新詩的產(chǎn)生與時代的變化有關(guān),與時代精神有關(guān),不是哪個想當(dāng)然地要變,是時代精神催促它改變。這無疑是對的。而按照廢名的意思,中國詩到宋詞為止,雖然內(nèi)容發(fā)生了變化,但仍然還是舊詩的格局,因為其詩的思維方式?jīng)]有發(fā)生徹底的改變。甚至連初期的白話詩,也仍然在舊詩的束縛之下掙扎生長。所以,僅僅是語言的變革還不夠,還得有與時代精神相吻合的思維方式、審美方式,而這恰恰成為后來新詩值得驕傲的地方。可以這樣說,舊詩有新詩無法表現(xiàn)的內(nèi)容,新詩也有舊詩無法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二者不能相互取代,不能相互轉(zhuǎn)譯。這就決定新舊詩不應(yīng)該相互輕視,相互嘲笑。而應(yīng)該取長補短,相互借鑒,共同提高,開創(chuàng)一個新舊詩共同繁榮的新局面。
2017年1月14日于且齋
(作者系黃岡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教授、湖北作家協(xié)會會員、黃岡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