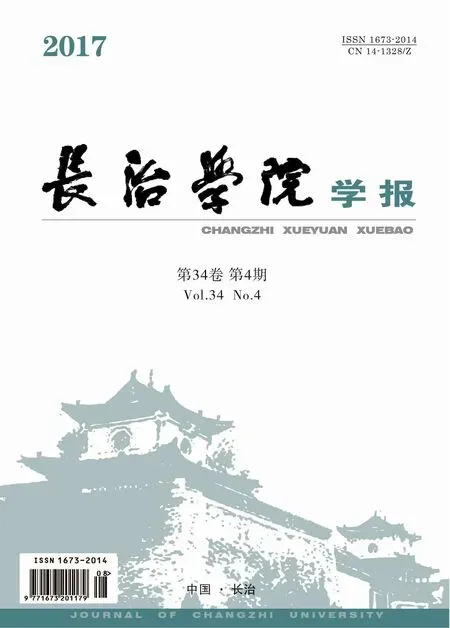福澤諭吉文明論哲學(xué)的理論缺陷及現(xiàn)實影響
李 聰,趙本義
(西北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127)
福澤諭吉文明論哲學(xué)的理論缺陷及現(xiàn)實影響
李 聰,趙本義
(西北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127)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哲學(xué)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日本社會看到的多是其積極的啟蒙意義,而其諸多理論缺陷卻被人為隱藏。對后世的日本社會和國民的歷史觀造成了極大的誤導(dǎo)作用,并導(dǎo)致了日本戰(zhàn)后受害者意識普遍的現(xiàn)象,消極影響十分惡劣。因此,全面認識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哲學(xué)就顯得極為重要。
文明論;受害者意識;戰(zhàn)爭;國權(quán);民權(quán)
一、引言
福澤諭吉是對日本具有重大影響的“啟蒙式人物”的代表。在近代日本歷史上,他似乎始終扮演著動蕩時局中清醒的“正義使者”,時至今日,還依然“閃耀”在日本一萬日元紙幣之上。其文明論哲學(xué)經(jīng)過后人的完美化“包裝”,成為改變近代日本精神風(fēng)貌的一劑良藥。但是,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深淵,又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化身為“受害者”去面對歷史,個中原因雖紛繁復(fù)雜,但骨子里對戰(zhàn)爭行為的合理化辯解讓我們不得不追溯到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哲學(xué)。
二、福澤文明論哲學(xué)的背景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哲學(xué)植根于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后所面臨的國際環(huán)境的巨變,尤其是與日本一衣帶水的我國的遭遇。被動挨打的中國一度讓福澤唏噓不已,起初言語中也多是對中國的同情和對西方列強卑劣行徑的憤怒。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沉睡的”亞洲各國逐漸被扯入西方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深淵。地處東亞一隅的島國日本自然難逃厄運。13年后,“黑船來航”打開了堅鎖的日本國門,在幕府統(tǒng)治漸露頹勢的內(nèi)憂外患之下,經(jīng)歷倒幕運動、明治維新等一系列社會運動和改革,不得不奮起直追的日本積極應(yīng)對著來自世界的變化。相較之下,鄰國中國似乎還沉浸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思想和行動上都顯得過于遲鈍。停滯不前甚至一步步退縮的中國和忍痛前進的日本,這兩者對于時局劇烈變化的應(yīng)對確實迥異。由此,潛藏在日本人心中,企圖扭轉(zhuǎn)從古至今中日力量對比不平衡局面的念頭借著國際局勢風(fēng)云變幻之時的混亂聚集、生發(fā)并最終付諸行動。福澤的中國觀也相應(yīng)地經(jīng)歷了同情、觀望、批判、厭惡等多個階段。如果說鴉片戰(zhàn)爭之初的福澤還對中國的遭遇抱有一定的惻隱之心,那么此時的福澤已然變成了曾使其痛恨、畏懼的列強的模仿犯。
三、福澤諭吉文明論哲學(xué)的雙重標準
在《文明論概略》中他既說“拿起武器殺害界外兄弟,掠奪界外土地,爭奪商業(yè)利益等等,這決不能說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這些罪惡,姑且不論死后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這種人應(yīng)該說是耶穌的罪人。”[1]174之后又說道“殺人和爭利雖然為宗教所反對,難免要被認為是教敵,但是,在目前的文明的情況下,也是勢非得已……戰(zhàn)爭是伸張獨立國家的權(quán)利的手段。”[1]175他一方面倡導(dǎo)要“順應(yīng)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使全體人民的智德自然發(fā)展,使其見解自然達到高尚的地步……人心有了變化,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礎(chǔ)才能建立起來。”[1]14在此,他主張教化民眾、伸張民權(quán)。另一方面又認為民眾智德之進步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國家獨立,文明僅僅是國家獨立的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從而要推進國權(quán),甚至不惜犧牲民權(quán)。如此這般前后矛盾的論說不勝枚舉,實際上顯示了其觀點的混亂和偽善。日本著名學(xué)者安川壽之輔對此批評到,“福澤所提出的命題和演說,是根據(jù)倒退的歷史現(xiàn)實主義,即根據(jù)現(xiàn)實追隨主義和漸進主義,不斷追從和追隨現(xiàn)實,像變色龍似地變色和變節(jié),由此確立了不修邊幅、毫無節(jié)操的思想。”[2]306福澤赤裸裸的戰(zhàn)爭邏輯完全是將文明作為推行侵略戰(zhàn)爭的借口,在歷史風(fēng)云變幻之際,化身為所謂的啟蒙思想家,用文明論哲學(xué)為日本對外擴張的軍事行為護航甚至可以說成為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同謀。
四、對“文明”本質(zhì)的偏頗理解
(一)將文明片面理解為西方工業(yè)文明
福澤諭吉所指稱的“文明”僅僅是盛極一時的西方工業(yè)文明。他斷言“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1]11為了接近這樣的文明發(fā)展水平,日本最終仿效西方列強實施侵略擴張。但是“文明”最早起源于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法語詞“c ivilisé”,意為“有教養(yǎng)的”。因此,“文明”從產(chǎn)生之初就被打上了脫離蒙昧的印記,是人類發(fā)展到較高程度時才可使用的詞匯。它與人類不斷求索,積極進取息息相關(guān)。從茹毛飲血、衣不蔽體的遠古時代發(fā)展到當代社會,可以說人類經(jīng)歷了一部超越野蠻,追求文明的進步史。文明并非西方世界工業(yè)文明下的極度物化,不是積累的財富越多就越文明,也不是科技越進步就越文明,更不是福澤認為的越接近強者就越文明。不僅如此,凡是追求諸如此類片面的文明反而更易被其掌控乃至異化,成為人類背上的沉重枷鎖。實際上,文明應(yīng)該是一種狀態(tài),一種向上奮進的延續(xù),所有這一過程下積累的超越自身過去的物質(zhì)財富、精神財富等都可以成為文明的表現(xiàn)。只有這樣才符合“文明”一詞的起源和其蘊含的最初意義。
(二)將戰(zhàn)爭作為實現(xiàn)文明的一種手段
福澤宣稱“沒有比對外戰(zhàn)爭更能激發(fā)全國人民之心令國民全體感動的了,……因此當今面對西洋各國,能夠激發(fā)我國人民報國心的方法,沒有比戰(zhàn)爭更好的了。”[3]133他認為“殺人和爭利雖然為宗教所反對,難免要被認為是教敵,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況下,也是勢非得已……戰(zhàn)爭是伸張獨立國家權(quán)利的手段。”[1]175由此,福澤將戰(zhàn)爭與獲取文明之間,文明與西方強勢文明之間完全劃上了等號。福澤將侵略戰(zhàn)爭理解為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賦予侵略戰(zhàn)爭以實現(xiàn)文明的意義。但是,文明既然是一種動態(tài)的過程,那自然并非一種終極目標,更不應(yīng)該如福澤所言,竟可以通過侵略戰(zhàn)爭這種本身反文明的極端手段去獲取。相反,侵略戰(zhàn)爭只會摧殘人類世世代代來之不易的文明成果,傷害不斷創(chuàng)造文明奇跡的人類社會。
(三)將文明與野蠻完全對立
當日本開始用西方列強強加于自身的手段瞄準周邊國家之時,福澤便積極發(fā)聲表示支持,福澤認為“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后,那么,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1]168在他看來,被動挨打的弱者就是野蠻,主動進攻的強者就是文明。此時的福澤認為被侵略國家的人民都是丑陋和冥頑不靈的,只有用武器去改造他們,才能使他們進步。類似這樣的帝國主義邏輯為日本不久之后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可以說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福澤個人立場的轉(zhuǎn)換映射出日本既善于應(yīng)變又容易走向極端化的特征,也反映出福澤試圖轉(zhuǎn)嫁戰(zhàn)爭責任的企圖,其所謂的文明論哲學(xué)使得日本對亞洲的介入言之鑿鑿。文明從來都不該是唯一的、精準的。以文明和野蠻,進步和落后的“二分法”相區(qū)別,這樣只會陷入非此即彼,企圖用唯一的文明取代異質(zhì)文明的錯誤深淵。當代的文明是在新時代背景下要求的文明,它意味著我們要顧及屬己文明以外的異質(zhì)文明,并接納不同的文明,共同促進文明的多樣發(fā)展。
(四)視文明為國家獨立的手段而非目的
福澤著重說到了國體與文明的關(guān)系,宣稱“日本人當前的唯一任務(wù)就是保衛(wèi)國體,保衛(wèi)國體就是不喪失國家的政權(quán)。”[1]124他認為“國體并不因文明而受到損害,實際上正是依賴文明而愈益提高。”[1]27并最終得出結(jié)論“國家的獨立是目的。現(xiàn)階段我們的文明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1]192在福澤看來,文明從來都不是其本身的目的,而只能是國家獨立的手段。由此,文明就被弱化為一種工具。“只是把有助于本國獨立的東西,姑且定名為文明。……國家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1]192這種觀點比起審時度勢,見風(fēng)使舵的性質(zhì)更為明顯。到后來發(fā)展為鼓勵侵略擴張、恃強凌弱的“脫亞入歐”等軍國主義思想,之后更以維護“國權(quán)”抗衡歐美為名肆意妄為,為日本的戰(zhàn)爭行為推波助瀾,將無數(shù)無辜的亞洲人民卷入戰(zhàn)爭的深淵。
另外,福澤還肯定了保留皇室的積極作用。在它看來“政府的體制只要對國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應(yīng)拘泥名義如何,而應(yīng)求其實際。……君主政治決定改與不改的標準,只在于它對文明是否有利而已。”[1]32福澤大膽闡述了天皇制的實際作用,“君國并立……維持了我國的政權(quán)和促進了我國的文明。”[1]29他認為要學(xué)會“去其虛飾迷惑而存其實際效用。”[1]29然而天皇制國家在整個昭和時期不斷發(fā)酵,愈演愈烈,以致戰(zhàn)后天皇逃脫了戰(zhàn)爭責任的懲罰。作為這場侵略戰(zhàn)爭背后的核心領(lǐng)導(dǎo)者和精神支柱,天皇的責任本難以推卸。“假使一個以其名義處理日本帝國外交和軍政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為發(fā)動和領(lǐng)導(dǎo)這場戰(zhàn)爭負起應(yīng)有責任的話,那么,還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費心思量這些事情,或者嚴肅地思考他們自己的個人責任呢?。”[4]9天皇在侵略戰(zhàn)爭中不僅應(yīng)該負一定責任而且應(yīng)該負主要的責任。對天皇的免責,是日本戰(zhàn)爭責任意識淡薄的重要來源。福澤諭吉從倡導(dǎo)民權(quán)到疾呼國權(quán)、默許皇室。他這種急功近利式的立場轉(zhuǎn)化既是對文明認識的偏差也是對戰(zhàn)爭行為的縱容。
五、福澤諭吉文明論哲學(xué)在當代面臨的問題
站在國家命運的十字路口,日本再次選擇了追隨強者,甚至成為一個不惜一切“求取文明”的盲從者。福澤行事也無不以西方文明為標準,企圖從方方面面全盤吸取西方文明。然而日本社會在近代卻逐漸感受到了身份認同的迷惘。“當歷史發(fā)展到‘泛西方化’時代終結(jié)期的20世紀末葉時,非西方世界的人們在經(jīng)歷了全盤西化的迷狂之后,終于發(fā)現(xiàn)西方化的道路并不能解決自己國家和地區(qū)的根本問題,尤其是不能解決自己文化的精神根基問題。”[5]2此時,福澤諭吉文明論哲學(xué)的缺陷便暴露無遺。究其原因,這個在民族根基和西方強勢文化之間搖擺、平衡的日本,也會不可避免地遭到這種猶豫的反撲。湯因比在談到“泛西方化”過程中給非西方世界的人們帶來的精神苦惱時說道“事實上,他們?nèi)掏捶艞壸孑叺纳罘绞蕉扇⊥鈦淼奈鞣降纳罘绞剑@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然而他們卻由此不無寬慰地虔信,以如此代價換回的其實只是由于陷入了迫近的西方精神危機所受到的懲罰。”[5]294當文明的沖突越來越表現(xiàn)為精神根底與文化差異的不同。作為弱勢一方的東方文明,在近現(xiàn)代面臨的不僅是外在的挑戰(zhàn),而更多是自身的定位和歸屬感的危機。但是絕非一味學(xué)習(xí)強勢文明就能解決自身遇到的一切問題。戴季陶曾說道“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進步,不能在文化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沒有一種自己保存,自己發(fā)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6]17所以福澤設(shè)想的全面學(xué)習(xí)西方文明就能使日本脫離困境的想法不可避免會落空,并且會在之后的發(fā)展道路上陷入迷惘和錯亂。不論是福澤諭吉還是日本社會,對于本國身份認知的錯誤所導(dǎo)致的曖昧、糾纏的局面是日本在短時間內(nèi)快速學(xué)習(xí)西方文明所付出的相應(yīng)代價。
六、余論
福澤諭吉文明論哲學(xué)的啟蒙意義越過歷史的長河,在日本民眾的心中根深蒂固。由于日本在戰(zhàn)后一直企圖擺脫所謂的“自虐史觀”,甚至不惜扭曲歷史,美化侵略行為。福澤的文明論哲學(xué)對戰(zhàn)爭的理論支撐作用在此之下逐漸被人為掩埋。呈現(xiàn)在日本國民和社會面前的只是作為“啟蒙思想家”偉大的一面。這般人為的美化蒙蔽了國民的雙眼,是日本國家和社會的悲哀。但是時間會證明,一個美化戰(zhàn)爭的思想家將無法永遠保持啟蒙家的光明形象,一個不能正視歷史的民族終究也是無法前進的。
[1]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
[2]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與丸山真男——解構(gòu)“丸山諭吉”神話[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
[3]福澤諭吉.通俗民權(quán)論.通俗國權(quán)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
[4]約翰·W·道爾.擁抱戰(zhàn)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日本[M].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
[5]趙林.告別洪荒——人類文明的演變[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5.
[6]戴季陶.日本論[M].長沙:岳麓書社,2013.
(責任編輯 楊曉娟)
B313
A
1673-2014(2017)04-0001-03
古希臘政治哲學(xué)與中國先秦政治哲學(xué)的比較研究(12C031)
2017—04—13
李 聰(1993— ),女,陜西西安人,碩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方向研究。趙本義(1958— ),男,陜西安康人,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