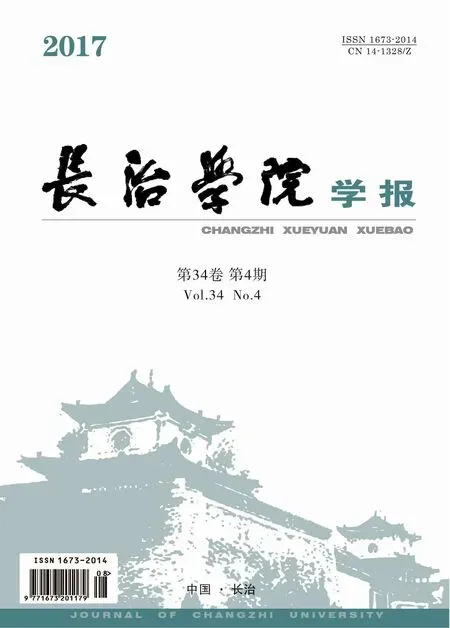“私”在夏目漱石小說《心》中的關系及意義
李德平,廖志翔
(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私”在夏目漱石小說《心》中的關系及意義
李德平,廖志翔
(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在夏目漱石的小說《心》中,“私”(日語“わたくし”即“我”)因其指涉的對象不同而具有不同含義。作為學生“我”的“私”是一位心路歷程的見證者和希望的寄托者;作為“先生”的“私”則是一位告白者、懺悔者。同為知識分子的兩個“私”之間表現出一種授受關系和精神父子關系。這一關系不僅具有新舊更替的意義,它還連接著作家的社會期待和對人生道路探索的哲學思考。
《心》;“私”;“我”;“先生”;夏目漱石;關系及意義
夏目漱石被譽為日本的“國民作家”,他的作品歷來深受讀者的喜愛,也不斷被解讀,表現出無窮的魅力。作為他后期三部曲之一的著名長篇小說——《心》,尤其深受讀者的青睞,對其進行的研究也經久不衰。從國內對該作品的研究來看,從“先生”的角度來分析探討其自殺原因及內涵反映的文章比較多,但從文本中的人物即“私”的敘述角度來分析“我”和“先生”兩者關系及其意義的文章還相對較少。因此,本文也將試圖從這一視角來進一步探討作為敘述者的“私”在小說《心》中的關系及存在意義。
一、“私”的指涉對象
小說《心》由上、中、下三篇構成。它們分別為上篇《先生和我》、中篇《雙親和我》、下篇《先生和遺書》。從小說的整體來看,文本中出現了兩個敘述者“私”,其所指涉的對象不同。第一個“私”是指上、中篇里出現的敘述者即作為學生的“我”。第二個“私”是指在下篇中作為遺書的敘述者“先生”以第一人稱方式出現的“我”。這兩個敘述者“私”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內涵,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二、“私”之間的關系及意義
小說《心》中的兩個“私”之間,體現為一種敘述與被敘述、見證與告白的關系。這一關系包含著一種經驗授受和精神父子的關系。
小說從現時的視角敘述過去還是年輕大學生時的“我”在鐮倉與“先生”相遇,對“先生”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從而逐漸與他熟識起來并常去他家中拜訪。先生最開始對我盡量保持著一種疏遠和懷疑的態度。他每月到雜司谷公墓供奉亡靈一事激發了“我”的好奇心,但他不能告訴他人的理由使“我”感到奇怪。他重復講說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他對跟太太之間“我們應該是人世間天生最幸福的一對”[1]24的表達也使“我”充滿疑問。他認為戀愛就是罪惡,他表現出的對全人類都不信任這一所謂來自他實踐的認識,也讓“我”難以理解。他的一些話,如“平常都是好人……至少都是普通人,就是這種人,在發生什么事情時,會一下變成壞人。這才可怕呢,所以不能大意呀”[1]68、“我從別人那兒收到的屈辱和損害,過上十年、二十年也絕不會忘掉的”[1]73常常讓“我”感到意外和不得要領。這一系列的疑問只有等到下篇中“先生”給“我”的遺書之后才得以解除。在下篇中,“先生”向我告白了他的過去。他從小失去雙親,被叔父欺騙了財產后從此決心永遠離開家鄉,認為別人都靠不住的觀念也浸透到他的骨子里。“對于金錢,雖然我已懷疑了全人類,但是對于愛,我還沒有對全人類發生懷疑”[1]159的他,對寄宿房東太太的女兒“靜”產生了愛戀之情。當他發現被自己邀請來一同寄宿的好友K也對“靜”產生苦戀后,“先生”由于獨占意念和嫉妒心理,對一向追求“精進”和“道”的K,他用K原來用過的話語“在精神方面沒有進取心的人,那是混蛋”[1]222來堵塞好友K通向戀愛的道路,之后裝病并趁機提前與房東太太取得和她女兒“靜”的婚約。好友K由于“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和“先生”的背叛而自殺。自此“先生”深感自己的罪孽,一直生活在懺悔和陰影籠罩的孤獨生活中,最終以“殉死”的托詞而自殺。在此,“我”成了“先生”命運的見證者,“先生”也以遺書的方式向“我”告白了他的心路歷程。文本至此也完成了“我”的敘述與“先生”的被敘述書寫。
在“我”與“先生”的交往、“先生”向“我”告白的過程中,實際上蘊含著一種經驗授受關系和精神父子關系。
在日語中,老師被稱作“先生”,而能稱之為“先生”的人則是能給予學生或年輕人以必要指導的人。表示“我”的“私”在日語發音中除了“わたし、わたくし”等以外,還有發音“し”。而能表示“先生”的“師”其發音也有“し”。如果說作為“先生”的“私”能夠真正成為老師的“師”,那么“先生”就能給予作為學生“我”的“私”有益的指導。從文本的敘述我們可以得知,“先生”是明治時期的一位知識分子,而“我”當時是一名大學生,可以算作知識分子中的一員。然而,因為受到“金錢”和“戀愛”這兩個事件的影響,“先生”變得既不工作也不到社會上去活動,逐漸變得討厭和人見面,對“我”畢業論文也不打算擔負指導的責任等。但是,當他發現“我”想認真地從人生獲得教訓時,他才準備把自己的過去毫無保留地“講”給“我”。正如他在遺書中描述的那樣,“我要把黑暗的人世的陰影,毫不客氣地投在你的頭上。……你要定神注視著這個黑暗的東西,從這里邊抓住可以供你參考的東西。……所以對于要在今后有所發展的你,我想也許有幾分參考價值吧”[1]137、“我現在正在自己剖開自己的心臟,要把它的血潑到你的臉上去。如果當我心臟停止搏動的時候,能夠在你胸脯里孕育著一個新生命的話,我就滿足了”[1]138。由此看來,這時的“先生”已把“我”當作真正的傳授對象,準備把他的個人實踐和經驗轉接到“我”身上。畢竟,當時的“我”太年輕,還是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正如“先生”自認為年輕時既無經驗又不能區分好壞那樣。“先生”所傳授的東西,也是“我”在和他交往過程中想要獲取的。“我”在小說的上篇里有講到,“每逢回憶起那個人,立刻就要說‘先生’。在我提筆寫的時候,我的心情也是一樣”[1]1。這里稱呼“先生”,跟“這就是第一次從我嘴里喚出來‘先生’”[1]7的感受不太一樣。除了同樣表達一種對長者的尊敬外,還表達了一種獲得經驗教訓后的感激,因為這里的“我”是在回憶過去,而回憶能加深對過去的認識和理解。
精神父子的關系,表現為一種召喚力量和精神對話的關系。
作為學生的“我”一開始對作為“先生”的似曾相識,也就是一種所謂的“既視感”。“我”對“先生”充滿好奇和無數次的“預期”,加之“先生”對“我”的認真態度進行多次確認之后,“我”成了他告白人生經歷的期望對象。況且他自嘲遭受“天罰”而不能生子,來自外界的且又表現認真的“我”則可成為思想的寄托。當“我”回到故鄉,對于“無知”的父母,“我”還把他與“先生”進行比較,而當收到先生遺書、得知先生恐怕已不在人世時,“我”卻不顧病危的父親而奔赴東京關注“先生”的安危。“先生”對于“我”,從更大程度上來講,具有一種精神層面的召喚力量。畢竟“我以為先生的談話要比學校里的講義有益,先生的思想要比教授的意見值得感謝”[1]32。最終“先生”在幾千萬日本人中特別選擇了“我”作為他的告白對象,這似乎也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安排。
朋友K自殺之后,“先生”是孤獨和懺悔的,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而生活在不安、寂寞和罪孽之中,盡管后來有太太“靜”的陪伴,可是“先生”由于對人的討厭和不信任,他跟太太缺少真正的交流,這常常使他們彼此之間產生誤解。他對太太的愛是一種近乎“神圣”的愛,他不愿讓太太知道他的過去,是為了想盡可能地讓太太對他過去的記憶能純潔地保存下去。另外,“先生”又不愿與社會接觸,更是缺少了能真誠對話的對象。然而,當時作為青年學生的“我”的出現,則讓“先生”看到了希望,“二者展開的是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實踐經驗與渴望得到人生指導的兩代人之間的對話”[2]91。這種對話的形式,后來因為“我”父親的病危,則轉換成了書信這一書面的對話形式。不過,這種對話形式則能更好地把“先生”的精神生活和心路歷程用文字表達出來,對寂寞、懺悔的“先生”來說,也能更好地得到解脫和安慰。
三、“私”與作家的關系及意義
戴維·洛奇在《小說的藝術》里曾說,“小說里的名字決不是無的放矢的,就算它們是再平常不過的名字,它們肯定也有特殊的意義”[3]43。在小說《心》里,作家用敘述者“私”替代了“先生”和“我”具體的名字,使其成為兩者的代名詞。小說文本也隱去了兩者所處詳細地址的名稱,而且也沒有明確那站在現時角度來敘述的“我”的職業身份。誠然,第一人稱的敘述是常用的手法之一,但對于《心》這部小說來講,這一特殊設置應具有特殊的含義。作為“先生”的“私”,不僅代表個人,還代表了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這一類人。作為“我”的“私”,也不僅代表個人,還代表了要改變前一種精神狀態的希望的寄托者。對于“先生”和“我”兩者的關系,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其關系即二人并不只代表‘個人’也寓意著‘時代’”[4]91。這兩者的關系也都最終走向了所指對象的不確定性,即具有了泛指的意義,而且,兩者的關系更蘊含著新舊事物之間的哲學思考。
正如大家所知,明治維新實行全盤西化,而這種西化完全是一種“外化”,并不是一種自然的“內化”。“文明開化”反映在精神層面,最為推崇的就是西方思想體系核心的“個人主義”思想。開化以來,社會對那種“自由、獨立、自我”的“明治精神”極力推崇。在這急劇變化的時代,這種“明治精神”對傳統的重倫理道德和人情的東洋文化構成了巨大沖擊。然而,知識分子對時代的變化往往是比較敏感的,但也常常是無力的。他們一向生活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之中,維新后的自我覺醒,使其逐漸擺脫傳統文化而轉向西洋文化。但這一西方倡導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卻與作家漱石先生倡導的“個人主義”是有區別的。漱石先生提倡的“個人主義”是既要尊重自己,又要尊重別人。在行使“個人主義”時,要避免向“惡”的方向即向“利己主義”方向轉化。從小說《心》中“先生”在寄宿中自朋友K出現后的命運變化歷程來看,它正體現了“個人主義”已經“開始一步步向利己主義轉化”[5]52,其后果是不僅害了朋友K也害了自己。正如“先生”在信中所言,“我們這批人誕生在充滿了‘自由’、‘獨立’、‘自我’的現代,恐怕誰都要成為它的犧牲,不得不嘗嘗這種寂寞的味道吧”[1]34。作家也同樣是明治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他正是通過剖析以“先生”為代表的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彷徨與孤獨的精神世界,從而對“明治精神”進行批判。
那么,批判之后的解決之道何在?除了作家提倡的那種既要尊重自己又要尊重他人以外,在小說《心》中也已經有了暗示。作為另一個“私”存在的“我”就是一個希望的寄托。正如前文所述,“我”是“先生”心路歷程的見證者,同時也是他傳授經驗教訓的對象,還是精神召喚和精神對話的應對者。從文本內容可知,“先生”早已把自己當作死了似地在生活,認為“我們受到明治的影響最深,此后生存下去,總歸要落后于時勢”[1]253,既然如此,那么,作家就選擇去“舊我”而換“新我”,用新時代的青年代替舊時代的“木乃伊”似的存在。如果說去舊“私”(“し”)就是選擇“死”(“し”),那么,換新“私”(“し”)就會是選擇新的開“始”(“し”)。兩者的更替,不僅僅是兩個時代的更替,更具有哲學上永恒意義的新舊事物之間的更替。同時,也體現出作家的一種社會期待和人生道路探索的哲學思考。
[1]夏目漱石.心[M].周大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2]鄧傳俊,李素.夏目漱石的《心》中的稱謂藝術[J].名作欣賞,2014,(27):91.
[3]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M].盧麗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4]張博.夏目漱石對明治“時代精神”的反省—兼論《心》的天皇制批判[J].日本研究,2016,(01):91.
[5]常驕陽.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J].外國問題研究,1998,(02):52.
(責任編輯 史素芬)
I106
A
1673-2014(2017)04-0053-03
2017—05—16
李德平(1985— ),男,四川宜賓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廖志翔(1992— ),男,四川資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