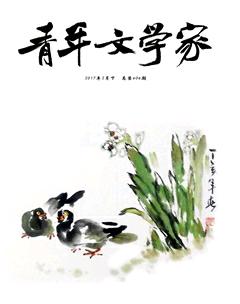蘭姆文學批評思想探究
作者簡介:魏英杰(1991-),女,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6--02
1775年,著名的浪漫主義散文家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1775-1834)誕生于英國倫敦。自幼視書為友,勤奮好學并以讀書為樂。由于生活所迫,蘭姆未能進入高等學府接受教育,只能在工作之余進行文學創作與研究。他以“伊利亞”為筆名完成的兩部作品:《伊利亞隨筆》和《后期隨筆集》集中體現了其在散文方面的卓越才能。然而蘭姆的文學成就并不限于文學創作上,他同時還是一位頗有建樹的文學批評家。蘭姆的這一身份卻往往容易被人忽視,雖然他并未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論,也未曾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批評,但他在應用批評方面的貢獻充分展示了這位文學批評家在文本閱讀與評論中獨到的見解與思想。因而對蘭姆的文學批評思想探究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對我們今后的文學文本的閱讀與分析起到一定的借鑒和啟示作用。因此對蘭姆批評思想的研究應該受到學界的更多關注。
蘭姆的文學批評主要體現在對莎士比亞戲劇的評論上面。他對莎士比亞的戲劇情有獨鐘。蘭姆曾在名篇《古瓷器》中回憶道,他從前生活十分清貧,但每個季度也要擠出幾先令去看上三、四場莎士比亞戲劇演出。雖然那時他無錢購買池座正廳的票,而只能坐在一先令一張票的樓座中看戲。對于蘭姆而言,只要有個位子能看戲,其他什么都無法阻擋其對莎劇的熱愛。他寫道:“幕一拉開,思想一下子就被阿爾登森林中的洛薩琳、伊利里亞宮中的維奧拉吸引進去了,誰還顧得去想自己在戲院里坐在什么位子上?以及,坐在什么地方究竟意義如何?”[1]由此蘭姆對莎翁戲劇的喜愛程度可見一斑。1808年,蘭姆和姐姐瑪利·蘭姆共同合作,完成了《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對莎翁的20部戲劇進行了改寫。姐弟倆創作這本書的初衷是為了將莎劇改編成孩童皆可欣賞的通俗讀物,后來大獲成功,頗受各個年齡層讀者的青睞,在英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現如今此書已成為研究莎翁戲劇必讀的一本入門書籍。
《論莎士比亞的悲劇》是蘭姆筆下非常杰出的一篇較長的莎評文章,它亦屬莎翁戲劇評論中一篇頗有價值的參考文獻。在蘭姆看來,莎劇中的人物本身有別于其他戲劇中的人物,但是觀眾從演員對莎劇表演中獲得的快樂與其他戲劇家筆下的人物相比并無二致。蘭姆并非是在貶低演員的技能,因為舞臺上的演員語音、語調、表情、著裝、演講、表演技巧等方面再怎么完美,也無法將戲劇人物的真實面目展現在觀眾面前。更何況是莎翁這樣天才級的作家,他的人物獨一無二,各具特色,演員是無法真正模仿出像哈姆雷特、奧賽羅這樣的偉大心靈的。因此,觀眾很難通過觀看戲劇表演來感受作家百態式的人物,因此莎劇不適宜在舞臺上表演。觀看戲劇表演與閱讀戲劇文本之間往往存在很大差異,人們唯獨通過閱讀劇本才能更加真實、更為接近作者期望地感受到每個劇中人物區別于其他人物的獨特性以及莎翁的偉大所在。蘭姆認為莎劇不適合舞臺表演而更適合閱讀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發現當時戲劇的“場景藝術著重表露激情,表演者的激情展現的越粗俗,越易被人覺察,則越能吸引觀眾的眼球”[2],這種不良的劇風不利于人們對莎劇藝術性的欣賞與探索。
《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戲劇家評選》是蘭姆對伊麗莎白時期一些戲劇家的作品進行匯編的一本選集,開啟了對莎翁之外的古典英語戲劇研究的復興之門。蘭姆除了選取當時人們耳熟能詳的像克里斯托弗·馬洛和喬治·皮爾這樣的大學才子的作品之外,還將人們不太熟識的劇作家介紹給英國讀者,諸如弗朗西斯· 博蒙、約翰·弗萊徹和托馬斯·海伍德。在伊麗莎白女王當政時期,道德主義十分盛行。此部作品很好地再現了這一時期的道德風貌。但是那種極端的道德主義令蘭姆非常反感,在書中有所體現:“枯燥的道德說教使舞臺不被允許出現帶有滿是美妙激情的場景。極度拘謹、愚蠢地對待情感”。[3]此選集的一大特色就是蘭姆將自己對戲劇的批評思想寫入其中。從個人的閱讀感受和主觀印象出發,從不以權威自居,通過對文本的分析評論,細心挖掘戲劇中蘊含的真與美,進而使作品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被郁達夫稱為“中國的伊利亞”的著名散文大師梁遇春曾這樣評價蘭姆在該選集中所做的批評論述:“吉光片羽,字字珠璣,雖然只有幾十頁,是一本重要文獻”[4]。
蘭姆的許多批評思想還散見在他的散文隨筆及與親友之間的往來信件中,漫評他看過的書,讀過的詩歌和戲劇。蘭姆的批評思想往往是針對某一篇隨筆和書信的特定內容有感而發,通過聯想把談論的話題內容在頭腦中進行加工,并逐步形成自己對文學文本的獨特個人感受與印象式批評,再現作品的深遠意境。蘭姆的批評雖屬一家之言,但其中不乏許多他對文學創作方面的真知灼見。
蘭姆的散文隨筆是英國浪漫主義的產物,擺脫理性主義束縛,彰顯個性特質。而他的批評思想之泉則流淌在這些頗具個性的散文隨筆之中。“風格即人”這一說法用來形容蘭姆的寫作特點再恰當不過。生活中的蘭姆為人隨和,有時在外人面前略顯羞澀,加之名字中的Lamb有“羊羔”之意,好友柯勒律治總是喜歡戲稱其為“溫和的蘭姆”。在創作上,他開創了屬于自己的蘭式文風:文字淺顯易懂,貼近生活,平和,隨意。蘭姆的風格與其人生閱歷密切相關,為了維持生計,十幾歲就到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工作;因照顧時常犯瘋病的姐姐,一生未娶。家庭的悲劇、凄苦的生活使他的文風略帶憂傷和懷舊之調,但又不乏幽默甚至諷刺之感,有時嘲諷他人,有時也是對自身的一種嘲諷。
蘭姆的文學批評思想與他的創作風格也是互為映照,他認為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應該擁有專屬于自己的獨特風格,避免矯揉造作或一味迎合他人,只有展現自己才是最真實、最適合和最自然的表現手法。他的這種觀點在《故伊利亞君行述》中有所記載,“一個作家,與其硬要裝出一種和自己格格不入的所謂自然風格,還不如在自己所喜愛的古色古香情調中保持一點兒自然的風味”[5]。這種對個人自然風格的追求與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的觀點不謀而合,“如果詩不像葉子長在樹上那樣自然地來,最好就不要來了”。[6]浪漫主義作家強調情感的彰顯,在作品中高舉“我手寫我心”的旗幟。蘭姆極為贊同這一主張,“在人物熱情洋溢的臺詞掩蓋之下”,作家“往往不受責難地吐露出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含蓄地說出自己的經歷”[7]。
再如,在一篇題為《關于京城內乞丐減少一事之我見》的隨筆中,蘭姆就乞丐這一形象引申到去談論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技巧上來,“當詩人和傳奇作家們要把命運的錯訛非常尖銳、非常動人地描寫出來,他們若不把主人公一直寫到破衣爛衫、提囊要飯就決不罷休。”[8]只有將主人公進行乞丐式塑造,才能達到作家揭示人物落魄到極致的境地。例如克麗西達失去王子之愛后,隨即也就失去美貌,變成了一個可憐的乞丐的形象塑造就恰恰符合蘭姆的“淪落就要跌落到谷底”的觀點。讀者不難發現,在莎劇中,也有很多人物最終都被刻畫成了悲涼命運的絕望承受者,處境似乞丐一般。如在《李爾王》中,暴風驟雨之夜,李爾王被趕出宮后,暫駐于荒原時孤寂悲慘的凄苦老人形象;在《威尼斯商人》中,敗訴后的夏洛克被定有謀害威尼斯市民的罪名,因而也喪失了全部財產的所有權,劇中其他人物歡歡喜喜,唯獨這位可憐的猶太人卻好像乞丐一般一無所有。在蘭姆看來,遭受厄運的人物如若不像前面所述的手法進行塑造,而是把他們寫的上不上,下不下,反倒會使讀者、觀眾心生厭惡之感,影響對戲劇的喜愛程度。此番論述雖看似有些極端或片面,會有人持反對意見,但讀者很容易被他精彩的散文論述風格深深折服,無暇顧及反對他的觀點。若深思熟慮過后,讀者會發現他的這一評論并非理不勝辭。因此針對蘭姆的這一乞丐形象塑造的評論,也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蘭姆除了在散文方面的高深造詣之外,同時還是英國文學史中屈指可數的優秀書信作家之一。他的書信以散文的風格寫作而成,對個人家庭、社會百態和時代風貌等內容均有涉及,其中許多信件是他與志同道合的友人之間珍貴友情的呈現。這些信件中還不乏大量蘭姆對當時一些重要文學作品的精彩品評。在1801年寫給華茲華斯的一封信中,蘭姆指出《抒情歌謠集》中,“《古舟子詠》、《瘋狂的母親》和《廷騰寺》是首屈一指的,詩集中其他任何一首都不如它們有力”[9]。他指出《古舟子詠》在進行著這樣一種嘗試:“壓制和埋葬一個人所有的個性和記憶——就像是人在做噩夢的時候一樣,此時最可怕的特點就是一個人的意識都失去了。”蘭姆還對詩集中的其他詩歌進行了點評,甚至詩歌中某個字詞的使用是否得當都進行了反復推敲。例如,他認為《詩人的墓志銘》一詩“被開頭對牧師和律師的諷刺和第六節中那個粗暴的形容詞‘精心的給弄壞了”[10],談及到該詩的其他部分時,蘭姆給予充分肯定,認為都非常精彩,并恰好符合華茲華斯本人的風格。他對作品的評論可謂做到了客觀公正。
蘭姆反對詩歌作品中出現過于直接的說教成分,因為在讀者還未來得及注意到會有什么內容出現時,那些說教成分就會有意無意地被讀者吸收,從而干擾讀者閱讀。蘭姆指的說教成分也就是后來被稱為元小說的一種敘事策略。廣義上來講,元小說敘事策略就是指作家在進行寫作的過程中將自己的創作過程注入小說文本,并會時常告誡讀者應該如何讀,怎么讀。《坎伯蘭乞討人》這首詩的瑕疵便是說教過于直接,讀者閱讀就好像在聽一場演講一般。“一個有頭腦的讀者在被告知‘我要教你怎樣去理解這首詩的主題的時候,會感到這是一種侮辱”[11],蘭姆發現上述問題也同樣存在于斯特恩和許多其他小說家以及現代詩人們的作品中,“他們總是在其作品中標上記號表明到哪兒就該如何感受了。他們總是假設他們的讀者都是傻瓜——這和《魯賓遜漂流記》、《韋克菲爾德的威卡》、《羅德利克·蘭德姆》及其他優美、純粹的敘事作品甚為迥異。”[12]
縱觀蘭姆的文學批評思想,蘭式批評可用“印象式批評”(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進行高度概括。他所使用的批評方法不如好友柯勒律治等批評大家那樣具有邏輯性和哲理性,評論皆是自身情感的坦誠表露,隨筆式的風格,無拘無束,屬于蘭式的一家之言。然而,蘭姆的批評其價值所在則恰恰得益于作者獨特的個人閱讀、審美品位與個性的有機結合。因此,蘭式批評是一種充分展現個人特質的純粹式文學批評,這種在批評中融入評論家個人內心真實情感的做法也是英國浪漫主義者們所高贊的“情感自然流露”理念的一個集大成之體現。蘭姆雖然只能算是一個業余的文學創作者和批評家,無法與柯勒律治、華茲華斯、哈茲利特等人并駕齊驅,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頗具個性特質的蘭式創作以及文學批評思想為英國浪漫主義文學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1]查爾斯·蘭姆,《伊利亞隨筆選》,劉炳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295頁。
[2] Lamb, Charles. The Works of Charles Lamb. Vol. 4, Boston: William Veazie, 1864. p. 82.
[3] Roy Park, ed., Lamb as Critic.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22.
[4]梁遇春,《春醪集,淚與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52頁。
[5]查爾斯·蘭姆,《伊利亞隨筆選》,劉炳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201頁。
[6]Keats, John.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7.
[7]查爾斯·蘭姆,《伊利亞隨筆選》,劉炳善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202頁。
[8]Ibid., p. 172.
[9]查理·蘭姆,《蘭姆書信精粹》,譚少茹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5頁。
[10]Ibid., pp. 201-203.
[11]Ibid., p. 203.
[12]Ibid., p. 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