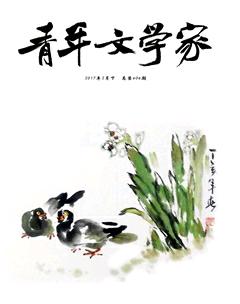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回顧
吳小夏
摘 要:譯者風格是近年來語料庫翻譯學研究的新方向和趨勢。本文對近年來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進行回顧,重點關注國內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模式,希望對為今后相關的研究提供啟示。
關鍵詞:語料庫翻譯學;譯者風格;研究回顧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6--03
1.相關概念
1.1 語料庫翻譯學
“語料庫翻譯研究是運用語料庫的技術和統計方法,在考察了大量的翻譯事實或翻譯現象的基礎之上,系統分析和解釋翻譯現象和翻譯過程,揭示翻譯本質的研究”(胡開寶、毛鵬飛,2012)。
Mona Baker(1993)認為語料庫的將給翻譯研究帶來新的研究思路,也給翻譯理論家觀察翻譯現象與翻譯行為提供獨特的機會。在語料庫方法尚未運用于翻譯研究前,研究者只能局限于對小范圍的譯文進行觀察,舉例說理,多屬于定性研究。
Baker(1996)明確提出“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y)”這一概念。
1.2譯者風格
譯者風格是“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語言和非語言的個性特征”(Baker 2000:245),是指譯者在語言應用方面所表現出的典型特征以及包括作為翻譯對象的文本選擇、翻譯策略和方法的選用、前言、后記和譯注等在內的非語言特征。
在傳統的觀念看來,翻譯是創造性活動的衍生活動。譯者被認為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的風格。譯者的任務就是盡可能以目標語重現原作。Baker(2000)認為“就如同握住一個物體不可能不留下指紋,我們也不可能說出或寫出一段文字而不帶有個人風格。譯者風格或許包括譯者選擇何種類型的材料進行翻譯,譯者一直慣用的特定翻譯策略”。對譯者風格的研究必須抓住譯者語言使用的特點,確定譯者語言使用的模式,使其與其他譯者區別開來。
Venuti(1995)提出了“譯者聲音”(translators voice)的概念,認為譯者在譯本中“無處不在”。
Hermans(1996)認為,當我們閱讀翻譯的敘事文章時,不僅能感覺到源文的作者的聲音,也能辨別出譯者的聲音,譯者的聲音存在于譯文的字里行間。“譯者聲音”反映了研究者開始關注譯者存在于譯本中的“第二種聲音”(second voice),即譯者的風格。譯者風格的顯露表現在譯者對譯本的公開干預,包括譯者在翻譯準文本層面的一系列表達。
2.Mona Baker的研究
最早提出運用語料庫方法研究譯者風格的是Mona Baker。
Baker(2000)從類符/形符比,平均句長,英文中最常見的報道性動詞SAY(say,says,said)等幾方面切入,運用Wordsmith檢索翻譯英語語料庫(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研究兩位英國翻譯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譯風格。數據統計分析表明,Clark的譯文形符/類符比 Bush的譯文低,Clark的譯文豐富程度不及Bush;Clark的譯文的平均句長也比Bush的短。Clark的譯文中報道性動詞出現頻率很高,尤其是過去式said,Clark比較偏好使用過去時態,即使有時源語文本是現在時態。
Bush喜歡用says,能將讀者拉近作者的世界,讓讀者覺得如同親身經歷了書里的事件。Clark喜歡用直接引語而Bush喜歡用間接引語。Baker討論了兩位譯者的風格存在差異由于各自的翻譯策略,目的以及源語文本對于目標語讀者來說難易度不一樣。
3.國內研究回顧
筆者以“語料庫”和“譯者風格”或“譯者文體”為主題詞檢索中國知網期刊全文數據庫(2010年至2016年),共檢索到48篇文章,其中有9篇是研究英翻漢之漢語譯本的譯者風格,其余39篇是都是研究漢翻英之英文譯本的譯者風格。本文主要關注的是英譯本的譯者風格的文章。下表1.歸納了39篇漢翻英譯者風格文章的語料選取。
從上表1.可以看到,比較多的學者在研究譯者風格的語料選取上傾向于小說,其次是散文。在小說中又以經典小說《紅樓夢》為最多,而散文中選擇儒家經典《論語》為語料的最多。原因是《紅樓夢》與《論語》都是中國經典文學的代表,其譯者和譯本最為豐富,較易取材,也比較有研究價值。
此外,從2010年到2016年發表在國內14種外語類核心期刊上以語料庫方法研究譯者風格的文章有21篇。有2篇是評介,其余19篇都是都對具體的譯本運用語料庫進行譯者風格的實證研究。文章發表的年份分布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可以看出,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總體呈上升的趨勢。2014年發表的文章篇數是6年中最多的,為5篇。而2015年與2016年文章篇數都只有3篇。筆者認為以下兩個原因造成文章數量沒有持續增長:一是大規模的雙語平行語料庫創建需要較長的時間,因而研究周期比較長;二是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頸,多是圍繞譯本的類符/形符、詞匯密度、詞長、句長、敘事結構等幾個方面進行數據統計。
國內學者們運用語料庫方法研究譯者風格,最早的對象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眾多英譯本。劉澤權、閆繼苗(2010)從報道動詞“道”,即原文中的“某人道”等的翻譯切入,對《紅樓夢》的三個英譯本,分別是喬利的譯本、霍克斯和閔福德的譯本和楊憲譯、戴乃迭夫婦的譯本進行譯者風格調查。研究發現,霍譯對“道的翻譯”多使用said,比較單一;楊譯多省略;喬譯則使用了多種詞匯對“道”進行翻譯。三位譯者在句式使用方面也不盡相同,彰顯了各自的翻譯風格。
另外,劉澤權、劉超明、朱虹(2011)運用語料庫檢索工具WordSmith,從詞匯密度、詞長、平均句長等數據統計中考察《紅樓夢》的四個譯本之間的譯者風格差異。這四個譯本分別為喬利,傳教士邦斯爾,霍克斯和閔德福,楊憲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譯本。研究發現,楊譯的詞匯密度最大,邦譯的詞匯密度最小,并且,楊譯的詞匯長度明顯高于其他三個譯本,故認為楊的譯本閱讀難度是最達的。在句長方面,楊譯和邦譯的平均句長較短,比較忠實地反映源語漢語作為意合語言的特點。
美國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文譯者。莫言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其作品的英譯多是由葛浩文完成。莫言作品能為西方國家所認可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葛氏的翻譯。因此,在莫言獲獎之后,有一些學者就開始著手研究葛浩文的譯者風格。
黃立波,朱志瑜(2012)從標準類符/形符比、平均句長、敘事結構使用的轉述動詞SAY切入,研究葛文浩的譯者風格。與劉澤權等人做法不同的是,黃立波,朱志瑜(2012)并不是比較同一作品的不同英譯本。其語料庫組成是來自葛氏獨譯的17部譯著與戴乃迭翻譯的10部譯著,從而比較兩位的譯者風格。黃立波等(2012)認為單純統計譯本的某些參數,并不能很有效地區分不同譯者的風格;提出學界在識別譯者風格的方法上還有待創新,識別譯者風格的標準也需統一,考察譯者風格時需要將源文本的特點考慮進去。
趙穎(2015)對中國古代典籍《道德經》的吳經熊和阿瑟·韋利所譯的兩個譯本進行比較分析,考察二者的譯者風格。在語篇層面,從敘述人稱“you”與“he”入手,發現韋氏使用第三人稱“he”的次數遠高于吳氏,而韋氏使用第二人稱“you”的次數卻明顯少于吳氏。趙穎(2015)認為韋氏的譯文與讀者有距離感,而吳氏的譯文則營造了與讀者平等對話的氛圍。
通過梳理近幾年國內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相關文章,學界主要運用的研究模式有單語類比與雙語平行對比的研究模式,如下表所示:
如表2.所示,單語類比語料庫研究模式就是對不同譯者的翻譯文本進行比較,并運用參考語料庫,討論不同譯本的翻譯顯化程度的差異。這種研究模式沒有將源語文本的風格考慮在內,源語文本的風格會影響譯文的風格,表現的差異并不能算是譯者的風格,故此研究模式在區分譯者風格方面的說服力不強。雙語平行對比模式是將源語文本與目標語文本一起組成雙語平行語料庫,在區別譯者風格方面能剔除源語文本的影響。這種研究模式是目前最常用的,也比較有說服力。
而在分析模式方面,現行的語料庫方法考察譯者風格的研究主要從詞匯、句子、語篇層面切入,進行數據統計和翻譯策略差異的探討。詞匯層面可以利用參照語料庫,考察目標語文本,即譯本的主題詞表,比較不同譯本的主題詞表差異。常用的詞匯層面考察方法還有統計不同譯本標準形符/類符比(即詞匯密度)、詞長、詞性、文化特有詞、情態動詞等。句子層面的分析常常統計譯本的句子數目,平均句長,句子類型。語篇層面的分析則從多從敘事方式和話語方式著手。
4.結束語
語料庫作為研究語言現象的方法,亦可研究翻譯現象,隨著語料庫翻譯學的不斷進步和改善,通過語料庫對譯本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解釋,譯者風格的研究從純粹的定性舉例研究發展為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譯者風格研究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有利于研究者發現以往沒發現的翻譯事實。然而,運用語料庫方法研究譯者風格的理論框架還有待進一步豐富,譯者風格的標準還有待統一的界定。譯本語料的選取上沒有統一的規范,有些研究的譯本語料庫選取比較隨意。此外,學界多限于對語料庫的數據統計,描寫和歸納不同譯者風格,但較少討論造成不同譯者風格背后的社會、時代背景等因素。
參考文獻:
[1]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A].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233-250.
[2] Baker, M.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A]. In H. Somers(ed). Tech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175-186.
[3]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2000(12/2):241-266.
[4 ] Hermans. T.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J]. Target,8,1,1996a.
[5]Venuti,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6]黃立波、朱志瑜,譯者風格的語料庫考察——以葛文浩英譯現當代中國小說為例[J].外語研究,2012(05):64-71.
[7]劉澤權、劉超朋、朱虹,《紅樓夢》四個英譯本的譯者風格初探[J].中國翻譯,2011(01):60-64.
[8]劉澤權、閆繼苗,基于語料庫的譯者風格與翻譯策略研究——以《紅樓夢》中報道動詞及英譯為例[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10(04):87-92.
[9]趙穎,基于語料庫的《道德經》兩譯本的翻譯風格研究[J].中國翻譯,2015(4):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