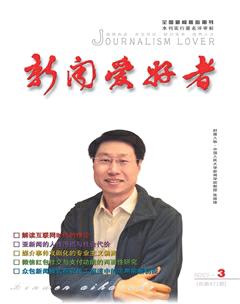晉察冀詩歌的大眾傳播學意義探析
叢鑫 閆文君
【摘要】晉察冀詩歌作為抗戰宣傳形式之一,很好地發揮了社會協調與聯系、環境監視、社會遺產傳承、提供娛樂等社會傳播功能;貼切地運用了針對受眾心理的“自己人效應”,推動了抗日宣傳的全民性認同;巧妙地運用了訴諸感情的宣傳技巧,鼓舞了我方軍民士氣,瓦解了敵軍斗志。對晉察冀詩歌從傳播學層面進行打量,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其思想與藝術價值。
【關鍵詞】晉察冀詩歌;抗戰宣傳;社會傳播功能;自己人效應;訴諸感情
新中國成立后,自《晉察冀詩抄》(魏巍編,1958)出版以降,晉察冀詩歌又一次引起了文藝界及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成為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視點。在晉察冀詩歌的文學史意義得以確立的同時,其傳播學意義卻鮮有人論及。事實上,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晉察冀詩歌從創作之初,就注定了其政治性遠大于藝術性。當然,如果從文學的角度來分析,這些詩歌中同樣有修辭、有想象,有與現實結合的革命浪漫主義,很多詩歌都具備較高的藝術水準,是中國新詩史上的一座豐碑。但不可否認,這些詩歌的內容、形式及創作手法全都以達到宣傳效果為旨歸,而且值得時人歡呼與后人銘記的是,這些頗具藝術感的詩歌在戰時比武器更鋒利,起到了教育團結人民群眾與動搖感化敵人的極佳宣傳效果,對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起到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因而,對晉察冀詩歌傳播學意義的考量,既是我們對其文學史意義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晉察冀詩歌的社會傳播功能
概而言之,大眾傳播主要有5種社會功能:環境監視功能、社會聯系與協調功能、社會遺產傳承功能、經濟功能、娛樂功能。除經濟功能外,傳播的其他4種社會功能在晉察冀詩歌中都有體現,其中尤以社會聯系與協調功能表現得最為突出。
傳播的社會聯系與協調功能是指大眾傳播能“形成全社會范圍內基本一致的意見、態度和看法,用以調節社會內部的矛盾沖突,使其逐步趨于緩和乃至消除,實現社會協調”。[1]
1937年年底晉察冀軍區初成立之時,僅有黨政干部及士兵共3000余人,若僅靠自身力量難以存身,與社會各界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必然選擇。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但未經組織的群眾卻如一盤散沙,因而統一群眾思想使其共同抗日就成了當時最迫切的任務。傳播學先驅拉斯韋爾在《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中曾論及,平民的思想是經過新聞報道,而不是軍事訓練,才被統一起來的。[2]在新聞傳媒資訊極為匱乏的晉察冀邊區,以詩歌、戲劇為代表的抗戰文藝工作在統一群眾思想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自1938年末始,以田間、魏巍、邵子南、陳輝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詩人陸續來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他們創辦了《詩建設》《詩戰線》等詩刊,成立了“戰地社”“鐵流社”等詩社,形成了中國新詩史上一個獨立的流派——“晉察冀詩派”。詩人們以滿腔的熱情開展街頭詩、傳單詩、詩朗誦等群眾性詩歌運動,將全部的村莊與全部的墻頭作為宣傳陣地,來響應黨中央倡導的“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革命文藝工作宗旨。
詩歌中有對黨和邊區民主政權的熱情謳歌,多為對民主政府管轄下的邊區新人、新事、新景象的描述,讀來既形象又寫實。曼晴的《我們選舉得很好》借老鄉之口,生動地講述了邊區民主制度在基層開花結果的落實情況。“女的,/……/是婦女自衛隊的指導員,/比男人更能干,/站崗、放哨、抬擔架,/沒有落后過,/今年又親自送自己的丈夫,/參加了青年營。”詩歌不僅抒發了邊區人民積極擁軍抗日的熱情,還通過事實依據寫出了男女平等思想在邊區的深入人心。婦女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中歷來起著巨大的作用。馬克思曾說“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變革”,[3]毛澤東也曾于1940年指出“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則不能進行”。[4]所以,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必須發動婦女參與生產斗爭。但是,中國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等封建思想可謂根深蒂固,農村婦女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更是普遍缺乏獨立的主體意識,因而婦女解放是很艱巨的一項工作。基于此,晉察冀詩歌在婦女思想解放方面是頗為注重的。比如孫犁的《梨花灣的故事》寫王蘭不懼丈夫的權威與鄰里的風言風語,照顧抗日英雄幼年失恃的孩子;于六洲的《劉桂英是一朵大紅花》敘述劉桂英掙脫婆婆所象征的封建思想的束縛,投身于集體活動的轉變過程。這些詩作是對新人新風的頌揚,也是為抗日工作進一步爭取婦女支持所作的宣傳與勸服。
通過晉察冀邊區軍政人員的努力,邊區百姓很快就普遍接受了抗日宣傳,與八路軍同心同德共御外敵。史輪的《歌謠》則從兒童的視角入手:“哥哥打仗整一年,/我也參加兒童團,/東鄰幫咱種谷子,/西鄰幫咱澆菜園。”詩歌中對軍民魚水情深的描述取材于生活,真切地再現了邊區軍民互幫互助的情景,刻畫出二者親如一家的感情。
因原型眾多且都是詩人身邊活生生的人,晉察冀詩歌對群眾模范與民兵英雄的頌揚更是隨處可見。邵子南的《模范婦女自衛隊》《好樣兒》《李勇要變成千百萬》等詩從不同角度歌頌了在抗日戰爭的大潮中涌現出的平民英雄。其中以當時的爆破能手、民兵英雄李勇為原型的《李勇要變成千百萬》被改編成歌曲《李勇對口唱》《爆破英雄李勇》等,這些歌曲在當時的民兵訓練中成了鼓舞士氣的精神食糧,在老百姓中也被廣為傳唱,真正做到了婦孺皆知。[5]
街頭詩運動的感召力是巨大的,晉察冀邊區的人民群眾不僅閱讀、傳唱這些詩歌,有些甚至還嘗試著自己創作。比如《晉察冀詩抄》共180首詩歌中收錄的民謠就多達45首。美國傳播學者格伯納曾就大眾傳媒的社會影響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論,即長期接觸一致的傳播內容會導致大眾的意見趨同,可以起到社會整合的作用。經各種形式的抗日文化宣傳,晉察冀邊區人民群眾的思想很快就被統一起來。到1944年年底,全區總兵力已由邊區成立初期的3000余人增加到9萬余人,民兵增加到63萬余人,而當時全區總人口170多萬。[6]晉察冀邊區軍民抗戰的光輝歷史已永載史冊,根據現有史料我們無法定量地去統計晉察冀詩歌的凝聚力。但眾所周知,大眾傳播的影響力與其普及程度呈正相關性,故毫無疑問,晉察冀詩歌在鼓舞人民進行對敵斗爭中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綜上所述,晉察冀詩歌在團結群眾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社會聯系與協調功能。不過,其傳播學意義還不僅于此:在強敵環伺而傳媒資訊又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無處不在的街頭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環境監視與提供娛樂的作用,很好地緩解了大家惶惶不安的群體心理。昨天的詩歌就是今天的歷史,當年波瀾壯闊的晉察冀邊區的斗爭及民俗風情畫卷之所以呈現在后人眼前,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晉察冀詩歌的社會遺產傳承功能。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成長起來的“晉察冀詩歌”,以深情的筆觸記錄下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根據地的戰爭場景和軍民生活及其精神意志,在硝煙彌漫的陣地上寫下了戰斗和犧牲、民族大義和個體價值、死亡恐怖和人性關注。
二、晉察冀詩歌與自己人認同
在大眾傳播學中有一種對于受眾心理描述的“自己人效應”,意即在傳播活動中,如果受眾覺得傳播者與自己在立場、背景或個性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就會將其視為“自己人”,從而更易接受并認同其所傳遞的信息與觀點。因此,要想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就要求傳播者具備與受眾的“同體觀”。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競選演說就充分利用了“自己人效應”,載他演說的農用馬車及他演說中的平民立場,使他打動了選民,順利當選總統。
對于傳統的中國來說,“自己人認同”對于傳播的有效進行更為重要。大眾傳播所要達到的效果可簡要概括為“認同”,即受眾認可接收到的信息,贊同信息中所包含的觀點。但是,影響認同的因素很多,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傳受雙方是否有相同之處。這一點從認同(identification)一詞的詞源“idem”(拉丁文,相同的事物)來看就很明了。對于華人而言,最為突出、最為直接的認同動機就是關系基礎(包括血緣、地緣、業緣等)。[7]費孝通在其“鄉土社會”研究中曾論述道,中國社會從基礎上來說是鄉土性的,“自己人/外人”是人際關系的基本信任結構。對于鄉土中國構成的基礎農村來說,由于村落的相對封閉性,這種“自己人/外人”的傳統人際關系更為典型。
晉察冀詩人深諳這一中國國情與受眾心理,致力于在詩歌中拉近和人民群眾的心理距離。自己人認同的兩個重要依據是“身份”和“立場”。身份往往是客觀的,包括出身背景、生存環境和社會地位等;立場則指向主觀層面的態度與觀點。晉察冀詩歌中最常見的一個主語就是“我們”,這充分表明了詩人之于邊區民眾的自己人姿態。如“我們農村的小鬼”“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等詩句,表明了詩人與群眾在出身背景與生存處境上的一致;“我們有了真的友愛了,還有組織了”“我們選舉得很好”則表明詩人與群眾在抗日斗爭和基層民主生活立場上的一致。詩人自覺站在群眾的隊列之中,邊區群眾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心理上將詩人們所代表的八路軍定位為自己人,進而接受其詩中的抗日宣傳理念。
詩人們所做的努力還不止于此,為進一步強化自己人效應,他們還深入老百姓生活,與他們一鍋吃飯,同炕休息,熟悉他們的生活與文化背景,學習他們的語言。這是從地緣性層面加深受眾的自己人認同。地緣性正是我們除血緣關系之外判斷自己人身份的最基本要素。費孝通認為,中國鄉土社會是富于地方性的,[8]中國的社會關系是從血緣結合發展到地緣結合的,地緣關系正是血緣關系的投影。[9]晉察冀詩歌呈現出與晉察冀邊區極為緊密的地緣性關系。
詩人用一支支飽蘸深情的健筆描述了晉察冀壯美的山河景色、淳樸的風土民情,傾訴了對晉察冀的熱愛、對戰爭的憎惡,以及對和平的向往。陳輝的《平原手記》中,有唐河畔空余蘆葦與麥苗的靜寂的村莊、太行山的月夜、六月的麥田、三月的杏花與微風,寫滿了對晉察冀平原風物的感情;孫犁筆下的梨花灣,陳隴筆下的神仙山,雷燁筆下的灤河曲……對晉察冀邊區民眾來說,生于斯、長于斯的那片熱土是他們最熟悉的事物,從時間軸而言承載著世代相傳的文化記憶,從空間軸而言是他們日常賴以生存的家園,這些都是激發自己人認同意識生成的地標。因為這種認同,他們加入了抗戰隊伍,把這種對土地的執著升華為對祖國的守護,“親愛的土地”既是參加抗戰的情感基礎,也在家國情懷上實現了高度的統一。
在語言方面,晉察冀詩人不僅能根據當地百姓的文化水平使詩歌做到通俗易懂,而且還力求用鄉音表達鄉情。出生于晉察冀地區的曼晴和孫犁等詩人對方言土語的運用可謂得心應手,“朝山”(朝拜山上的寺廟)、“大集”(農村的集市)、“大秧歌”(地方戲曲)、“嘎咕”(壞)等詞為詩歌涂抹上了濃郁的地域色彩,如同出自百姓之口一般。語言維系著另一種重要的地緣性認同。人類對于本國、本族群、本地域的語言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認同本能,這種認同滲入我們的血液,成為終身不滅的最顯著的地緣標識。
格伯納在對其著名的傳播學理論“培養分析”的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共鳴效果”理論,也可以用來加以印證我們要闡述的問題。即如果大眾傳播的內容與個人的經驗、發表的觀點與個人所持觀點相一致或相接近,則培養效果就有顯著擴大的趨勢。晉察冀詩人選用這些淳樸、鮮活的方言土語,使詩真正為人民而歌,貼合了人民群眾的文化背景,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因而也取得了極佳的傳播效果:“我們”有著相同的出身,對新舊社會的對比都一樣感同身受;“我們”操著相同的鄉音,對晉察冀這片熱土都愛得深沉;國難當頭,“我們”同呼吸共命運。
三、晉察冀詩歌中訴諸感情的心理宣傳
戰時宣傳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激起我方軍民的斗志,二是瓦解敵軍的士氣。在這兩個方面,晉察冀邊區都做得較為成功。
(一)以仇恨激起我方斗志
拉斯韋爾對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進行研究后得出結論,戰時對公眾宣傳的目的應為喚起公眾對敵人的仇恨情緒。[10]晉察冀詩歌一直在貫徹這樣的宣傳原則。
詩人們以或憤怒或哀傷的詩句,一行行記錄下日寇對邊區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陳輝的《到柳沱去望望》一詩描繪出遭日寇燒殺后的一個村莊的悲慘景象,并借“小鴿兒”這一意象表達出對和平的向往。喚起公眾仇恨情緒的一條十分便于應用的規律就是暴露暴行。在人類所知的每一場沖突中,這一規律屢試不爽。[11]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引發協約國人民眾怒的卡維爾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英國護士卡維爾因涉嫌幫助協約國士兵逃跑被德軍秘密處決,這件事被英國大肆報道后引發了英國民眾應征入伍的熱潮。而據資料顯示,抗日戰爭時期的晉察冀邊區,可謂全民皆兵,“老大娘拿著針線活,坐在村邊的柳蔭里放哨;小孩子拿著扎槍,仰著臉,睜著機警的眼睛,向你盤查路條”。[12]從未接受過現代文明熏陶的老人孩子做出這樣的行為,顯然出于最樸素的人類情感的激蕩。
(二)以家園情瓦解敵軍斗志
激起我方民眾斗志是內部宣傳的目標,瓦解敵軍斗志則是對敵宣傳的目標。侵略戰爭總是以正義或愛國的名義發起的,對所謂的“正義之師”要攻其謊言與荒謬之處,而對志在為本國開疆拓土的“愛國之師”則要進行反愛國主義宣傳。日寇對華侵略顯然屬于后一種。
在士氣高昂的戰爭初期,反愛國主義宣傳是不易奏效的,但“一旦戰爭變得讓人疲憊不堪,和平時期的意識形態抬頭,反愛國主義的宣傳就有機會得逞”。[13]所以,在抗戰開始一年多時間后,我們的對敵宣傳就收到了明顯效果。1939年2月,在日軍榆次師團司令部會議上,一些日軍高級將領承認:“因為華軍的反戰宣傳,總覺得士兵的思想起了動搖和變化,實在難于指揮。”[14]
1939年的前兩個月中,晉察冀邊區就書寫標語21370條,散發傳單7.9萬份。“凡是接近敵人的房屋、樹林、廁所、室內外,差不多已布滿并相當帶藝術化”。[15]標語與傳單的藝術化,只能以詩歌或圖文并茂的形式呈現。因此晉察冀詩歌在這場瓦解敵軍的心理戰中充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陳輝的《一個日本兵》是其中最著名的詩篇。這首詩歌寫于1942年2月12日夜,應該源于詩人的戰斗體驗。詩歌寫一個“被正義的槍彈”射穿了“年輕的胸膛”死在晉察冀土地上的一名日本士兵,眼角“凝著紫色的血液,/凝結著淚水,/凝結著悲傷”,被兩名中國農民“埋在北中國的山崗上”,詩歌中沒有激烈的家國情感,沒有你死我活的緊張對立,而是充滿了對生命的凝視:冰冷的年輕生命無力地捂住生命的傷口,客死他鄉的日本兵眼角“紫色的血液”“淚水”“悲傷”構建的情感溫度讓個體生命從宏大的民族國家敘述中游離出來,被埋葬在異國山崗上的冰冷和孤獨體驗取代了戰爭的喧囂,所幸中國寬厚的黃土讓日本士兵找到了自己農民式的歸宿,完成了生命的儀式。詩歌在這里實現了對戰爭中士兵生命價值的、身份的置換,從個體生命的體認切入戰爭中的死亡,緊接著用“寂寞的夜晚”“遼遠的故鄉”“有一位年老的夫人/垂著稀疏的白發,/在懷念著她這個/遠方戰野上的兒郎”,進一步從母親對兒子的牽掛、思念的情感角度加深了這首詩的人道主義關懷,讓生命的溫度和情感的濃度超越了戰爭,達到了某種人性的深度和寬度。
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看到這樣的詩句,遠離家鄉與親人的日本士兵興起家國之思實乃人之常情。比如有日本士兵寫道:“你也有父母在等待著你歸來/你也有妻子在祈求你安然無恙//為了散華而去的戰友/我流下眼淚/我要把那一滴淚水分享給你。”詩中對親情的描述與前述晉察冀詩歌一般無二。甚至有日本士兵寫出這樣的詩句:“你的鮮血將成為一個美麗的傳說/美好的中國肯定會凸顯而出/巨大的中國肯定會涌動而出。/我要把你的血色記憶一直保留到那一天……”當家園情懷一再發酵,所謂“為愛國主義而戰”在日軍心目中便成了一句蒼白的謊言,而且當被日本軍閥所鼓動的盲目的愛國熱情退去,對正義也就有了清醒而深刻的思考。
四、結語
從傳播學角度對晉察冀詩歌進行打量,我們發現晉察冀詩歌作為當時的宣傳形式之一種,很好地發揮了社會協調與聯系、環境監視、社會遺產傳承、提供娛樂等社會傳播功能;貼切地運用了針對受眾心理的“自己人效應”,推動了抗日宣傳的全民性接受;巧妙地運用了訴諸感情的宣傳技巧,鼓舞了我方軍民士氣,瓦解了敵軍斗志。總之,由于形式的短小精悍與傳播媒介的豐富多樣,及在傳播形式上可依環境與對象不同而進行的靈活變通,晉察冀詩歌不愧為當時晉察冀邊區如火如荼的抗日宣傳工作中最活躍的文藝樣式。對晉察冀詩歌從傳播學層面進行打量,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其思想與藝術價值。
(基金項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政治美學視域下的晉察冀詩歌研究”,項目批準號:HB15WX002)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01.
[2]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M].張潔,田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3.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7-398.
[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毛澤東主席論婦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
[5]程峰典,李文錄,劉松峰.抗戰老民兵英雄系列報道之五:令鬼子聞風喪膽的“民兵爆破英雄”[J].中國民兵,2005(9).
[6]周繼強.晉察冀軍區簡史[J].軍事歷史,1995(1).
[7]趙卓嘉.自己人認同:基于西方內群體認同概念的研究[J].社會心理科學,2015(5).
[8]費孝通.鄉村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4.
[9]費孝通.鄉村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72-75.
[10]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M].張潔,田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49.
[11]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M].張潔,田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6.
[12]魏巍.晉察冀詩抄[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9.
[13]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M].張潔,田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41.
[14]吳杰明.攻心奪氣:20世紀世界軍事心理作戰紀實[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3.
[15]吳杰明.攻心奪氣:20世紀世界軍事心理作戰紀實[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2.
(叢鑫為燕山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閆文君為洛陽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新聞學博士)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