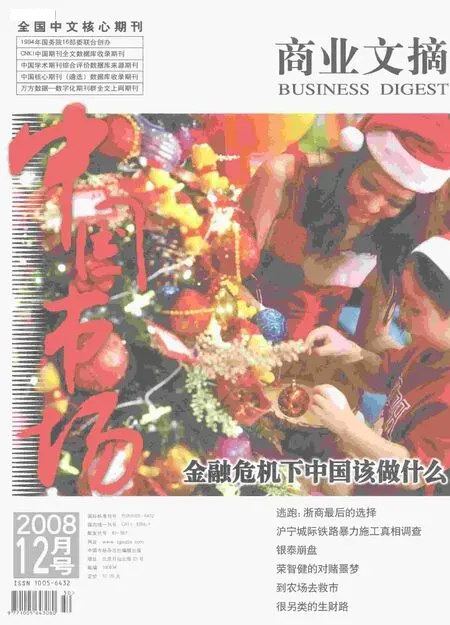我國三次產業結構變動的經濟效應研究

[摘要]文章按三個階段對1978—2014年我國經濟勞動生產率的變動進行了分解,第一、二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產業內部增長效應,即技術進步,而整體經濟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卻主要依靠產業結構轉換效應,即資源配置。整體經濟和三次產業結構轉換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日漸減弱,但這并不表明結構紅利已經消失,各產業間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差別的長期存在,使得我國依然可以通過推進改革來提升生產效率。
[關鍵詞]Shift-Share分析法;產業結構變動;勞動生產率;三次產業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038
1引言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表明我國經濟進入了“結構性減速”階段,即勞動力由生產率較高的第二產業部門轉移到了生產率較低的第三產業部門,從而導致了我國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這是我國現階段面臨的亟須解決的問題。為了有效地解決經濟增速問題,防止我國經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深入分析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判斷我國經濟增長是來自產業結構變遷(即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移動)還是來自產業內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以此確定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進而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更深層次地挖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模型構建
本文利用Shift-Share分析法研究勞動生產率變化中的結構變遷效應,將勞動生產率結構分解為三次產業內在勞動生產率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動兩個部分,即分析各產業自身的內部增長效應以及產業結構變動的動態轉移效應和靜態轉移效應。模型如下:
[SX(]ΔP[]P0[SX)]=[DD(X]i[DD)]([SX(]Pi0ΔSi[]P0[SX)]+[SX(]ΔPiΔSi[]P0[SX)]+[SX(]Si0ΔPi[]P0[SX)])
123
式中等號的左邊表示從基期到T期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等號右邊的第一部分代表產業結構變動中的靜態轉移效應,該效應是衡量當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時,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產業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業轉移對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產生的影響。若該項為正值,則表示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業吸引了更多的勞動力,因而增加了該產業的就業比重,即存在“結構獎賞”;相反,若該項為負值,則表示存在“結構負擔”。第二部分代表產業結構變動中的動態轉移效應,該效應是衡量在就業結構變化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共同作用下,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若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就業比重同時出現上升或下降,則該項值為正;若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業的就業比重下降,或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產業的就業比重上升,那么該項值為負。如果該項值為負,說明勞動力再分配對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構成“結構負擔”。第三部分代表產業內部增長效應,該效應是衡量當不存在結構變動,即各產業的就業比重保持不變的情況時,三次產業自身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對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產生的影響。
3實證分析
根據以往國內外學者所作的研究,產業結構變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可能會對勞動生產率產生不同的影響。為平滑產業結構變動的波動以提高其貢獻率度量的準確性,需要對各經濟階段進行劃分。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個歷史事件對我國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二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1992年、1993—2001年和2002—2014年。三個階段我國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及其分解如下表所示。
總體來看,1978—2014年產業內部增長效應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為6063%,而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則有3937%,其中靜態轉移效應的貢獻率僅為085%,動態轉移效應的貢獻率為3852%,說明整個經濟存在一定的“結構獎賞”。分階段來看,三個階段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均以產業內部增長效應為主,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雖然低于內部增長效應,即整個經濟的“結構獎賞”還比較弱;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上升到了2501%,為三個階段的最高水平,未來我國經濟很可能出現越來越強的“結構獎賞”。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我國產業結構和勞動生產率的狀況,我們對三次產業分別測算其在三個階段中的勞動生產率及分解,結果顯示,第一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無論是從長期還是分階段來看都是負數,僅存在“結構懲罰”,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的不斷轉出進而導致勞動力份額下降;而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主要依靠產業內部制度變革和技術進步。
第二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4268%)長期來看只是略低于產業內部增長效應(5732%),說明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對于第二產業的發展同樣重要。但從各個發展階段來看,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與產業內部增長效應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分別為2690%和7310%、-070%和10070%、3590%和6410%),說明第二產業的發展需要以技術進步為主,輔之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及資源的配置。
第三產業分階段來看,三個階段其結構變動效應對其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先下降后上升(分別為4546%、3322%和3588%),但從長期看,產業內部增長效應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率僅為2960%,遠遠低于結構變動效應(7040%)。說明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是依靠資源配置特別是勞動力的轉移,其技術水平還比較低。
4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一產業而低于第二產業,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低的第一產業轉移至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第二、三產業這一資源配置過程顯著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對于第一產業應通過促進技術進步來保證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不是單純依靠勞動力轉出效應;對于第二產業應摒棄粗放式的生產方式,通過資本積累、技術研發和產業升級等,特別是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對于第三產業,其生產率要低于第二產業且難以提高,因而在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上追求技術效率以降低生產成本,加速技術進步。
參考文獻:
[1]李小平,陳勇勞動力流動、資本轉移和生產率增長——對中國工業“結構紅利假說”的實證檢驗[J].統計研究,2007(7):22-28
[2]干春暉,鄭若谷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演進與生產率增長研究——對中國1978—2007年“結構紅利假說”的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09(2):55-65
[作者簡介]金文翰(1990—),男,安徽人,南京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