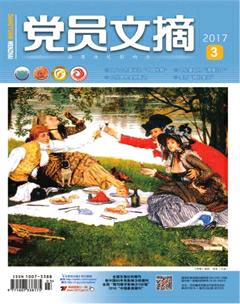別以矯飾的“愁鄉(xiāng)”偷換真誠的鄉(xiāng)愁
田朝暉
近幾年春節(jié),回鄉(xiāng)過年抒發(fā)鄉(xiāng)愁,“返鄉(xiāng)體”盛極一時(shí),成為一種獨(dú)特的文化景觀。這其中,那些真情抒發(fā)鄉(xiāng)愁的文字,被人們默默地分享,而一些故意劍走偏鋒,或戴著有色眼鏡的“愁鄉(xiāng)”式“返鄉(xiāng)體”,卻讓“返鄉(xiāng)話題”本身就成了話題。
村莊凋敝,民風(fēng)頹廢,道德淪喪,孝心缺失……數(shù)說故鄉(xiāng)淪陷的“返鄉(xiāng)體”連續(xù)幾年呈刷屏之勢,讀來觸目驚心。這些大部分被證偽甚至被發(fā)現(xiàn)帶有商業(yè)營銷目的的“愁鄉(xiāng)”文字,快速傳播,迅猛發(fā)酵,成為一種帶有“異味”的文化現(xiàn)象。
“愁鄉(xiāng)”式“返鄉(xiāng)體”,有著明顯的套路化痕跡: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描寫農(nóng)村凋敝,以偏概全,以局部描寫代替整體;二是碎片化呈現(xiàn),對(duì)個(gè)別極端案例不惜筆墨,羅列道聽途說的故事,不管邏輯,不交待背景;三是在人性最脆弱的地方發(fā)力,夸大其辭,嘩眾取寵。
鄉(xiāng)愁是真情,“愁鄉(xiāng)”則是矯飾。“愁鄉(xiāng)”式“返鄉(xiāng)體”,是如何“矯”成的?
毋庸諱言,隨著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加快,中國農(nóng)村尤其是中西部農(nóng)村,正在發(fā)生前所未有的裂變。與此同時(shí),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尚未發(fā)生根本性改變,很多人離開了農(nóng)村,但他們的根仍然在農(nóng)村。當(dāng)他們帶著某種個(gè)人情感來重新認(rèn)知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勢必會(huì)加入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滲透進(jìn)個(gè)人情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返鄉(xiāng)日記出現(xiàn)片面和失真。
“愁鄉(xiāng)”式“返鄉(xiāng)體”之所以失真,失就失在無視鄉(xiāng)村的進(jìn)步。不管你怎樣“愁鄉(xiāng)”,總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shí):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鄉(xiāng)村的進(jìn)步是巨大的。農(nóng)村貧困人口在迅速減少,2011年至2016年,每年脫貧人口都超過1000萬;農(nóng)村基礎(chǔ)設(shè)施和居住條件在大幅改善,不少農(nóng)村生活條件不比城市差多少,僅2015年,全國新建改建農(nóng)村公路就達(dá)到20萬公里,小汽車進(jìn)村越來越便利,越來越普遍。
當(dāng)然,中國鄉(xiāng)村在迅猛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存在地區(qū)差異和不均衡問題,部分地區(qū)是真“凋敝”,青壯年流失造成人口空心化,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帶來環(huán)境污染。對(duì)這些問題,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應(yīng)當(dāng)真誠地“愁一愁”。
不僅如此,有些地方,“凋敝”是因?yàn)閷?shí)在不適合生存——“十三五”期間,全國要實(shí)現(xiàn)1億左右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zhèn)落戶,僅脫貧異地搬遷的人口就將達(dá)1000萬。人都搬走了,這些村莊自然要荒廢。那些要尋找“原生態(tài)”故鄉(xiāng)的人,完全有權(quán)利抒發(fā)一下“失鄉(xiāng)”之愁。
不過換個(gè)角度看,這種現(xiàn)象不能簡單地以“凋敝”冠之——一方面,鄉(xiāng)親們搬離了“窮山惡水”,起碼能過上溫飽的生活;另一方面,環(huán)境少了人類的“打擾”,能得到休養(yǎng)生息。這其實(shí)都是好事。
我們之所以批評(píng)“愁鄉(xiāng)”式“返鄉(xiāng)體”是矯飾,不僅是這類文字以高高在上的姿勢,對(duì)鄉(xiāng)村的進(jìn)步視而不見,極盡夸張地放大鄉(xiāng)村的種種“不如他意”,更由于,一些人虛幻地把記憶中的鄉(xiāng)村與田園牧歌畫等號(hào),選擇性地遺忘昔日鄉(xiāng)村最大的“愁”——貧困,甚至把閉塞當(dāng)幽靜,把木訥當(dāng)淳樸,把安貧當(dāng)幸福。
說到底,說“返鄉(xiāng)體”片面、失真,并不是抵制對(duì)農(nóng)村的反思,更不是無視發(fā)展不均衡,無視局部凋敝與困境。恰恰相反,隨著城鎮(zhèn)化演進(jìn)以及農(nóng)村面貌的變遷,我們需要對(duì)農(nóng)村進(jìn)行更深入更細(xì)致的觀察、記錄與反思,需要尋找和破解真正改變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答案。但這些觀察與記錄,應(yīng)該建立在準(zhǔn)確、客觀、真實(shí)、全面的基礎(chǔ)上。
每個(gè)人都有鄉(xiāng)愁。鄉(xiāng)愁,無非是兒時(shí)那些美好的記憶。人們選擇了遠(yuǎn)方,卻把那些記憶留在了故鄉(xiāng),總是希望有人守在那里,維系和保持著記憶里的美好。似乎唯其如此,故鄉(xiāng)才是人們想要的故鄉(xiāng)。然而,這只是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奢望——
你不可能自己離開故鄉(xiāng)尋找想要的機(jī)會(huì)與生活,而讓同村的伙伴們都留下,替你原汁原味地守護(hù)故鄉(xiāng)吧?
你不可能自己在大城市享受各種新奇的商品、專業(yè)分工的服務(wù)帶來的生活舒適,而讓你的鄉(xiāng)親替你留住故鄉(xiāng)原有的生活節(jié)奏吧?
你不可能自己計(jì)算著收支賬單,盤算著怎樣能掙更多的薪水、更多的財(cái)產(chǎn)性收入,而讓故鄉(xiāng)的農(nóng)民繼續(xù)自給自足吧?
總之,你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俯視故鄉(xiāng)的一切,無視鄉(xiāng)村系統(tǒng)性的演進(jìn),只抽離自己最鐘情的記憶把玩。
總之,你不能以矯飾的“愁鄉(xiāng)”偷換真誠的鄉(xiāng)愁。
別讓故鄉(xiāng)在頹廢而迷茫的文字里一次次被淪喪。
(杜啟榮薦自2017年1月20日《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