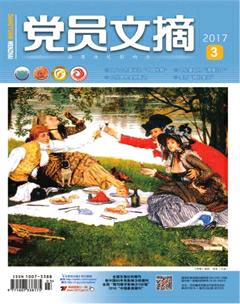“老漂”:流動(dòng)大軍中的銀發(fā)族
楊智杰
2016年10月19日,國(guó)家衛(wèi)生和計(jì)劃生育委員會(huì)公布《中國(guó)流動(dòng)人口發(fā)展報(bào)告(2016)》稱,我國(guó)流動(dòng)人口達(dá)2.47億人,其中流動(dòng)老人將近1800萬。
他們無聲地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分散在各個(gè)角落,是在某個(gè)家庭的廚房里忙碌做飯的父母;是工作日下午5點(diǎn)在幼兒園門口等待孩子下課的爺爺奶奶;是在漢堡店里拉著孫子用不標(biāo)準(zhǔn)的普通話詢問哪種漢堡不辣的顧客。現(xiàn)在,人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新詞來稱呼這群流動(dòng)的銀發(fā)族——“老漂”。
為了下一代而“漂”
2006年10月,當(dāng)董亞珍和老伴坐上從遼寧鐵嶺駛往北京的火車時(shí),她沒有想到自己會(huì)在這座超級(jí)大城市里一住就是10年。
那年董亞珍57歲,唯一的兒子在北京已經(jīng)結(jié)婚落戶。他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幫自己照顧照顧家,等有了孩子也能幫幫忙。
當(dāng)聽到兒子要接她到北京時(shí),董亞珍并沒有多想就答應(yīng)了。在她內(nèi)心里,幫兒子照顧下一代是自己的責(zé)任。
隨著像董亞珍這樣的流動(dòng)老人逐年增多,從2011年起,一些社會(huì)學(xué)者的研究就開始聚焦于“老漂”這個(gè)群體。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社會(huì)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zhǎng)、研究員唐鈞關(guān)注到,和其他“漂族”比,除了代際差異,老人的漂泊并非為了就業(yè),主要是為了下一代。
董亞珍沒想到,到北京以后會(huì)遭遇這么多“水土不服”的問題。
董亞珍住進(jìn)了兒子在常營(yíng)社區(qū)買的70平方米的新房——扣除公攤面積,這房子遠(yuǎn)不如同是70平方米的鐵嶺的家住著寬敞。
初來乍到,董亞珍碰到的第一個(gè)難題就是不認(rèn)路。兒子、兒媳白天上班,老太太早上出門站在馬路邊,不知道該往哪兒走。每次要東張西望半天,或者向路人打聽,時(shí)間久了才慢慢熟悉一些。
每天在家和超市之間的“兩點(diǎn)一線”,把原本喜歡忙活的董亞珍難受壞了。兒子家所在的社區(qū)里也有老人,但大家來自天南海北,摸不清對(duì)方的底細(xì),不敢隨意搭訕。兒子、兒媳早出晚歸,董亞珍不懂他們的生活圈,嘗試和他們聊自己早年的故事,年輕人對(duì)這些陳年舊事不理解,也不感興趣,幾句話就糊弄過去了。
“子代權(quán)威”時(shí)代
首都師范大學(xué)公共管理專業(yè)負(fù)責(zé)人劉亞娜在研究中總結(jié),“老漂族”普遍存在“精神空巢”的問題——老年人離開熟悉的故鄉(xiāng),需要重建社交圈,但由于語言、生活習(xí)慣等原因而難以融入新城市,缺乏歸屬感和認(rèn)同感;而且與兒女有觀念和習(xí)慣的分歧,家庭中也有代溝和隔閡等。
到北京時(shí)間不長(zhǎng),董亞珍的老伴兒就去世了。為了給自己找點(diǎn)樂子,董亞珍每天跑到樓下跟著人們跳廣場(chǎng)舞。
寂寞的生活在第二年有了轉(zhuǎn)機(jī)。董亞珍認(rèn)識(shí)了一位50來歲的北京婦女。
“你想干活兒?jiǎn)幔俊?/p>
“干啥活?”
“掃馬路去不去?”
“去!”
第二天董亞珍被領(lǐng)到了管理處,了解工作內(nèi)容和時(shí)間——每天早上8點(diǎn)上班,下午5點(diǎn)下班,中午可以休息一小時(shí),負(fù)責(zé)打掃樓下一公里左右的馬路段,月薪700元。
“我不是為了掙錢,主要是沒事兒干,解決寂寞。”回家后她將此事通知了兒子、兒媳,他們也表示贊成。
掃地的工作只持續(xù)了一年,孫子出生后便結(jié)束了。但是這段時(shí)間卻是董亞珍來北京后最開心的日子。
董亞珍這10年來一直在主動(dòng)適應(yīng)和接受兒子這一代人與自己的不同。最大的分歧是在孫子的撫養(yǎng)和教育問題上。董亞珍以前從來不知道抱嬰兒之前要洗手、換衣服,更不懂營(yíng)養(yǎng)配餐。
兒子、兒媳給上一年級(jí)的孫子報(bào)了三四個(gè)輔導(dǎo)班,董亞珍不理解這么小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學(xué)會(huì)。她曾勸過兒子,但是兒子有自己的主意。
董亞珍的失落感是在人口流動(dòng)的潮流下現(xiàn)代家庭結(jié)構(gòu)變遷的一個(gè)縮影。“人口流動(dòng)”是分家的重要影響因素,“撫養(yǎng)孫輩”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合家”。
這一次“合家”意味著大部分流動(dòng)老人“投奔”子女,“子代權(quán)威”取代了“父代權(quán)威”。流動(dòng)老人來到新的城市,不僅失去了社交圈,也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主導(dǎo)權(quán)。
政策的空白
不知不覺間,董亞珍來到北京已經(jīng)10年了,她不再是當(dāng)初那個(gè)站在路口找不到方向的老人,而是對(duì)周邊大大小小的超市都如數(shù)家珍,她漸漸習(xí)慣了這個(gè)城市。她每年還會(huì)回鐵嶺一次,而那邊的朋友卻漸漸生疏了。但是,10年時(shí)間讓她從57歲走到了67歲,她不得不關(guān)注與自己身體健康息息相關(guān)的醫(yī)保異地報(bào)銷問題。醫(yī)保報(bào)銷是令許多流動(dòng)老人發(fā)愁的問題。
“很多流動(dòng)老人在農(nóng)村參加了新農(nóng)合,但是這個(gè)該怎么用?有些政策本身就已經(jīng)制定好了,但是宣傳不夠。所以一方面需要完善政策,一方面需要對(duì)現(xiàn)有的安排和政策加強(qiáng)宣傳,讓老百姓了解這個(gè)政策,有效地使用這些政策。”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社會(huì)與人口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段成榮也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很大的問題。
2016年11月18日,遼寧、吉林、黑龍江、海南、四川、貴州、陜西、甘肅等省份簽署了跨省就醫(yī)聯(lián)網(wǎng)結(jié)報(bào)服務(wù)協(xié)議。協(xié)議省內(nèi)參合患者經(jīng)轉(zhuǎn)診至協(xié)議定點(diǎn)聯(lián)網(wǎng)機(jī)構(gòu)就醫(yī),可享受出院窗口直接結(jié)報(bào)服務(wù)。國(guó)家衛(wèi)計(jì)委隨后稱,將開展省內(nèi)異地就醫(yī)直接結(jié)報(bào)工作和跨省就醫(yī)結(jié)報(bào)試點(diǎn)。
“流動(dòng)人口最初是大量的就業(yè)人群,所以國(guó)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圍繞就業(yè)收入、培訓(xùn)、工商勞動(dòng)合同等問題來完善政策。對(duì)于‘老漂,目前來講還是一個(gè)比較新的現(xiàn)象,相關(guān)的制度安排和設(shè)計(jì)甚至可以說是空白。”段成榮說。
了解“老漂”這個(gè)群體的需求,是段成榮認(rèn)為首先要做的事情。多數(shù)老年人的生活重心不是就業(yè),而是進(jìn)城多年后社保的接續(xù)和異地轉(zhuǎn)移。“整個(gè)社會(huì)包括政府和學(xué)術(shù)界,對(duì)這群人的需求知之甚少。所以需要迅速開展調(diào)研,了解他們的需求,針對(duì)需求來制定政策、提供服務(wù),至少使得基本的公共服務(wù)迅速改善起來”。
(摘自2017年1月2日《中國(guó)新聞周刊》 圖:耿玉和/視覺中國(gu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