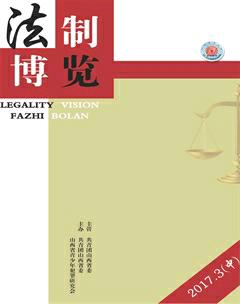對經濟法的現代性解讀
摘要:文章從經濟法概念入手,從法律精神、結構制度及客觀事實角度對經濟法進行現代性分析。
關鍵詞:經濟法;現代性;解讀
中圖分類號:D922.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08-0272-01
作者簡介:閆浩展(1987-),男,漢族,浙江寧波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經濟法學。
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律不同,究其根本是其具有較強的現代性特點,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隨之發生變化。深入了解經濟法概念及其現代性,能夠進一步掌握經濟法內涵,明確法律權責,為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活力。
一、經濟法概念
經濟法是立足于國家發展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及控制的總稱。經濟法地位在國家對經濟決策方面非常重要,也是各個國家關注的重點,且對于經濟法概念提出獨到的見解[1]。如日本認為經濟法是與經濟相關法律的總稱;法國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對傳統商法的拓展。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受到多個國家經濟法的影響,對于經濟法的定義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如“國家協調說”、“國家調節說”等,雖然學者對于經濟法定義理解不同,但是他們都承認經濟法是對現代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的應對,其終極目標是為了有效解決市場經濟缺陷,維護普通社會公眾的利益。
二、經濟法現代性分析
現代性是綜合性、整體性概念,涉及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內容,其核心價值是理性、自由的,具體來說:
(一)精神層面
個人追求具有差異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具備良好的經濟基礎,才能追求更高層次需求。現代社會背景下,我國國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愈發關注自身精神需求,維權意識日益覺醒。而法律以其特殊性成為人們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人們對于不同法律關注度有所差別。從表面來看,經濟法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制度等都存在密切聯系。因此經濟性與機制性成為經濟法的核心特征。而從本質層面上來看,經濟法與現代性具有保持統一,在現代經濟快速發展趨勢下,經濟要跟隨時代腳步,才能夠實現長足發展,協調社會與經濟之間的矛盾,才能夠最大限度上保障公眾利益。所以現代經濟法兼顧目標與效率兩個方面,以國家利益為核心,最大限度上保障私人權益,以此來協調集體與個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構建和諧的社會秩序。
(二)結構制度層面
個體全面發展才能夠取得更加優異的成績,對于社會而言,同樣如此,社會多元化發展才能夠包容更多,實現快速發展目標。因此經濟法也要全面發展,才能夠避免被時代淘汰。基于結構制度層面來看,保持現代性能夠促進經濟法發展,尤其是保持經濟制度結構現代化,要及時發現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靈活的解決策略,最終實現制度形成、構成等現代性目標[2]。從根本上來說,構成現代性體現在自足性,而在運作層面上,要重視政府權力、經濟制度可行性,能夠為經濟活動提供制度依據,規范經濟行為,營造良好的經濟秩序。此外,社會制度新要求發展,使得使用者能夠體會到現代經濟法自身存在的優劣勢,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總體來看,我們能夠發現經濟法結構制度具有現代性特點。
(三)客觀事實層面
目前,經濟法對于經濟活動具有積極意義,但是較傳統部門法來看,從我國國情出發,很多行業仍然處于市場失靈、國家干預等狀態當中,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研究中的應用價值,在服務方向上基本上趨于國家高層次,對于個體合法權益保護力度較為薄弱,缺乏均衡性。基于客觀追求來看,經濟法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性。經濟法正是建立在原始社會至現代社會基礎之上。經濟法的核心宗旨是為了保護個體、公眾領域合法權益。當代社會,經濟活動存在盲目性、矛盾性特點,對于經濟法需求非常迫切。只要完善的經濟法,才能夠協調好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保障經濟社會處于平穩狀態當中[3]。故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法保護的權益具有多重性特點,除了關注經濟領域,還需要關注主體利益,兼顧效率與公平。
除此之外,經濟法中認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行為,肯定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夠成熟和完善,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權力合法性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多項內容。合法的化解危機需要將社會與國家政治相互獨立。當前,經濟法中不能夠否認國家政府作用市場現象,因此這種認同正充分體現了經濟法的現代性。
三、結論
綜上所述,新經濟形勢下,經濟法具有鮮明的現代性,無論是客觀事實、還是結構制度較其他部門法更具優勢,也是其區別于部門法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通過深入認識經濟法的現代性,可以根據時代要求,適當干預經濟活動,豐富我國經濟理論體系,為經濟活動提供指導,協調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合法權益,保障集體與個體利益,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始終處于和諧狀態當中。
[參考文獻]
[1]李穎惠.論經濟法的現代性——以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對比分析為視角[J].經營管理者,2013(28):244.
[2]孫艷,滿娜.對經濟法的現代性的思考[J].赤子(上中旬),2015(13):227.
[3]王玉.回應型經濟法淺析——兼論經濟法的回應性[J].法制與經濟,2016(06):128-12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