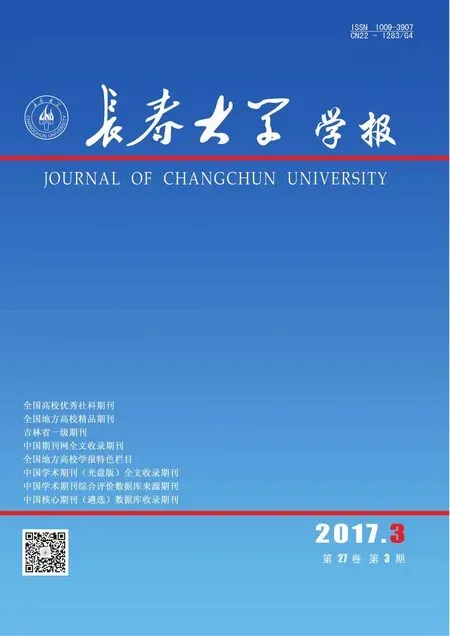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的政府補貼研究
——基于三重螺旋視域
張 健,吳 均
(1.天津農(nóng)學院 經(jīng)濟管理學院,天津 300384;2.天津市農(nóng)業(yè)廣播電視學校 西青區(qū)分校,天津 300380)
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的政府補貼研究
——基于三重螺旋視域
張 健1,吳 均2
(1.天津農(nóng)學院 經(jīng)濟管理學院,天津 300384;2.天津市農(nóng)業(yè)廣播電視學校 西青區(qū)分校,天津 300380)
在三重螺旋視域下構建了政府對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協(xié)同創(chuàng)新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予以補貼的博弈模型,分別研究了納什均衡、斯坦克爾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條件下的政府補貼問題。研究表明:政府補貼可以有效平衡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利益分配結構;共性技術的復雜程度越高、可獲得性越難、應用范圍越廣、經(jīng)濟社會效益越大,政府給予的資助越多;在收益相同的前提下,合作博弈下政府付出的補貼成本要小于非合作博弈。
三重螺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政府補貼
0 引言
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是以重大技術突破為基礎,通過創(chuàng)新引進新的生產(chǎn)函數(shù)帶動產(chǎn)業(yè)結構轉換的新興產(chǎn)業(yè)。也就是說,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具有典型的創(chuàng)新驅(qū)動特征,可以借助關聯(lián)效應將新技術擴散到整個產(chǎn)業(yè)系統(tǒng),促使整個產(chǎn)業(yè)技術基礎實現(xiàn)更新?lián)Q代,并逐漸建立起產(chǎn)業(yè)間新的技術經(jīng)濟聯(lián)系,從而引起產(chǎn)業(yè)結構的轉型升級,在為經(jīng)濟增長增添新的潛力和可能的同時,最終推動我國經(jīng)濟進入新的發(fā)展軌道[1,2]。目前,培育和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已然成為我國增強自主研發(fā)能力、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的重要契機,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結構優(yōu)化升級、轉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的重要途徑,拉動國民經(jīng)濟增長、增加就業(yè)機會的重要引擎,改善國民生活水平、刺激消費需求的重要手段。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還大多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著共性技術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成為了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現(xiàn)階段遇到的重大瓶頸和障礙[3,4]。
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是一種在整個技術創(chuàng)新鏈條中處于基礎性支撐地位的前瞻性技術,對于確保整個產(chǎn)業(yè)的培育和發(fā)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帶動作用。與此同時,它可以幫助產(chǎn)業(yè)內(nèi)企業(yè)以此為基礎根據(jù)自己的實際需要進行后續(xù)的商業(yè)化研發(fā),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企業(yè)間相互競爭的技術,從而在短時間內(nèi)迅速提升整個產(chǎn)業(yè)的自主研發(fā)能力和技術層級[5]70。但是,共性技術基礎性、超前性、外部性、風險性和集成性的特點,增加了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難度,在現(xiàn)實中往往面臨著“政府缺位”、“市場失靈”和“組織失效”的問題,從而直接導致共性技術的供給主體長期處于相對匱乏的尷尬境地[6]。
1995年,Etzkowitz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三重螺旋理論,以便解釋知識經(jīng)濟時代下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他認為,創(chuàng)新的主體不僅僅局限于企業(yè),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作為平等的合作伙伴都可以作為創(chuàng)新的主體,三者之間日益增加的“交疊”才應該是創(chuàng)新的核心單元[7,8]。在三重螺旋模型中,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被形象化地描述為彼此之間有著緊密聯(lián)系的互相纏繞的三根螺旋線,它們在關注自身發(fā)展的同時,還在某種程度上擔負著其他兩者的職能,三重螺旋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從而推動技術創(chuàng)新呈現(xiàn)出螺旋式上升的態(tài)勢[9]。有鑒于此,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培育和發(fā)展,彌補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主體的不足,能夠?qū)崿F(xiàn)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三者創(chuàng)新資源最大整合和優(yōu)化的三重螺旋協(xié)同創(chuàng)新就成為了理想的選擇。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準公共物品性、外部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政府補貼的作用不容忽視。因此,在三重螺旋視域下,如何有效發(fā)揮政府補貼效用、合理配置政府補貼資源,對于實現(xiàn)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并最終推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穩(wěn)步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是典型的創(chuàng)新驅(qū)動型產(chǎn)業(yè),體現(xiàn)了新興科技和新興產(chǎn)業(yè)的深度融合。所以,只有共性技術的不斷突破,才能催生和支撐產(chǎn)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曾繁華和王飛(2014)提出,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躍遷的實質(zhì)是:當一個產(chǎn)業(yè)升級到較高水平之后,產(chǎn)業(yè)內(nèi)企業(yè)可以開辟新的技術通路來擺脫特定發(fā)展階段出現(xiàn)的技術束縛,從而幫助產(chǎn)業(yè)在全球價值鏈中從較低增值環(huán)節(jié)升級到較高增值環(huán)節(jié)。欒春娟(2012)、王敏等(2013)、賀正楚等(2014)、朱建民等(2016)都強調(diào)了共性技術對于推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培育和發(fā)展以及增強產(chǎn)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所起到的至為關鍵的作用[10-12]。近年來,學者們圍繞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薛捷和張振剛(2006)、劉洪民(2013)、殷輝和陳勁(2015)表示,“官產(chǎn)學研”協(xié)同合作是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最有效的組織形式。Tassey(2008)認為,共性技術的外部性,加之社會分工和專業(yè)化發(fā)展的日益深入,決定了合作研發(fā)的必要性[13]。李紀珍(2011)發(fā)現(xiàn),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往往面臨著“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的狀況,并強調(diào)了政府在解決“雙重失靈”中的重要作用[14]。熊勇清等(2014)提到,在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中,作為一種能夠兼顧政府公共目標與企業(yè)利益目標的“公私合作”研發(fā)模式,通過政府引導和企業(yè)主導的有機結合,可以幫助政府在推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進步的同時,解決企業(yè)“搭便車”過度消費公共技術產(chǎn)品的問題[5]68。劉洪民和楊艷東(2016)表示,能夠?qū)崿F(xiàn)優(yōu)勢互補、風險共擔、共同發(fā)展的官產(chǎn)學研各類主體參與的模塊化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共性技術研發(fā)的必然選擇[15]。王宇露等(2016)指明,可以通過搭建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平臺,整合企業(yè)、大學、政府、研究機構等創(chuàng)新主體的分布式資源,為共性技術的研發(fā)和擴散提供全方位服務,從而推動產(chǎn)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的有效提升[16]。與此同時,有些學者也探討了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中的政府補貼問題。孫鰲(2005)指出,在直接資助、稅收減免和政策性貸款這三種政府常用的手段中,直接資助更能誘導企業(yè)投入更多的研發(fā)成本。方福前等(2008)認為,政府補貼能夠激發(fā)企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劉新同和肖立范(2012)提出,政府應該采取直接補貼或者稅收減免等措施,鼓勵產(chǎn)學研合作從事共性技術研發(fā)。馬曉楠和耿殿賀(2015)利用博弈模型,驗證了政府補貼對于促進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積極作用[17]。綜上所述,雖然學術界普遍認為涵蓋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參與的能夠?qū)崿F(xiàn)創(chuàng)新資源最大整合和優(yōu)化的三重螺旋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保障共性技術有效供給的理想選擇,但是相關的系統(tǒng)研究卻并不多見,而在這一框架下深入探討政府補貼問題的文獻則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在三重螺旋視域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在分析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三者之間互動機理的基礎上,尋求最優(yōu)政府補貼策略,以便于完善相關理論和提供實務參考。
1 模型構建
1.1 模型假設
在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政府除了扮演組織協(xié)調(diào)者的角色之外,還要在制度供給、價值引導、信息公布、平臺建設、金融支持和環(huán)境保障等多個方面履行職能;企業(yè)應該以市場為導向,在共性技術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發(fā)揮核心作用;大學(科研機構)可以憑借豐富的人才、知識和技術儲備為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提供必要的支撐。因此,根據(jù)三者的角色功能定位,本文的假設條件如下:
假設1:政府G作為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推動者、調(diào)控者和管理者,不參與具體的研發(fā)工作。同時,為了簡化模型,假設共性技術的研發(fā)主體僅僅包括一個企業(yè)I和一個大學(科研機構)U。
假設2:政府作用的體現(xiàn)是對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創(chuàng)新投入分別進行補貼。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三者之間的信息是完全公開的,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博弈方式會影響政府的最優(yōu)補貼水平。同時,創(chuàng)新投入與創(chuàng)新收益成正比。
假設3:選取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創(chuàng)新投入為影響創(chuàng)新收益的關鍵變量,其他因素對創(chuàng)新收益的影響以隨機因素的形式呈現(xiàn)。
假設4: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成果會帶來一定的收益,研發(fā)主體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將共享這一收益。由于企業(yè)在共性技術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處于主體位置,所以在收益分配時企業(yè)獲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大學(科研機構)獲得的收益。此外,政府獲得的收益是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成果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效益。
假設5: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均是風險中性的,也都是理性“經(jīng)濟人”。政府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三者之間利益共享、成本共擔、風險共擔。
1.2 模型構建
(1)基本參數(shù)。模型所涉及的相關變量和參數(shù)的定義:
X:表示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投入,X≥0;Y:表示大學(科研機構)的創(chuàng)新投入,Y≥0。
α,β:分別表示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創(chuàng)新投入的彈性系數(shù),假設0<α+β≤1,0<β<α<1。
θ:表示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收益帶來的收益系數(shù),θ>0。
γi:分別表示政府對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創(chuàng)新投入的補貼系數(shù)。0≤γi≤1,i=1代表企業(yè),i=2代表大學(科研機構)。
ρi:分別表示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邊際收益。其中,i=1代表企業(yè),i=2代表大學(科研機構),ρ1+ρ2=1,0<ρ1<ρ2<1。
δ:表示社會的邊際收益。由于共性技術具有準公共產(chǎn)品的特性,所以δ≥1。而且,共性技術復雜程度越高、可獲得性越難、應用前景越廣、經(jīng)濟社會價值越大,δ越大。
R:表示協(xié)同創(chuàng)新帶來的收益總和,R=R(X,Y)。
φ:表示其他對創(chuàng)新收益產(chǎn)生影響的隨機因素。
(2)構建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能夠較好地反映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二者投入產(chǎn)出的相互依賴性和非線性。假設:
協(xié)同創(chuàng)新收益:R=θXαYβ+φ
(1)
其中,E(φ)=0,D(φ)=σ2,相應R也服從方差σ2的正態(tài)分布,即
協(xié)同創(chuàng)新期望收益:
E(R)=θXαYβ,D(R)=σ2
(2)
協(xié)同創(chuàng)新期望利潤:
E(π)=E(R)+γ1Y+γ2Y-X-Y
(3)
企業(yè)期望利潤:
E(πI)=ρ1E(R)+γ1X-X
(4)
大學(科研機構)期望利潤:
E(πU)=ρ2E(R)+γ2Y-Y
(5)
政府期望利潤(社會期望利潤):
E(πG)=δE(R)-X-Y
(6)
2 模型求解
在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政府希望通過給予一定的補貼提高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創(chuàng)新投入水平,而政府的最優(yōu)補貼水平受到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之間博弈方式的影響。因此,本文在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納什博弈、斯坦克爾伯格博弈和合作博弈3種情況下求解最優(yōu)政府補貼。
2.1 納什均衡博弈分析
在納什均衡博弈條件下,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關系,在看到政府的補貼政策后同時采取行動。博弈的順序為政府先規(guī)定補貼比例,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看到后同時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采用逆向歸納法,根據(jù)(4)(5)式可以得到:
(7)
由以上方程組解得:
(8)

(9)
由式(9)可知,在納什均衡博弈下,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邊際收益對政府的補貼系數(shù)有著明顯的影響,二者之前呈現(xiàn)反比例關系。研發(fā)主體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在創(chuàng)新總收益中分得利益較少的一方,政府補貼政策應該給予一定的傾斜。因此,在非合作納什均衡博弈下,政府補貼可以有效平衡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收益分配狀況。同時,政府補貼與社會邊際收益成正比,所以共性技術復雜程度越高、可獲得性越難、在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或者其他行業(yè)中應用前景越廣,帶來的經(jīng)濟和社會價值越大,政府給予的資助應該越多。
2.2 斯坦克爾伯格均衡博弈分析
在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企業(yè)為領導者、大學(科研機構)為跟隨者的情況,此時政府、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進行三階段博弈,博弈的順序是:政府先確定補貼系數(shù),企業(yè)確定最優(yōu)創(chuàng)新投入,大學(科研機構)根據(jù)企業(yè)的決策確定自己的最優(yōu)創(chuàng)新投入。
首先,大學(科研機構)在既定的政府和企業(yè)決策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根據(jù)(5)式可得:
(10)
(11)
其次,企業(yè)根據(jù)政府的補貼政策最大化自己的利潤函數(shù)式(4),將式(11)代入式(4)可得:
(12)
式(12)一階條件等于零,可得:
由此可得:
(13)
最后,將式(13)代入式(6),可得政府的最優(yōu)補貼方案:
(14)

2.3 合作均衡博弈分析
在合作均衡條件下,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作為戰(zhàn)略合作伙伴達成了合作協(xié)議,二者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博弈的順序是:政府先規(guī)定補貼系數(shù),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看到后最大化共同的利潤。二者的期望利潤目標函數(shù):
maxE(π)=max(θXαYβ+γ1X+γ2Y-X-Y)
(15)
采用逆向歸納法,根據(jù)上式可以得到:
(16)
由以上方程組解得:
(17)

(18)
在合作博弈中,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博弈偏好是:整體利益最大化高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即在協(xié)同創(chuàng)新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個體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據(jù)式(18)可知,合作博弈下,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獲得的政府補貼系數(shù)相等,且與各自的邊際收益無關,僅僅與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成果的社會邊際收益正相關,即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的復雜程度越高、可獲得性越難、應用前景越廣、經(jīng)濟社會效益越大,政府給予的支持應該越多,政府補貼的價值也越能有效凸顯。
3 結果分析
結論1:由于0<α+β≤1,0<β<α<1,由式(8)(13)和(17)可知,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創(chuàng)新投入與政府補貼成正比。
結論2:由式(8)(9)(13)(14)(17)(18)可知:X=X=X,Y=Y=Y,所以在不同博弈條件下,政府實施最優(yōu)補貼方案時,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最優(yōu)期望收益相同,政府的最優(yōu)期望利潤也相同。同時,結合式(4)和(5)可知,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最優(yōu)期望利潤與政府補貼正相關。
結論3:由式(9)(14)和(18)可知,政府的最優(yōu)補貼與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成果的社會邊際收益有正向關系。因此,無論在哪種博弈條件下,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共性技術的復雜程度越高、可獲得性越難、應用前景越廣、經(jīng)濟社會效益越大,政府給予的支持就應該越多。


4 結束語
本文在三重螺旋視域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構建政府對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合作研發(fā)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予以補貼的博弈模型,分別研究了納什均衡、斯坦克爾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3種博弈條件下的最優(yōu)政府補貼問題,闡述了政府補貼通過調(diào)整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之間的博弈關系從而激勵二者從事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內(nèi)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①政府補貼可以有效平衡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三重螺旋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收益分配結構;②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的復雜程度越高、可獲得性越難、應用前景越廣、經(jīng)濟社會效益越大,政府給予的支持力度應該越大,相應地政府獲得的回報也越豐厚;③在政府獲得利益相同的前提下,合作均衡博弈條件下政府付出的補貼成本小于非合作均衡博弈條件下的政府補貼成本。所以,在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出于對政府補貼資源利用效率和企業(yè)與大學(科研機構)參與程度的考慮,政府應該采取多種舉措積極促成企業(yè)與大學(科研機構)之間形成能夠真正實現(xiàn)資源互補、緊密合作和良性互動的合作博弈關系。
本文的政策啟示是明顯的:①政府作為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導者,應該樹立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理念,積極推動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的建立和完善,從而確保實現(xiàn)政府、企業(yè)、大學(科研機構)三者創(chuàng)新資源的最大整合、優(yōu)化和互補。②政府作為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的三大創(chuàng)新主體之一,雖然不參與具體的研發(fā)工作,但需要充分發(fā)揮宏觀調(diào)控作用,從資金支持、規(guī)劃指導、制度供給、信息公布、平臺建設、組織協(xié)調(diào)和環(huán)境保障等方面積極采用多種措施促進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精誠合作,提高合作研發(fā)的機會和效率。③鑒于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準公共物品性、外部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等固有特性,政府應該直接提供一定的補貼資助,以便降低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的成本與風險,助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活動的順利開展。④政府補貼的力度應該控制在一個適當?shù)姆秶畠?nèi),從而使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一定的運行規(guī)律下進行調(diào)控。因此,政府需要區(qū)分三重螺旋視域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協(xié)同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企業(yè)和大學(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情況,進而合理配置政府補貼資源,避免資助不當,最終確保政府補貼政策能夠切實、有效地發(fā)揮作用。
[1] 李少林.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與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協(xié)同發(fā)展:基于省際空間計量模型的經(jīng)驗分析[J].財經(jīng)問題研究,2015(2):25-32.
[2] 劉暉,劉軼芳,喬晗,等.我國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路徑研究:基于北京市生物醫(yī)藥行業(yè)的經(jīng)驗總結[J].管理評論,2014,26(12):20-28.
[3] 于斌斌.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與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創(chuàng)新鏈接機理:基于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企業(yè)進化博弈模型的分析[J].研究與發(fā)展管理,2012,24(3):100-109.
[4] 熊勇清,李鑫,黃健柏,等.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市場需求的培育方向:國際市場抑或國內(nèi)市場:基于“現(xiàn)實環(huán)境”與“實際貢獻”雙視角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5(5):125-138.
[5] 熊勇清,白云,陳曉紅.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開發(fā)的合作企業(yè)評價:雙維兩階段篩選模型的構建與應用[J].科研管理,2014,35(8).
[6] 賀正楚,張蜜,吳艷,等.生物醫(yī)藥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服務效率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4 (2):130-139.
[7]EtzkowitzHenry,LeydesdorffLoet.TheTripleHelixof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Relations:ALaboratoryforKnowledge-BasedEconomicDevelopment[J].EASSTReview,1995,14(1):14-19.
[8]LeydesdorffL,MeyerM.TheScientometricsofATripleHelixof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Relations(IntroductiontoTheTopicalIssue) [J].Scientometrics, 2007,70(2):207-222.
[9]AndyCosh,AlanHughes.NeverMindTheQualityFeelTheWidth:University-IndustryLinksandGovernmentFinancialSupportforInnovationinSmallHigh-TechnologyBusinessesinTheUKandTheUSA[J].TechnologyTransfer,2010(35): 66-91.
[10] 王敏,方榮貴,銀路.基于產(chǎn)業(yè)生命周期的共性技術供給模式比較研究:以半導體產(chǎn)業(yè)為例[J].中國軟科學,2011(9):125-132.
[11] 賀正楚,張蜜,吳艷. 我國生物醫(yī)藥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供給研究[J].中國科技壇,2014(2):40-45.
[12] 朱建民,金祖晨.國外關鍵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發(fā)展的做法及啟示[J].經(jīng)濟縱橫,2016 (7):113-117.
[13]TasseyG.Modelingandmeasuringtheeconomicrolesoftechnologyinfrastructure[J].EconomicsofInnovationandNewTechnology,2008, 17(7):615-629.
[14] 李紀珍,鄧衢文.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供給和擴散的多重失靈[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32(7):5-10.
[15] 劉洪民,楊艷東.制造業(yè)共性技術研發(fā)協(xié)同知識鏈及知識流動模型:模塊化協(xié)同視角的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33(9):41-46.
[16] 王宇露,黃平,單蒙蒙. 共性技術創(chuàng)新平臺的雙層運作體系對分布式創(chuàng)新的影響機理:基于創(chuàng)新網(wǎng)絡的視角[J].研究與發(fā)展管理,2016,28(3):97-106.
[17] 馬曉楠,耿殿賀.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共性技術研發(fā)博弈與政府補貼[J].經(jīng)濟與管理研究,2014(1):73-78.
責任編輯:沈 玲
Study on Governmental Subsidy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Generic Technologyfor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iple Helix
ZHANG Jian1, WU Ju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2. Xiqing District Branch, Tianjin Agricultural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chool, Tianjin 300380,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iple helix,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ame model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enterprises and a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bsidy for generic technology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respectively studies 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al subsidy under three conditions of Nash equilibrium, Stackelberg equilibrium and cooperative equilibri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al subsidy can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structur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more aids to those generic technologies with higher complexity, difficult acquirement, wider application and greater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governmental subsidy cost of the cooperative game should be less than that of the non-cooperative game in the premise of the same benefits.
triple helix;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generic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governmental subsidy
2016-12-0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4YJCZH205);天津市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計劃項目(13ZLZLZF06200);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后期資助項目(TJGLHQ1404)
張健(1978-),女,天津人,副教授,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技術經(jīng)濟及管理研究。
C93
A
1009-3907(2017)03-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