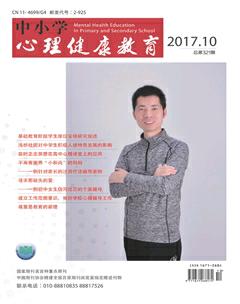建立工作范圍意識,做好學校心理輔導工作
孫開霞
〔關鍵詞〕心理輔導;工作范圍;心理教師
一、引子
2016年9月,我接到某地級市心理教研員的邀請,參與該市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輔導案例、教學課例的評選工作。輔導案例有76篇,是各個學校的心理健康教師根據工作中做的輔導個案寫成的。在評審時,我注意到有不少教師在評估來訪者的心理問題時,超越了學校心理輔導工作的范圍。
比如:一位教師在為一個厭學的學生做輔導時,對他的厭學行為進行了“診斷”,并在“診斷”過后,制定了“治療”方案。一位教師僅僅在請家長填寫“兒童感覺統合能力發展評定量表”后,就診斷這位家長的孩子患有感統失調。另一位教師在沒有經過精神科醫生給出診斷結果的情況下,就認定一位學生患有強迫癥,并對其進行長達三個月的心理輔導,最后還徹底治愈了來訪學生的強迫癥。以上所舉的僅是76篇案例中的3篇,其他涉及“診斷”或“治療”的案例,還有18篇。從百分比上來考量,這21篇案例占總案例數的27.6%。在評分時,我對這些帶有“診斷”或“治療”字眼的案例都打了中等偏下的成績。
上述所舉例子,是我工作中遇到的個例之一。在更廣范圍內的個案交流、討論中,時常聽到有中小學心理教師說出“診斷”或“治療”詞匯;去外地學習參觀時,也經常會看到在學校心理工作的專門場所出現“診斷”字眼。在此過程中,我會適時地表達出我的看法,并建議對方改變口頭上的說法或者進行書面上的更正。因為現行的由國家教育部頒布的文件《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2012年修訂)》、《中小學心理輔導室建設指南》(2015年)已經對中小學心理教師的工作范圍作了更為嚴格的規定。很顯然,他們還沒有注意到有這樣的規定,所以,在工作中很自然地做出了超越范圍的事。
二、規定
2002年國家教育部頒發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授予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診斷、矯治的權力:“開設心理咨詢室(或心理輔導室)進行個別輔導是教師和學生通過一對一的溝通方式,對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出現的問題給予直接的指導,排解心理困擾,并對有關的心理行為問題進行診斷、矯治的有效途徑。”這份文件距今已有14年的時間,雖不能直接認為上述三位教師對來訪學生進行診斷是受到這份文件的授權,但它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中小學心理教師們對自身工作能力的認知和對個別心理輔導工作范圍的評估,以至到現在仍有很強的作用力。
2012年12月,教育部出臺修訂版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在修訂版中,教育部收回了心理教師的診斷、矯治權力。它這樣規定:“在心理輔導過程中,教師要樹立危機干預意識,對個別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能夠及時識別并轉介到相關心理診治部門。”在這條規定中,心理教師在面對嚴重心理疾病時,工作職責是“識別和轉介”。
2015年7月教育部出臺的《中小學心理輔導室建設指南》(以下簡稱《建設指南》)對個別心理輔導工作又做出進一步界定:“心理輔導室應與相關心理診治部門建立暢通、快速的轉介渠道,對個別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或發現其他需要轉介的情況,能夠識別并及時轉介到相關心理診治部門。轉接過程記錄詳實,并建立跟蹤反饋制度。”對學校心理輔導室的規定,就是對學校心理健康教師的規定,心理教師不僅要“識別和轉介”,還要做好前提性的工作:應與相關心理診治部門建立暢通、快速的轉介渠道;同時做好后續延展性工作:轉接過程記錄詳實,建立跟蹤反饋制度。可以說,這則條例系統化了學校心理教師的工作范圍和職責,比修訂版的《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對心理教師的規定更完善。 在對上述援引的文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教育部對中小學心理健康教師工作范圍的限制是愈來愈趨向于嚴格的。心理健康教師是個別心理輔導工作的具體執行人,除進行日常的個別心理輔導工作外,還要有識別嚴重心理疾病的能力,并須做好相應的轉介工作,以及和專業心理咨詢機構或心理診治部門的對接工作。也就是說,在教育部的規定里,中小學心理教師是沒有權力對來訪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診斷和治療的,能進行診斷和治療的是具有專業資質的心理咨詢機構或心理診治部門。
可以說,2012年的修訂版《綱要》和2015年的《建設指南》在這方面做出的規定,區分清楚了學校心理工作和醫學心理工作的職責和界限,使學校個別心理輔導工作在規定的范圍內更加具有專業性,并能切實保護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的利益。
三、建議
中小學學生是特殊的群體,心理變化復雜多樣,人格沒有定型,因此,對他們表現出來的嚴重心理疾病必須由專業人員鑒定。如果由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嚴重心理疾病專業知識培訓的心理教師做出鑒定,極易導致對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做出不合適的應對方案,甚至可能延誤病情。因此,為提升中小學心理教師心理輔導的專業素養,做好中小學學生的心理輔導工作,需要開展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強化心理教師的工作范圍意識。
在心理輔導工作中,心理教師要樹立工作范圍意識:做自己能做的心理輔導,不做超出自身工作范圍的心理輔導。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做好非嚴重心理疾病的來訪學生的日常輔導工作;二是做好在專業機構診斷出的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的協同合作、回歸保健和后續心理支持工作。在67則案例中,絕大多數心理教師能遵守學校心理工作的基本規則,對來訪學生做出適合的心理輔導。在撰寫案例報告時,他們也沒有使用“診斷”和“治療”這樣的字眼。這在一定程度上能說明他們有明確的職業范圍意識,并且在工作中能夠切實把握好這個界限。當然,我也看到有兩位教師在做回歸保健和后續心理支持工作。一位教師為一名經南京市兒童醫院診斷為ADHD混合型的兒童的父母做輔助性的心理輔導工作,促成了父母關系的調整及他們養育孩子方式的改變。另一位教師在接待某個個案時,根據她的專業知識,評估出來訪學生可能患有抑郁癥,她立即建議家長帶孩子到專業機構進行診斷治療。確診后,這位教師一直保持和家長的聯系,并指導家長與孩子進行良性的交流和溝通。一年后,孩子的抑郁癥好轉,情緒恢復健康,家長也非常感激這位教師的幫助。
中小學學校里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畢竟是少數,但正是這些為數極少的學生最考驗心理健康教師對自身工作范圍的把握能力及應對能力。這兩位教師在處理個案時,切實把握住了學校心理輔導工作的任務和范圍,為我們樹立了好的榜樣。
其次,加強對心理教師嚴重心理疾病知識的培訓。
在國家教育部2012年及2015年出臺的兩份文件中,所提及的嚴重心理疾病只是一個統稱的概念,并沒有給出可以參考的標準。對此,我認為,在這項工作中,還需要對中小學心理教師進行系統的培訓,增進他們對嚴重心理疾病的類型、診斷標準的了解,以提升他們的識別能力,這是基礎性的工作。因為,心理教師只有具備嚴重心理疾病的基礎性知識,才能有能力識別出超出其工作范圍的學生個案,然后通過特定的渠道,轉介到相應的專業機構。這既是對中小學來訪學生負責,也是對心理教師自己的保護。
再次,建議出臺可轉介的心理診治機構名冊。
《建設指南》要求“心理輔導室應與相關心理診治部門建立暢通、快速的轉介渠道”,對這項工作,我認為不能把權限下放給心理教師,因為心理教師沒有能力和資質去判定哪個心理診治部門具有相應的資質。我在一所高中工作,每年都會接觸一到兩個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在轉介時,都會建議其到南京腦科醫院。但有些家長并不滿意這樣單個單位的建議,他們希望有更多可以選擇的診治機構。另外,對一些超出我的輔導能力又沒有嚴重心理疾病且需要轉介的來訪學生,工作往往變得更加復雜:家長們懷疑教師推薦的機構不能真正地幫到他們的孩子和他們自己。所以,鑒于此,我的想法是教育部可以出臺一個可供參考的全國性的專業心理機構或心理診治機構的名冊。這樣,便于像我這樣的基層學校心理工作者在轉介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學生時,能做到快速轉介,盡快幫助到學生,同時,也最大限度地降低家長們的擔憂。
四、后續
在本次案例評選結果出來后,我在獲獎名單上看到了上述提及的兩位教師的姓名,也看到了她們的職業身份:專職心理教師。另外也有一部分有診斷字眼的案例也獲了獎(21篇中有16篇),作者中有專職心理教師,也有兼職心理教師。出現這樣的結果,與評選標準有密切的關系,凡出現診斷、治療詞匯的,減5分。心理教研員和評委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各抒己見,表達不同想法,但最后達成的共識也只能是對這個現象持保留態度,畢竟中小學學校里的心理健康工作才起步,畢竟寫案例的教師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專業出身,而是從其他學科半路出家做兼職。但愿,到下一次案例評比時,這樣的現象及這樣的妥協態度不再出現。 從規則出臺到完全被實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現在還處于過程中,離終點還有一段較長的路程。道路雖然曲折,但我堅信,未來肯定會更好。
(作者單位:江蘇省大港中學,鎮江,212028)
編輯/杜文姬 終校/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