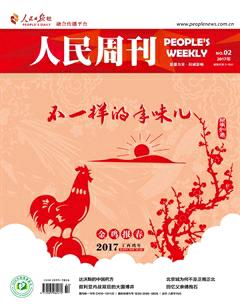中國火藥并非只用來造煙花
趙新宇



在不同的軍事環境下,東西方的“爆炸性火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漸走進科學之后,中國卻還在以玄學為基礎探討軍火。
中國人使用火藥比西方人“早幾百年”,而西方人只花100多年就造出比中國厲害得多的火炮,是中國人特別熱愛和平,還是西方人“開掛”了?
70多年前,魯迅曾發表過一句感慨:“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此后至今,每當人們討論“國民性”“屈辱的近代史”之類的話題,這句話都會反復出現,仿佛從東西方火藥應用的差異入手,即可參透各文明發展不均等的天機。
然而,火藥、槍炮與爆竹的歷史不是像魯迅唏噓的那么簡單。西方人的火藥應用并不晚于東方人太多,而古代的中國人也絕非一味熱愛和平。
魯迅錯了
一般認為,火藥發明于隋末唐初的東亞。也有些當代人出于民族自豪感,將早至東晉時期的煉丹家葛洪封為火藥的發明者。魯迅的感嘆和許多人的困惑都由此而起:既然中國擁有火藥比歐洲早了至少500年,那中國人怎么沒早造出槍炮彈藥來?
事實上,與魯迅的想象相反,古書上記載的煉丹術中的“火藥”,與后世打仗開礦的火藥不完全是一回事。
實際上,在1161年的宋金采石戰爭中,才出現了史上第一種用于爆炸的火藥“霹靂炮”。這是一種摻有石灰的紙炮,其功能并非傷人性命,而是以爆炸揮散的石灰煙霧迷住敵兵的眼睛,使對方無法發揮戰斗力。顯然,這種火藥武器并非現代軍火的同類,而更像是武俠小說中的斗毆伎倆。
真正意義上的爆炸性火藥,是在1221年的戰場上第一次被記錄下來的。作為最早的鐵制外殼炸彈,金人的“鐵火炮”威力巨大,能夠將不幸中彈的宋兵頭部炸掉一半。有了這種革命性的爆炸性火藥,我們日常所說的槍支彈藥才有可能出現。
在此后一段時期內,東方的軍火發展也不落后于西方。比如說,中國人造出管狀火器的時間比西方要早——后人會從陳規火槍算起。最早能“射出彈丸”的火器也出現在中國,即1259年南宋軍隊制造的“突火槍”,它“以巨竹為筒”,可發射“子窠”——應該是顆粒裝的散彈。不過,這種竹制“突火槍”沒有批量生產,也沒有留下任何作戰記錄。
此后,元朝出現的第一批真正的類槍炮武器看上去比西方同時期的“鐵瓶炮”要靠譜一些,發明時間也很可能更早。到元朝末年,已經出現了不同口徑銅火銃的區分:小口徑的以手持發射散彈,大口徑的裝在架子上發射單發石彈。
西方甩開中國
不過,只過了不到100年,西方火炮就把中國同類遠拋在身后了。
“鐵火炮”在宋金戰爭中亮相后,其革命意義一目了然,配方遂迅速傳遍歐亞大陸。1262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抵御基督徒軍隊進攻時使用了一種會爆炸的鐵球,這是炸彈在西歐最早的使用記錄。相比之下,南宋制造使用“鐵火炮”的記錄也是在1257年才第一次出現。中國人在開發槍炮炸彈方面,與西方人幾乎是齊頭并進,沒占到什么先機。
隨后,重達10多噸的巨炮——臼炮——的誕生,一舉扭轉了東西方軍械的實力對比。
從尺寸上,這種氣勢驚人的新武器口徑往往超過50厘米,動輒可以把六七百磅的石彈射出一公里,氣勢驚人。中國人從未造出過這樣的龐然大物,像明朝的碗口炮,最重不過“上百斤”。《武備志》里的“天字號神炮”,重量也只有280斤而已,還不如臼炮的炮彈重。
不過,西方人之所以能夠造出臼炮,也不是因為他們在火器技術上占據了什么優勢。真正導致東西方軍火發展差異的,還是各自軍火實際應用上的差別。
與西方不同,中國不存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人造堡壘,夯土城墻一直到明朝才砌上了磚。而且,東亞戰爭的參與人數雖遠多于西方,單兵裝備卻落后甚遠——在裝甲方面,只有御林軍級別的軍人才配有鎖子甲。無論是在元末內戰還是在明蒙戰爭中,大家都不會感受到研發先進軍械、勇攀科技之樹的必要性,把太多資源投入到這個方面反而可能是不太明智的行為。
在這一點上,奧斯曼土耳其與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直到14世紀,土耳其還對火器毫無建樹,而隨著戰事的不斷推進,1453年,他們就能搬出巨炮,轟擊君士坦丁堡的城墻了。土耳其巨炮的發射過程極為復雜,搬運也需要幾十匹馬加200多人,但其發射的600磅石彈,還是能在連續兩個月的炮轟下,將偉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堅固城防擊垮。
到16世紀時,西方軍事科技突飛猛進。鑄鐵技術已能夠鑄造一體成型的炮筒,發射火炮因此變得更加安全,射擊的威力也更加巨大。粒化火藥技術為不同用途的火器提供了合適的彈藥,再也不必以木塞提升膛壓,槍炮裝填變得容易。
近代彈道學也逐漸成形,1537年,塔爾塔利亞出版了史上第一部射擊理論著作,把槍炮從原來的巫術領域拉到了計算與實驗的世界。
文人們忙著吹牛
在不同的軍事環境下,東西方的“爆炸性火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逐漸走進科學之后,中國卻還在以玄學為基礎探討軍火。不但本國火藥研究拘泥于舊理論,就連引進西方軍事科技的《西法神機》,在解析火藥配方時都要用上陰陽五行。
由于缺乏科學知識,一般文人都沒有準確描述軍火的能力,而往往在文字中極盡夸張之能事。《金史》介紹早期炸彈“震天雷”,說它的爆炸聲“聞者百里”;《武備志》記載手銃“單飛神火箭”,只用三錢火藥就能傷敵于三百步之外,敵軍人馬中彈后被直接射穿,一次還能貫穿好幾個。
當然,文人筆下火力強大的“嘴炮”,其缺陷一經前線將領使用就會暴露無遺。比如手持火銃“神槍”,邱濬稱其能射出百步之遠,敵人聽到槍響就已經被射中了;到了面臨實戰考驗的戚繼光手里,便發現其射出的箭矢歪來扭去,甚至常把箭屁股朝前打出去,幾近廢品。對于碗口炮,《武編》認為它聲勢很大,射擊角度調一點點,射程就變了一大截;戚繼光卻說它“腹小口大”,火藥裝填量小,炮彈又太重,發射無力,派不上大用場。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對火器吹過牛的不只中國人。1622年來華的傳教士湯若望,在他與中國人合作編著的《火攻挈要》中聲稱,小弗朗機炮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弗朗機炮仰放可到三四千步,把射程夸大了兩倍都不止。作為接受過歐洲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湯若望顯然也在他的中國生涯中習得了卓絕的“放衛星”技術。
明朝士子忙著吹牛的同時,西方火器開始進入東方,并在明朝后期戰爭中叱咤風云。弗朗機炮、嚕密炮、日本鳥銃、紅夷大炮等等西方色彩濃厚的名字,給東方戰場上的人們帶來空前的震撼。
而后又過了兩個世紀,東西方兩個世界帶著各自的軍火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并以其慘烈的戰果,引發魯迅和無數中國文人的爆竹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