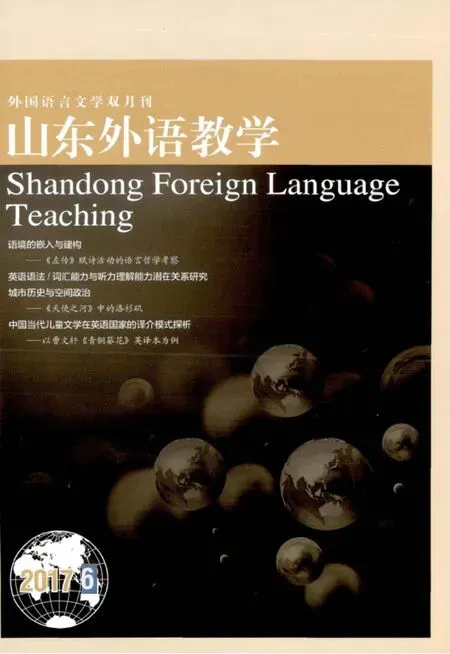譯語話語權:基于譯者主體性分析
南華, 梅艷紅
(廣西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 廣西 柳州 545006)
譯語話語權:基于譯者主體性分析
南華, 梅艷紅
(廣西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 廣西 柳州 545006)
譯語話語權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將由符號組成的話語進行語義和文化傳遞的結果,其目的是實現原語的話語意圖。本文主要是從譯者主體性角度界定譯者主體性和譯語話語權的概念及其關系,分析譯者在譯語話語權的再現與表達過程中的參與或作用發揮,闡釋在一定程度上譯語話語權也是譯者主體性的文化和權力的訴求,旨在通過譯者主體性在譯語話語權構建中的參與或作用發揮,幫助原語文化在譯語文化環境中建立屬于自己的本土語域和原語作者實現譯語話語權的再現與表達,從而促進原語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譯語話語權;譯者主體性;話語意圖
1.0 引言
譯語話語權主要關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通過適切的譯語話語形式進行語義和文化的傳遞,以實現原語話語意圖。與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研究不同,它更突顯譯者在譯語話語權力訴求過程中的獨特身份和作用。譯語話語權不僅涉及原語和譯語,還包含原語作者的說話意圖和譯者的翻譯意圖。已有文獻大多是基于譯語受眾接受(張瑜,2001)、話語意識形態(王東風,2003)、譯者話語權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金敬紅、周茗宇,2004)、譯者話語權的翻譯策略(金敬紅、張艷新,2007)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關注的是譯者主體性在譯語話語權構建中的參與或作用發揮,以及在譯語話語權中譯者主體的權力訴求和文化訴求。
2.0 概念界定
2.1 譯者主體性
譯者主體性的內涵衍生于對“主體性”的論述。“所謂‘主體性’是指行為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本質力量的外化,能動地改造客體、影響客體、控制客體,使客體為主體服務的特性”(王玉樑,1995:6),也就是指主體的能動性。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主體也會受到客體的反作用與制約,因此主體也具有受動性。但主體的能動性發揮并非是隨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所以除能動性和受動性之外,主體還具有為我性。據此,譯者主體性可以界定為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在尊重原語的前提下,在譯語中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受動性和為我性,以達到翻譯的目的。行為主體是譯者,對象性活動指的是翻譯活動。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表現得最為顯著。譯者總是會根據自己所理解的譯語文化需要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與翻譯方法,以體現譯者主體性的“為我性”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更多體現在譯者的翻譯目的上。如目的論(Skopos Theory)認為,“翻譯是在目標語情境中為某種目的及目標受眾而生產的語篇”(Vermeer,1987:29)。為達到這種目的,譯者需要發揮其主體作用。因此譯者在進行翻譯活動時,是在對原作的話語意圖進行傳遞,其傳遞過程中的語言形式或表達方式則由譯者主體決定。但鑒于翻譯活動的特殊性,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參與或作用發揮不僅需要考慮到原作者,還要考慮到讀者。換言之,“譯者主體地位的確立并不以排斥作者為前提,也不以否認讀者的作用為目的,其主體作用是與作者和讀者的作用緊密相聯”(許鈞,2009:120)。但作者、譯者、讀者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主體,而是一種共在的自我。因此譯者需要充分理解原作者的話語意圖以及譯文接受,從而選擇出適切的話語形式與話語表達方式進行原語意義和原語文化的傳遞。
2.2 譯語話語權
根據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權理論,“話語并不是簡單地根據某種語法規則將詞匯和句子進行組合,更為重要的是話語中所蘊含著的極為復雜的權力關系”(文貴良,2007:7)。“權力寓于話語語言,即一個社會群體根據某種言說規范將其自我意義傳于他者,為他者認知和接受,從而樹立其相應的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王治河,1999:56)。從中可以看出,言語所表達的不僅是語言層面的內涵或意義,更包括該言語對目標受眾的一種潛在影響力。因此譯語話語權強調的是將原語轉化成譯語之后,對譯語受眾的影響力。
但由于語言文化、表達方式以及譯語受眾等的差異,譯者傳達的譯語話語權與原作者試圖建立的話語權之間不盡相同。亦即原語作者的話語存在其目標受眾和話語意圖,由于目標受眾與原作者的語言文化環境相同,所以其話語意圖很容易實現,然而譯者的譯語受眾絕非是原作受眾,他們之間存在語言文化等差異。具體表現為:第一,當原作者的目標受眾涵括所有讀者(包括譯語受眾)時,譯者就需要通過一定的語言手段將原作者的話語意圖“真實地”轉換成譯語,傳輸給譯語受眾。第二,當原語作者的話語意圖僅僅針對原語環境中的某些受眾,而并非針對所有讀者(包括譯語受眾)時,譯者便需要發揮其主動性,對原作進行再認知,將原作中獨特的意蘊在譯語環境中樹立出屬于譯者的話語權,也就是譯者本人傳達的譯語話語權。但譯語話語權并不等同于話語霸權,譯語話語權強調的是譯語作為一種軟實力潛移默化地滲入到譯語環境當中,而話語霸權則是指話語的強勢植入,逼迫譯語受眾全面而迅速地接受外來文化。因此在“權力關系”研究中,話語霸權探究的是文化間的權力關系,征服與屈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控制。而譯語話語權中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之間并非權力關系,而是旨在將原語文化中的各種社會因素用譯語受眾能夠接受的話語形式展現出來。
2.3 譯者主體性與譯語話語權之間的關系
譯語話語權與譯者主體性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與差異。首先,譯語話語權的產生來源于兩方面。第一,譯者根據原作者的話語意圖和話語目的,盡量用最適切的譯語話語表達方式再現原作者的話語權。第二,譯者在充分理解原作之后,出于某種翻譯目的,對原作話語意圖進行改寫,從而產生譯者在譯語環境中建立起的話語權。因此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主要體現在譯語話語形式的構建以及譯語話語內容的選取;而當譯者出于某種翻譯目的,不以純粹地傳達原文的意圖為宗旨時,譯語話語權的建立則需要譯者主動解讀原作,并參與譯者自身的創造。譯語話語權與譯者話語權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時空上,即譯者話語權的產生是由于原語文本在完成之后,成為一種歷史,而歷史是無法重現的,因而讀者無法站在歷史情境中解讀作品,但譯者可以跳出原語文本的限制,對原文進行有目的的控制,顯示其獨立的話語權,將依附于原語話語之上的社會因素(如政治、經濟、文化等訴求)在譯語話語中最大限度地加以表達,強調的是譯者在原語文本“歷史”的范圍內,發揮其主體作用,即通過適切的譯語形式最大限度地獲得譯語受眾的認可,“將讀者送到國外而不是將外國作者帶回給讀者”(熊欣,2015:210)。
3.0譯語話語權的再現與表達:譯者主體性的參與
3.1 譯語話語權的再現
隨著國與國之間對話與交流的增多,各國對能夠在國際舞臺上擁有發言權的意識逐漸強烈起來,強調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在翻譯活動中,原作的翻譯也不再是簡單的語義的傳達與文化的傳遞,而是需要再現自身語言與文化在譯語環境中的訴求,說到底就是原語話語權要再現于他者語言與文化中自身權力和文化。譯語話語權并不僅僅局限于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而是在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過程中,顯示出原語的某種寫作意圖或翻譯意圖,但這種意圖卻并不能夠完全在原語文本中得以體現,這種帶有一定話語意圖的翻譯不再是“原語中心論”的實踐,也不再是“被動”或“機械”地將原語語言轉換成譯語語言形式,因此需要譯者的主動參與,幫助完成原語意圖的實現。另外,在從“語言翻譯”到“文化翻譯” 轉向中,譯者得到解放,地位和身份也得到極大的提高,譯者也從隱身變為現身,使得譯語話語權的實現成為可能,譯者能主動參與譯語話語權的實現需要。譬如,在我國外宣文本中“中國夢”的翻譯,外國媒體曾將其翻譯為 “China dream”,而我國的官方英語譯文則是“Chinese dream”。它們不同之處在于,我國的英譯版本“Chinese dream”想要表達的是中國人民的夢想,體現的是我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中國夢的實現者;而譯語“China dream”表達的僅僅是國家作為上層建筑想要實現的夢想,是“中國國家之夢”,并沒有深入到人民的層面,也未體現出人民主體的內涵。這充分說明在譯語環境中完成譯語話語權的再現,需要以語言的考究為基礎,在譯者根據某種翻譯目的參與翻譯過程中達成,從而使一個國家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總是有意識地將一些本國的因素(政治、經濟、文化等)移植到目的國,再現譯語話語權,實現在他語語言文化中譯語話語的自身權力。
因此,譯語話語權的再現不僅要仰仗原語作者的寫作意圖,也要仰仗譯者的翻譯目的和具體的譯語語言形式的構建。而在此過程中,無論是原作者寫作意圖的再現,還是翻譯目的的實現,都需要譯者的主動參與,幫助原語在譯語語言環境中建立譯語話語權。
3.2譯語話語權的表達
“譯語話語權主要是關于譯語在譯語環境中對譯語受眾產生的影響力,即譯者通過合適的譯語表達方式最大限度地獲得譯語受眾的接受和認可,謀取話語主動權,達到對外傳播的根本目的”(熊欣,2015:210)。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譯者需要參與譯語話語權的表達,從而改變譯語話語權的影響層面及影響力。譬如,為促進國家更好地融入世界的舞臺,在文化傳播過程中,譯者應盡可能地貼近原語文化國家的語言風格,充分保留并凸顯原語文化特色,實現譯語話語權的表達。以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詞匯英譯為例,從最初為英語受眾所接受的中國英語“豆腐(tofu)”“麻將(mahjong)”“風水(fengshui)”“陰陽(yin-yang)”等,到最新的熱詞,如“土豪(tuhao)”“大媽(dama)”等,譯者一般采用“音譯”、“直譯”或“音譯加注釋”等異化策略,實現譯語話語權的表達。盡管這類熱詞的翻譯并不完全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和方式,但是卻也逐漸地被英語受眾接受和認可,甚至收錄到《牛津詞典》當中,為英語國家受眾所用。這些內涵豐富且具有獨特思想和詼諧語音的文化詞的英譯看似是在對譯語文化實施語符暴力,然而卻使譯語更易獲得話語權,并通過譯語話語的表達將通俗且富含時代氣息的中國新詞匯移植到譯語國家中,折射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話語影響力。
因此,譯語話語權力的實現不僅指原語語言轉換成譯語語言或譯語話語形式,更涉及對原作者寫作意圖的理解和解讀以及對譯語受眾接受能力的思考。同時,譯語話語權的表達并不是原語文化的語符的暴力植入,也不是選用譯語語言中某個語義相似或相關的詞匯進行代替,而是透過譯者的加工或再創造,以一種平和的方式傳播到譯語語言之中。
4.0譯語話語權:譯者主體性的訴求
4.1譯者主體性的權力訴求
正如福柯所說,我們生活在話語的世界里,話語是“權力”的表現形式,而所有的權力通過“話語”來實現(王治河,1999)。在翻譯中,任何譯語都暗含某種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一方面由原語作者的寫作目的決定,該目的暗含著原作者的某種話語意圖和話語權力,并且任何作品的產生也一定存在作者對讀者輸入某種思想的期待。譯者的參與,無論主動還是被動,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譯者主體性的權力訴求。
譯者主體性的權力訴求是指譯者幫助原語主體在譯語環境中實現其話語活動的話語意圖。原作者、原語讀者、譯者以及譯語讀者之間的關系復雜,一方面,原作者寫作的意向讀者不一定是其譯文的期待讀者,所要表達的思想以及暗含在原作品中的話語權力在譯語中很難顯現出來,或者說很難為譯文讀者所發現。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語言文化以及歷史條件的差異,原話語主體話語活動的訴求需要借助譯者的參與才能達成,突顯譯者的主動參與性,尤其是在幫助原話語主體在他語文化中實現其話語意圖、話語權力方面。如以前在他語文化環境中,中國特色類的譯語話語并不多見,“中國常常處于一種‘失語’、‘失聲’的狀態”(熊欣,2015:210)。外國人對輸入的中國商品起些“外國名”,如絲綢(silk)、茶葉(tea)、陶瓷(china)等等,在今天看來,這樣的翻譯完全符合英文的表達習慣和語言風格,但是從這些商品的英文譯名上看,英語受眾卻絲毫看不出這些是中國生產的商品。這說明譯者并不是通過語言植入的方式將原語文化移植到英語環境之中,而是借助譯語的語言形式或表達方式將本土文化融入到譯語文化中。
因此,在對外傳播原語文化時,譯者應在充分考慮原話語主體話語活動的訴求的基礎上,采用適切的譯語話語形式傳達原語的訴求,甚至在需要的情況下,創造出屬于原語文化的譯語話語形式,從而實現譯語話語權力的表達。但是這樣的傳播方式需要譯者充分發揮其主體創造性,創造出符合譯語話語表達習慣,描述或指代原語文化的話語形式。
4.2 譯者主體性的文化訴求
由于譯者從事的翻譯行為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之間的轉換活動,譯者除幫助原作者達成其寫作意圖之外, 還應在語言上盡量再現原語文化, 同時實現譯者主體性的文化訴求。傅雷在《傅雷家書》中寫到:“唯有不同種族的藝術家,在不損害一種特殊藝術的完整性的條件之下,能灌輸一部分新的血液進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完滿,愈來愈光輝燦爛”(董明,2006:12)。正是由于“新的血液”的存在,翻譯才具有藝術性和審美性。通過譯者傳遞的原語文化信息或意義,不僅使譯語受眾在不同文化之間產生心靈的碰撞,還對自己國家的文化產生更深的認識和了解。
然而,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由于文化的民族獨特性,一般情況下,譯者很難,甚至幾乎不能找到功能相似的譯語表達形式進行表達,因此譯者多采用音譯,或“音譯/直譯+釋譯/詮釋的譯法”(熊欣,2015:210)進行文化詞語的翻譯。如在2015年11月份的“習馬會”中,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帶給習近平主席的禮物“臺灣藍鵲”和“馬祖老酒”富有中華民族民俗文化的風韻。那么譯者是如何將這兩份賦有中華民族民俗文化的禮物的意象傳遞給其他國家的受眾的呢?手工瓷器“臺灣藍鵲”的官方譯文是“a handmade china carving of a blue magpie”,譯者采用的是 “直譯+釋譯”的翻譯方法。“藍鵲”(blue magpie)字字對應,喜鵲(magpie)在漢語文化中是好運與福氣的象征,如“喜鵲叫,好事到”,對外界傳達出兩岸關系和平友好的含義。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鵲”在不同語言文化環境的意象的區別,就不難發現,盡管在漢語文化中,“鵲”代表的是幸運,但在英語文化中卻是“噩兆”的象征,詩人John Clare曾寫道:Magpie that chatted, no omen so black(鵲噪是最壞的兆頭),那么若譯者將“藍鵲”翻譯成“blue magpie”,不但與其原先的翻譯意圖相悖,而且還沒有達成譯者的傳遞原語文化的訴求,反而傳遞一種負面的情感給譯語受眾。“馬祖老酒”的官方譯文是“vintage rice wine made in Taiwan”。官方的譯文采用的是釋譯,即將酒的成分和產地翻譯出來,目的在于譯語受眾可以直觀地了解“馬祖老酒”的成分以及釀造方式。但是,如果我們把“藍鵲”音譯處理成“Lan Que”,“馬祖老酒”音譯為“Ma Zu Lao Jiu”,只傳音暫不傳意,不僅可以激發英語受眾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且還促使他們了解其中包含的中國文化寓意,以此達到傳播中國文化以及得到譯語受眾的認可的目的,進而建立起漢語在英語環境里的話語體系。“盡管在譯語話語中話語體系的建立絕非是譯語受眾自動給予的,它需要譯者通過恰當的譯語語言和文化轉換去主動爭取更多的受眾認同”(熊欣,2015:211),但譯者卻可通過把握譯語受眾的好奇和探究的心理,促使譯語受眾主動探求原語文化的內涵,這就為譯語話語中原語文化的建立減少話語開拓的難度,從而達成譯者傳播原語文化的訴求。
原語文化的傳播并非是簡單的音譯過程或簡單地將原語文化符號硬生生地移植到譯語體系當中,而是在譯者充分考慮譯語受眾的“期待視野”,即文化背景、興趣、需求等因素之后呈現的翻譯方式,因為只有被譯語受眾接受并認可的原語文化才算真正得到傳播,才能在譯語環境中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領地,從而滿足譯者主體性的文化訴求,實現譯語話語權的再現與表達。
5.0 結語
譯語話語權的建立不僅關系到話語主體在譯語環境中的語言存活度,也關系到其文化的傳播,但譯語話語權的構建則很大程度上由譯者決定,也是譯者主體性的文化與權力的訴求,所以譯者對于譯語話語權的建立具有很大的主動參與性。通過譯者主體性在譯語話語權構建中的參與或作用發揮,不僅有助于原語文化在譯語文化環境中建立屬于自己的本土語域,而且還有利于原語作者實現譯語話語權的再現與表達,從而促進原語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1] Vermeer, H. J.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J].Indian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 1987,(2):29-37.
[2] 董明. 翻譯:創造性叛逆[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3] 金敬紅,張艷新. 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J].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451-455.
[4] 金敬紅,周茗宇. 從“隱形”翻譯看譯者的主體性[J].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452-454.
[5] 王東風. 一只看不見的手——論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操縱[J]. 中國翻譯,2003,(5):16-23.
[6] 王玉樑. 論主體性的基本內涵與特點[J]. 天府新論,1995,(6):34-38.
[7] 王治河. 福柯[M].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8] 文貴良. 話語與生存:解讀戰爭年代文學(1937-1948)[M].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
[9] 熊欣. 對外傳播中的“譯語話語權”[J]. 湖南社會科學,2015,(8):208-211.
[10] 許鈞. 翻譯概論[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11] 張瑜. 權力話語下的讀者接受[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01,(2):58-61.
AnalyzingDiscourseRightofTargetTextfromthePerspectiveoftheTranslator’sSubjectivity
NANhua,MEIYan-h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Guangx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Liuzhou545006,China)
Discourserightoftargetlanguageisdesignedtotransmitthesemanticmeaningandtheexoticcultureofthesourcetext,anditsaimistoconveytheintentionofthediscourse.Fromtheperspectiveoftranslators’subjectivity,thispapermakesananalysisofthereasonsandrolesoftranslators’participationinbuildingdiscourserightofthetargettextonthebasisofthedefinitionsoftranslators’subjectivityanddiscourseright.Toestablishtheindigenousregisteranddiscourserightofthetargetlanguage,ananalysisismadetoexploreexpressionofdiscourserightandculturefromtheperspectiveoftranslators’subjectivityinordertopromoteculturalexchanges.
discourserightofthetargettext;translator’ssubjectivity;discourseintension
10.16482/j.sdwy37-1026.2017-06-011
2016-07-29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對外傳播中的譯語話語權研究”(項目編號:16BXW052);廣西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課題“產學結合背景下地方高校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協同培養機制研究”(項目編號為JGY2015117)的階段性成果。
南華(1973-),男,湖北浠水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研究方向:英漢翻譯、英語學科課程與教學論。
梅艷紅(1992-),女,江蘇南通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H059
A
1002-2643(2017)06-0094-06
楊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