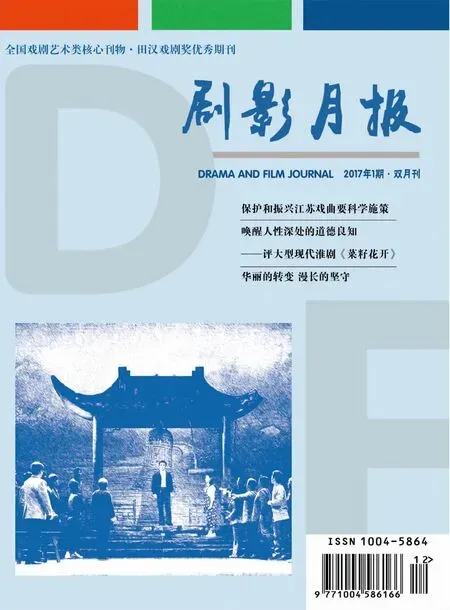二胡協奏曲《春江水暖》第一樂章中的音色描述
■顧懷燕
二胡協奏曲《春江水暖》第一樂章中的音色描述
■顧懷燕
二胡協奏曲《春江水暖》是金復載先生在1994年創作的二胡作品。樂曲取自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詩境:“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在這類詩情畫意的、以景抒情的樂曲中,色彩性的描繪特征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也正因為這樣,在對此類樂曲的演繹上,通過捕捉色彩來進行音色的選擇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樂章為奏鳴曲式,整個樂章的標調是G大調。主題的呈示為G宮調,在樂隊兩小節的間奏后進入:(見譜例一)。

譜例一
這是主題的首次亮相,代表著這個樂章,乃至整個協奏曲的基調——綠色。這既是色彩,也是形象。可是綠色有很多種,怎么區分呢?
首先看調性:G大調的聽起來是平穩的、清晰的、不張揚的明亮;其次看調式:宮調式的色彩是端正的、光明的、親切的;再看協奏聲部與主題的和聲:協奏聲部的兩小節前奏和主題呈示的前兩小節和聲都沒有變過,是G宮和弦,第5小節其實已經離調到了D宮,但是低音“G”卻還持續地保留著,可是為什么不說這只是加了變宮“F#”的G宮呢?在10到12小節的鋼琴縮譜中可以看到,主題出現在了協奏聲部,而在同第5小節一樣的12小節里,和聲是D宮系統的,而且這小節主題的旋律走向也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至于為什么要在第5小節持續使用低音“G”,一是因為先要鞏固“G”這個綠色的基調,二是通過“G”來淡化D宮和弦明亮、燦爛的色彩,以符合主題“不張揚的明亮”的特質,三是為了第7小節的D宮出現時而保留的新鮮感。第6小節的兩個和弦G宮和G徵的交替,用它作一個轉折點,亮出后面兩小節的D宮和D徵的交替。一方面來說,G轉到上方五度的D,有一種向上的、升華的、強調的、明媚的色彩,在主題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出現D色彩充分顯現了音樂形象的豐滿和層次感,并為下文(副題)埋下伏筆;另一方面,連續三小節的宮徵對比的色彩交替也是點題——水,讓人有蕩漾之感,從“水”這個角度來聽這兩個和弦:“宮”是伏、是流淌,“徵”是起、是回溯。第9小節轉到具有下屬功能性質的C宮和弦,色彩含蓄、內斂、平靜、回歸,在最后一拍進入屬功能的D,然后結束二胡聲部的主題,轉入樂隊。綜合這些,主題呈示的顏色是春天所特有的,鮮活、清新、平和、充滿期望的、心曠神怡的、明亮而不張揚的綠,其中還帶有偶爾的燦爛的閃爍,或者是含蓄的、回歸的情感涌動。
主題的完整呈示在獨奏聲部僅僅是這一次,它代表了整個作品的主旨,至關重要。通過對這些調性、調式的分析,可以捕捉到在綠色基調下的、時刻變幻著的色彩。演奏上,首先要抓住綠色基調,這是整個作品的基本音色。弓毛不能太緊,要調得比較松弛,讓每一根弓毛都能在弦上得到充分的摩擦,弓桿走直走平,右手臂放松,力量集中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換弓盡可能地連綿,減少痕跡;左手按弦盡量靠后,用指腹肉墊較厚的地方,揉弦時力量集中在指尖,多用音波較大的滾揉,而且單個音波的進行要從偏低到準。這些做到后,音色就會顯得圓滿、平和、潤澤、清透、松弛,有綠色的春天的氣息。然后,在這個基礎音色之上,可以視樂句中調性調式的色彩變化作出相應的音色處理。比如說表現“不張揚的明亮”時,揉弦就不能過快;第7小節出現D宮的明媚色彩時,弓要拉開,弓速和揉弦幅度都要增加,并且要不過火地稍稍強調一下,亮出第八小節的第一個音“B”,它是主題的最高音,也是主題情緒的最高點,它正是前面提到的所謂“偶爾的燦爛的閃爍”,這三小節宮徵交替的流淌之感并不單是樂隊的任務,獨奏也要就著旋律本身的起伏依靠運弓來表現“蕩漾”的形象,運弓要連綿,避免生硬,可是也不能連成一片,要有層次感;第9小節是主調的下屬和弦C宮,色彩柔和,有朦朧的美感,運弓的速度和力度都要減弱,顯得悠遠、寧靜、回歸。
只要能夠掌握這個綠色的基調,就已經理解了整個音樂作品的氣質。這種氣質會讓“春江水暖”這個形象清晰地顯現于音色之中,下面的副題等內容則是豐富和具體化了這個形象,使它展現出不同的側面。
在第一樂章中,副題一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呈示自第25小節進入,至32小節:(見譜例二)

譜例二
副題的旋律線較主題相比,更平穩、悠緩些,起伏中展露出更多局部的細致的描繪,和愜意的情致。
第一次副題的出現為A宮系統的E徵調,從主題的G宮到副題的E徵,這種色彩的對比是怎樣的?上方大二度的調性,也許意味著“亮出”;徵調式與宮調性對比,也許是更深切的情感。但是主題與副題的第一次出現并不單純的是從G宮到E徵的簡單的色彩轉換,在它們中間長12小節的連接部中,經過了數個調性調式的變化——先從G宮到上方五度的D宮調,再轉為D宮系統的b羽調,又回到G宮系統的D徵和G宮,但這時的G宮只是下文C宮的屬方向,接著是C宮系統的G徵、d商,然后進入C宮調,樂隊演奏主題,離調到e羽,進入副題下屬方向D宮系統的e商和A徵,然后是屬,——最終轉到A宮系統的E徵調。孤立地分析A宮的色彩是不夠的,看G宮到A宮的色彩對比還是不夠的。從這12小節的調性調式變化可以發現,主題到副題的色彩對比絕不僅僅是上升一個大二度那么簡單,這是分析副題色彩的第一個方面。第二個要看的是副題前兩拍的和弦性質(見譜例三)。

譜例三
很明顯,第24小節的最后兩拍是A宮調的屬和弦,典型的終止式,進入A宮。可是在主題結束的終止式中,也就是第9小節的最后兩拍(見例一),獨奏的旋律和第24小節樂隊的旋律相同,而和聲卻在下屬方向,最后的八分音符才出現了屬音“D”。這里作曲家淡化了終止式,而且前后的調性原本就是一樣的,這樣處理也顯得流暢、連綿,更加自然。用這個來對比副題出現前兩拍的典型的終止式,仿佛作曲家在強調和加固這里的調性的轉變,十分清晰地引出副題。經過這些色彩的起伏明暗變化,副題“千呼萬喚始出來”,令人耳目一新,有種新鮮、舒緩、穩定、祥和的感覺。如果說主題是贊嘆畫中美景,副題便是身臨其境。A宮的出現,帶有明媚、盛裝、清澈的色彩,第28小節離調至b羽調,色彩暗下來,這里的暗不是黯淡陰渾的感覺,好象只是一片淡淡的云飄過,遠遠的,高高的,遮住了一些陽光,有點朦朧罷了。樂句的最后兩小節(第31、32小節)結束在E徵調上。整個第一副題明媚、悠遠、恬淡,是初春最淺、最淡、最嫩、透著點黃的綠。
第33、34小節樂隊聲部在D宮調上出現主題的片段,像一陣清風拂過,吹散了b羽調的那朵云,引出獨奏聲部燦爛、明亮、鮮活、溫暖、熱情、閃爍著金色粼粼波光的第二次副題(見例二)。在這里有一個疑惑:這次副題出現在D宮調上,正好是主題的上方五度調,這是副題的重要調性特征。而上次副題出現在A宮調上,是主題的下屬方向調,而且副題的呈示淺嘗輒止,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與這次的相比,顯得低調很多。所以也可以說,所謂的副題的第二次出現,其實卻是副題的真正意義上的呈示,樂隊聲部的織體在這里、也發生了變化。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三#的A調應該比兩#的D調色彩上更加明亮,可是在這里卻相反,就是這個緣故。每個調性或調式固然具有各自本身的色彩,但這只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樂曲環境,色彩也會發生改變。前兩小節與上次的呈示是相同的,第37小節卻轉入了C宮調,是D宮的下屬的下屬調,和聲的內在空間被瞬間拉開,色彩清澈、深邃、柔和,有移步換景之感。第40、41小節是a羽,也同是C宮系統,然后是b羽、G宮,最后結束并沒有像上次一樣停在徵調式上,而是停在了a商,整個樂句色彩的明暗、起伏、遠近的層次十分清晰自然。
第95小節開始是第一樂章的再現部,主題由樂隊在C宮調上奏出,之后從第103小節開始,是副題的最后一次完整出現:(見譜例四)

譜例四
主題在樂隊聲部中再現時用了C宮調,調性本身就有純凈的色彩,而且C宮調同時又是樂章主調G宮調的下屬調,使再現部在一開始就營造出了一種純凈、平和、優雅的氛圍。在這個基礎上,獨奏又在C宮調的下屬調F宮系統上再現副題,更加顯出幽深、恬淡、寧靜、漫溯的意境。然而這一次又是副題中和聲變化最豐富的,第103、104小節都是F宮和弦,之后的每一小節都是不一樣的,從第105小節開始,依次是:C宮、d羽、a羽、G宮、D徵、D宮、C宮、G宮,再回到F宮,呈現出層次豐富、明暗交融、色澤斑斕、隱隱透出金紅色的霞。作曲家用這些更多的和聲變化來平衡下屬的下屬調在調性上略有偏暗的色彩,使副題的再現在寧靜的回歸中不失活潑的變化,同時也把再現部轉化成為一種偏向內在的,更加深邃的、豐富的、飽滿的、立體的情感涌動,這非常關鍵,是景和情這兩個不同側重點的轉換。
在演奏上,運弓需要更加地松弛和舒緩,音量為mp,但是左手的按弦卻要比先前略有加重,這樣演奏出的音色結實、清透、含蓄、內斂,揉弦可以依據每小節不同的色彩作快慢和大小的調整,運弓也根據揉弦作出相應變化,使這次副題的再現展現更多主觀因素的情感流露。
副題的三次出現調性調式的不同,使各自有了鮮明的色彩的個性對比。這使得演奏時的音量、運弓和揉弦的方法、速度都有不同的講究。第一次的副題呈示音量和速度適中,運弓連貫而清晰,揉弦偏淡,是透著點嫩黃的草綠色,演奏力度在p的范圍內,清新而柔軟。第二次的副題得到詳盡的發展,煥然一新,色彩明亮熱情,運弓要舒展、飽滿,揉弦音波幅度加大,音量在整體較強的前提下作出較大的起伏對比,首先用f的力度亮出,是燦爛的金色。第三次是副題的再現,運弓平穩而內在,揉弦按弦力度稍有加大,更多地偏重情感的抒發,是朦朧而深邃的金紅色,力度mp。了解了這些,三次副題演奏起來就不會聽上去差不多,毫無層次感,而是一個音樂形象的不同角度和側面,都具有各自鮮明的性格和特征,在一個整體中發展、推進、升華。
經過對一個音樂作品調性、調式的細致入微的分析和體會,以感受到的色彩,通過演奏家用實際的音響結構表現出的音色,它所構件的是這個作品的音樂形象。音色在塑造音樂形象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音響結構的第一直觀感受,尤其是其中色調的變化,使音樂形象的塑造由表及里地被聽者所感受。音樂形象就建立在對音色的異質同構的聯想中,它是由演奏家在演奏時由色彩和情感搭建起來的。搭建形象的同時,也同樣體味出了音樂作品的意蘊,正是這些富于變化的音色,幫助聽眾在腦海中塑造音樂作品的形象,感受到作品的情感和內在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