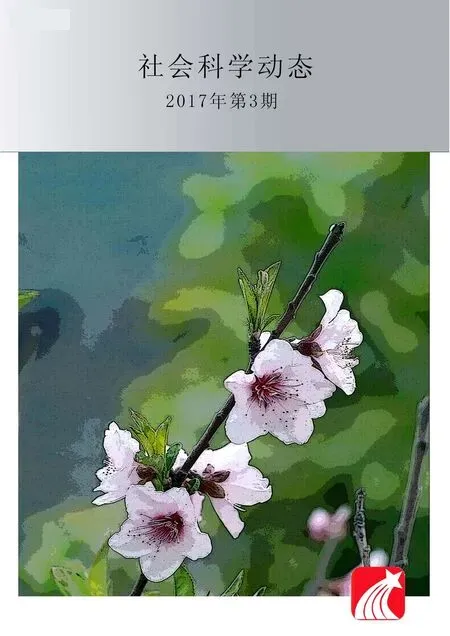唐代宦官管理制度述論
杜文玉
唐代宦官管理制度述論
杜文玉
唐代宦官管理機構前后變化頗大。唐前期主要由內侍省進行管理,唐后期分別由樞密院與宣徽院進行管理,內侍省僅負責對宮廷內部事務及雜役的管理。南衙諸司只是針對宦官的勛爵、品階、蔭補、俸祿等方面進行協調,并不過問宦官的選用、升遷、差遣、獎懲等事,一切均以皇帝的制敕為準。
宦官階層;內侍省;樞密院;宣徽院
中外學術界對唐代宦官專權以及內諸司使制度的研究較多,但是對有關唐代宦官管理制度的研究卻極少,即使對樞密院、宣徽院有所研究,也很少從宦官管理制度的角度切入。遂使有些相關問題至今說不清楚,而這些問題又比較重要,有必要將其一一論述清楚。
一、內侍省的管理職能
唐朝前期的職官制度實行的是分塊管理的體制,即朝官歸宰相管理,宦官歸內侍省 (或內坊)管理,宮人歸宮官系統管理,即所謂六尚二十四司。這三個系統互不統屬,平行發展。即使針對它們的監察體制也不相同,朝廷文武官員由御史臺監察,宦官階層由內寺伯負責,宮官則由宮正負責,御史臺不能干預內寺伯、宮正的工作,甚至連工作指導關系都不存在。 《后漢書·宦者傳》 載:“《易》曰: ‘天垂象,圣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 《周禮》置官,亦備其數。”古人認為宦官的設置取于天象, “后世因之,才任稍廣”。①因此宦官的出現與設置,自古以來就與朝官不屬于同一系統,在管理上也有異于朝官。
唐內侍省在設置之初,唐太宗出于對歷史經驗的借鑒,防止出現宦官專權,故不為其置三品官,內侍僅為從四品上的官階,有意使內侍省的地位低于三省六部、九寺等南衙機構, “但在閤門守御,黃衣廩食而已”。②在這一時期由于宦官并不出宮充使,與南衙其他機構沒有多少事務往來,雙方長期相安無事,內侍省所屬人員自然由其內部管理,也很少見士大夫們對宦官提出指責。從內侍省的管理職能看,內侍為其長官,除了維護本省的正常運轉外, “總掖庭、宮闈、奚官、內仆、內府五局之官屬。”即內侍省所屬大小宦官皆歸其管理。如果內侍省所屬人員有不法之事,則由內寺伯負責糾察懲處。宦官的遷轉、獎賞,亦由內侍、內常侍負責,重要的人員則要報皇帝批準。史載: “元和十五年四月,內侍省奏:應管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云云。③從 “應管”二字也可以看出,宦官的日常管理應在內侍省。
內侍省所屬五局均分管宮中各種事務,涉及人員管理事務的主要有三個局,即掖庭局、宮闈局、奚官局。其中掖庭局涉及到有關宮人的管理事務,所謂 “凡宮人名籍,司其除附”,即宮人的名籍檔案歸其管理,日常管理則歸于六尚二十四司。此外,對宮人的文化、才藝的教育亦歸掖庭局,具體由宮教博士負責。真正負有管理宦官職責的是宮闈局,不過其所管對象為低級宦官,所謂 “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親王府名散使。若有官及經解免應敘選者,得令長上。其小給使學生五十人。皆總其名籍,以給其糧廩。”宦官中曾經有官職,解免后重新敘選者,亦歸其掌管。宮闈局不僅掌管宮中小給使,親王府的給使即散使,亦歸其管理。奚官局掌管 “宮官品命”,女官及嬪御的廢黜亦由奚官局管理,史籍中常有失寵嬪御被幽禁于內侍省的記載。奚官局還掌管一些事務, “凡宮人有疾病,則供其醫藥;死亡,則給其衣服,各視其品、命,仍于隨近寺、觀為之修福。雖無品,亦如之。”宦官的喪葬之事不由內侍省管理,應歸鴻臚寺掌管。④
內坊為太子東宮的宦官機構,設典內2人為長官,主要掌管東宮閤內之事,包括對東宮系統的宦官管理。在唐前期其與內侍省并不存在隸屬關系。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739)四月二十八日敕曰:“義方之訓,固在親承。太子既絕外朝,中官自通禁省,有何殊異,別立主司!其內坊宜復內侍省為局。”⑤因為在這一時期太子不居東宮,移住于少陽院,所以玄宗將內坊并入內侍省,成為其下屬的一個局。從 “有何殊異,別立主司”一句看,也說明內坊在此之前是獨立于內侍省之外的另一機構。
天寶十三載 (754),玄宗在內侍省增置內侍監2員,正三品,從而打破了內侍省不置三品官的祖制。唐后期宦官專權擅政,權勢熏天,許多宦官在外充使,并不在內侍省供職,不過從唐朝關于宦官必須帶有內侍省官銜的規定看,他們還是與內侍省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二、宣徽院的管理職能
唐長安大明宮內置有宣徽院,據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 載: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舊官也。置院在樞密院之北……”⑥樞密院位于中書省之北,而中書省位于月華門之西,所以宣徽院的具體位置應在月華門西、樞密院北。⑦宣徽院分為南、北院,“二使共院而各設廳事”。⑧宣徽院設置于何時?史書沒有確切的記載,馬端臨說: “樞密、宣徽院皆始于唐,……蓋因肅、代以后,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⑨有學者據此認為宣徽使當產生于唐代宗大歷年間,而樞密使建立在永泰二年 (766)。⑩實際上永泰二年所設僅是掌樞密,并未有使名, 《冊府元龜》載: “憲宗元和中,始置樞密使二人。”原注: “劉光琦、梁守謙皆為之”。?其實是錯誤的。據 《資治通鑒》卷 237元和元年 (806)八月條載,劉光琦時任“知樞密”。 《梁守謙墓志銘》說他元和四年才 “總樞密之任”。?可見他們兩人并非同時任樞密之職,也未稱使。根據 《資治通鑒》等有關史書看,樞密使名的出現應在長慶三年 (823)至寶歷二年(826)之間,并同時設置了2人。約在宣宗時出現了樞密院,至唐末樞密院機構有所擴大,并分為東、西兩院, “東院為上院,西院為下院”。?從這一過程看,宣徽設使建院當在大歷之后,因為上引馬端臨之文也說 “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也就是最初其并沒有相應的機構。已出土的較早的碑志資料中有 “宣徽供奉官”、 “宣徽庫家” 的記載,但卻未見院名與使名出現,直到唐憲宗元和八年才出現了宣徽院的記載?,文宗、武宗時出現了宣徽北院使?,既有北院當有南院之置。據此推斷,宣徽正式建院應在憲宗時期,亦有可能在德宗貞元時期。
宣徽院除了置有宣徽使、副使外,還置有宣徽承旨、宣徽供奉、宣徽庫家等官職,其中南院使地位比北院使略高。唐長孺認為唐代宣徽院統管北衙諸司,其長官地位與樞密使相亞。?史稱: “樞密、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宣徽院的下屬機構分為四案, “曰兵案,曰騎案,曰倉案,曰胄案”。?關于其職能,宋人徐度的 《卻掃編》卷下有詳細的記載,錄之如下: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北院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群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圣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圣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武臣多以節度使或兩使留后為之,又或兼樞密。
從 “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一句可知,宋代宣徽院的這些職能是沿襲唐制而來的,故可反映唐時的情況。據此可以將宣徽院的職能歸結為三個方面:其一,掌管北司諸使、崇班內侍名籍,包括供奉于內廷的各種技術人員以及諸司所屬之工匠、兵卒名籍,涉及整個宦官系統;其二,管理各種郊祀、朝會、宴會、典禮的供應與服務;其三,管理內外進貢物品。?其中最重要的職能是對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的管理,故古人在總述宣徽院職能時,只說 “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
宣徽院管理內諸司使的情況,由于史籍及政書均未有記載,從一些史籍與碑志的零星記載,也可以反映出這一點。比如內諸司使之一的五坊使,《舊唐書·裴度傳》有 “宣徽院五坊小使”的記載。胡三省亦曰: “五坊屬宣徽院”。?《冊府元龜》卷101《帝王部·納諫》載:五坊, “宣徽院供奉官為其使”。內教坊使亦為內諸司使之一, 《冊府元龜》卷533《諫諍部·規諫十》有 “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等語。唐文宗開成 (838年)三月 “辛未,宣徽院 《法曲》樂官放歸”。?《法曲》則為教坊所掌。唐內諸司使中有內酒坊使之置,在陜西耀縣出土了一批唐代銀器,其中一件銀碗刻有 “宣徽酒坊宇字號”字樣。?西安西郊魚化寨出土的一件唐代銀酒注底部共有62字,上有 “宣徽酒坊……地字號”字樣,為咸通十三年 (872)造。?據此可知酒坊使亦歸宣徽院管理。唐人李磎 《授內官韓坤范等加恩制》中有: “宣徽小馬坊使”、 “宣徽含光使”等字樣。?前者為唐后期的另一馬政管理機構,與飛龍使對掌國家馬政。唐長安西內苑中有含光殿,含光使當是掌管其事的使職。此外,還有宣徽雞坊使的記載?,亦是內諸司使之一。由于史料欠缺,尚無法找出更多的例證,盡管如此,亦可證明宣徽院的確掌管內諸司事務。
宣徽院既然統管內諸司事務,地位較低的使職自然不在話下,內諸司使中的一些高級使職,如飛龍使、軍器使、內弓箭庫使等,是否亦歸其管理呢?從制度上看,應當歸于宣徽院,白居易 《賀雨》詩云: “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此詩寫于元和三年,由于自冬至暮春,沒有降雨,憲宗為此下罪己詔,并采取赦宥囚犯,釋放宮女,減少廄馬等一些措施以祈雨。這句詩將宣徽院與飛龍廄相聯系,說明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以上這幾種使職地位雖高,仍然排在宣徽使之后,他們與宣徽院的關系只是業務統屬關系,其遷轉獎罰自然由皇帝負責,宣徽院能決定的,只是普通宦官的遷補、假故、鞫劾。
關于宣徽院與內諸司的關系,從唐哀帝天祐二年 (905)的一道敕文亦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云:“樞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并停。其樞密公事,令王殷權知。其兩院人吏,并勒歸中書。其諸司諸道人,并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并于中書論請。”?文中所謂 “諸司”,就是指內諸司,所謂 “諸道人”,是指在諸道從事各種差遣的宦官 (不包括監軍使)。以前內諸司使及在諸道辦事的宦官,凡有公事皆詣宣徽院,由于宣徽院已停廢,所以這道敕令要求其到中書門下論請。
有一點需要說明,自唐后期設置宣徽院以來,內侍省雖然仍然保留,但其許多職能已被宣徽院侵削,尤其是對內給使及宮人的管理事務,已完全轉移到了宣徽院。至于宣徽院所掌管的其他事務,由于與宦官管理制度無關,就不多說了。
三、樞密院的管理職能
唐代樞密院亦分為上、下兩院,其長官樞密使與兩神策中尉合稱 “四貴”,為宦官階層的首領之一,權勢極大,位在宣徽使之上?,宣徽使再向上升遷,即可任樞密使。由于其地位尊貴,故任命樞密使時皆降白麻,如唐僖宗廣明元年 (880)五月,“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于閤門出案,與將相同。”胡三省注曰: “唐制,凡拜將相,先一日,中書納案,遲明,降麻,于閤門出案。”?中書省掌黃、白麻詔書,其中白麻用于任命將相大臣,唐后期由翰林學士院獨掌。樞密使掌機密,可赴政事堂與宰相共同決策軍國大事,甚至有決定宰相人選的權力。唐武宗拜崔鉉為相,史載: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 ‘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之所以引起老宦官的埋怨,是因為樞密使有權參與此事而沒有預聞之故,可見其權力之重。有關樞密使的研究成果甚多?,就不多說了。下面將其管理宦官的職能論述如下:
憲宗元和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锜叛亂平定,憲宗下令將其聚斂的財富運到長安,翰林學士李絳與裴垍諫曰:
锜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愿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 “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
既稱 “故事”,可見是一貫的做法。遣宦官充使赴諸道是唐朝長期以來的做法,本不奇怪,問題是為什么由樞密使派出中使?而不是宣徽使,這一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解答。還有一件事也非常令人費解。史載: “荊南監軍使呂令琮從人擅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觀察使韋長無法制約監軍使,不向皇帝申奏,反而申狀于樞密使,那么樞密使與監軍使之間是什么關系?
敦煌文書伯3723《紀室備要》共3卷?,是鄉貢進士郁知言為 “護軍常侍太原王公”所草擬的書儀性質的文書,其中卷中專門針對擔任各種官職的宦官,為首的有中尉、軍容、長官、兩軍副使等,共計32首題目,而宣徽使排內諸司使中的第9位,顯然在諸道監軍使的心目中宣徽使并不十分重要。為首三位宦官,中尉即神策中尉,軍容是指觀軍容使,都是權勢顯赫,不容輕視的大宦官。排在第三位的 “長官”是指什么人?文書中沒有點明,只是說 “今者秉握璿樞,調和玉燭;九有戴勛天之德,萬邦瞻捧日之榮”云云。 “秉握璿樞”,指掌握中樞機要, “調和玉燭”,是指與皇帝很親近。在唐代宦官中只有樞密使的地位與職能才與這種說法相稱。另據日本僧人圓仁所記:會昌三年 (843)六月三日, “以內長官、特進楊欽義任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當日便上任。”?楊欽義在此之前與劉行深同任樞密使,可知在唐代樞密使也被稱為內長官,所以文書中的 “長官”就是指樞密使。由于樞密使是諸道監軍使的頂頭上司,所以監軍使遂稱其為長官。?
關于這一結論,還有一些旁證可以進一步證明。唐武宗會昌中討伐昭義鎮,調集諸道大軍圍攻,卻久久不能得手。宰相李德裕分析軍情后認為其弊有三: “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于是,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李德裕之所以與兩樞密使商議此事,而沒有找擁有禁軍兵權的神策中尉,根本原因就在于諸道監軍使皆受樞密使節制。另據 《新唐書》載,楊復恭任樞密使時, “以諸子為州刺史,號 ‘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說楊復恭收養600名宦官為諸道監軍,當然是一種夸大之辭,然而其在諸道監軍中大量地收養假子,與其任樞密使不無關系。
弄明白了這一問題,上面的疑問便迎刃而解了。需要說明的是,樞密使與諸道監軍使之間雖然存在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但是監軍使的遷轉還是以皇帝的制敕為準的,不過以樞密使之權勢,操縱此類事務不過是舉手之勞,這是監軍使們畏懼樞密使的根本原因。
四、南衙諸司與宦官管理
在宦官管理制度方面,唐制與宋制的最大不同,就是唐朝并沒有專門針對宦官階層另搞一套制度,即在散官、勛爵、俸祿、章服等方面,士大夫與宦官并無根本的區別。而這些方面均由南衙諸司管理,于是對宦官的管理便不能不涉及到南衙諸司。
1.入仕途徑
唐代宦官入仕的途徑與士大夫階層不同,主要有:諸道進獻、良胄入仕、罪犯子弟、門蔭入仕、宦官養子等。有唐一代仍然存在著壓良為賤的現象,如郭元振 “前后掠賣所部千余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安樂、長寧、定安三公主家廝役掠民子女為奴。?此外,在南方一些地區存在著嚴重的賣良為奴現象。這些都成為唐五代宦官的來源之一。 《新唐書·宦者傳》說: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 號 ‘私白’,閩、 嶺最多, 后皆任事, 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 ‘敕使墓戶’”。可見通過這種途徑入宮的宦官數量之多。如高力士、金剛等大宦官,就是嶺南討擊使李千里買來并進獻宮中的。據不完全的統計,全國十道中有九個道皆出宦官?,可見唐代宦官來源十分廣泛,其中應有不少是諸道進獻而來的閹兒。
關于良胄入仕,這是唐五代時期補充宮中小給使的途徑之一。 《李輔光墓志》載: “建中歲,德宗御宇,時以內臣干國,率多縱敗,思選賢妙,以正宮掖。故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李輔光的曾祖為縣令,祖父為涇王府長史,其父為果毅都尉,世代為中下級官吏家庭。所謂良胄入仕就是從中小官吏子弟中選擇一些人入宮。這一做法并非始于唐德宗時期,早在唐玄宗甚至更早一些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再比如劉弘規,穆宗、敬宗時任左神策軍中尉,云陽人,其父祖均為中級軍官,“公十有五乃應選”。?如此年紀而能入宮,父祖又沒有犯罪,只能是所謂良胄入仕了。根據碑志記載,以良胄身份選入宮者,多在京畿地區,范圍再大一些也不出關內道,其他諸道人數極少。這是唐代宦官中關內道和京畿地區人數較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五代時期在法律上已經廢除了宮刑,但是并不徹底。由于存在著將犯罪官員家屬沒為官奴婢的法律規定,這就為一些人上下其手提供了便利。如大宦官李輔國, “以閹奴為閑廄小兒”。?再比如安祿山帳下李豬兒, “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為閹人”。?《舊唐書·安祿山傳》說李豬兒為契丹人,“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祿山頗寵之。”顯然是私閹行為。在這一時期私閹現象還不少,除了李豬兒外,史載:韋陟 “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十數”。?楊國忠得勢時, “珍玩狗馬,閹侍歌兒,相望于道。”?后唐大宦官孟漢瓊, “本鎮州王镕之小豎也”。?王镕為成德節度使,說明其也是私閹的宦官。在唐代還存在一些前代被閹的宦官,如北齊尚書仆射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受冤而死,其三人之子“并及淫刑”,入宮成為宦官,唐太宗為其平反,“宜免內侍,褒敘以官。”?即免除其宦官身份,另行任官。
門蔭入仕也是宦官來源之一。唐朝規定文武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可以通過門蔭入仕,高級宦官子孫通過這一途徑入仕者也不少。由于宦官收養的男性子孫有兩類人,一類為正常男性,另一類為閹兒,前者通常通過充當衛官、挽郎、齋郎獲得參選資格而入仕,后者通常則以養父祖官資而入宮當宦官。如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 ‘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51證明宦官亦可以蔭子。鄭薰在懿宗時任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卻之不肯敘。”52鄭薰不肯給宦官用蔭,并非制度不允許,而是出于對宦官的偏見。宦官蔭子成功的實例也不少,如宦官張居翰, “咸通初,掖廷令張從玫養之為子,以蔭入仕。”53“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為假子。”54
唐代宦官收養假子的數量很大的,少者數人,多者甚至數十人,其中相當部分本來就是閹兒,或者收養幼兒閹后再送入宮中為小宦官,也有直接收養小給使為假子。如高力士閹后被李千里進獻,從而成為小給使。不久卻因犯錯被趕出宮,遂又被宦官高福收為假子,再送入宮中。大量還是收養后再閹,然后送入宮中。如 “楊思勖,本姓蘇,羅州石城人。 為內官楊氏所養, 以閹, 從事內侍省。”“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內侍省為宦者。” 楊復恭, “以父, 幼為宦者, 入內侍省。”55類似事例甚多,如楊志謙本人又收養了7個假子,除一人非閹人外,其余6人均入宮當了宦官。劉弘規也收養了5個假子,全部入宮充當了宦官。其養子劉行深至少也收養了5人,宦官劉遵禮即為其第五子。劉遵禮共收養了4人,全都當了宦官。56
宦官來源的渠道除了以下數種外,還有一些其他途徑。如民間貧窮之人因生活困苦而被迫受閹入宮者,犯罪官吏子弟被強制為奴后自愿受閹者,或出于某種原因被閹割入宮者等。 “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教宮人。”57則是具有某種特殊技藝的人因宮中需要而閹為宦官。唐代內教坊的供奉人員中象這類情況當不止一人。因這些原因而入宮的宦官,其原籍雖不一定都是長安人,至少也是生活在京師或附近之人。
2.散官與章服
唐后期宦官出現了官僚化的趨勢,在職官管理方面與士大夫階層無根本的不同。唐代的散官分為文武兩種,職事官所帶散官,稱為本品,無職事官者所獲散官,稱為散品,散官官階表示官員的資歷與等級。對于宦官而言,亦是如此,凡從九品以上宦官皆帶有散官銜。唐代宦官所帶散官沒有任何限制,文散官的第一階開府儀同三司 (從一品)與武散官的第一階驃騎大將軍 (從一品)均給宦官授過,前者如高力士、李輔國、第五守亮、俱文珍、楊復恭,后者如楊思勗、程元振、竇文場、王守澄等。至于獲得中下級文武散官階的宦官就更多了,這一點出土的宦官墓志中有大量的記載。
唐代官員的章服是由本品決定的,貞觀初規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高級職事官散官不及三品,可以賜紫,不及五品可以賜緋,中下級官員不及八品,可以賜綠。由于皇帝對宦官的寵信,僅唐玄宗時期宦官 “衣朱紫者千余人”58,可見高級宦官人數之多。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衣朱紫宦官,并不是宦官中真有如此之多的人擁有三品或者五品以上的散官階,更多的則是皇帝隨意賜紫、賜緋形成的。在唐后期能夠獲得 “賜金紫”和 “賜緋”的利益集團,以宦官階層最多,而且還出現了職事官或使職與賜章服同時授與的情況。59賜綠的宦官,主要是入仕不久的小宦官與高級宦官的養子,如敬宗在長慶四年 (824)正月即位,在這一月內,先給白身宦官孫奉滿賜綠,接著又給白身元孝思等20人賜綠,不幾天又分兩批給白身 40人、28人賜綠,“而元孝溫、劉仲孺,昨日賜綠,今日賜緋”。60總之,唐代宦官在散官與章服方面與南衙朝官并無什么不同,在后期宦官勢力膨脹之時,在這個方面還要優于朝官。
3.勛爵與俸祿
在勛官方面,宦官與朝官一樣均可以獲得勛官。本來勛官之授以功勞以準,唐前期尚能堅持此制,甚至出現宰相僅獲得低等級勛官的現象。唐后期勛官濫授現象十分嚴重,不僅朝官如此,甚至有軍士、樂工帶上柱國銜者,在出土的墓志中就有不少這樣的事例,至于宦官階層亦是如此。如宦官孫常楷獲勛官最高階上柱國 (視正二品)時,散官為朝議郎 (正六品上)、 職事官為內給事 (從五品下)。宦官劉守義獲上柱國時,職事官仍為內給事。劉奉芝獲此官時,職事官為內寺伯 (正七品下)。劉仕侗獲此官時,任內府局丞 (正九品下),散官為中散大夫 (正五品上)。至于高級宦官無不有上柱國的勛官。
唐代的爵制分為九等,宦官同樣亦可授爵。第一等親王,是授給皇子或者皇帝的兄弟的,他人不能染指。從第二等郡王,至最后一等開國縣男,宦官階層都曾經獲得過。如李輔國封博陸郡王,至于封國公的人就更多了,如高力士為齊國公,楊思勗為虢國公,程元振為邠國公,魚朝恩先封鄭國公,后徙封韓國公,馬存亮為岐國公,仇士良為楚國公,田令孜為晉國公,楊復恭為魏國公。其他等級的爵位獲得就更多了。
封爵必須同時授與相應的封戶,如親王、萬戶,郡王、五千戶,國公、三千戶,最低一等開國縣男,也有三百戶,這些都是虛封,沒有經濟方面的實惠。親王,皇帝會授給一定數量的實封,稱為食實封,其他人員必須有功才可以得到實封。宦官的爵位也是如此,如李輔國有實封 800戶、高力士500戶、魚朝恩1000戶、馬存亮200戶、仇士良300戶、楊復恭800戶。獲得實封就可以享受這些封戶租稅了。至唐末五代時期,由于國家經濟困難,遂罷去了實封之給。食實封的多少與爵位的高低沒有關系,對宦官而言除了看功勞大小外,更多的則是視皇帝的恩寵程度。如吳承泌是開國縣侯,實封僅為100戶,王公素僅為開國縣男,卻有300戶的實封。
在俸祿之制方面,宦官與士大夫階層享受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說在唐五代宦官與士大夫適用同一種俸祿制度。比如唐朝給朝官職分田,規定一品12頃、二品10頃。據載:元和十四年規定: “左右神策中尉,準令式二品官,令受田一十頃。”61唐初宰相為三品官,大歷時升為二品,可知神策中尉的職事官品是比照宰相而確定的。唐后期官員的月料錢來自于公廨利錢,而諸司公廨本錢則由朝廷統一劃撥,宦官擔任的內諸司使亦是如此,史載:長慶“三年十一月,賜內園本錢一萬貫、軍器使三千貫”。 次月, “賜五坊使錢五千貫, ……以為食利”。62唐后期規定節度使每月給俸錢300貫、監軍使150貫。有些經濟落后地區無力承擔當地官員的俸錢,會昌六年 (846)八月敕曰: “夏州等四道土無絲蠶,地絕征賦,……夏州、靈武、振武節度使,宜每月各給料錢、廚錢共三百貫文,監軍每月一百五十貫文。……天德軍使料錢、廚錢每月共給二百貫文,監軍每月二百貫文”。63
朝官致仕者多給俸祿,通常是年齡70歲以上,五品以上的致仕官員,可給半祿。宦官致仕亦是如此,甚至有一些深受皇帝寵信的宦官還可以拿到全俸。如大和三年 (829)三月,右神策中尉梁守謙致仕,文宗下詔 “仍全給俸祿”。梁守謙是壯年致仕的,按照唐制連半祿也不該享受。同年六月,左衛上將軍、內侍監魏弘簡致仕,也給全俸祿。64有關宦官俸祿的問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65,可以參看,就不多說了。
除此之外,宦官還經常受到皇帝的各種賞賜,包括錢物、土地、宅第等,加贈或追贈父祖官爵,卒后授與謚號,陪葬帝陵等。就這些方面而言,宦官階層與朝官階層并無根本的區別。
4.南衙諸司的管理職能
唐代宦官官僚化的特點,決定了南衙諸司中有不少部門參與了對宦官階層的管理事務。有關這方面的史料少且零散,但是仍能看得出,對宦官管理的許多方面都由南衙諸司負責。一般而言,對宦官階層的管理大都是通過詔敕進行,然具體執行者則為南衙相關部司。如內侍省人員的編制,由吏部掌管,據 《唐六典》載: “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員。凡諸司置直,皆有定制。”這里是指諸司所置之直官的編制,其中 “內侍省一百人、內坊四人”。66據此可知,內侍省人員的編制是由吏部掌管的。宦官有關人事方面的不少事務都歸吏部管理,如大和四年八月, “內侍省奏: ‘當省官員,從掖庭局令以下至監作,并居本品之下。或注擬難于區別,伏乞請重下有司詳定。’敕旨: ‘宜付所司,詳定聞奏。’”67這里所說的 “所司”,顯然是指吏部,因為官員注擬之事為吏部所掌管。對內侍省所轄吏員的待遇由敕書規定,吏部執行, “景云二年四月二日敕:內侍省令史資勞,宜同殿中省令史。其五局令史,同殿中省諸局。”68可見內侍省人員的資歷是比照南衙的一些部門確定的。此外,吏部還掌管官員的蔭子之事,包括宦官亦在其內,前述的吏部侍郎鄭薰抵制宦官蔭子之事,說明此事仍然歸吏部管理。雖然鄭薰此舉是出于對宦官的歧視,但從唐朝制度的角度看,這一抵制并不合法,而是出于政治偏見。
有關宦官的事務還要受到門下省的制約,前述大宦官仇士良蔭子之事,被給事中李中敏駁回。說明中書省已經同意其請求,并起草了敕書,經過門下省審議時被李中敏駁回。這一切都是唐朝政事運作的正常程序,只是由于朝官對宦官的不滿,有意不予執行而已。
吏部司封司與宦官的爵位管理有關,凡宦官階層的封爵、母妻邑號的敘封等事務,無一不是通過司封司進行的。司勛司則掌管宦官所授之勛官,授與不授,授哪一級的勛官,具體規定都由其掌握。
戶部也掌管一些與內侍省相關的經濟事務,如內侍省人員的糧廩、衣賜等,皆由戶部如數撥給。由于人員增減變化引起衣糧不足,也歸其管理。貞元 “十五年四月詔:內侍省內給事,加置二員。至元和十五年四月,內侍省奏: ‘應管高品品官白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數內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高品諸司使并內養、諸司判官等,余并單貧,無屋室居止,須稍優恤,宜各加衣糧半分,度支據數支給。’”69度支指戶部度支司,主管國家財政收支之事。開元七年 (719)敕: “內侍省將軍、中郎、內侍、內給事,五品已上官,宜準宿衛官給酒料。”70這些都涉及到了戶部的職能。
內侍省設在京師長安,因此有些事務不能不涉及到京兆府,如 “開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內侍省內坊單身給使,有品無品,并免戶例差科。”71差科之事均由地方官府掌管。 《唐六典》載: “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72由于宦官多在京師任職或當差,故其差科應由京兆府所屬諸縣,即長安、萬年縣掌管,免其差科的敕令也是由當地官府執行的。
內侍省的有些事務還與中書門下 (政事堂)有關, 《唐六典》卷12《內侍省》條載: “凡宮人之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 計其多少,春、 秋二時,宣送中書。”為什么要宣送中書呢?因為這些開支需要宰相審定,然后以詔敕通知戶部執行。唐朝以比部為國家最高審計機構,其中也包括對內侍省的審計,這一點在史籍中也可以找到證據。史載:其衣物 “若用府藏物所造者,每月終,門司以其出入歷為二簿聞奏。一簿留內,一簿出付尚書比部勾之。”73比部司隸屬刑部,給其呈報簿書以供其“勾之”,即進行審計。據此而推,可知內侍省所有經濟收支與國家其他部門一樣,均由比部審計。
史載: “天復三年二月敕:諸道監軍使、副監、判官并停。其院印當日差人赍納禮部銷毀。”唐朝在諸道置有監軍使院,貞元十一年 (795),首先給河東監軍使鑄印, “監軍有印,自茲始也”。74天復三年 (903),時任宰相崔胤在強鎮朱全忠的支持下打擊宦官勢力,率先罷廢諸道監軍使印,以限制和削弱其勢力。唐內外諸司并非建立之初皆置有印,從史籍記載看,是陸續為諸司鑄印的。然而此類事務歸哪個部門管理,因不見于記載,一直不大明確。 《唐六典》卷 4《尚書禮部》條: “凡內外百司皆給鋼印一鈕。……凡內外百官有魚符之制。”再結合上引銷毀監軍使印的記載,基本可以確定此事當為禮部所掌管。此外,從 《唐六典》記載看,各級宦官的章服亦歸禮部管理,內侍省的廨署、公廨田歸工部管理。
從現存史籍記載看,對宦官的管理更多的是通過詔敕進行的,有關這方面的記載,在 《唐會要》卷65《內侍省》中有不少,甚至包括收養假子的規定、官階的確定、丁憂的期限、內侍人員的增減、衣糧的增減等。然而這些詔敕的執行卻與南衙諸司的職能密切相關,從而將宦官的管理納入到了國家的正常制度范圍之內。
注釋:
① 《后漢書》卷78《宦者傳》。
② 《舊唐書》卷184《宦官傳序》。
③ 67 68 69 70 71 74 《唐會要》卷65《內侍省》。
④⑤ 73 《唐六典》卷12《內侍省》。
⑥ 20 葉夢得: 《石林燕語》卷3,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7、37頁。
⑦ 參見杜文玉: 《大明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頁。
⑧⑨ 18 《文獻通考》卷58《職官考十二》。
⑩ 15 19 王永平: 《論唐代宣徽使》, 《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1 《冊府元龜》卷665《內臣部·總序》。
12 周紹良等: 《唐代墓志匯編》大和0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3頁。
13 《資治通鑒》卷263“唐昭宗天復三年正月條”胡注。
14 《冊府元龜》卷160《帝王部·革弊二》。
16 唐長孺: 《唐代的內諸司使及其演變》, 《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46—248頁。
17 孫光憲: 《北夢瑣言》卷6《內官改創職事》,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41頁。
21 《資治通鑒》卷236“唐順宗永貞元年正月條”胡注。
22 《舊唐書》卷17下 《文宗紀下》。
23 陜西省博物館: 《陜西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一批唐代銀器》, 《文物》1966年第1期。
24 朱捷元等: 《西安西郊出土唐 “宣徽酒坊”銀酒注》, 《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1期。
25 《文苑英華》卷 418,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2118頁。
26 周紹良等: 《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天復00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7頁。
27 《全唐詩》卷424,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653頁。
28 《舊唐書》卷20下 《哀帝紀》。
29 《資治通鑒》卷272“后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條”胡注: “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
30 《資治通鑒》卷253“唐僖宗廣明元年五月條”。
31 《資治通鑒》卷247“唐武宗會昌三年五月條”。
32 王永平: 《論樞密使與中晚唐政治》, 《史學月刊》1991年第6期;黃潔瓊: 《唐代樞密使與神策中尉之比較研究》, 《福建論壇》2005年第12期。
33 《新唐書》卷152《李絳傳》。
34 《舊唐書》卷176《魏謨傳》。
35 趙和平輯校: 《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26頁。
36 圓仁: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頁。
37 趙和平: 《敦煌書儀研究》一書對此有詳盡的考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3頁。
38 《資治通鑒》卷248“唐武宗會昌四年八月條”。
39 《新唐書》卷208《宦者·楊復恭傳》。
40 《舊唐書》卷97《郭元振傳》。
41 《新唐書》卷83《中宗八女傳》。
4256 杜文玉: 《唐代宦官的籍貫分布》,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43 周紹良等: 《唐代墓志匯編》元和0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7頁。
44 《全唐文》卷711,李德裕: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 (弘規)公神道碑銘》。
45 《新唐書》卷208《宦者·李輔國傳》。
46 《新唐書》卷225上 《安祿山傳》。
47 《舊唐書》卷92《韋安石傳附陟傳》。
48 《舊唐書》卷106《楊國忠傳》。
49 《舊五代史》卷72《孟漢瓊傳》。
50 《新唐書》卷2《太宗紀》。
51 《資治通鑒》卷246“唐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條”。
52 《新唐書》卷177《鄭薰傳》。
53 《舊五代史》卷72《張居翰傳》。
54 《舊五代史》卷72《張承業傳》。
55 58 《舊唐書》卷184《宦官傳》。
57 《資治通鑒》卷203“武則天垂拱二年六月條”。
59 張蘋、馬冬: 《墓志所見晚唐內侍省官員與 “賜紫緋”》, 《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6期。
60 64 《冊府元龜》卷665《內臣部·恩寵》。
61 《冊府元龜》卷507《邦計部·俸祿三》。
62 《唐會要》卷93《諸司諸色本錢下》。
63 《冊府元龜》卷508《邦計部·俸祿四》。頗疑天德軍監軍每月二百貫料錢的記載有誤, “二”字極可能是“一” 字之誤。 待考。
65 杜文玉: 《唐代宦官俸祿與食邑》, 《唐都學刊》1998年第2期。
66 《唐六典》卷2《尚書吏部》。
72 《唐六典》卷30《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
(責任編輯 張衛東)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唐宋時期職官管理制度研究”(項目編號:12BZS032)
K242
A
(2017)03-0086-08
杜文玉,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西安,7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