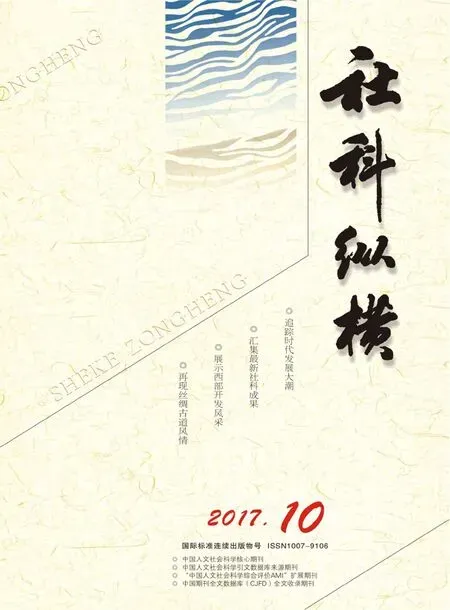儒家人倫思想對當代道德重建的意義
劉銀軍 朱良鈺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甘肅蘭州730070)
儒家人倫思想對當代道德重建的意義
劉銀軍 朱良鈺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甘肅蘭州730070)
儒家人倫是人類血緣中特有的一種自然等級。當下對于人倫的創新要注重人倫的秩序性,而淡化人倫的等級性。從等級性來講,人的生命體具有獨立性,任何人不能占有和控制他人的生命,作為獨立意識存在的生命體,在存在的意義上來說,都是平等的,包括父母無權占有和控制子女的生命體。從秩序性來講,人倫的價值依據來自于仁愛,一種自然而然的天性之愛。只有建立在天然之愛基礎之上的秩序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人倫是一個家庭有序的基石,也是社會能得以穩定的根本所在,能夠在社會層面上維系一個民族的道德體系和價值判斷,形成這個民族的道德自覺,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人倫和諧道德自覺重建
先秦文化是中國文化成熟的源頭,而儒家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儒家的人倫思想是維系整個人倫體系的道德基礎,形成了一個以道德為旨歸的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
一、對儒家人倫的理解
人倫是人類對自己存在方式反思而充分意識到人之為人的原因,它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原則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凡是有人類存在的地方就有人倫。在此,我們關注古代的中國儒家對圣賢們是怎樣來思考、規定人倫的,換言之,其特質何在?造成這種特質的原因何在?傳統人倫的界定,是指封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通過禮教所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及各種尊卑長幼關系。定義本身的意義并不是我們考量的重點,而重點應是處理這些關系的原則和價值在古代人這里是怎么去思考的,形成這種人倫自覺的根據是什么,傳統人倫定義本身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輩序,二是輩序所形成的等級。任何一種關系從現實的角度講都有自然等級,而這種自然等級在特定的社會表現出它特定的社會屬性。對于自然等級,《周易》里講:“天地生萬物,萬物生男女”,天地、祖先、父母、長子、次子等就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自然等級,這種自然等級是宇宙秩序的一種表現,是一種自然規律,而這種自然等級之間的關系必須有一套原則得以維持,才能得以讓這種倫理秩序和諧。先秦時期,孔孟等儒家先哲已提出人倫學說,孟子以“君臣、夫婦,父子、長幼、朋友”這五種關系為五倫,認為這是人生所要面對的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五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核心是在人倫關系中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基本準則。拋棄了這些準則,人不成其為人,即所謂“無父無君,入于禽獸”,這正是孟子人禽之辨的要義。從倫理層面講,這種道德倫理的基本方式是建立在血緣關系之上的。血緣關系,在鞏固中華民族持續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價值者,當首推家族觀,它使任何人不能忘卻本人祖系之所屬,這種由血緣形成的觀念深根蒂固。家在中國人心中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錢穆說:“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庭觀念筑起”。[1]血緣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結合方式,而在中國古代,國是放大的家的形式,家國同構是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起點。因此說,在古代,人倫的基礎和起點是以血緣結成的家或家族,而儒家的親親思想就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個人與群體的關系也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形成的。依據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中國文化從古至今是一種關系本位的文化,由此決定了人倫關系建設是社會秩序建設乃至中國文化復興的基礎[3]。
二、當今人倫存在問題及成因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人與外界的關系中,主要有三種關系方式,一是血緣關系,二是地緣關系,三是職緣關系。而人倫主要是指由血緣關系形成的熟人社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就是有著遠近不同的血緣群己關系。也可以理解為由這種血緣關系鏈接出的群己關系,道德人倫關系通過表現出來,費孝通先生認為,只有在現代社會中,由于社會變遷,在越來越大的社會空間里,人們成為陌生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社會的轉型,傳統的以血緣關系為主的社會形式逐漸過渡為地緣關系和職緣關系,血緣關系逐漸被邊緣化,人倫也被淡化,這一道德基石的淡化,成為當今道德失落的焦慮。我們從費老的話語里不難看出,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人倫自覺是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中建立起來的,所謂的道德自覺實際上只是對熟人而言。我們對陌生人天然的具有排斥的心理,在一個陌生的社會里,人會對陌生人有多少道德自覺,也就是說,道德的滑坡與熟人社會關系遭到解構有很大的關聯。
就其原因,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類開始了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從那時起的幾十年里,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新的成果,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馬克思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傳統社會中科學技術落后,生產力不發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依附的關系,社會分工不發達,因而,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依附主要表現為熟人之間的依附。近代以來,理性的啟蒙和科技的進步,人對物的依附取代了對人的依附,人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但又成為物的奴役對象,科技成為特殊的工具使人的本性屈服于它所創造的物質形式之下。正如馬爾庫塞批評的那樣,人在物質增長中喪失了自我,雖然說科學技術的非理性給人類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同時難以舍棄物質富裕所帶來的無限欲望,在物質與道德的權衡上,追求物質滿足所帶來的價值觀念進一步覆著人們傳統的主體價值觀。馬克思說,“只有消除拜物教的客觀物質基礎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的價值信念。”這種強大的拜物觀強烈地沖擊著當下人的傳統價值觀,道德自覺的形成更是難上加難。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在當代受到嚴峻挑戰,面對這樣一種格局和社會風氣,人倫重建還可能嗎?怎樣才能在當下形成人倫自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者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三、儒家人倫在當下的新義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為種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當前的社會問題中,普遍反映出道德的下滑和人倫的淡化,這就需要在新的時期,新的時代重新建立道德基石,由于時代不可逆性,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傳統時代,恪守傳統時代道德準則和道德標準。但面對社會問題,與傳統時代具有的相似性,可以對人倫中的傳統美德進行相應的創新和轉化。因此說,對人倫的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國度,人們有著不同的社會公意,因而人類的道德文明、價值文明呈現出一定的歷史性,民族性。人倫在當下以失去家族宗法與等級這樣一個平臺,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與公平”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人無貴賤之分,更無等級之別,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依靠理性而達成自覺,實然與應然之間的悖論,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永遠是理性難以解決的,儒家人倫是人類血緣中特有的一種自然等級。人何以為人,是人從動物獸性中走出,具有了人性,人倫是人性最基礎的表達。人性是一個民族道德體系的根本,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礎之上的價值判斷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人倫是一個家庭有序的基石,也是社會能得以穩定的根本所在,能夠在社會層面上維系一個民族的道德體系和價值判斷,形成這個民族的道德自覺,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首先,當下對于人倫的創新要注重人倫的秩序性,而淡化人倫等級性。從等級性來講,人的生命體具有獨立性,任何人不能占有和控制他人的生命,作為獨立意識存在的生命體,在存在的意義上來說,都是平等的,包括父母無權占有和控制子女的生命體。從秩序性來講,人倫的價值依據來自于仁愛,一種自然而然的天性之愛。孔子說“親親,仁也。”孔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愛首先是從血緣關系開始的。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的仁愛思想里有一種差序格局,仁者愛人,首先是從自己的親人開始,孔子認為,親親是人之所以為人,推己及人的邏輯起點,也是建立大愛的起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人倫的核心價值觀念,一般來說,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任何一個國家,在人與人的關系上,首先是親人關系,也首先是愛自已的父母,這種血緣之愛是普世的,這種愛是創造秩序和維持秩序的基礎。
孟子在繼承了孔子的仁愛的基礎上,再次將仁愛的邏輯起點擴展為普便化的惻隱之心,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同情心,他主張性善論,其根據在于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他認為四端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尺度,是道德的內在根據。在這里,孟子超越了血緣親情來論證道德自覺的根基和動力。孟子對愛的推廣,使孔子的仁愛落實到血緣之外,使人們在地緣關系和職緣關系上學會了愛人,和自覺愛他人的能力。這種愛在愛己和愛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孟子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是指建立在愛有差等基礎上的,愛以親情之愛為起點,進一步上升到對他人,對萬物和整個世界的愛,也體現了中國人是從親情出發開始學會理解人并擔負起做人的責任,仁這種愛區別于其他類型的愛的另一重要特點在于,它建立在對他人真實,深切的情感的基礎上,因而也應當是自然的愛,通過它同樣讓一個人的人格獲得尊嚴,靈魂獲得升華,生命獲得價值,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也引導了人的意義世界,使人與社會之間達成了一種和諧狀態。
四、人倫重建何以可能
從中國傳統文化本身來講,何以要傳承。一方面,因為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現代價值意識并不是很快就能建構起來的,這并不是因為其建構確立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文化過程,而且因為傳統文化模式仍然還起作用,它不僅決定人的行為方式,也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是其文化長期積累及功能過程形成的,它不僅有歷史個性也有價值定向和模式化傾向。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它就對人的價值心理和價值觀念有很強的規定性,即使現代人也往往難以完全擺脫傳統文化模式的影響[4]。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既要淘汰一些與現時代不適應的舊文化舊特質,也要吸收、融合、整合一些能與現代化適應的新文化、新特質。這二者不是簡單的雜燴拼湊,而是深厚的民族文化結構在新的文化積累中實現突變和飛躍。這種突變和飛躍離不開原有民族文化積累,離不開這種積累所形成的遺傳趨勢,必然在整個遺傳突變中保持著原來的某些個性,保持著它的自我選擇、自我組織的能力。如果要完全打破它的價值體系,就會使之失去自我組織能力,使國家民族的文化遭到巨大的破壞,而其現代化的價值建構也將必然失敗[5]。
人倫代表著幾千年以來的中華傳統美德,是唯系中國人精神家園的根脈。從個人層面講,仁義禮智信和忠孝,是一個家庭和諧的基礎,中國之所以稱為禮義之邦,就是因為中華道德文化是中華文明中最主要的內容,而人倫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外在規范和內在修養的必由之路。孟子說,“仁之安宅,義之路也”這句話是說要成為一個仁者,首先要走在正義的道路上,走在正義的路上才能回到仁愛之所,孟子表達了儒家的內圣外王思想。內圣是成己之要,外王是處理好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從正義角度講,羅爾斯的公平的正義只是一種理想,是有其成立的前提與條件的,而現實中公平的正義是相對的,總有部分人必須要得到社會和他人的幫助,中華民族的和諧思想正好補充和升華了羅爾斯公平的正義思想。從實踐層面講,仁愛與忠是維系社會和諧的重要價值觀,講仁愛就不會有小月月事件,講“忠”就不會有貪污腐敗。宋明理學家常常說“盡己之謂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忠”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給自己一個交待,也就是他用自己的人格向另一個人,乃至向國家甚至天下人作出了一項神圣的承諾,即自己將盡最大努力來完成它,這是一種人格的力量。正是在這種“忠”的精神中才能樹立一個人的人格尊嚴,中華民族過去幾千年歷經無數艱辛一路走來,它的每一步前進,它的每一項成就,它所熬過的每一道難關,都有這種“忠”的精神在其中[5]。在抗日戰爭時期,正是無數中華兒女憑著對自已民族的忠誠,拋頭盧,灑熱血,取得了抗戰的勝利,有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社會主義。同時,之所以說仁、義、禮、智、信、忠、孝等價值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因為這些價值都是以人際關系為導向,主要功能在于維護一種合情合理的人與人關系,因而它們不像自由主義價值那樣以個體的需要為導向,五常和忠孝鮮明地體現了關系本位的中國文化自我整合即盡倫的需要,也體現了中國人從親情出發,從齊家做起理順一切人際關系,特別是社會關系的文化邏輯。
其實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并不是人們不清楚、不明白,是我們自己被各種思想的誤區所誤導,才對這些價值視而不見甚至嗤之以鼻,也正是這個原因。[5]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扭曲了,找不到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園,重建人倫,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里有人倫,只不過是被亂象所遮蔽,撥開迷霧,反樸歸真、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
[1]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九州出版社,2011.
[2]陳曉龍.中國傳統文化概論[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3]費孝通.鄉土中國[M].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4]方朝暉.人倫重建是中國文化復興必由之路[J].文史哲期,2013(3).
B82-092
A
1007-9106(2017)10-0065-04
*本文為甘肅省社科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中的中國傳統親子倫理及現代轉換”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YB167)。
劉銀軍(1977—),男,中共甘肅省委黨校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朱良鈺(1975—),男,中共甘肅省委黨校副教授,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