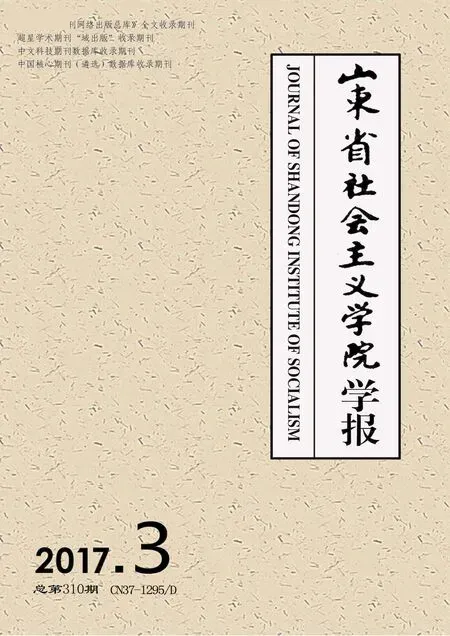為中華文明確認(rèn)世界坐標(biāo)
楊朝明
為中華文明確認(rèn)世界坐標(biāo)
楊朝明
中國曾經(jīng)閉關(guān)鎖國,在世界上被邊緣化,而今,在世界舞臺的坐標(biāo)軸上,在全球政治經(jīng)濟(jì)的定位系統(tǒng)里,中國靠近了中心。當(dāng)我們在全球政治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中定位和確立發(fā)展坐標(biāo)的時候,必須看到并繼續(xù)書寫中國文化的變化。政治、經(jīng)濟(jì)是文明土壤孕育的花果,當(dāng)下,中國正逐步成長為世界經(jīng)濟(jì)的重要“動力源”和“穩(wěn)定錨”,由中華文明自身的特質(zhì)所決定,中華民族也將為世界文化貢獻(xiàn)“定心丸”與“穩(wěn)定劑”。然而,包括許多研究者在內(nèi)的國人,對我們自身文明的認(rèn)識還模糊不清,特別需要懷有更多的敬意與溫情,走入我們自身的文化世界。
中華文明的高度與深度
今人認(rèn)知世界文明,多提及德國哲學(xué)家雅斯貝斯的“軸心期”概念 ,認(rèn)為公元前八世紀(jì)至公元前二世紀(jì),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各個文明都出現(xiàn)了偉大的精神導(dǎo)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進(jìn)入了社會發(fā)展的特殊階段,人們熟知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認(rèn)為是中國思想與中國智慧的繁榮與高峰,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它遠(yuǎn)不是中華文明的初期,也不是所謂中華文明的“形成期”。實(shí)際上,雅斯貝斯的所謂“軸心時代”理論,并沒有關(guān)注中華文明在諸子時代以前的漫長發(fā)展,沒有注意中國許多思想家何以那樣尊崇古代“先王”。
近四十年來,學(xué)術(shù)研究的重要進(jìn)展與考古材料的驚人發(fā)現(xiàn)都一再證實(shí),堯舜以來尤其夏、商、周“三代”時期,中華文明已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歷程,有較高的發(fā)展水準(zhǔn)。走在學(xué)術(shù)前沿的學(xué)者其實(shí)早已經(jīng)看清楚這一點(diǎn),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李學(xué)勤先生就呼吁人們“走出疑古時代”“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其實(shí),無論是3000多年前甲骨文這一完備的文字形態(tài),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還是8000年前舞陽賈湖遺址中的骨柄笛,都一次次地沖擊了我們的固有思維,使我們重新認(rèn)識古代文明的發(fā)展水平,理解我國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創(chuàng)造,再也不能對上古典籍中那些豐富記載視而不見!
人們意識到,“百家爭鳴”其實(shí)是對歷史文化的繼承、總結(jié)與反思,諸子思想的形成有廣闊的文化背景。夏、商、西周“三代”已經(jīng)是“有道”時期,已經(jīng)是中國文化形成與確立的時期,只是到了春秋末年卻變得“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如果孔孟老莊的年代是我們民族文明的初創(chuàng)期,那么中華文明、儒道學(xué)說的“價值”或“超越意義”就會打很多折扣。而事實(shí)是,在雅斯貝斯所說世界文明的“軸心”之前,中華文明已經(jīng)有了漫長的發(fā)展歷程,有了豐厚的文化積淀,有著自身深沉的精神凝結(jié)與創(chuàng)造。
中國的先民們認(rèn)知世界,以天地為師,著眼古往今來,關(guān)注四方上下。“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文子·自然》),在中華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之詞十分常見,這源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系統(tǒng)論,在與世界的互動中,他們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變”“道彌益而身彌損”之類的道理,講究注焉不滿,酌焉不竭,當(dāng)位而行,允執(zhí)厥中。
看清中華文明的綿延之路,探悉中華文明的深遠(yuǎn)遼闊,就會看到這樣一個一定會越來越清晰的事實(shí),早在孔子以前數(shù)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時期,中華文明就已經(jīng)為人類確認(rèn)了坐標(biāo)。中華“先哲”“先王”站在人類發(fā)展的中心點(diǎn),思考“人心”與“道心”的關(guān)系,為人類謀福祉,系統(tǒng)而完備。如果更多地走近中國早期文明,更多地了解中華文明,看到它的高度,了解它的深度,那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之夢,就不僅是嘹亮的呼喚,更是洋溢的動力。
孔子儒學(xué)的時空維度
孔子所創(chuàng)立的儒學(xué)是中國思想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歷代儒家之所以“宗師仲尼”,其實(shí)是內(nèi)在地決定于孔子學(xué)說本身,決定于孔子學(xué)說的特性與特質(zhì)。
孔子的思想學(xué)說不像世間有的智者那樣依靠“面壁”或“頓悟”而來,也不是受到了哪個神靈的啟示。孔子自幼好學(xué),他的“好學(xué)”成就了他的“博學(xué)”。《禮記·中庸》中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他也自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論語·述而》),那么,我們必須思考什么是“祖述”與“憲章”,并理解孔子何以“好古”?為何“不作”?顯然,孔子的“思想高峰”立于三代的“文化高地”,所以柳詒徵先生認(rèn)為“自孔子以前數(shù)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中國文化史·孔子》),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中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
我們不妨思考孔子儒家思想的“時空維度”。孔子考慮的不是“一時一地”的問題,包含了“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所以,《莊子》中才稱“內(nèi)圣外王之道”是“道術(shù)”而不是“方術(shù)”。可是,我們想到孔子,往往首先浮現(xiàn)的是孔子棲棲遑遑、到處奔走的身影,往往是那個駕著馬車“周游列國”的形象。
看起來,孔子為政沒有成功,但他清楚“窮達(dá)以時”的道理。孔子信念堅定,也有充分的自信。孔子初仕,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家語》)。他治理中都僅僅一年時間,便成為樣板,各地諸侯紛紛效仿學(xué)習(xí)。魯國國君問孔子:用你治理中都的辦法治理魯國,怎么樣?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孔子家語》)孔子相信自己的為政方略有廣泛的適用性。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對禮樂本質(zhì)的把握,源自他對人性和人的價值的思考,所以,有弟子問他“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子回答,別說“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認(rèn)為:“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人組成社會,成為社會的人,就必須明于禮義。社會治理的根本,無非就是人心的端正,無非就是在人們的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夏、商、周三代,禮的形式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fā)生了“損益”,但禮的根本精神永遠(yuǎn)不會變,這就是人人都應(yīng)該按照個人的社會角色做好自己。
由“中都”而“魯國”而“天下”,由“三代”而“十世”而“百世”,顯示的正是孔子思維的“時空維度”,他的高度與宏闊由此可見一斑。孔子倡言“內(nèi)圣外王之道”,主張推己及人、修己安人、明德新民。他思考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時,往往從根本上著眼,從簡單處著手。
孔子弟子請教有沒有一個字可以終身奉行,孔子認(rèn)為這個字應(yīng)該就是“恕”,孔子解釋所謂“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張請教“行”,問如何才能使自己無論到哪里都能通達(dá),孔子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言忠信,行篤敬”,說話忠誠守信,行事莊重嚴(yán)肅。人如果時刻牢記,將“忠信”“篤敬”裝在心中,指導(dǎo)自己的行動,即使走到與自己文化不同的“蠻貊之邦”,也一樣順暢通達(dá)。
中華文明的精神氣象
每一種文明都有它的精神氣象,中華文明最為突出的精神氣象莫過于它的“王者之風(fēng)”。中華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繼承發(fā)揚(yáng)三代文化傳統(tǒng),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
孔子常談“王天下之言”,談以“道”治國才能“致霸王”;孟子則言及“王”“霸”之別。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動屈服,埋下隱患,自食惡果。王道,以德行仁,人們主動臣服,心悅誠服。《孔子家語》有《王言》篇,記述孔子的王道言論,孔子思考“王天下之道”,希望聽“王天下之言”。
王者氣象使得中華文明有著多姿多元而又貫通如一的氣質(zhì)稟賦。中華文明崇尚禮讓,源于禮讓,使得許多矛盾不解自消。內(nèi)心有王者情懷,才會能讓則讓,讓于可讓,同時還會在原則面前當(dāng)仁不讓,正如今天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心的過程中,中國不能以犧牲本國利益為代價。在風(fēng)云變幻、紛爭逐利之中,立足長遠(yuǎn),謀劃全局,正是中華文明氣象的時代彰表。
中華文化氣象使中國主流價值追求清晰而堅定。中國者,執(zhí)中而立于天下,安定四海,天下大同。王者的終極追求是什么?是仁、義、禮、智根于心、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當(dāng)內(nèi)在的美德豐厚盈溢之時,光輝燦然的生命就巍然聳立。
在王者氣象的追求中,言念君子,溫潤如玉,“庶幾夙夜,以永終譽(yù)”(佚名《振鷺》)。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表示他一直致力于學(xué)習(xí)“確定自我身份的時候,不以降低別人來顯示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而應(yīng)該以抬高他人來找到彼此的相同”。其實(shí),幾千年前,“和而不同”“成人之美”“立己達(dá)人”等準(zhǔn)則就在中華厚土擲地有聲,而且在斗轉(zhuǎn)星移的千年過往中從未間斷,至今回響,使得近者悅,遠(yuǎn)者來。
中華文明的王道精神經(jīng)得起時空的檢驗(yàn),她從人心與人性出發(fā),致力于滿足人們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遠(yuǎn)歷史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是天地智慧的體悟;向下扎根,是對多方利益的兼顧與平衡,求得最大公約數(shù),昭示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在疑惑中超越,于不確定中憧憬。《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中華文明的精神氣象、氣質(zhì)稟賦、價值追求,夯實(shí)了中華文明在世界價值體系中心點(diǎn)的坐標(biāo)。
中華文明的思維模式
思維模式標(biāo)識、代表著價值取向,決定著行動走向。比如,以何為本,以何為末;以何為先,以何為后;以何為始,以何為終。在中華文明的思維模式中,榮譽(yù)與責(zé)任高于一切,兼顧多方利益;遵循并行并育,沒有相悖相害;信奉“創(chuàng)造、分享、助給”,創(chuàng)造在自己,分享給他人,助給予弱者。
中華文明價值取向清晰,更可貴的是,它以“一以貫之”的思維模式落地,思索古與今、我與世界、價值觀與方法論。這樣的思維模式,成為通往中心坐標(biāo)的最優(yōu)路徑、至佳選擇。
在“一以貫之”的過程中,關(guān)注根本,將個人的修養(yǎng)放于中心點(diǎn),反求諸己,從而聚焦于發(fā)展,聚焦于成長。人們看重內(nèi)在的功力,如火之始燃,泉之始涌,擴(kuò)而充之可保四海,反之,甚至不能事父兄。這樣的思維并不東張西望,沒有左顧右盼,而有深邃的動力和發(fā)展的持續(xù)性。朱熹云:“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中庸章句》)由“天地位”而“萬物育”,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源于一以貫之,自尊,尊人,被人尊;自敬,敬人,被人敬;自愛,愛人,被人愛;自知,知人,被人知;自信,信人,被人信。開放大度,和諧包容,智慧持中,踏實(shí)穩(wěn)重。與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神圣觀念相類似,儒家最重仁愛精神和敬畏觀念。孔子和儒家十分看重“愛”與“敬”,《論語》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說“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又說“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美國的愛默生說:“我們確信,武力會招致另一種武力,只有愛和正義的法則才能實(shí)現(xiàn)徹底的革命。”[1]對于愛與正義,幾千年前的中華傳統(tǒng)文明就已深刻全面地闡釋。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面對復(fù)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面對紛紛擾擾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國度,有德之文明,會像北辰燦然居中,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坐標(biāo)。
[1]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EB/OL].(2015-12-28).http://dushu.qq.com/read.html?bid=785675.
楊朝明,男,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