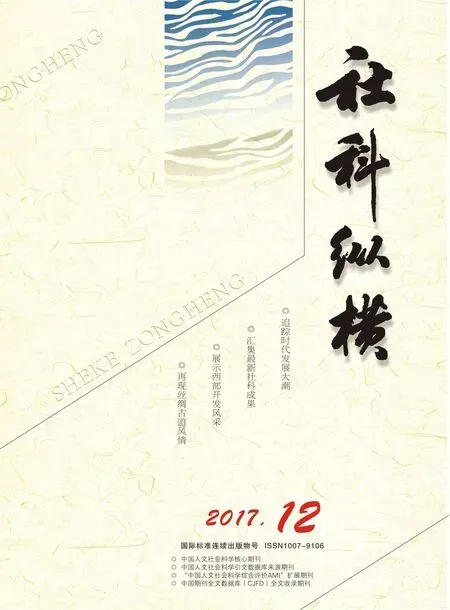中國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關系的理論分析與歷史考察
顧 碧劉俊杰
(1.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范學院 江蘇 無錫 214153;2.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 無錫 214122)
中國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關系的理論分析與歷史考察
顧 碧1劉俊杰2
(1.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范學院 江蘇 無錫 214153;2.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 無錫 214122)
理論上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互有側重、互有優缺、互為補充;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中國人民追求和實現人民民主的進程中創建了兩種民主形式并一直推動兩者共同發展。兩種民主形式未來需要在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協同發展。
協商民主 選舉民主 關系 理論 歷史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1]這就指出了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但兩種民主形式的關系如何,目前學界存在爭議。由于兩者的關系問題涉及未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和路徑選擇,因此,對此問題展開理論分析和歷史考察十分必要。
一、理論分析
厘清兩種民主形式的關系需要首先明晰兩者的基本內涵。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的民主形式,詳細地說,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各方面圍繞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形成共識的重要民主形式。”[2]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重要優勢,主要地說,第一,有利于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通過廣泛有序協商,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第二,有利于促進科學民主決策,通過決策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的協商,廣納民言、廣集眾智、廣求良策,使黨和政府的決策更順應民意、更切合實際;第三,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通過協商理念、方法和制度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的運用,使協商治理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途徑和方式;第四,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沖突,通過利益訴求的協商表達和解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第五,有利于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通過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的協商,增強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同時,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也存在一些固有局限,大致地說,第一,協商民主對協商主體數量的要求是有一定限制的,否則會因為人數過多導致協商難以開展,即便是開展,其實效也難以令人滿意;第二,協商民主的運行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精力、物力和時間成本,協商效率往往成為問題;第三,協商民主關注權力的運行,并不關注權力的來源,換句話說,關注掌權者如何掌權,而不關注誰成為掌權者。
社會主義選舉民主是“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的民主形式。通過票決方式匯聚民眾偏好并以此選擇公職人員和公共決策是這一民主形式的基本表征。社會主義選舉民主總體來講包括“選人”和“選事”兩方面。所謂“選人”即按著多數原則通過票決授權代表行使權力以賦予權力合法性;所謂“選事”即按著多數原則通過票決進行公共決策以賦予決策合法性。社會主義選舉民主具有重要優勢,主要地講,第一,有助于賦予權力機關和公職人員權力合法性以及公共決策合法性;第二,有助于選民監督候選人、監督成為權力行使者的候選人行使權力;第三,有助于彰顯公民的權利與權力,成為公民廣泛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第四,有助于民意的形成和表達,通過民主選舉可以較大程度地緩和化解矛盾沖突,促進社會和諧;第五,有助于打破權力壟斷,防止個人或少數人長期壟斷權力特別是壟斷權力又不當用權,做到權為民所用;第六,有助于培育提升公民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民主觀念,提高選民與候選人的參政能力。同樣,社會主義選舉民主也存在諸多固有不足。主要地說,一是遵循多數原則,認為多數即合理,少數人的主張和利益容易被忽視;二是從“選人”角度看,關注權力產生,忽視權力運行,也就是說,關注誰成為掌權者,而不關注掌權者如何掌權;三是同樣從“選人”角度看,它是一種周期性、階段性民主,幾年一度的選舉使得民眾參與過于稀疏,不能充分實現和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就區別來講,第一,協商民主以對話為中心,表現形式是協商討論;選舉民主以投票為中心,表現形式是票決。第二,與協商民主相比,選舉民主操作起來更為簡便易行,效率更高。第三,協商民主要求參與主體的數量不宜過多;選舉民主作為代議民主,參與主體的數量可以很多。第四,作為“選人”的選舉民主關注權力來源;協商民主關注權力運行。第五,選舉民主的基本前提假設是主體的偏好不變,認為選舉是偏好的集聚;協商民主則相反,認為偏好可以通過協商實現轉變。第六,選舉民主“求同”,堅持多數原則,少數人的主張和要求容易被忽視;協商民主“求同存異”,少數人的主張和意見得到表達和尊重。第七,選舉民主“求善”,主張多數即合理;協商民主“求真”,提倡凝聚主體理性和智慧,盡可能做出科學決策。第八,協商民主是民眾經常性參與的民主形式;從“選人”角度看,選舉民主則不是。就聯系來講,一是,兩者本質相同,目的都是要實現人民當家做主,都是實現民主價值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形式和手段;二是,兩者遵守基本原則相同,都突出共產黨領導,都以憲法法律為依據,都主張平等、有序、公開、公平、公正的參與;三是,兩者諸多功能相同,比如,保障公民政治權利、推動公民廣泛參與、促進民主決策、表達社會利益訴求等。
通過以上理論分析可以看出,兩種民主形式互有側重、互有優缺。同時,兩種民主形式也互為補充。協商民主能夠彌補選舉民主忽視權力運行、參與周期過長的不足,推動民眾廣泛經常參與;能夠彌補選舉民主簡單多數的不足,使得少數人的主張得到尊重和表達,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和提升決策合法性。選舉民主能夠彌補協商民主僅關注權力運行的弊端,推動掌權者積極主動協商,避免協商民主運行中出現的“議而不決”、“議而難決”、耗費民眾參與熱情等現象,提升決策效率。
二、歷史考察
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綜合運用協商和選舉兩種民主形式進行建黨和管黨的相關事宜。中共一大就是在充分討論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基礎上就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等主要問題取得了基本一致意見,并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當然,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推動兩種民主形式的實踐主要限于黨內。局部執政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將黨內實踐運用于所掌政權之中。1931年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凡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3]。這里的“選派”以及工農兵會議大會的“討論和決定”體現了選舉與協商原則在政權之中的運用和結合。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建立了“三三制”政權。“三三制”政權中參議會是各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參議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參議會閉幕后由其選出的政府成為代表人民的行政最高權力機關。在參議會和政府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共產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他們本著“一切有關原則性的爭議,應當平心靜氣的商討,在施政綱領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之下,求得合理解決,以達到鞏固三三制之目的。”[4]所以,可以看出,“三三制”政權是民主選舉與民主協商充分發展且緊密結合的政權組織形式。進入解放戰爭后,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民主協商和民主選舉的發展與結合,從而極大地調動了黨和人民的革命熱情,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當然,由于當時歷史和環境的局限,這一時期的選舉和協商實踐盡管還稱不上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但它們堅持和體現了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原則、理念與方法。
伴隨中國革命的步步勝利,與中國共產黨有著長期協商合作關系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等紛紛拋棄蔣介石政權在革命的最后關頭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9年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籌備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等通過這次會議完成了協商建國大業。政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由此政治協商作為我國協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得以確立,人民政協成為這一制度的重要載體和組織形式。當然,建國之初,由于通過普選成立國家權力機關的條件尚不成熟,因此人民政協曾經一度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召開。從此,人民政協不再代行人大職權,但其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仍繼續發揮作用,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從這時開始,在國家政治制度層面,人大選舉民主與政協協商民主的結合開始形成。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的實踐在全國層面正式確立,兩者的共同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當然,這時的實踐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及人大選舉民主和政協協商民主,并不是說政協沒有選舉民主,人大沒有協商民主,實際上,政協領導人的產生、政協章程及決議的通過都需借助選舉民主,人大在重大決策前、在立法工作中也都會根據需要展開協商。政協協商民主與人大選舉民主是就兩種民主形式在兩個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換句話說,政協是以協商民主為主要民主形式,人大是以選舉民主為主要民主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兩種民主形式的共同發展。一方面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斷發展。198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201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中央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頒布實施,各地根據中央的意見陸續制定了實施辦法。這些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協商民主的發展。我國協商民主已經從改革開放前的政治領域延及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涉及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廣泛多層的協商民主體系。另一方面推進社會主義選舉民主不斷發展。比如,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按照城鄉人口相同比例選舉;促進各級人大代表的廣泛性和結構的合理性,增加基層代表比例;規范和完善選舉的方式、程序及機構;完善代表監督、罷免、辭職程序;完善候選人產生制度,推進差額選舉,規范代表候選人的宣傳介紹;等等。此外,推進兩種民主形式的結合。從政治體制層面看,實行政協先于人大召開,重大方針政策和問題在程序上首先是政協協商,之后由人大票決通過上升為國家意志,最后由政府貫徹執行。從民主政治過程看,實施掌權者的產生首先經過協商醞釀,之后通過選舉民主加以確認,要求掌權者在行使權力過程中按照中央意見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開展協商,協商過程既是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過程,也是集智納言實現科學民主決策的過程,同時還是凝聚共識的過程,當然,由于共識的達成并不容易,因此當共識不能達成時仍需借助選舉民主作出決策。改革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這些努力,推進了兩種民主形式的發展、銜接和融合,形成了我國協商的選舉民主與選舉的協商民主相統一的互契互濟式民主發展格局。
通過歷史考察可以看出,我國的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實踐早已有之,中國共產黨創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在創建和發展兩種民主形式的艱難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對待兩者一直是“一視同仁”,積極推進兩者的發展和有機結合。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兩種民主形式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共同發展,但兩者的共同發展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如發展機制匱乏或不完善、發展范圍和內容有限、發展條件不足等。
三、結語
綜上所述,理論上看,社會主義與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互有側重、互有優缺、互為補充;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中國人民追求和實現人民民主的進程中創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并積極推進兩者的結合,從而形成了兩者互濟互契共同發展的格局。展望未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要在兩種民主形式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兩者的協同發展。所謂兩種民主形式的協同發展,不是兩者的簡單相加、平均發展,而是它們的同步推進、相互協調、有機銜接、有效融合和良性互動。相對于共同發展,協同發展更強調兩種民主形式的協調、銜接、互動和融合。推進兩種民主形式協同發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盤活我國民主“存量”,發揮民主政治綜合優勢,取得更大民主實效。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民主制度和形式是由其社會歷史發展狀況、現實國情以及國家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是具有中國特色和優勢的民主形式,其與西方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有著根本區別。因此,認識和研究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的關系及發展取向必須要立足中國實際。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9-22(2).
[2]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5-02-10(1).
[3]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73.
[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577.
(責任編輯:潘維永)
D62
A
1007-9106(2017)12-0053-04
* 本文為江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西協商民主比較研究”(14MLC004);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十八大以來黨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發展研究”(2016SJD710011);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協同發展研究”(15CKS019)。
顧碧(1983—),女,碩士,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范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政治發展史研究;劉俊杰(1982—),男,博士,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