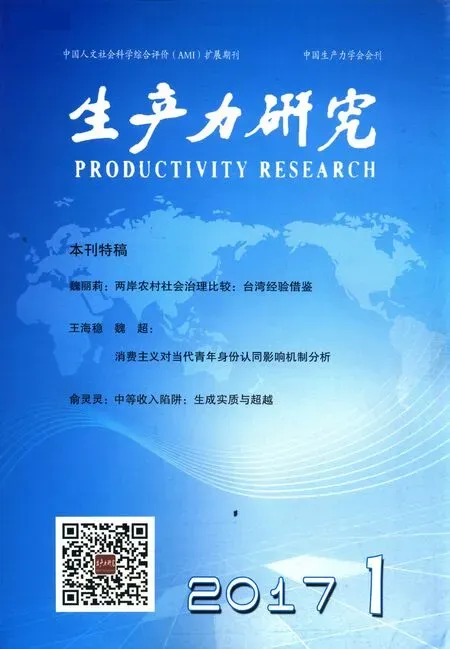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典型模式綜述及其啟示
(1.新疆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54;2.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新疆烏魯木齊830011)
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典型模式綜述及其啟示
張鵬1,杜宏茹2,倪天麒2
(1.新疆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54;2.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新疆烏魯木齊830011)
新型農村社區是新時期我國鄉村建設、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建設背景、空間區位、建置與邊界以及產業基礎等不同視角對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典型模式及主要特征等進行了歸納總結,并從村民參與、社區自治等方面提出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若干建議。
新型農村社區;典型模式;建議
一、我國農村社區建設歷程
社區是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1887年最早提出。他認為社區是建立在血緣、鄰里和朋友關系等基礎上的一種具有親密感和無可置疑的連帶關系的共同體,社會實質是個體間的相互分離[1]。20世紀30年代初費孝通首次將“社區”概念引入我國。社區具有地域、人口、區位、結構、社會心理五個基本要素[2],是一種基于情感和意志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形式。
1978年以后,伴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社區發展進行了多種模式的積極嘗試[3],為現代農村新型社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快速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進程同時改變著農村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差序格局和以鄰里關系為基礎的合作格局受到沖擊,傳統農村社區固有弊端日益凸顯[4-5]。城鄉資源的不對等流動使得城鄉差距逐漸擴大,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不足、人口經濟“空心化”以及留守群體擴大等現象成為農村衰敗的集中體現。加快建設現代新型農村社區,是我國現階段城鎮化快速發展和城鄉統籌的迫切需求。
2000年以來,全國多地展開了自發的農村社區建設試點探索,大致可以歸納為試點階段(2000—2006)、實驗階段(2007—2008)、全覆蓋階段(2009—2014)和深入推進階段(2015年至今)。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農村社區建設”的概念和基本目標。2007年《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縣(市、區)工作實施方案》下發后,在全國確定了304個建設實驗單位[6]。2009年,民政部下發了《關于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全覆蓋”創建活動的通知》,共命名106個縣(市、區)為“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全覆蓋示范單位”,全國農村社區建設覆蓋面擴大,發揮了巨大的模范引領作用[7]。2015年,《關于深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出臺,在肯定了實驗試點工作成效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了深入推進試點建設的工作目標[8-9]。天津、江蘇等10省(區)也出臺了省級層面具體實施意見,進一步加強全國農村社區建設示范單位指導標準建設,初步形成了農村建設指標體系[10]。全國農村社區試點建設進入深入推進和優化提升階段。
二、新型農村社區概念界定
關于新型農村社區的概念,高強[11]、馬芒[12]、徐勇[13]、劉君[14]等國內學者均有相關定義。本文認為,新型農村社區是在農村地域范圍內,以小城鎮或者中心村為集聚中心,引導人口集中居住,加強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升農村管理與服務能力,以達到集約利用農村土地、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促進城鄉一體化的農村生產生活綜合體。與傳統農村社區相比,新型農村社區呈現出基礎設施完善、居住環境改善、公共服務齊全、基層管理創新、法治文明開放等典型特征。
三、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主要模式
我國幅員遼闊,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呈現較大區域差異,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也是因地制宜,既體現不同區域發展特征,又適應不同地域發展需求。本文結合甘信奎、滕玉成、項繼權等前人研究成果,從建設背景、空間區位、建置邊界和產業基礎等不同視角,將目前我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模式歸納如下:
(一)按照建設背景進行劃分
甘信奎(2009)[15]、滕玉成(2010)[16]等從社區建設背景角度進行了類型劃分。一般可將全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歸納為城市化型、就地城鎮化型與村民自治型三種模式。
1.城市化型模式。在城市化空間迅速擴張的背景下,位于大都市城鄉結合部地帶的城中村、城郊村通過撤鄉設街道辦事處或居委會兩種方式完成社區建設。深圳市于2004年全面撤銷鎮政府成立街道辦事處,撤銷村委會成立居委會,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鎮和村的城市。這一類型的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取決于當地相對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村莊發展應納入城市長遠發展規劃之中,進行合理規劃定位,以“社區建設”為途徑推動村莊發展和全面轉型。
2.就地城鎮化模式。農村工業化是農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也是農村社區建設的根本動力[17]。以江浙等地為代表的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在村落集體工業、村辦企業大規模發展的支撐下,形成了“超級村落”、“億元村落”等形式的單位社區以及村落集鎮化或鄉鎮政府所在地形成的小城鎮大社區。該模式是一種發自農村內部的社區發展需求,是村級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一般適用于村級集體經濟狀況較好或有村級工業企業的村莊。
3.村民自治型模式。江西、湖北是我國最早開展新型農村社區探索的地方,開創了基于共同文化紐帶的“村民自治型”農村社區。江西以自然村落為基本單位,以“五老”人員為中心,以“一會五站”為平臺,構建了“自然村落”社區。湖北秭歸縣楊林橋鎮撤銷村民小組改建社區,成立社區理事會,建立了以“村委會-社區理事會-互助組-農戶”為基本結構的村小組社區模式。上述模式成功之處在于社區建置于村民小組或者自然村落,具有高度的親和力與認同性。基于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紐帶,依托五老人員等村里較有威望的人員進行服務管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村民情感認同、增強合作自治氛圍。但社區規模小、數量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成本較高,只著眼于村組內部關系的穩定,沒有實現更大范圍內的開放融合,自治過程需要依托村中精英人物的權威。
(二)按照空間區位進行劃分
滕玉成[16]、《山東省新農村建設以及社區建設規劃(2014—2030年)》[18]等依據空間區位進行了社區類型劃分,一般可分為中心城鎮集聚型與中心村集聚型兩種形式。
1.中心城鎮集聚型模式。中心城鎮集聚型模式是指隨著城鎮的對外擴張,處于城鎮規劃用地范圍內的村莊進行選址合并,納入城鎮社區管理范圍的農村社區類型[18]。一般包括城市集聚型與小城鎮集聚型兩種類型。城市集聚型社區是指位于城市周邊地區的城中村與城郊村,受城市影響逐漸加強,其“鄉村性”逐漸減弱,居民身份和生活方式逐漸城市化,最終納入“城市社區”管理范圍的社區類型。小城鎮集聚型社區是指在建制鎮或者鄉集鎮域中心,依托其區位交通的優勢,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完善,積極引導鎮域人口經濟等集聚而建立的集鎮型農村社區。
2.中心村集聚型模式。中心村集聚型模式是指在遠郊地區,村莊受城市發展影響相對較小,通過選擇建設中心村來整合人口土地等資源基礎上而開展的農村社區建設。一般包括強弱組團型、多村合并型、搬遷集中型、邊遠村直改型四種類型[18]。強弱組團型指空間距離較近而經濟水平存在差距的村莊之間,選擇強村作為中心村、弱村作為基層村形成組團,強村帶動弱村發展。多村合并型指多個村莊規模較小,不存在明顯差異,多村進行合并選擇交通方便、用地充足、多村交界處新建農村社區。搬遷集中型指村莊現狀位于地質災害易發區、偏僻山區或者生態環境保護區,由于原址不適于繼續建設而搬遷到其他安全地帶新建農村社區。邊遠村直改型指原村莊規模較小,周邊沒有可合并的村莊,或者出于特殊保護的目的,原村莊直接改造為社區。該模式以村莊為集聚中心,以村莊合并為主要方式,在村莊地形復雜的區域可因地制宜選擇適當模式進行社區建設。
(三)按照社區建置與邊界進行劃分
滕玉成[16]、項繼權[19]等學者按照社區建置及其邊界進行了社區的劃分。本文以此為基礎,將我國社區建設類型劃分為四種模式。
1.一村一社區模式。該模式將社區建置于行政村,既保留行政村建制,又將其納入到職能更加完善的社區平臺進行工作,實行“村社合一”[20]。該模式典型案例有四川宜賓、山東膠南、膠州、萊西以及甘肅省金昌、臨澤等。浙江、江蘇、重慶、四川、甘肅等省份多采用此模式,是目前實施最普遍的一種模式。該模式的優點是未增加管理層與管理成本,容易處理好社區與村委會之間的關系,也不涉及村莊之間、居民之間的關系變動,村民認同感強,推行阻力較小。缺點是“村社合一”導致社區力量相對薄弱,制約了社區職能的發揮;一般需要較為雄厚的村級集體經濟的支撐,發達地區依靠村集體經濟或企業帶動,欠發達地區則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支持[21]。
2.多村一社區模式。該模式是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公共資源集約配置的原則,將相鄰兩個或兩個以上行政村規劃為一個社區,選擇人口、經濟或區位最佳的村莊作為中心村建立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并引導周邊村莊人口向中心村集聚,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共享。該模式典型案例有山東諸城、莒南,按體制建構可分為“社區-行政村-農戶”、“社區(行政村)-農戶”兩種形式。
“社區-行政村-農戶”模式,僅將若干建制村納入一個社區開展服務,社區與原有建制村沒有隸屬關系,也不干預村里工作,只在社區層面上成立協調議事機構,主要定位在服務,能較好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共享。但是面臨著管理層的增加和機構的重疊問題,會相對弱化鄉鎮政府及行政村職能。該模式適用于集體經濟實力相對落后、原來村莊規模較小,農村公共服務相對匱乏以及鄉鎮地域面積較大,邊遠村莊到鄉鎮中心距離較遠的情況。
“社區(行政村)-農戶”模式,原有若干建制村規模較小,合并為一個建制村的基礎上成立社區。該模式可以減少村莊散弱帶來的資源浪費以及公共服務不足,也可以突破固有的村莊界限構建起村民之間更廣范圍的交流與融合。但是開展行政村撤并,涉及原建制村債務債權、土地資源、集體經濟的整合問題。
3.一村多社區模式。該模式是將社區建置于自然村莊或村民小組,一個建制村設立多個社區。組織形式上是“行政村-社區-農戶”或“行政村-自然村落-社區-農戶”。該模式村民認同感強、參與熱情高,利于實現村組范圍自治與穩定。缺點是社區規模小,服務人員少,社區職能不夠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成本大,需要政府層面的大力推動,社區治理過分依賴“五老”人員,缺少長遠考慮。農村社會變化加劇,村民的認同日益跨越原有的村組范圍,在更大范圍內推動社會的融合成為可能和必然。該模式一般適用于建制村由若干較為分散的自然村所組成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偏遠山區,村莊分散不宜組織集中規劃建設,或是出于特殊村莊保護的目的,視其規模設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社區。
4.集中建社區模式。該模式是對多個規模較小的村莊進行合并,在異地集中新建社區,或者在農牧民原聚居地附近規劃新建社區,對周邊一定服務半徑內的村莊開展社區服務。以天津、成都、甘肅阿克塞縣等地為例。該模式優點是不受建制框架束縛,以一定的空間范圍為半徑整合散居村莊資源,可以很好的推進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共享。缺點是完全異地新建成本較高,村民搬遷意愿以及在新社區的融合問題突出,與原有建制村在具體的管理服務工作上可能存在重疊或者空缺。該模式適用于農牧民聚居區或者原來村莊規模較小、區位不佳,需要集中搬遷的地區。
(四)按照產業基礎進行劃分
產業是農村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支撐,產業非農化程度是衡量社區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17]。按照社區建設所依托的產業基礎,可以將其劃分為農牧業主導型社區、工業主導型社區、商旅主導型社區[22]。
1.農牧業主導型模式。農牧業主導型村莊建立社區,是大多數村莊開展社區建設的主要方式。該類型村莊應該按照主要農牧業類型選擇建設模式以及具體方案。種植業主導型村莊,應該依據作物類型、耕地分布等確定社區建設方案,積極進行土地資源整合,確定合理的耕作半徑、服務半徑。牧業主導型村莊,需要依據牧業類型及特點配置相應的環境設施及確定具體實施方案。
2.工業主導型模式。村辦企業或者有在村莊周邊布局的企業時,社區建設與企業發展融合進行,推行“村企共建”社區。企業為社區建設投資建設資金,而社區需要為企業發展提供土地或者勞動力等必備條件。東部沿海多此類型農村社區,“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均是借助農村工業化實現農村現代化發展起步而建成新型農村社區的典型案例。
3.商旅主導型模式。商旅主導型社區建設,主要是利用近郊地帶農田等鄉村特色景觀開展農家樂、農業觀光、農業休閑度假、商貿流通等經營活動基礎上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完成了農村發展的轉型[22]。該模式以近郊村莊為主,需要積極利用村莊區位優勢,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掘村莊內部所有旅游觀光、商貿物流、民俗文化等方面的資源,推動農村服務業發展,建設“服務型農村社區”,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四、對我國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啟示與思考
(一)以村民為主體,調動多方參與共建
村民在社區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是社區建設的主體和社區建設成敗的關鍵因素。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應促使農民地位由外局群體向內局群體轉變,提升村民的主體性地位,使其發揮更大作用[20]。堅持以村民需求作為設施配置及改善環境的主要導向,積極調動村民參與的積極性,培育村民互助合作的精神。同時,積極吸納駐村企業或者個人參與社區建設,形成政府投入、村民籌建、個人與社會團體幫扶、企業投資等方式共存的多元化融資建設渠道通過社區平臺統籌使用。
(二)重視培育社區組織,強化社區自治
社區組織在參與社區建設、整合社會資源、豐富社區文化、提高社區服務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社區組織建設程度是衡量社區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新型農村社區是村民生活共同體,應該突出“生活”共同體功能,積極培育社區組織,強化社區自治。應將社區居民納入各類社區組織、企業,以行業為紐帶培育村民競爭、合作精神,推動村民由“血緣人”向“社會人”轉變,以業緣、組織為基礎的新型村民自治替代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傳統村民自治,強化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與服務能力[23]。農村社區建設成熟地區,應積極擴大社區自治范圍,賦予社區更多的自治權利,加快農村社區自我發展。
(三)突出社區整合功能,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新型農村社區是對農村村莊“空心化”、弱勢留守群體擴大等問題的積極整治,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目標和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配套工程[8]。社區建設過程中應該突出資源整合功能,加大對農村“空心化”、弱勢留守群體擴大等問題的關照。應該以新型農村社區為平臺,按照不同社區特點加強分類指導,加大對農業生產、社區管理與服務等方面資源的整合,增強社區服務管理以及自我發展能力。農業生產方面,以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為目標,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生產經營,保障農業的基礎地位。社區管理與服務方面,積極整合各類社區組織等社會資源,節約管理成本,提升服務質量。
(四)培育社區主導產業,強化經濟支撐
農村工業化是農村社區建設的根本動力[17]。產業非農化程度客觀反映著社區的發展程度。產業的支撐奠定社區經濟基礎,不僅為社區建設提供資金來源,而且能夠帶動解決社區居民就業,是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產業發展與社區建設必須并軌同行,同步推進,具備產業支撐才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農村社區。新型農村社區應當突出全新的生產組織功能,以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組織為紐帶,積極培育社區特色產業。產業類型是影響社區建設模式選擇的重要因素,應該按照農牧業、工業、服務業等不同產業發展特點,加強社區建設的分類指導,并借助社區平臺,積極引導農民規模化、集約化生產,完善以農業為基礎的產業發展鏈條,發揮社區生產共同體的組織作用。
(五)因地制宜,不同地區應有不同側重
全國各地自然地理條件、資源稟賦、風俗習慣、發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異,社區建設應按照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農村社區實際情況,突出重點、加強分類指導,建成充分體現當地特色文化資源的地域性特征明顯的農村社區。東部各省份自然地理條件相對優越,非農產業基礎好,村莊經濟獲得較好發展,而且基層村民自治基礎牢固。政府角色轉變上,應由政府主導地位轉向引導地位[24];社區組織建設上,更加注重培育特色社區組織,突出各級社區自治;目標導向上,更加注重村莊內在需求,以“城市化”向“現代化”轉變。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基礎更加薄弱,加強基層政權建設與社會穩定的任務艱巨。開展農村社區仍需要以政府為主導,以村莊內部五老人員等鄉村精英為依托,同時加強社區組織建設,強化行業能人帶動作用,形成以行業為基礎的幫扶帶動與社區互助局面。而且經濟欠發達地區社區建設過程中更要注意借鑒與整合不同地區建設經驗,重視社區建設的階段性特征,做好過渡工作[25]。
[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8-66.
[2]黎熙元.現代社區概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6-9.
[3]夏周青,2010.中國農村建設:從鄉村建設運動到農村社區創建的興起[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121-124.
[4]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34.
[5]王霄.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4-18.
[6]民政部關于印發《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縣(市、區)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民函〔2007〕79號[EB/OL].(2007-03-29).http://www. mca.gov.cn/article/zwgk/gzdt/200711/20071100003904.shtml.
[7]民政部《關于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全覆蓋”創建活動的通知》民發〔2009〕27號[EB/OL].(2009-03-06).http://www.mca.gov. cn/article/zwgk/fvfg/Jczqhsqjs/200903/20090320028133.shtml.
[8]《關于深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中辦發〔2015〕30號[EB/OL].(2015-05-31).http://www.gov.cn//2015-05/ 31/content_2871051.htm.
[9]民政部關于學習貫徹《關于深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的通知民發〔2015〕95號[EB/OL].(2015-06-02).http:// 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506/20150600827398.shtml.
[10]民政部.2015年民政工作報告[R].2015(12):22-25.
[11]高強,2006.新農村公共服務新型社區建設平臺的探索——新型農村社區“內源式”和“外推式”的建構模式分析[J].天府新論(2):96-100.
[12]馬芒,2005.農村社區發展的特征與功能[J].中國發展觀察(10):22.
[13]徐勇,2007.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推進農村社區建設[J].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4):12-15.
[14]劉君.農村社區建設問題研究[D].四川大學,2007:5-7.
[15]甘信奎,2009.新農村社區建設模式及政策推進[J].江漢論壇(2):134-137.
[16]滕玉成,牟維偉,2010.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模式及其完善的基本方向[J].中國行政管理(12):95-98.
[17]周沛,2000.農村社區發展道路與模式比較研究——以華西村、南街村、小崗村為例[J].社會學研究(10):59-66.
[18]《山東省農村新型社區和新農村發展規劃(2014-2030)》[EB/OL].(2014-09-05).http://www.jinxiang.gov.cn/art/2014/9/5/art_3044_ 66319.html.
[19]項繼權,2009.論我國農村社區的范圍與邊界[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7):4-10.
[20]陳旭峰,2013.農村社區建設模式的現實選擇及其發展方向[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3):41-45.
[21]李方才,2009.“一村一社區”模式的利弊剖析[J].鄉鎮論壇(3):22-23.
[22]劉彥隨.中國新農村建設地理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234-238.
[23]甘信奎,2007.中國當代新農村社區建設的現實條件與路徑選擇[J].理論學刊(1):57-59.
[24]諸葛鵬,岳書銘.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政府角色轉換探析[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0,21(9):30-32.
[25]項繼權,王明為,2015.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動態與階段特征[J].青海社會科學(2):1-8.
(責任編輯:D 校對:T)
F320.3
A
1004-2768(2017)01-0042-04
2016-10-18
中國科學院特色研究所主要服務項目3課題3(TSS-2015-014-FW-3-3)
張鵬(1991-),男,甘肅秦安人,新疆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地理學;杜宏茹(1974-),女,河北唐縣人,博士,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城市與區域發展;倪天麒(1964-),男,山東人,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區域與城鎮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