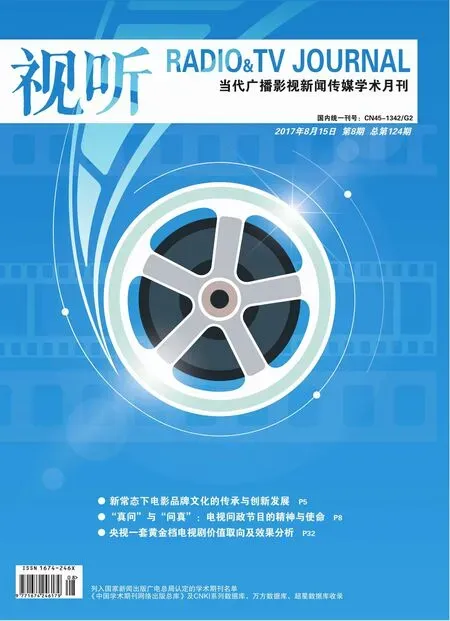中國特色傳播學發展路徑初探
□ 蘭志文 楊熙
中國特色傳播學發展路徑初探
□ 蘭志文 楊熙
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應在全方位梳理西方傳播學發展軌跡(包括理論背景、研究范式、研究主體等)的基礎上,借鑒西方的傳播學理論,并融入中國的歷史、經驗、文化交往、價值觀及哲學,逐步構建屬于中國特色的傳播學流派和理論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以中國的傳播實際為材料;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要吸納其它學科最新的理論和研究成果;要抓住互聯網所帶來的機遇。
傳播學研究;網絡社會;現代傳播學;傳播機遇
傳播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人類社會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以及目前所處的電子傳播時代。從歷史的發展軌跡來看,傳播技術的每一次升級變革,人類社會都會經歷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快速變革、全球傳播技術快速升級和傳播主體日益多元化,傳播學的研究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在近幾年不斷地表達對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高度關注。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一直在實踐新聞傳播思想。“8·19講話”“2·19講話”等無不體現了國家對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的高度重視。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說到,“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關鍵是要提高質量和水平,把握好時、度、效,增強吸引力和感染力”,這段話分析了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各種現狀,同時也為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就是要把握好“時、度、效”。把握好這三個關鍵詞,其實就是要把握好傳播規律,要深入分析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形態的新特點和新趨勢,結合中國具體實際,發展屬于中國的傳播理論。
一、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的內涵
傳播學是一門與人類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息息相關的學科,傳播活動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一環。現代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路徑是其在中國的實踐,也是中國對傳播學理論的發展與補充。
李彬和劉海龍①將20世紀現代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分為兩次“引進”和三次“突進”。他們認為早在20世紀初,現代傳播學便引入到中國大陸,當時引進的主體學科是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哲學等,傳播學作為其它學科的分支引入中國。王怡紅和楊瑞明②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傳播學發展進行了分段,他們認為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主要經歷四個階段,該研究認為,傳播學研究在中國大陸萌芽是在20世紀50、60年代。這兩個研究都認為傳播學在中國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新聞機構改革、倡導科學技術革命和追趕西方信息社會,共同構成了現代傳播學引進中國的社會背景。傳播學在中國的“突進”節點是在1978-1982年傳播學的引進與興起;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傳播學學習和學術研究規范確立;20世紀90年代-2008年,傳播學學科體系建立、學術思想和學術資源多元化。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變遷,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媒介化社會的到來,傳播學逐步得到政府、社會、高校等的認可,擺脫邊緣學科的境地,從一個舶來學科逐漸成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
現代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受到了當時的社會政治的影響,就如學者李彬和劉海龍③所言,傳播學引入中國不是單純的學科發展和單向度的學術積累的問題,更是一個文化政治的問題。在傳播學剛進入大陸的早期,被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物,對于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來說,思想上還未能完全解放,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語境中,作為“舶來品”傳播學理論被賦予了濃厚的階級色彩,被認為是階級斗爭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如“mass communication”一度被翻譯為“群眾思想交通”“公眾通訊”等。1978年,復旦大學使用的傳播學教材名稱也是用帶有“翻譯政治”意味的詞匯來解釋,如《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共傳播學》。1982年11月,全國第一次傳播學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確定對西方傳播學研究的16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這個觀念是一種學術自主性的表現,是中國學術界突破文革時期思想之繭的里程碑,但是囿于當時社會政治的因素,傳播學在20世紀一直處于“思想的他者”,一直未能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自傳播學引入中國開始,學術界就開始注意到西方的理論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才能夠有所發展。中國的信息傳播也有相當長的歷史,但是傳播學的主流陣地已被歐美等西方國家占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傳播學發展格局呈現“西強我弱”的局面。上世紀80年代初,傳播學初入中國,當時學者對傳播學盲目崇拜,缺乏對西方傳播學具體歷史語境的考察,對學術研究缺乏基本的學術規范,西方傳播學的理論是作為一種理論工具使用。到了90年代,學者開始將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當中,全面分析西方傳播學理論的進化過程,并進一步規范學術研究。他們逐步意識到,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是建立在戰爭、資本主義市場轉型基礎上,是在西方社會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學者們意識到必須結合中國的傳播實際才能使傳播學真正在中國落地生根,“第九屆傳播學研討會”就提出了要建設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科的設想。
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全新的轉型期,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應在全方位地梳理西方傳播學的發展軌跡(包括理論背景、研究范式、研究主體等)的基礎上,借鑒西方的傳播學理論,并融入中國的歷史、經驗、文化交往、價值觀及哲學,逐步構建屬于中國特色的傳播學流派和理論體系。
二、中國特色傳播學研究動因
現代傳播學之所以在中國逐漸步入顯學行列,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的。西方傳播學是外因,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是中國特色傳播學的內因。以下主要從國內背景、國際背景和技術這三個方面來分析中國特色傳播學研究的動因。
首先,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改革開放至今已近40年,中國在全球化、市場化的大背景下,社會財富快速累積,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社會快速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懸殊、食品安全問題、環境污染(霧霾、水污染等)、惡性事件等。這些問題又產生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如社會信任缺少、抽象憤怒、群體極化等。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面臨的社會現狀有很多的相似之處,西方的傳播理論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基礎。然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新中國成立之后又經歷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中國積貧積弱的國情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起點是不同的。此外,中國所處的文化氛圍也影響著信息的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通過對中國的大眾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人際傳播等的詳細剖析,尋求疏解社會怨氣、消解社會戾氣的路徑,凝聚社會共識,促進中國社會的穩步發展。
其次,塑造國家形象,傳播中國好聲音的需求。當前的輿論格局仍由西方世界主導,中國處于世界輿論格局的邊緣,這就導致了中國的聲音無法在世界范圍內流傳并產生影響。目前中國國際傳播能力不足,讓我國陷入輿論困境,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不被國際輿論認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沒有被公正報道、國內社會問題被外媒肆意扭曲抹黑等,正面報道少,負面信息偏多。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要提升國際話語權,提高國際對外傳播能力,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傳播中國好聲音,闡釋好中國聲音。可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已成為中國邁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體系建構,符合目前我國對外傳播的需求,最根本的路徑就是尋找到國際交流的最大公約數。正如學者文建所言,中外利益交匯點、話語共同點、情感共鳴點就是國際交流的公約數。④
最后,科技更新周期縮短,網絡社會崛起使傳播格局重新洗牌,新媒體技術促進傳播主體多元化。進入新世紀以來,傳播技術快速革新和硬件設備的便捷化改變了信息的單向度的傳播格局。正如所有新的技術一樣,網絡技術進入中國之后,傳統媒體對它的態度經歷了由不屑一顧、抵抗到最后主動融合的歷程,如垂直化產品快速崛起,擴展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新媒體技術不僅改變了傳統媒體的思維方式,也在改變普通民眾的信息接收方式以及信息的傳播方式,通過微博、微信、論壇等就可以傳播自己的聲音。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鏡像,很多現實問題都會映射到虛擬社會之中,如近幾年關于網絡群體事件、民粹主義等研究快速崛起,反映出了網絡社會傳播也具有強大的殺傷力,能夠調動群體的行動力。傳統的傳播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大眾傳播領域,對于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的研究較少。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大眾傳播研究一面獨大的格局,新媒體語境下,傳播環境、傳播主體變得更加復雜。如果按照西方的傳統模式去進行傳播學研究,沒有結合中國的實際,就很容易出現水土不服。
三、傳播學研究在中國的困境
現代傳播學從舶來的學科逐步變成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國家建設以及每個社會個體活動密切相關的顯學。自傳播學引入中國到發展成為一整套完整的學科體系也就不到40年的時間,從盲目崇拜到反思批判,再到針對鮮活的中國實際經驗,有機吸收內化外來經驗,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目前中國的傳播學研究還存在很多問題。
研究的功利化取向限制了傳播學理論的發展。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應該切中服務中國傳播事業。我們不能說現在中國傳播學研究已淪為爭名逐利的場域,但功利化的研究已成為傳播學研究學術場普遍的現象。陳力丹認為,學術研究雖然可以服務于功利目的,但是它的本性拒絕功利目的。⑤功利化使得傳播學的研究一直緊跟策略性的研究項目,而忽略了傳播基礎理論的研究。目前多數的研究運用國外的傳播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傳播現象,而不是立足于中國的傳播實踐,發展出中國自身的傳播學理論。過于追求“實用、管用、易用”的學科評價制度,以及目前依靠項目和成果多少的人才評價體系,使得很多人忙于追求短期的成果,而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
傳播學的研究跟不上媒介技術的更新速度。新媒介技術打破了信息傳受不平等的地位,傳統媒體的受眾在新媒體時代具有了雙重的身份,即信息接受者和信息傳播者。網絡社會快速崛起,但目前很多研究仍然用紙媒時代和影像時代的研究范式來思考當前的網絡社會,這顯然不能夠全面把握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特征。任何一種新媒介的出現,都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果不能使用恰當的研究方法來評價和研究新媒體,那么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將陷入困境。
高校過于注重大眾傳播學理論的教育,忽視了自身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等分支的研究。1997年,新聞傳播學成為我國的一級學科,傳播學是其下屬的二級學科。現代傳播學是通過新聞學者引入的,因此中國的傳播學從一落地就被刻上了大眾傳播學的烙印,這也導致了大眾傳播學的研究一直是傳播學研究和高校教育的重點。顯而易見,用大眾傳播學的理論來闡釋目前的網絡傳播過程顯得力不從心,理論遠遠跟不上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網絡社會從web2.0過渡到web3.0,自身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的理論更切合網絡傳播的規律。
四、推動中國特色傳播學研究發展
中國特色傳播學研究首先應該以中國的傳播實踐為材料。經過對西方的傳播學理論的發展脈絡和社會背景的梳理,我們發現,不管是經驗學派還是批判學派,都是扎根于當下社會,通過對具體問題的分析,進一步總結提升至理論層面。中國的快速變遷,為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如群體沖突事件、社會泄憤事件、網絡群體行為等,這些事件背后是信息的傳播、接收、信息如何轉換為行為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如果不能扎根于中國的實踐,而是濫用西方社會的理論,只會讓傳播學與大眾之間的隔閡進一步加深。
其次,中國特色的傳播學應該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唯物主義,是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它們要求發展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應該做到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面分析,將具體的傳播學現象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不能脫離語境談傳播現象;注意不同傳播現象之間的聯系,從聯系的觀點來看待傳播現象;規律是普遍存在于傳播現象之中的,在具體傳播現象的基礎上分析,用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發現事件發展的規律。
再者,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要吸納其它學科最新的理論和研究成果。西方傳播學是建立在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基礎上的,傳播學是跨學科的產物。目前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問題分散、沒有突出的理論成果,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充分吸納和內化其它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喪失了傳播發展的理論基礎。
最后,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要抓住互聯網所帶來的機遇。進入21世紀以后,互聯網在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從web1.0到web3.0,各類新聞網站、社交平臺、購物平臺等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網絡把日常生活變成了網絡虛擬空間,虛擬社會成為人類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景。而現實社會的很多問題也映射到了網絡社會當中,網絡社會信息的傳播加速,不斷激活人們的需求動機,在網絡傳播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致使網絡行動增多。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需要主動研究中國的互聯網,運用多學科的理論來分析網絡社會的運行機制,為網絡社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注釋:
①李彬,劉海龍. 20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1):32-43.
②王怡紅,楊瑞明.歷程與趨勢: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傳播學.http://www.cssn.cn/xwcbx/xwcbx_xwll/201310/t20131026_606365.shtml
③李彬,劉海龍. 20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1):32-43.
④文建.把握國際話語權 有效傳播中國聲音——習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J].中國記者,2016(4):35-37.
⑤陳力丹.傳播學在中國[J].東南傳播,2015(7):43-45.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州市番禺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