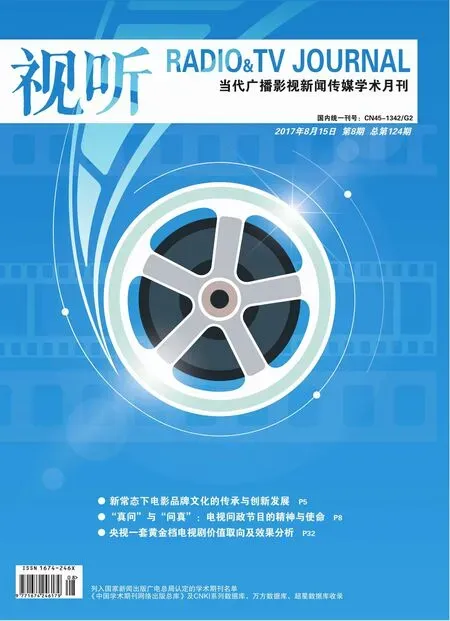儀式觀視域下青春影視中的集體記憶建構
□ 李曉雯 羅彬
儀式觀視域下青春影視中的集體記憶建構
□ 李曉雯 羅彬
近幾年,青春影視作品成為人們的關注點,由懷舊情懷引發的“集體記憶”也在不斷被編排和重構,本文在傳播儀式觀的視角下從符號的記憶再現、時空中的記憶認同、參與中的記憶建構幾個方面分析了當代青春影視作品中“集體記憶”的呈現,同時也反思在建構過程中,各種刻意的敘事安排和符號堆砌導致電影意義的缺失和單質化傾向。本文著重分析儀式觀視域下影視中的集體記憶建構。
青春影視;集體記憶;傳播儀式觀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在2011年贏得了高票房,此后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同桌的你》《梔子花開》《左耳》等一批聚焦青春期生活的影片輪番上映,形成一片“青春集體記憶熱”的新景象。
不同于一場聲勢浩大的直接進行儀式化感召的成人禮,也不同于新聞媒體關于高考、校園的一系列零碎報道,青春影片更加注重在觀影的過程中,通過身體的在場逐漸地喚起受眾心中青春情感的共鳴,進而建構青春集體記憶,在這一點上,與詹姆斯·凱瑞所說的“儀式觀”不謀而合。相對于“傳遞觀”而言,儀式觀認為傳播過程是各種有意義的符號形態被創造、理解或使用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更加注重平等參與,共享表征,打破時空障礙,維系社會情感。因此,青春題材影視中的集體記憶也是一個符號和意義相互交織的系統,那么這些影視作品是如何一步步打造一場青春儀式的?又是怎樣在儀式中喚起受眾對青春的懷念與感嘆的?
一、符號中的記憶再現
索緒爾將符號分為“能指”與“所指”。前者指符號的可感知部分,后者指意義、對象與解釋。符號的意義作用基本上是通過符號形式(能指)和符號內容(所指)之間的相互關系構成。當然羅蘭·巴特也提出“意指化”過程,即一個符號已經超越其物質實體所代表的涵義,在約定俗成和共同的語義空間交融中形成了深層意義,形成新的“迷思”。也就是說,在一級意指系統中,能指和所指組成的意指符號在更高一級的意指系統中成為新的能指,而其所指則是具有更深意義的內涵。青春影視就運用了許多符號表征來形成不同的“迷思”,這些迷思都印在受眾腦中形成一定程度上共同的認知,喚起集體記憶。
揚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每個社會和每個時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圖片和禮儀儀式……的總和”。通過這些符號的運用,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時代都鞏固了自身形象,同時社會中的集體也依靠這些知識塑造群體認同和群體依賴。青春影片通過一系列具體視覺符號,連接受眾與過往的文化記憶,快速進入情境之中并自動與自身經歷相結合。如影片中干凈的人物造型符號:校服、齊耳短發、白襯衫等,同時還有特定情境中的具象符號:自行車、課桌、黑板、教室……,以及80、90年代的文化記憶符號:收音機、超級瑪麗游戲。還有《那些年》中,沈佳宜用筆戳柯景騰以及共同罰站的情形,上課睡覺被抓,為考試通宵熬夜的場景都十分具有代表性。觀影過程中,受眾會不自覺的感嘆電影情節與自身經歷的相似,以往的經歷會歷歷在目,受眾內心與影片無形的交流。這種個人記憶通過熒幕的放大,迅速成為一種集體記憶。這些視覺符號正如羅蘭巴特所說已經超越其本身涵義,勾勒的是青春。
聽覺符號同樣必不可少,影片中承載著時代文化記憶的流行歌曲會時常響起:《紅日》《同桌的你》《當》《梔子花開》這些耳熟能詳的歌曲伴隨著受眾的成長。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烙印,無論是老狼蒼涼沙啞聲音帶來的沖擊還是的激昂《紅日》,都表達了這一代人對愛情美好純潔的向往和對未來積極向上的態度。聽覺符號的營造儀式功能更強并且潛移默化,觀眾走出場外之后仍然哼著劇中的歌曲并可佐證。同時其他媒介平臺也開始設置議程,音樂節目的青春電影主題曲欣賞,眾多音樂軟件相繼推出懷舊歌曲專輯。
視覺符號中圖片的沖擊力、人物的代表性、影像的生動性以及聽覺符號的音樂感受性、語言觸動力等,都從不同的方面沖擊著不同的感官,形成不同的心理感知。不斷重復出現或強調某種典型意義的青春符碼,都可以成為青春懷舊的對象。媒介運用各種符號營造儀式感,為受眾打造了一場關于青春的儀式,人們在這個現實中尋求解脫和記憶。
二、時空中的記憶認同
哈布瓦赫認為,類似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的行為往往成為記憶傳承的重要手段。儀式化的紀念活動成為集體記憶的共同集中點,青春片中的盛大儀式事件為受眾提供了共同的時空,受眾個體經驗的差異化被排除,觀眾被高度“同化”,在共同的情感體驗下產生強烈的共鳴和認同感。因此媒介事件和封閉的空間區域營造了一種同時性、同地性,受眾仿佛置身于一場神圣儀式中。
(一)封閉的空間區域
電影中除了對日常生活的儀式化處理達到對記憶的重構,空間作為記憶的載體也是不能忽視的。青春片中的場域限定在學校,將空間與外界隔離,相對于社會的浮躁和喧囂,校園這一場域象征的是純凈、積極。除此之外,校園也是青春記憶聚集之地,當敘述進入這一場域,校園中的黑板、操場、擁擠的宿舍樓、每天的廣播體操,這些場所和情節與受眾的認知基模發生作用,受眾自動進入這一場域,暫時與外界社會脫離,回到自己的青春歲月中。相對于變幻莫測的現代社會,影片中不變的校園載體更加凝聚了受眾關于美好青春的一切想象與賦予。
(二)媒介事件重現記憶
美國著名的傳播學家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將媒介事件定義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宣揚和解的、頌揚進取精神的以及以崇敬的態度制作、播出的電視節目,是具有儀式感的電視事件”。這樣的媒介事件發生往往是萬人矚目的,其中充斥著媒介的大量報道。眾所周知,人們無法親身經歷所有的媒介事件,他們對國家曾經經歷的重大事件的記憶都來自于大眾媒介的報道和記敘。這種深刻的記憶就成為了他們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而這種集體記憶是大眾媒介“書寫”的。影片《同桌的你》中屢次插入引起共鳴的媒介事件,從主角義憤填膺到現場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到電視中9.11事件發生后的巨大震驚以及全民抗擊非典的情節;《最好的我們》第一集主角偷用教室電視觀看2008年奧運會劉翔跨欄比賽,焦急等待和獲勝后的狂歡;《80后》中沈星辰參與北京申奧成功的慶功隊伍中的狂喜,再到和朋友在電視前觀看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的威嚴表情。涂爾干認為“按時定期地強化和確認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只有這種情感和意識才能使社會獲得其統一性和人格性精神的重新鑄造”。青春影視中利用媒介事件,表面上是表達角色參與其中發展劇情,實質是隱喻觀影受眾,為其營造主角+觀眾共同在場的氛圍,通過對媒介事件本身所凝聚的集體情感價值,來規訓受眾的個人情感,從而被集體情感收編,感受作為事件共同體的記憶。
三、參與中的記憶形成
傳播儀式觀強調人們接受信息時特定的世界觀得到描述和強化,而不在于不確定性的減少,就仿佛是參加一場宗教儀式,在于一種參入和體驗。和宗教儀式不同,青春電影通過定檔上映代替了其規律的周期性,但也形成了一種“約會意識”,大家共同參入、共同體驗、共同建構“儀式”。
(一)身體在場的狂歡
蓋內普認為,儀式的日子是與“最引人注目的圣時事件”緊密聯系的,其選擇具有必然性。電影的上映往往是各方綜合考慮之后的結果,一旦定檔,片方則會開始大力度宣傳,設置議程,受眾也提前進入儀式情境中。上映時間也成為受眾特別關注的特別時刻,意向觀影群體互相邀約,安排好時間迎接影片上映。這一天來臨時,全國意向觀影群體則如約而至,直接身體在場參與整場儀式,安德森認為大眾媒介為人們塑造了“同時性”,處于世界各地的人們同時觀看同一份報紙的行為構建了“民族共同體”。在這觀看首映電影則建構了“觀影共同體”,且不同于現場活動的空間隔閡,青春影視作品通過各種傳播渠道攬收大量受眾,不僅包含電影院的直接觀眾,觀眾的身體參與方式也擴展到現場的“空間性”甚至時間的“即時感”之外,包括新媒體平臺上的大量轉發和熱點置頂以及觀影后的產業鏈形成,受眾在此過程中完全平等參與,沒有身份設置,只需要擁有新媒體平臺和一定的操作知識即可。
(二)情感參與的共鳴
回歸是懷舊問題最表層、最直觀的特征,也是懷舊主體最容易產生的心理沖動。在電影院這一空間中,大家約定俗成保持安靜,受眾快速投入影片中,影片各種青春符號會感召受眾情感的共鳴,電影藝術將人們關于過往的回憶完美化,懷舊情愫油然而生,這些影像承載的集體記憶與現實剝離,形成唯美的記憶框架。在此種回歸式情境中,人們對過往青春時代的美好贊不絕口,對當時的社會風氣萬分想念,所以很多人用影評緬懷青春、在新媒體上發起回憶殺話題則在意料之中。集體的文化記憶成為群體共享的意義,青春片中的文化意義不僅僅是一個物質實體,而是存在各種時代符號中,而受眾一旦解碼成功,則將自身的故事與唯美的電影畫面相勾連,建立起自己這一代人的青春回想,營造出一種對集體記憶的敬畏感。
四、結語
在這場儀式當中,通過符號的遴選豐富著能指的外延和內涵、通過打造時空的共時性建構一種神圣的儀式過程,更通過各種渠道吸引全民熱忱參與來打造一場狂歡盛宴,建構了青春的集體記憶。但同時正如鮑德里亞提出的“擬像”理論,青春電影使用各種表征雖然指向過去,但真正追求的目的在于懷舊的消費價值、娛樂價值。受眾消費的是一宗虛擬的體驗,而不是真正的意境。確實觀眾觀影結束之后,更多的是心理的放松和回憶青春的美好,但是缺乏自身對青春的深層思考,后來的青春影視則看著飚高的收視率競相模仿,使得青春電影呈現景觀化趨勢,而肆意的復制品并不能散發出原始作品儀式的莊嚴和耀人的“光暈”,人們關于青春的集體記憶也是存在片刻之間,其情感與記憶的勾連短暫,集體記憶的建構會大打折扣。正確看待青春片熱潮并制作精良的影視作品,豐富青春影視片類型,講好故事,自然可以喚起受眾深層次情感和打造認同感。
1.[德]哈拉爾德·韋爾著,季斌、王立君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6.
2.張紅軍、朱琳.論電視綜藝節目對“集體記憶”的建構路徑[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03.
3.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著,麻爭旗譯.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14.
4.[法]愛彌爾·涂爾干著,渠東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62.
(作者單位:新疆財經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