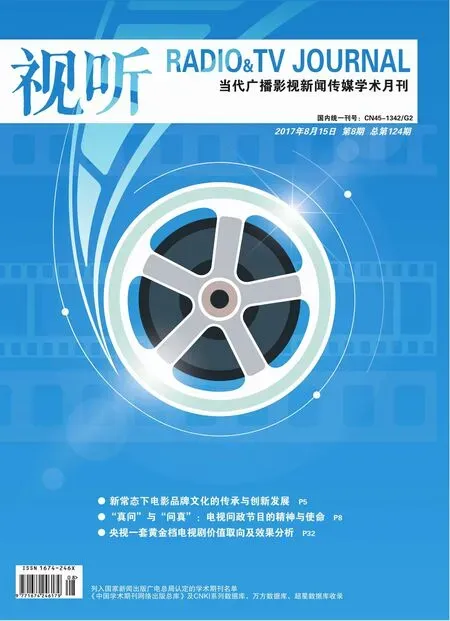后喻文化時代紀錄片如何講故事
——以紀錄片《海洋》與《伊斯坦布爾的貓》為例
□ 戚麗霞
后喻文化時代紀錄片如何講故事
——以紀錄片《海洋》與《伊斯坦布爾的貓》為例
□ 戚麗霞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科技發展迅猛之際,人類即將進入后喻文化時代,影視語言又無所不能,我們需不需要講故事?人類文化不斷發展,無數新鮮的故事被講述,但是講故事的原理永遠沒有變化。講故事,是紀錄片的思想深度所在,體現的也是導演對人生、對社會的領悟能力和掌控能力,體現出對人本身、對人性的深層關注和思考,影片本身的內容,更為接近人類學和民俗學,于是深入人心,贏得觀眾的認同。
后喻文化時代;互聯網;自然生態類紀錄片
時間回到1927年10月12日,“我的心意已決,一定要按照卡爾·馬克思書中的場景那樣將《資本論》拍成電影”,這是蒙太奇學派奠基人謝爾蓋·愛森斯坦坐在長六萬米的膠片堆上寫下的豪言壯語。今天,盡管有人依然嘲笑愛森斯坦此言,但觀眾已經在時空自由的影視敘述語言中習慣各種組接交錯了。
再提起一人,瑪格麗特·米德,美國的人類學學會主席,現代人類學最重要的學者之一。晚年的她,在重磅作品《文化與承諾》一書中,將人類社會劃分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個時代。在后喻文化時代,長輩反過來要向晚輩學習,知識以解構、重構等多元的方式產生與傳播。
回到主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科技發展迅猛之際,人類即將進入后喻文化時代,影視語言又無所不能,我們需不需要講故事?如果需要,我們需要如何講述故事?紀錄片的攝制和編輯又該如何處理?在后喻時代,謝爾蓋·愛森斯坦的豪言壯語不再是癡人說夢,但更需要了解本質。無論宏大偉岸還是細碎微小,都將被精彩講述。姑且拿2011年上映的法國紀錄片《海洋》和2016年上映的《伊斯坦布爾的貓》為論述之據。
講故事和聽故事,是人類人性的需求及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類文明前進的過程中,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口頭文學階段,比如《詩經》,都是整理廣為傳播的口口相傳的詩歌,那就是最早被敘述的故事。還有孔子、莊子等著述,都不是作者本人寫作的,而是后代弟子所整理的;二是有表演動作的戲劇舞臺,比如南戲、元雜劇等;三是用文字符號寫就的文學作品,代表性就是近現代的小說了;四是聲光電階段,代表就是1895年12月28日誕生的電影了。最有意思的是,電影誕生之初,第一批觀眾看到的就是紀錄片。路易斯·盧米埃爾兄弟放映的《工廠的大門》《嬰兒的午餐》《火車進站》等片,就是身邊生活的表現,是攝影機直接曝光所攝取的。后來,當電影告別雜耍,人們對鏡頭畫面已經習以為常,當火車再迎面開來時,也無動于衷了,不會再慌不擇路地逃出影院,也不會津津樂道地談論影像。雖然觀眾對電影再不覺得新奇,但電影中的故事仍然魅力不減。隨著技術的發展,以影視為手段的傳播越來越火熱,而影視無論是作為產品還是藝術品,始終能打動觀眾的一定是故事。
今天,影視藝術作為獨立的一門藝術而存在了,甚至上演一個又一個商業傳奇。自然而然,我們一定是需要講故事的,而且隨著觀眾欣賞口味的提升,還要更加努力地把故事講得更精彩。
假設我們不講故事,行得通嗎?回到影片上,在觀看紀錄片《海洋》時,大多數觀眾會覺得震撼和不可思議,這是拍出來的嗎?這種感受一直伴隨著壯美的海洋奇觀而縈繞在心里。看到片尾時,人們還沒回過神來,在憂傷的樂曲中看到拍攝花絮,又一次在回味中被震撼了,一切都是真的,仿佛看見了上帝,有了神性。誠然,講故事和聽故事是人類的基本需求,那么紀錄片首先要具有神性(震撼性),見所未見,知所未知,正所謂意外的深刻,哪怕是視覺呈現所帶來的表面現象。
了解一下《海洋》的拍攝背景就知其不凡。這是當今投資最高昂的紀錄片,耗時也最長。《海洋》劇組前后花了5年時間,動用12個攝制組,70艘船,在全球50個拍攝地,拍攝了超過100個海洋物種,收集了500個小時的視頻素材,最終剪輯了104分鐘的成片。簡單地羅列數據,再簡單地解讀一下,就知道他們做了其他人沒有做的事情。劇組還為了拍攝,改進已有的拍攝設備,才能在動蕩的大海里拍到那么平穩美麗的畫面。為了獲取各種精彩的畫面,制作組使用了遙控直升機、大型搖臂、防水殼等等現代化的攝影設備,甚至在法國國防部的幫助下將一枚魚雷改裝成了攝影機,只為了拍攝一個魚群追著攝影機游來的畫面。在巨量的辛苦付出之后,才有一席視覺大餐呈現在觀眾面前。
海洋神秘莫測,該片只要拍出來就會帶來震撼,但對于創作者來說還遠遠不止這些,還有可以挖掘的深度。這是要談的第二點,講故事和聽故事,除了見所未見的神性,還需要更深刻的人性挖掘。該片導演雅克·貝漢曾在談及他的另一部紀錄片《遷徙的鳥》時說:“飛翔對鳥來說,不是人們想象的什么樂趣,而是為了生存而拼搏……許多困難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確實如此,其實很多動物的自然行為被記錄進人類的鏡頭的時候,編導如何遴選,同樣涉及到“人性”的話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動物世界的規律,但人類社會何嘗不是如此?鳥兒是為了生存而年復一年地遷徙飛翔,人類也是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乃至顛沛流離。這是紀錄片的思想深度所在,體現的也是一名導演對人生、對社會的領悟能力和掌控能力。無論怎樣,都是體現出對人本身、對人性的深層關注和思考,影片的內容更為接近人類學和民俗學,于是深入人心,贏得觀眾的認同。
保護自然環境是今天全世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海洋》是自然生態類紀錄片,環保主題自然是抓住了人心。這其中還有一些技巧可尋。“自然類紀錄片,就是人類對客觀自然進行主觀描述的產物”,這是今天傳媒教材里的普遍認知。這種主觀描述,就是敘事方式,敘述方式就是講一個故事。
一是情節取勝。情節即是事件的安排,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如是說。在《海洋》中,海豹媽媽為了讓孩子下水游泳,在旁邊不停地鼓勵,還下水演示,小海豹終于邁出第一步。小海豹把頭伸進了水里又縮回去的過程,讓觀眾忍俊不禁,也讓人意識到其實動物的世界和我們人類的世界是一樣的,如此達到通感、共振,這個事件的安排,精彩之處在于有了“性格”,這種“性格”也是情節里的小事件安排體現出來的,互相印證,彼此生發。另外,據數據公司統計,中國觀眾的觀眾在觀看影片時,對情節的依賴最大,要有一系列的事件安排來建立起形象或性格,觀眾才能投入。例如這一情節:人類捕殺鯊魚,割了魚翅,就將鯊魚扔回大海,伴著血色,沒有魚鰭的鯊魚筆直地向海底深處墜去……畫面意象明確,視角獨特,這一事件的安排觸目驚心,更有警示的作用——那一垂直的墜落,仿佛是英雄犧牲,控訴得非常有力,典型的情節取勝。
再看看《伊斯坦布爾的貓》。這部關于伊斯坦布爾市民和流浪貓和諧互動的紀錄片打動了很多人,美國影評人評價匯總網站爛番茄新鮮度高達97%,IMDB網民打分也達到8分(滿分10分),中國網站豆瓣評分8.6分(滿分10分)。紀錄片原名Kedi,是土耳其語貓的意思。影片跟蹤拍攝了很多貓與人的故事,最終剪輯留下了7只性格各異的貓,展示了伊斯坦布爾街頭的貓與人共處的生活片段。其中,專門吃高檔西餐的貓非常有禮貌,在高檔餐廳的櫥窗口像人一樣舉手,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期間進出店門還有人專門開門送客,細節和事件的安排,無不散發著魅力。還有一只很霸道的貓,獨占一方,連街邊的小狗都怕它。如果說《海洋》宏大偉岸,那么《伊斯坦布爾的貓》就是微小細碎了,但兩者都有很好的事件安排,才能在大量素材里承載情感、建立情節,散發著敘事的魅力。
二是角色關系。承上,每個情節的出現都有一個使命和意義。至于為什么出現,那就是角色之間的關系了。角色之間組成了一個關系網,角色在關系網中通過不斷發生的事件去推動情節發展。這中間包括懸念設置和沖突展現,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沖突是一門考究的藝術,沖突要有鋪墊、積聚,還要環環相扣,沖突不能靠簡單粗暴的場面疊加,懸念有時是為了延遲沖突而服務的。在《海洋》中,主要講述海洋中生物的故事,但是片中有一個小男孩出現,通過他的視角來觀看海洋,來代入觀眾,從而將人和海洋聯系起來。通過這個設計,還增加了角色關系之間的沖突,尤其是以小孩視野審視人類破壞環境、危及自然生命的行為時,就與環境破壞者產生了強烈的沖突。有時,懸念還可以舒緩緊張的情緒,緩沖一下,慢慢累積力量。再看《伊斯坦布爾的貓》,每個貓的故事,都有一位與之親近的人來講述,加上敘述者自身的遭遇和生活、工作環境,在故事中又有了故事,事件講述者也是事件被講述者,意味無窮,所以該片才很好地代表了伊斯坦布爾,展示了城市的個性,這是角色關系設定帶來的講述魅力。這樣的魅力,無疑是成功的藝術處理。
三是節奏。很顯然,這是一個時間概念,簡單理解就是快慢。講故事,也就是敘事時間,專業上也稱之為“文本時間”,是故事內容在敘事文本中具體呈現出來的時間狀態,是對故事內容進行創作加工后提供的文本秩序。敘述節奏與敘事時間并不是等速的。就像電視紀錄片往往通過省略、概略、減緩、停頓或者加速、延緩等敘事方式來改變敘事時間,不斷破壞人們固有的心理程序,促使受眾心理活動增加,實現敘事張力的內在控制,敘事節奏與時間既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交錯的;既可以是快與慢的組合,也可以是一致與交錯的復合……有了情節,有了角色關系,是什么調動觀眾的情感呢?是節奏。想知道節奏如何重要嗎?讓人勻速地演唱流行歌曲,估計流行歌曲也不流行了吧?這就是節奏的作用,是它賦予了事件以變化。著名編劇王興東說:編劇法其實就是對比、省略、重復。編劇法不就是講故事嗎?對比帶來沖突,重復帶來加強……這一切說的就是節奏。再看《海洋》的段落,在廣闊平靜的海面上,有兩條座頭鯨的尾巴露出水面,仿佛在旋轉著跳舞;隨著鏡頭推進,兩條尾巴形成漩渦,伴隨著座頭鯨的鳴叫,海面恢復平靜。但是你感覺海面下一定是發生了什么,這個時候音樂也停止了,緊接著一大群座頭鯨浮出水面,畫面更加富于動感,隨之鏡頭時間縮短,密集而集中地帶給你沖擊力。先是慢,后是快,先是懸念(優雅),后是震撼(壯闊),這就是節奏,以時間的變化帶來情節的推進和升華。還有就是小海龜出生,畫面安靜祥和,然后在經過海灘進入海洋時,面臨著生死考驗,密集的海燕成群結隊地飛沖獵食小海龜,一只兩只成組的飛沖和叼起海龜的畫面,短促密集,最后一只小海龜終入大海活了下來。這組鏡頭在節奏中制造了戲劇效果和情感張力,不能不說精彩。之所以選擇以上兩部紀錄片來舉證,原因很簡單,拍攝動物的也會擬人化,也要講故事。那么拍攝人物和事件的紀錄片呢?就更應該講故事,講好故事。人類文化不斷發展,無數新鮮的故事被講述,但是講故事的原理永遠沒有變化,已經成為基本。
總之,后喻文化時代的內容和形式,無非是老瓶裝新酒。怎么能在傳播時增加傳播力呢?就是要講故事。如何講故事?要研究基本故事法,但選題上要避免刻板印象,不要一拍廣州就拍老幾樣,吃的是拉腸、住的看西關。后喻文化對內容有了更高的要求,廣泛而普及的故事還是故事嗎?要拍攝出新意和震撼,實在是難上加難,但影視工作者需勉力為之。
(作者單位:廣東廣播電視臺)